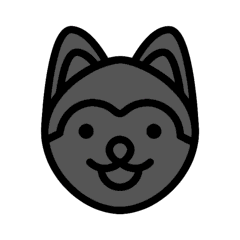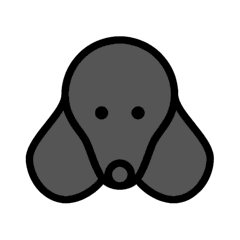【多施虐者日式轻小说】破碎与坠落的太阳9.22更新,第二卷第63章
连载中原创校园多结局JK棉袜原味羞辱气味犬化
yigeshenhouh发布于 2025-10-10 03:13
Re: 【多施虐者日式轻小说】破碎与坠落的太阳9.22更新,第二卷第63章
期待(✧◡✧)

Lk
lkh7758258发布于 2025-10-16 00:14
Re: 【多施虐者日式轻小说】破碎与坠落的太阳9.22更新,第二卷第63章
期待11111
2433发布于 2025-10-19 16:50
Re: 【多施虐者日式轻小说】破碎与坠落的太阳9.22更新,第二卷第63章
爽看,喜欢这种风格
585585发布于 2025-11-02 16:31
Re: 【多施虐者日式轻小说】破碎与坠落的太阳9.22更新,第二卷第63章
问一下大佬,这个结局预计是好结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