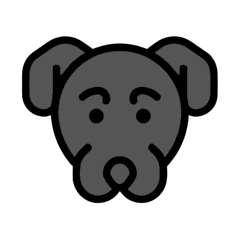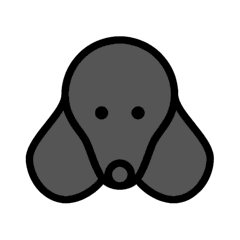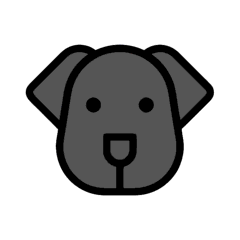关于我身为校霸的我被女同学的母亲调教成奴隶这件事是否搞错了什么
短篇原创萝莉御姐小男孩M臭脚黄金阉割圣水口水
开头剧情借鉴了一部漫画,但后面都是原创
陈烨是育才小学六年级三班的刺头,十二岁,父母离婚后扔给他奶奶带,从小没人管,养出一身无法无天的痞劲。老师管不住,同学不敢惹,他最爱欺负的,就是长得白净漂亮的张雪莉。
那天午休,他抓了只绿油油的蟋蟀,趁张雪莉趴桌子上睡觉,悄悄塞进她衣领里。虫子乱爬,张雪莉尖叫着跳起来,眼泪哗哗往下掉,怎么哄都止不住。她朋友围了一圈,手忙脚乱帮她拍衣服,可她抖得像筛糠,哭得嗓子都哑了。
放学回家,张雪莉憋到晚上,终于忍不住扑进妈妈怀里,把这些天被陈烨欺负的事全抖了出来。妈妈柳韵把女儿搂紧,轻拍她的背,等她哭够了,才抬手替她擦泪,声音低得像夜色里磨过的刀:“没事,宝贝。他既然敢做坏事,就别怪坏事找上门。”
第二天,四点半。
陈烨抄近路走那条窄巷,书包甩在肩后,嘴里叼着根棒棒糖。身后忽然响起高跟鞋敲地面的声音,脆生生的,像敲在心口。
“陈烨同学。”
他猛地回头,看见一个女人倚在墙边,三十出头,卷发红唇,黑色紧身裙裹得曲线勾人。她笑得温温柔柔,眼底却冷得像冰。
“你谁啊?”陈烨把糖咬得咔嚓响。
“我是张雪莉的妈妈。”柳韵走近一步,香水味混着淡淡皮革味钻进他鼻子里,“叫我柳姨就好。”
陈烨喉咙一紧,棒棒糖差点掉地上。他后退半步,干笑:“我……我没欺负她……”
“没关系。”柳韵弯下腰,脸凑到他面前,红唇几乎贴上他的耳朵,“姨知道你喜欢玩游戏……想不想跟姨玩点更好玩的?”
她舌尖轻轻扫过他耳廓,湿热痒得陈烨浑身一抖。纤细的手指像不经意地掠过他裤裆,声音软得滴水:“是色色的游戏喔……”
陈烨脑子轰地一声空白,脸红得像煮熟的虾,鬼使神差地点头。
柳韵直起身,冲他勾了勾手指:“跟姨回家。”
她家在巷子尽头,三楼,门一关,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脱光。”柳韵坐在沙发上,翘起腿,短靴尖在地板上点了点。
陈烨手抖着把校服扒光,赤条条站在她面前。小鸡鸡因为紧张缩成一小团。
柳韵掩唇笑出声:“哎哟,小男生的小鸡鸡可真可爱,这么小就想玩大人的游戏?”
陈烨臊得想找地缝钻。柳韵却起身,蹲在他身前,指尖捏住那团软肉,轻轻一撸,包皮被翻开,粉嫩的龟头露出来。
“这是什么?”陈烨声音发颤。
“自慰啊。”柳韵像教课似的,握住他小小的阴茎,上下套弄,“没自己玩过?姨教你。”
她手劲儿时轻时重,指腹刮过冠状沟,陈烨腿软得站不住,喘得像刚跑完八百米。
“舒服吗?”柳韵俯身,嘴唇贴着他耳朵,吐出一口温热的气,“张嘴。”
陈烨下意识张开,柳韵“啵”地吐了长长一口唾液进去,拉丝挂在他下唇,凉凉的,带着淡淡甜味。
“吞下去。”她命令。
陈烨咕咚一声咽了,喉结滚动。
柳韵满意地笑,抬脚脱下一只黑色短靴,靴口还热乎乎的,直接扣到陈烨脸上。
“闻。”她声音低哑,“大口呼吸,把姨的味道全吸进去。”
酸臭的脚汗味混着皮革和成熟女人的体香,像一股热浪直冲脑门。陈烨被熏得头晕,却舍不得挪开,鼻翼翕动,大口吸着。
“叫主人。”柳韵手下加快,拇指在马眼上打圈。
“主、主人……”陈烨声音发抖,带着哭腔。
就在他小腹紧绷,快要射出来的前一秒,柳韵突然松手,靴子重新套回脚上,站起身理了理裙子。
“啊?”陈烨急得抓耳挠腮,小鸡鸡涨得通红,直挺挺翘着,“别停啊……”
“急什么?”柳韵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粉色的小巧金属笼子,在指尖晃了晃,“想继续玩,就戴上这个。”
“这是啥?”
“贞操锁。”她笑得像只餍足的猫,“戴上它,你就是主人的小狗了。戴上它的人要对拥有钥匙的主人保持绝对的忠诚喔。
陈烨看着那冰冷的金属,脑子里却全是刚才的快感,咬牙点头。
咔哒。
锁扣合拢,小鸡鸡被硬生生压进笼子,龟头从网格里挤出一小点,涨得发紫。
柳韵把钥匙挂到脖子上,坠进深深的乳沟。
“明天放学,还来找主人。”她俯身亲了亲他汗湿的额头,“乖。”
陈烨提着裤子,腿软得几乎走不动,贞操锁的重量硌得他每迈一步都又疼又痒。
巷子口,夕阳拉长他的影子,像一条被拴住的小狗。
第二天放学铃一响,陈烨书包都没背稳,撒腿就往巷子跑。夕阳把影子拖得老长,他气喘吁吁冲到柳韵面前,一把抱住她腰,声音发颤:“主人……对不起,鸡鸡胀得要炸了,求您让我射吧……”
柳韵皱眉,膝盖顶开他胯下那硬邦邦的小笼子,冷笑的说:“松开,硌得我疼。”
陈烨讪讪放手,低头不敢看她。柳韵拎着他后领,像拎小鸡似的把他拽回家。
门一关,帘子拉严。
“脱。”
陈烨三两下扒光,赤条条站那儿,小腹鼓起,贞操锁把那团肉勒得青筋暴起。
柳韵坐进沙发,拍拍大腿:“坐上来。”
陈烨爬上去,屁股贴着她丝袜腿,热得发烫。柳韵抬脚,黑色短靴“嗒”一声落地,靴口热气腾腾。她抓起靴子,直接扣到陈烨脸上:“自己按住,大口吸。”
酸臭的脚汗味混着皮革,像一股热浪冲进鼻腔。陈烨双手捧着靴子,鼻翼翕动,贪婪地深吸,喉结滚动。
咔哒。钥匙插进锁孔,冰冷的金属笼子被取下,软肉啪地弹出来,涨得通红。
柳韵指尖勾住龟头,慢条斯理地撸,拇指在马眼上打圈:“乖,叫主人。”
“主人……”陈烨声音发抖,带着哭腔。
快感像电流爬满脊椎,眼看就要炸开,柳韵却突然松手,起身理裙子:“哎呀,主人又想起急事。”
陈烨急得抓她裙角:“别……求您……”
柳韵笑得像只猫,重新把锁扣上:“明天再来。”
接下来的日子,成了陈烨的炼狱。
第二天,柳韵让他跪在地板上,双手捧着两只短靴,像捧宝贝似的在小鸡鸡上摩擦。粗糙的靴底刮过嫩肉,疼得他直抽气,却又硬得发疼。柳韵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他,红唇轻启:“男人天生就该被女人踩,记住了?”
第三天,她让他跪得更低,靴子扣在脸上,大口呼吸,自己光脚踩上那团肉,脚趾夹住龟头,来回碾。陈烨被臭味熏得头晕,脚底的温度烫得他哆嗦,嘴里机械地重复:“男人……低贱……”
第四天,柳韵脱了丝袜,把汗湿的脚塞进他嘴里:“舔干净。”
陈烨舌头卷着脚趾缝里的咸涩,鼻腔全是她的味道,脑子空得只剩一个念头——射精。
每次都在顶点前停下,锁扣咔哒合拢,柳韵拍拍他脸:“明天继续。”
学校里,陈烨变了。不再往张雪莉书包里塞虫子,不再扯女生的辫子。他一个人坐在角落,眼神空洞,裤裆里那团金属硌得他坐立难安。午休铃一响,他就盯着钟,数着秒针,心里只有一个声音——下午,能不能射。
柳韵看着监控里那个曾经嚣张的刺头,如今缩在座位里,眼神像条求食的狗,满意地勾了勾唇。
计划成了。
陈烨的脑子里,再没有“欺负”二字,只剩跪在女人脚下、乞求射精的废物念头。
陈烨是育才小学六年级三班的刺头,十二岁,父母离婚后扔给他奶奶带,从小没人管,养出一身无法无天的痞劲。老师管不住,同学不敢惹,他最爱欺负的,就是长得白净漂亮的张雪莉。
那天午休,他抓了只绿油油的蟋蟀,趁张雪莉趴桌子上睡觉,悄悄塞进她衣领里。虫子乱爬,张雪莉尖叫着跳起来,眼泪哗哗往下掉,怎么哄都止不住。她朋友围了一圈,手忙脚乱帮她拍衣服,可她抖得像筛糠,哭得嗓子都哑了。
放学回家,张雪莉憋到晚上,终于忍不住扑进妈妈怀里,把这些天被陈烨欺负的事全抖了出来。妈妈柳韵把女儿搂紧,轻拍她的背,等她哭够了,才抬手替她擦泪,声音低得像夜色里磨过的刀:“没事,宝贝。他既然敢做坏事,就别怪坏事找上门。”
第二天,四点半。
陈烨抄近路走那条窄巷,书包甩在肩后,嘴里叼着根棒棒糖。身后忽然响起高跟鞋敲地面的声音,脆生生的,像敲在心口。
“陈烨同学。”
他猛地回头,看见一个女人倚在墙边,三十出头,卷发红唇,黑色紧身裙裹得曲线勾人。她笑得温温柔柔,眼底却冷得像冰。
“你谁啊?”陈烨把糖咬得咔嚓响。
“我是张雪莉的妈妈。”柳韵走近一步,香水味混着淡淡皮革味钻进他鼻子里,“叫我柳姨就好。”
陈烨喉咙一紧,棒棒糖差点掉地上。他后退半步,干笑:“我……我没欺负她……”
“没关系。”柳韵弯下腰,脸凑到他面前,红唇几乎贴上他的耳朵,“姨知道你喜欢玩游戏……想不想跟姨玩点更好玩的?”
她舌尖轻轻扫过他耳廓,湿热痒得陈烨浑身一抖。纤细的手指像不经意地掠过他裤裆,声音软得滴水:“是色色的游戏喔……”
陈烨脑子轰地一声空白,脸红得像煮熟的虾,鬼使神差地点头。
柳韵直起身,冲他勾了勾手指:“跟姨回家。”
她家在巷子尽头,三楼,门一关,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脱光。”柳韵坐在沙发上,翘起腿,短靴尖在地板上点了点。
陈烨手抖着把校服扒光,赤条条站在她面前。小鸡鸡因为紧张缩成一小团。
柳韵掩唇笑出声:“哎哟,小男生的小鸡鸡可真可爱,这么小就想玩大人的游戏?”
陈烨臊得想找地缝钻。柳韵却起身,蹲在他身前,指尖捏住那团软肉,轻轻一撸,包皮被翻开,粉嫩的龟头露出来。
“这是什么?”陈烨声音发颤。
“自慰啊。”柳韵像教课似的,握住他小小的阴茎,上下套弄,“没自己玩过?姨教你。”
她手劲儿时轻时重,指腹刮过冠状沟,陈烨腿软得站不住,喘得像刚跑完八百米。
“舒服吗?”柳韵俯身,嘴唇贴着他耳朵,吐出一口温热的气,“张嘴。”
陈烨下意识张开,柳韵“啵”地吐了长长一口唾液进去,拉丝挂在他下唇,凉凉的,带着淡淡甜味。
“吞下去。”她命令。
陈烨咕咚一声咽了,喉结滚动。
柳韵满意地笑,抬脚脱下一只黑色短靴,靴口还热乎乎的,直接扣到陈烨脸上。
“闻。”她声音低哑,“大口呼吸,把姨的味道全吸进去。”
酸臭的脚汗味混着皮革和成熟女人的体香,像一股热浪直冲脑门。陈烨被熏得头晕,却舍不得挪开,鼻翼翕动,大口吸着。
“叫主人。”柳韵手下加快,拇指在马眼上打圈。
“主、主人……”陈烨声音发抖,带着哭腔。
就在他小腹紧绷,快要射出来的前一秒,柳韵突然松手,靴子重新套回脚上,站起身理了理裙子。
“啊?”陈烨急得抓耳挠腮,小鸡鸡涨得通红,直挺挺翘着,“别停啊……”
“急什么?”柳韵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粉色的小巧金属笼子,在指尖晃了晃,“想继续玩,就戴上这个。”
“这是啥?”
“贞操锁。”她笑得像只餍足的猫,“戴上它,你就是主人的小狗了。戴上它的人要对拥有钥匙的主人保持绝对的忠诚喔。
陈烨看着那冰冷的金属,脑子里却全是刚才的快感,咬牙点头。
咔哒。
锁扣合拢,小鸡鸡被硬生生压进笼子,龟头从网格里挤出一小点,涨得发紫。
柳韵把钥匙挂到脖子上,坠进深深的乳沟。
“明天放学,还来找主人。”她俯身亲了亲他汗湿的额头,“乖。”
陈烨提着裤子,腿软得几乎走不动,贞操锁的重量硌得他每迈一步都又疼又痒。
巷子口,夕阳拉长他的影子,像一条被拴住的小狗。
第二天放学铃一响,陈烨书包都没背稳,撒腿就往巷子跑。夕阳把影子拖得老长,他气喘吁吁冲到柳韵面前,一把抱住她腰,声音发颤:“主人……对不起,鸡鸡胀得要炸了,求您让我射吧……”
柳韵皱眉,膝盖顶开他胯下那硬邦邦的小笼子,冷笑的说:“松开,硌得我疼。”
陈烨讪讪放手,低头不敢看她。柳韵拎着他后领,像拎小鸡似的把他拽回家。
门一关,帘子拉严。
“脱。”
陈烨三两下扒光,赤条条站那儿,小腹鼓起,贞操锁把那团肉勒得青筋暴起。
柳韵坐进沙发,拍拍大腿:“坐上来。”
陈烨爬上去,屁股贴着她丝袜腿,热得发烫。柳韵抬脚,黑色短靴“嗒”一声落地,靴口热气腾腾。她抓起靴子,直接扣到陈烨脸上:“自己按住,大口吸。”
酸臭的脚汗味混着皮革,像一股热浪冲进鼻腔。陈烨双手捧着靴子,鼻翼翕动,贪婪地深吸,喉结滚动。
咔哒。钥匙插进锁孔,冰冷的金属笼子被取下,软肉啪地弹出来,涨得通红。
柳韵指尖勾住龟头,慢条斯理地撸,拇指在马眼上打圈:“乖,叫主人。”
“主人……”陈烨声音发抖,带着哭腔。
快感像电流爬满脊椎,眼看就要炸开,柳韵却突然松手,起身理裙子:“哎呀,主人又想起急事。”
陈烨急得抓她裙角:“别……求您……”
柳韵笑得像只猫,重新把锁扣上:“明天再来。”
接下来的日子,成了陈烨的炼狱。
第二天,柳韵让他跪在地板上,双手捧着两只短靴,像捧宝贝似的在小鸡鸡上摩擦。粗糙的靴底刮过嫩肉,疼得他直抽气,却又硬得发疼。柳韵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他,红唇轻启:“男人天生就该被女人踩,记住了?”
第三天,她让他跪得更低,靴子扣在脸上,大口呼吸,自己光脚踩上那团肉,脚趾夹住龟头,来回碾。陈烨被臭味熏得头晕,脚底的温度烫得他哆嗦,嘴里机械地重复:“男人……低贱……”
第四天,柳韵脱了丝袜,把汗湿的脚塞进他嘴里:“舔干净。”
陈烨舌头卷着脚趾缝里的咸涩,鼻腔全是她的味道,脑子空得只剩一个念头——射精。
每次都在顶点前停下,锁扣咔哒合拢,柳韵拍拍他脸:“明天继续。”
学校里,陈烨变了。不再往张雪莉书包里塞虫子,不再扯女生的辫子。他一个人坐在角落,眼神空洞,裤裆里那团金属硌得他坐立难安。午休铃一响,他就盯着钟,数着秒针,心里只有一个声音——下午,能不能射。
柳韵看着监控里那个曾经嚣张的刺头,如今缩在座位里,眼神像条求食的狗,满意地勾了勾唇。
计划成了。
陈烨的脑子里,再没有“欺负”二字,只剩跪在女人脚下、乞求射精的废物念头。
很喜欢这种风格的文,作者加油
(ง •̀_•́)ง
(ง •̀_•́)ง
催更催更
情节应该是基于Mr.Hokke本子的改写吧。虽然知道情节发展了,但是这个情节还是好冲。
柳韵把陈烨带回家,门一关,她抬脚踹开扑过来的他,高跟鞋磕在地板上脆响。陈烨摔得一屁股蹲,抬头眼巴巴:“主人……我想舔您的脚……”
柳韵冷笑,弯腰揪住他衣领,像拎小鸡似的拖到客厅中央。她从柜子里翻出一个不锈钢狗盆,“咣”一声砸到地上,盆底震得嗡嗡响。
陈烨跪在那儿,眼巴巴看着她解开裤扣,黑色蕾丝内裤滑到膝盖。柳韵蹲下身,橙黄的尿液哗啦啦淌进盆里,溅起细密泡沫,骚味扑鼻。
“想舔脚?”她提好裤子,踢了踢盆沿,“像狗一样,把这盆舔干净。”
陈烨盯着那盆晃荡的液体,胃里翻腾,喉咙发涩。柳韵抱臂,冷眼扫他:“二选一——以后别想碰我的脚,或者现在丢掉你那点可怜的自尊,把主人赏的圣水喝光。”
男人低贱,女人的排泄物都比男人金贵——这些话像刀子刻在他脑子里。陈烨膝盖一软,趴到盆前,舌头伸进去,咸涩滚烫的尿液灌进喉咙,他干呕两下,硬吞下去。一口接一口,舌尖卷着泡沫,像狗舔水,最后把盆底舔得锃光瓦亮。
柳韵勾唇,坐回沙发,翘起腿:“奖励。”
陈烨爬过去,埋头在她脚间,舌头卷着脚趾缝的汗渍,酸臭味混着尿骚,像毒药钻进脑子。
第二天,第三天……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跪在狗盆前,喝光那盆热腾腾的尿。一星期后,陈烨不再反胃,甚至开始眼馋那股味道,舌头伸出来,像哈士奇等着骨头。
这天,柳韵拽着他进了卫生间,瓷砖冷得刺骨。马桶盖“啪”一声掀起,她脱了裤子坐上去,哗啦啦的尿声后,几坨软热的粪便扑通掉进水里,臭味炸开,像烂蛋捂在鼻下。
擦干净后,柳韵揪住陈烨后脑勺,猛地按进马桶。冰凉的马桶水没到鼻尖,粪便的恶臭直冲天灵盖。陈烨挣扎半秒,柳韵一脚踩住他后颈,马桶盖“啪”地合上,夹紧他的脑袋。
“闻。”她声音从外面飘来,带着笑,“一小时后我来看。要是吃了,主人有神秘奖励。”
门关上,电视声隐约传来。陈烨眼前是漂着粪便的黄水,臭得眼泪直淌。他大口喘气,熏得头晕脑胀,半小时后,恶心渐渐退去,脑子里只剩一个声音:主人说要吃。
他张嘴,咬下一小块,苦涩腥臭在舌尖炸开,胃里翻江倒海。他闭眼硬咽,第二口,第三口……粪便混着马桶水滑进喉咙,最后舌头贴着瓷壁,把屎痕舔得一干二净。
一小时后,柳韵推开门,掀起马桶盖,看见空荡荡的马桶,挑眉:“哟,小贱狗还真听话。”
她拽出陈烨,扔给他漱口水,冲掉嘴里的味道,然后拖到客厅让他跪下。柳韵从厨房端出一块草莓蛋糕,抬脚踩烂,奶油混着脚汗糊在脚趾缝。她伸到他嘴边,陈烨舌头卷着,甜腻的蛋糕裹着酸臭,舔得飞快。
地上剩一小坨,柳韵低头,“呸”一声,浓痰吐在烂泥似的蛋糕上,黏稠拉丝。
“吃。”
陈烨趴下去,舌头卷着痰和蛋糕,咽得干干净净。
柳韵看着他空洞的眼神,满意地拍拍手。门关上后,她靠在沙发,红唇勾起:最后一步,要开始了。
次日放学铃一响,张雪莉背着书包快步往家赶,妈妈早上叮嘱过:今天别去补习班,早点回来,有惊喜。她心痒难耐,脚步像踩了风火轮。
一推开门,屋里那股熟悉的酸臭味扑面而来,脚汗、尿骚、皮革味搅成一股热浪,熏得她鼻翼微皱。客厅灯光昏黄,门口跪着个光溜溜的小身影——陈烨,额头死死贴在地板上,屁股撅得高高的,贞操锁在胯间晃出细碎的金属碰撞声,像条被拴住的狗。
柳韵站在他身后,高跟鞋跟稳稳踩住陈烨的后脑勺,红唇弯出餍足的弧度:“女儿回来了,贱狗该怎么迎接?”
陈烨声音发颤,带着讨好的哭腔:“欢迎……小主人回家……”
张雪莉书包“啪嗒”落地,眼睛瞪得溜圆。她妈笑得像只狡黠的狐狸,鞋跟轻轻一碾:“不是一直吵着要条小狗吗?妈妈给你训好了,去,让它服侍你。”
陈烨立刻膝行爬到张雪莉脚边,牙齿咬住她运动鞋的鞋带,灵巧地解开蝴蝶结,再叼住鞋帮,一点一点往下拽。鞋子落地,热气腾腾的白棉袜露出来,印着可爱的小熊,袜底却黄渍斑斑,下午体育课的汗味浓得化不开,酸臭里混着泥土和橡胶的腥气。
他把脸埋进去,鼻尖贴着袜底,深吸一口,热浪直冲脑门。贞操锁里的小鸡鸡疯狂往外顶,金属网格勒得嫩肉发紫,疼得他眼泪汪汪,却又硬得发抖。
牙齿再次咬住袜口,卷到脚踝,张雪莉汗湿的小脚丫弹出来,脚趾缝里卡着黑乎乎的脚垢。他舌头探进去,一点点卷走咸涩的汗渍和泥垢,喉结滚动,咽得干干净净。
张雪莉看着曾经把虫子塞进自己衣领的恶霸,如今像条哈士奇一样舔她的脚底,胸口那口恶气终于化成快意。她咯咯笑着,右脚拇指捏住陈烨的鼻子,左脚猛地踹进他嘴里,脚趾直顶喉咙。
“呜——”陈烨喉咙被堵得死死的,窒息感像铁钳掐住脖子,眼泪瞬间飙出。张雪莉看他脸涨成猪肝色,才慢悠悠抽出来,让他喘两口热气,又塞回去。玩到尽兴才拔出,脚趾上挂满他的口水,晶亮拉丝。
陈烨立刻重新五体投地,额头磕得地板咚咚响,等待下一道命令。
柳韵牵着两人进卧室,窗帘拉得严丝合缝,空气里弥漫着润滑油的甜腥。她从床头柜摸出根黑亮的假阳具,绑在胯间,晃荡着像条狰狞的尾巴。
“小莉,妈妈带你完成最后的调教。”
张雪莉眼睛亮得像点燃的烟花,兴奋地点头。
柳韵往假阳具和陈烨的屁眼涂润滑油,冰凉油腻,顺着股沟滑到大腿内侧。她坐到床沿,拍拍大腿:“自己坐上来。”
陈烨掰开屁股,对准那根粗硬的东西,慢慢往下沉。“噗嗤”一声,整根没入,龟头直顶前列腺,疼得他惨叫,声音却带着战栗的快感。
柳韵把张雪莉下午的臭运动鞋扣到他脸上,鞋口热气裹住口鼻:“闻着小主人的味道,动。”
陈烨双手捧鞋,大口吸气,酸臭的脚汗味混着橡胶,像电流窜进下体。咔哒,贞操锁打开,小鸡鸡弹出来,涨得通红。
柳韵捏住他粉嫩的乳头,轻轻一拧:“小莉,坐对面。”
张雪莉盘腿坐在床边,把下午的臭棉袜套到陈烨的小鸡鸡上,袜口勒住根部,湿热的布料裹得严严实实。她脚掌夹住,上下撸动,粗糙的棉线刮过龟头,疼痒交织。
假阳具一下下撞击前列腺,棉袜摩擦马眼,陈烨腰眼发麻,哭叫着:“要……要射了……”
他以为又会像往常一样戛然停止,却听见柳韵低笑:“想射吗?想的话,以后别回家了。明天妈妈带你去个没监控的地方,阉掉你的蛋蛋,只留个空壳。你就彻底当我们母女的奴隶、厕所、贱狗,永远跪着。”
陈烨脑子轰地一声,阉割两个字像冰锥扎进心口,可脚汗味、尿骚味、女人脚底的触感早已把他脑子泡成浆糊。他哆嗦着点头,眼泪混着鼻涕糊了满脸。
柳韵勾唇,让张雪莉放慢动作,一句句带着他宣誓:
“我陈烨……自愿成为柳韵、张雪莉母女的奴隶……厕所……贱狗……”
每念一句,张雪莉的脚掌就加快一分,假阳具撞得更深。誓言念完最后一字,陈烨腰眼一紧,精液喷涌——
却在那一瞬,动作骤停。棉袜松开,假阳具抽出,射精戛然中断,成了干涩的抽搐,让他难受无比,喉咙里发出呜咽。
柳韵母女居高临下看着他,像看一条刚被阉的公狗。
夜色沉下来,陈烨踉跄着回到奶奶家,贞操锁重新扣上,硌得胯间生疼。奶奶在厨房喊他吃饭,他低头应了一声,脑子里却全是女人脚底的酸臭和明天即将失去的睾丸。
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柳韵冷笑,弯腰揪住他衣领,像拎小鸡似的拖到客厅中央。她从柜子里翻出一个不锈钢狗盆,“咣”一声砸到地上,盆底震得嗡嗡响。
陈烨跪在那儿,眼巴巴看着她解开裤扣,黑色蕾丝内裤滑到膝盖。柳韵蹲下身,橙黄的尿液哗啦啦淌进盆里,溅起细密泡沫,骚味扑鼻。
“想舔脚?”她提好裤子,踢了踢盆沿,“像狗一样,把这盆舔干净。”
陈烨盯着那盆晃荡的液体,胃里翻腾,喉咙发涩。柳韵抱臂,冷眼扫他:“二选一——以后别想碰我的脚,或者现在丢掉你那点可怜的自尊,把主人赏的圣水喝光。”
男人低贱,女人的排泄物都比男人金贵——这些话像刀子刻在他脑子里。陈烨膝盖一软,趴到盆前,舌头伸进去,咸涩滚烫的尿液灌进喉咙,他干呕两下,硬吞下去。一口接一口,舌尖卷着泡沫,像狗舔水,最后把盆底舔得锃光瓦亮。
柳韵勾唇,坐回沙发,翘起腿:“奖励。”
陈烨爬过去,埋头在她脚间,舌头卷着脚趾缝的汗渍,酸臭味混着尿骚,像毒药钻进脑子。
第二天,第三天……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跪在狗盆前,喝光那盆热腾腾的尿。一星期后,陈烨不再反胃,甚至开始眼馋那股味道,舌头伸出来,像哈士奇等着骨头。
这天,柳韵拽着他进了卫生间,瓷砖冷得刺骨。马桶盖“啪”一声掀起,她脱了裤子坐上去,哗啦啦的尿声后,几坨软热的粪便扑通掉进水里,臭味炸开,像烂蛋捂在鼻下。
擦干净后,柳韵揪住陈烨后脑勺,猛地按进马桶。冰凉的马桶水没到鼻尖,粪便的恶臭直冲天灵盖。陈烨挣扎半秒,柳韵一脚踩住他后颈,马桶盖“啪”地合上,夹紧他的脑袋。
“闻。”她声音从外面飘来,带着笑,“一小时后我来看。要是吃了,主人有神秘奖励。”
门关上,电视声隐约传来。陈烨眼前是漂着粪便的黄水,臭得眼泪直淌。他大口喘气,熏得头晕脑胀,半小时后,恶心渐渐退去,脑子里只剩一个声音:主人说要吃。
他张嘴,咬下一小块,苦涩腥臭在舌尖炸开,胃里翻江倒海。他闭眼硬咽,第二口,第三口……粪便混着马桶水滑进喉咙,最后舌头贴着瓷壁,把屎痕舔得一干二净。
一小时后,柳韵推开门,掀起马桶盖,看见空荡荡的马桶,挑眉:“哟,小贱狗还真听话。”
她拽出陈烨,扔给他漱口水,冲掉嘴里的味道,然后拖到客厅让他跪下。柳韵从厨房端出一块草莓蛋糕,抬脚踩烂,奶油混着脚汗糊在脚趾缝。她伸到他嘴边,陈烨舌头卷着,甜腻的蛋糕裹着酸臭,舔得飞快。
地上剩一小坨,柳韵低头,“呸”一声,浓痰吐在烂泥似的蛋糕上,黏稠拉丝。
“吃。”
陈烨趴下去,舌头卷着痰和蛋糕,咽得干干净净。
柳韵看着他空洞的眼神,满意地拍拍手。门关上后,她靠在沙发,红唇勾起:最后一步,要开始了。
次日放学铃一响,张雪莉背着书包快步往家赶,妈妈早上叮嘱过:今天别去补习班,早点回来,有惊喜。她心痒难耐,脚步像踩了风火轮。
一推开门,屋里那股熟悉的酸臭味扑面而来,脚汗、尿骚、皮革味搅成一股热浪,熏得她鼻翼微皱。客厅灯光昏黄,门口跪着个光溜溜的小身影——陈烨,额头死死贴在地板上,屁股撅得高高的,贞操锁在胯间晃出细碎的金属碰撞声,像条被拴住的狗。
柳韵站在他身后,高跟鞋跟稳稳踩住陈烨的后脑勺,红唇弯出餍足的弧度:“女儿回来了,贱狗该怎么迎接?”
陈烨声音发颤,带着讨好的哭腔:“欢迎……小主人回家……”
张雪莉书包“啪嗒”落地,眼睛瞪得溜圆。她妈笑得像只狡黠的狐狸,鞋跟轻轻一碾:“不是一直吵着要条小狗吗?妈妈给你训好了,去,让它服侍你。”
陈烨立刻膝行爬到张雪莉脚边,牙齿咬住她运动鞋的鞋带,灵巧地解开蝴蝶结,再叼住鞋帮,一点一点往下拽。鞋子落地,热气腾腾的白棉袜露出来,印着可爱的小熊,袜底却黄渍斑斑,下午体育课的汗味浓得化不开,酸臭里混着泥土和橡胶的腥气。
他把脸埋进去,鼻尖贴着袜底,深吸一口,热浪直冲脑门。贞操锁里的小鸡鸡疯狂往外顶,金属网格勒得嫩肉发紫,疼得他眼泪汪汪,却又硬得发抖。
牙齿再次咬住袜口,卷到脚踝,张雪莉汗湿的小脚丫弹出来,脚趾缝里卡着黑乎乎的脚垢。他舌头探进去,一点点卷走咸涩的汗渍和泥垢,喉结滚动,咽得干干净净。
张雪莉看着曾经把虫子塞进自己衣领的恶霸,如今像条哈士奇一样舔她的脚底,胸口那口恶气终于化成快意。她咯咯笑着,右脚拇指捏住陈烨的鼻子,左脚猛地踹进他嘴里,脚趾直顶喉咙。
“呜——”陈烨喉咙被堵得死死的,窒息感像铁钳掐住脖子,眼泪瞬间飙出。张雪莉看他脸涨成猪肝色,才慢悠悠抽出来,让他喘两口热气,又塞回去。玩到尽兴才拔出,脚趾上挂满他的口水,晶亮拉丝。
陈烨立刻重新五体投地,额头磕得地板咚咚响,等待下一道命令。
柳韵牵着两人进卧室,窗帘拉得严丝合缝,空气里弥漫着润滑油的甜腥。她从床头柜摸出根黑亮的假阳具,绑在胯间,晃荡着像条狰狞的尾巴。
“小莉,妈妈带你完成最后的调教。”
张雪莉眼睛亮得像点燃的烟花,兴奋地点头。
柳韵往假阳具和陈烨的屁眼涂润滑油,冰凉油腻,顺着股沟滑到大腿内侧。她坐到床沿,拍拍大腿:“自己坐上来。”
陈烨掰开屁股,对准那根粗硬的东西,慢慢往下沉。“噗嗤”一声,整根没入,龟头直顶前列腺,疼得他惨叫,声音却带着战栗的快感。
柳韵把张雪莉下午的臭运动鞋扣到他脸上,鞋口热气裹住口鼻:“闻着小主人的味道,动。”
陈烨双手捧鞋,大口吸气,酸臭的脚汗味混着橡胶,像电流窜进下体。咔哒,贞操锁打开,小鸡鸡弹出来,涨得通红。
柳韵捏住他粉嫩的乳头,轻轻一拧:“小莉,坐对面。”
张雪莉盘腿坐在床边,把下午的臭棉袜套到陈烨的小鸡鸡上,袜口勒住根部,湿热的布料裹得严严实实。她脚掌夹住,上下撸动,粗糙的棉线刮过龟头,疼痒交织。
假阳具一下下撞击前列腺,棉袜摩擦马眼,陈烨腰眼发麻,哭叫着:“要……要射了……”
他以为又会像往常一样戛然停止,却听见柳韵低笑:“想射吗?想的话,以后别回家了。明天妈妈带你去个没监控的地方,阉掉你的蛋蛋,只留个空壳。你就彻底当我们母女的奴隶、厕所、贱狗,永远跪着。”
陈烨脑子轰地一声,阉割两个字像冰锥扎进心口,可脚汗味、尿骚味、女人脚底的触感早已把他脑子泡成浆糊。他哆嗦着点头,眼泪混着鼻涕糊了满脸。
柳韵勾唇,让张雪莉放慢动作,一句句带着他宣誓:
“我陈烨……自愿成为柳韵、张雪莉母女的奴隶……厕所……贱狗……”
每念一句,张雪莉的脚掌就加快一分,假阳具撞得更深。誓言念完最后一字,陈烨腰眼一紧,精液喷涌——
却在那一瞬,动作骤停。棉袜松开,假阳具抽出,射精戛然中断,成了干涩的抽搐,让他难受无比,喉咙里发出呜咽。
柳韵母女居高临下看着他,像看一条刚被阉的公狗。
夜色沉下来,陈烨踉跄着回到奶奶家,贞操锁重新扣上,硌得胯间生疼。奶奶在厨房喊他吃饭,他低头应了一声,脑子里却全是女人脚底的酸臭和明天即将失去的睾丸。
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30分钟了,快更新🥳
周六的晨光像一层薄薄的金纱,柔柔地洒在那条荒凉的小巷里,巷口野猫蜷在垃圾桶旁舔爪子。柳韵的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滑过来,车窗降下,红唇弯出一抹慵懒的弧度:“上车,小狗。”
陈烨缩在墙角,校服皱得像被雨水泡烂的纸,贞操锁一夜硌得他腰眼发麻,闻言膝行爬上后座,金属碰撞声细碎,像碎冰滚进喉咙。车门“砰”地合上,隔绝了外面的蝉鸣。
车厢里冷气开得低,混着她那股熟甜的香水味,像无形的丝带缠住陈烨的鼻腔,熏得他头晕目眩。柳韵单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随意搭在档位上,指甲油鲜红得像滴血。车子平稳地穿过晨雾,拐进熟悉的小区,轮胎碾过落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到家了。电梯里镜面反射出陈烨狼狈的模样,柳韵的高跟鞋在瓷砖上敲出清脆的节奏,像倒计时的鼓点。门一开,空调的凉风扑面,混着屋里残留的脚汗与尿骚,熟悉得让人窒息。
“脱光。”柳韵甩掉高跟鞋,鞋跟磕在玄关瓷砖上,脆响像鞭子抽在心口。
陈烨抖着手扒得精光,膝盖跪在冰凉的地板上,冻得泛起一层鸡皮疙瘩。柳韵从冰箱旁摸出个银光闪闪的兽用无血去势钳,网购的,包装纸还带着快递的胶带味,撕开时发出刺啦的轻响。
她蹲下身,捏住左边睾丸,指尖冰凉得像蛇缠上来。钳口对准精索,咔哒一声合拢,血管、输精管瞬间被压扁碾碎,剧痛像雷劈进下腹,电流般窜遍四肢百骸,陈烨张嘴要惨叫——
张雪莉咯咯笑着从旁扑过来,右脚猛地踹进他喉咙,脚趾顶到嗓子眼,堵死所有声音,只剩鼻腔里呜咽的嗡鸣。她从洗衣框里捞出昨晚的臭棉袜,黄渍斑斑,汗味馊得冲鼻,一团塞进陈烨嘴里,顶到喉咙,咸涩的布料吸饱口水,胀得他眼泪横流。
柳韵把钳子递给女儿,笑得温柔如水:“宝贝,换你。”
张雪莉接过,学着妈妈的样子,钳口对准另一边,咔哒!碾碎声细如蚊鸣,痛感却炸得陈烨眼前发黑,额头砸地,闷出“咚”一声,地板震得他牙根发酸。
柳韵拿根粉色皮筋,熟练地勒住阴囊根部,打个死结。神经已断,疼痛竟诡异地淡下去,只剩钝钝的坠胀,像一团湿棉花堵在胯间。她拍拍陈烨汗湿的脸,声音轻柔得像哄孩子:“一周后,阴囊会坏死脱落。这是酒精、消炎药,自己涂,别弄脏地板。”
卧室里,新买的狗笼闪着冷光,角落铺了层旧毛巾,散发着洗衣粉的淡淡香味。柳韵指了指笼门:“以后这儿就是你家,好好适应。”
门锁咔哒合上,母女俩换上新裙子,拎包出门,笑声在走廊里飘远,像银铃:“走,宝贝,妈妈带你吃冰淇淋,草莓味的。”
周六、周日,陈烨蜷在笼里,胯间火烧火燎,酒精味呛得眼泪打转,铁栏冰凉,硌得骨头生疼。奶奶起初只当他贪玩,喊两声没人应,周一还做好饭等,周二开始慌了,拄着拐杖满街贴寻人启事——十二岁男孩,父母离异,跟奶奶相依为命。派出所敷衍地立案,查几天,监控盲区太多,草草结案,只剩一张泛黄的寻人启事贴在电线杆上,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一周后,凌晨三点,陈烨疼醒,阴囊像烂桃一样掉进笼底,血水混着脓,腥得刺鼻,空气里弥漫着腐烂的甜味。他抖着双手用酒精擦拭,空荡荡的裆部只剩小鸡鸡软软地耷拉,像被拔了刺的玫瑰,风一吹就颤。
柳韵推门进来,踩着毛绒拖鞋,睡眼惺忪,头发散乱却更显妩媚:“啧,掉了?乖,从今天起,你是我们家的‘小厨’。”
她扔给他一本菜谱,封面油渍斑斑,书页卷角。陈烨翻开,菜名花哨,他却像抓住救命稻草——奶奶教过他煎蛋,蛋黄要半熟。
从此,他的日历被脚臭味和剩饭填满。
凌晨五点,闹钟尖锐地响,陈烨像狗一样四肢着地爬出笼子,赤条条钻进卧室,舌头先卷上柳韵的脚心,酸臭的汗味混着昨晚的尿骚,他舔得啧啧有声,舌尖在脚趾缝里打转;再爬到张雪莉床边,舌尖轻扫她脚底,浓烈的少女脚汗带着奶香的甜腻,舔得她脚趾蜷缩,咯咯笑醒。张雪莉翻身,一脚踹他脸,脚跟砸在鼻梁,疼得他眼冒金星:“吵死了!”有时母女起床气重,拳脚雨点般落下,砸得他皮开肉绽,血珠渗出,他却只敢蜷缩,呜咽着继续舔,像条被雨淋湿的狗。
两人洗漱完,踩上特制的掏空板凳,陈烨趴在下面,晨尿热腾腾浇进喉咙,浓烈的骚味呛得他眼泪直流,却得一口不漏咽下,喉结滚动,发出咕咚咕咚的声响。
母女出门上班上学,门锁咔哒,他开始拖地、洗衣、擦窗,汗水混着消毒水味,地板反射出他扭曲的影子,下午备晚餐,刀工越来越利落,葱花切得细如发丝。
傍晚,门开,母女笑闹着进来,高跟鞋和运动鞋的脚步声交织,陈烨跪在玄关,牙齿咬住鞋带,脱下鞋子,鞋里闷了一天的脚臭像炸弹爆开,热浪扑面。他把脸埋进去,大口吸气,为两双脚除臭,再舌头卷着脚趾缝,把汗垢、皮屑舔得干干净净,舌尖在脚心画圈,带出细微的酥痒。
晚餐时,他跪在桌下,狗盆里盛着剩饭冷汤,油花漂浮,母女偶尔吐一块啃剩的骨头,或把不爱的青菜甩给他,像喂流浪狗,骨头滚到盆边,沾上酱汁。
饭后,他再次充当马桶。柳韵便秘时,他舌头钻进肛门,卷着硬结的大便吮出来,腥臭在嘴里炸开,像腐烂的果实;张雪莉拉得稀,他张嘴接住,热乎乎滑进喉咙,溅到下巴。
夜深,母女躺在床上,他跪在床尾,舌头为四只脚按摩,脚心、脚背、脚趾,一寸不落,力度时轻时重,直到两人呼吸均匀,发出轻微的鼾声,他才轻手轻脚爬回笼子,蜷成一团,铁栏冰凉,硌得骨头生疼。
笼门锁上,黑暗吞没最后一丝光,他闭上眼,脑子里只有脚臭味和明天凌晨五点的闹钟,循环往复,像永不磨灭的咒语。
陈烨缩在墙角,校服皱得像被雨水泡烂的纸,贞操锁一夜硌得他腰眼发麻,闻言膝行爬上后座,金属碰撞声细碎,像碎冰滚进喉咙。车门“砰”地合上,隔绝了外面的蝉鸣。
车厢里冷气开得低,混着她那股熟甜的香水味,像无形的丝带缠住陈烨的鼻腔,熏得他头晕目眩。柳韵单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随意搭在档位上,指甲油鲜红得像滴血。车子平稳地穿过晨雾,拐进熟悉的小区,轮胎碾过落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到家了。电梯里镜面反射出陈烨狼狈的模样,柳韵的高跟鞋在瓷砖上敲出清脆的节奏,像倒计时的鼓点。门一开,空调的凉风扑面,混着屋里残留的脚汗与尿骚,熟悉得让人窒息。
“脱光。”柳韵甩掉高跟鞋,鞋跟磕在玄关瓷砖上,脆响像鞭子抽在心口。
陈烨抖着手扒得精光,膝盖跪在冰凉的地板上,冻得泛起一层鸡皮疙瘩。柳韵从冰箱旁摸出个银光闪闪的兽用无血去势钳,网购的,包装纸还带着快递的胶带味,撕开时发出刺啦的轻响。
她蹲下身,捏住左边睾丸,指尖冰凉得像蛇缠上来。钳口对准精索,咔哒一声合拢,血管、输精管瞬间被压扁碾碎,剧痛像雷劈进下腹,电流般窜遍四肢百骸,陈烨张嘴要惨叫——
张雪莉咯咯笑着从旁扑过来,右脚猛地踹进他喉咙,脚趾顶到嗓子眼,堵死所有声音,只剩鼻腔里呜咽的嗡鸣。她从洗衣框里捞出昨晚的臭棉袜,黄渍斑斑,汗味馊得冲鼻,一团塞进陈烨嘴里,顶到喉咙,咸涩的布料吸饱口水,胀得他眼泪横流。
柳韵把钳子递给女儿,笑得温柔如水:“宝贝,换你。”
张雪莉接过,学着妈妈的样子,钳口对准另一边,咔哒!碾碎声细如蚊鸣,痛感却炸得陈烨眼前发黑,额头砸地,闷出“咚”一声,地板震得他牙根发酸。
柳韵拿根粉色皮筋,熟练地勒住阴囊根部,打个死结。神经已断,疼痛竟诡异地淡下去,只剩钝钝的坠胀,像一团湿棉花堵在胯间。她拍拍陈烨汗湿的脸,声音轻柔得像哄孩子:“一周后,阴囊会坏死脱落。这是酒精、消炎药,自己涂,别弄脏地板。”
卧室里,新买的狗笼闪着冷光,角落铺了层旧毛巾,散发着洗衣粉的淡淡香味。柳韵指了指笼门:“以后这儿就是你家,好好适应。”
门锁咔哒合上,母女俩换上新裙子,拎包出门,笑声在走廊里飘远,像银铃:“走,宝贝,妈妈带你吃冰淇淋,草莓味的。”
周六、周日,陈烨蜷在笼里,胯间火烧火燎,酒精味呛得眼泪打转,铁栏冰凉,硌得骨头生疼。奶奶起初只当他贪玩,喊两声没人应,周一还做好饭等,周二开始慌了,拄着拐杖满街贴寻人启事——十二岁男孩,父母离异,跟奶奶相依为命。派出所敷衍地立案,查几天,监控盲区太多,草草结案,只剩一张泛黄的寻人启事贴在电线杆上,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一周后,凌晨三点,陈烨疼醒,阴囊像烂桃一样掉进笼底,血水混着脓,腥得刺鼻,空气里弥漫着腐烂的甜味。他抖着双手用酒精擦拭,空荡荡的裆部只剩小鸡鸡软软地耷拉,像被拔了刺的玫瑰,风一吹就颤。
柳韵推门进来,踩着毛绒拖鞋,睡眼惺忪,头发散乱却更显妩媚:“啧,掉了?乖,从今天起,你是我们家的‘小厨’。”
她扔给他一本菜谱,封面油渍斑斑,书页卷角。陈烨翻开,菜名花哨,他却像抓住救命稻草——奶奶教过他煎蛋,蛋黄要半熟。
从此,他的日历被脚臭味和剩饭填满。
凌晨五点,闹钟尖锐地响,陈烨像狗一样四肢着地爬出笼子,赤条条钻进卧室,舌头先卷上柳韵的脚心,酸臭的汗味混着昨晚的尿骚,他舔得啧啧有声,舌尖在脚趾缝里打转;再爬到张雪莉床边,舌尖轻扫她脚底,浓烈的少女脚汗带着奶香的甜腻,舔得她脚趾蜷缩,咯咯笑醒。张雪莉翻身,一脚踹他脸,脚跟砸在鼻梁,疼得他眼冒金星:“吵死了!”有时母女起床气重,拳脚雨点般落下,砸得他皮开肉绽,血珠渗出,他却只敢蜷缩,呜咽着继续舔,像条被雨淋湿的狗。
两人洗漱完,踩上特制的掏空板凳,陈烨趴在下面,晨尿热腾腾浇进喉咙,浓烈的骚味呛得他眼泪直流,却得一口不漏咽下,喉结滚动,发出咕咚咕咚的声响。
母女出门上班上学,门锁咔哒,他开始拖地、洗衣、擦窗,汗水混着消毒水味,地板反射出他扭曲的影子,下午备晚餐,刀工越来越利落,葱花切得细如发丝。
傍晚,门开,母女笑闹着进来,高跟鞋和运动鞋的脚步声交织,陈烨跪在玄关,牙齿咬住鞋带,脱下鞋子,鞋里闷了一天的脚臭像炸弹爆开,热浪扑面。他把脸埋进去,大口吸气,为两双脚除臭,再舌头卷着脚趾缝,把汗垢、皮屑舔得干干净净,舌尖在脚心画圈,带出细微的酥痒。
晚餐时,他跪在桌下,狗盆里盛着剩饭冷汤,油花漂浮,母女偶尔吐一块啃剩的骨头,或把不爱的青菜甩给他,像喂流浪狗,骨头滚到盆边,沾上酱汁。
饭后,他再次充当马桶。柳韵便秘时,他舌头钻进肛门,卷着硬结的大便吮出来,腥臭在嘴里炸开,像腐烂的果实;张雪莉拉得稀,他张嘴接住,热乎乎滑进喉咙,溅到下巴。
夜深,母女躺在床上,他跪在床尾,舌头为四只脚按摩,脚心、脚背、脚趾,一寸不落,力度时轻时重,直到两人呼吸均匀,发出轻微的鼾声,他才轻手轻脚爬回笼子,蜷成一团,铁栏冰凉,硌得骨头生疼。
笼门锁上,黑暗吞没最后一丝光,他闭上眼,脑子里只有脚臭味和明天凌晨五点的闹钟,循环往复,像永不磨灭的咒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