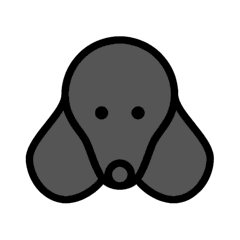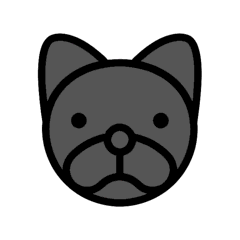春风若有怜花意(女女,母女主,严厉高压)2.20,第39章
女虐女连载中原创现实丝袜原味高跟鞋运动鞋乳头虐待母女S裸足
lxhniuniu159发布于 2026-02-11 11:02
Re: 春风若有怜花意(女女,母女主,严厉高压)1.22,第36章
第三十七章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跪了多久。
时间的概念,在无尽的痛苦中早已变得模糊。
厨房里没有钟,只有顶灯投下的惨白光线,和窗外那片一成不变的深沉夜色。
起初,是刺骨的疼痛主宰着我的一切感官。
膝盖下的地砖冰冷。
坚硬的触感,透过薄薄的皮肤,直接硌在我的骨头上,每一秒都像是在加深一道烙印。
胸前,那两个被林曼丽亲手夹上的木头夹子,更是持续不断的锐痛来源。
它们死死地咬着我胸前最柔软的组织,力道大得惊人,仿佛要将那两点彻底从我身体上分离出去。
随着我每一次微弱的呼吸,胸口起伏,夹子便会晃动,带来一阵阵更加尖锐的摩擦与拉扯。
双臂因为长时间高举而产生的酸麻感,也几乎让我发疯。
从指尖开始,那股无力的酸软,顺着我的小臂,蔓延到大臂,最后汇聚在我的肩膀。
我感觉我的两条胳膊,已经不再是我自己的了,它们变成了两根沉重的木头,悬在空中,唯一的任务就是捧住那只高跟鞋。
渐渐地,这些泾渭分明的痛苦似乎融为了一体。
它们不再是独立的、可以分辨的信号,而是变成了一种无边无际麻木的背景音,包裹着我的整个意识。
我的大脑,为了保护自己,似乎选择性地屏蔽了一部分感知。
支撑着我没有倒下的,只剩下那条命令本身带来刻在骨子里的绝对恐惧。
鞋子掉了,就要跪到天亮。
这句话,像一个魔咒,在我混沌的脑海里反复回响。
我手中的那只黑色高跟鞋,不再是一件物品。
它是有生命的。
它是我能否获得片刻喘息的唯一评判标准。
我甚至不敢眨眼,死死地盯着鞋跟那一点幽暗的反光,仿佛它随时会变成一条毒蛇,给我致命一击。
我的意识,在清醒与混沌之间来回漂浮。
有时候,我会想起下午在白杨房间里发生的一切。
想起她踩在我胸部上的重量,想起她命令我舔舐她脚上口水的语气。
有时候,我会想起我那间属于自己的客房,想起书桌上摊开的习题册。
那些熟悉的公式和定理,在此刻显得那么遥远,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眼泪早已流干。
只在冰冷僵硬的脸颊上,留下了几道干涸紧绷的痕迹。
我的身体,在濒临极限的痛苦中,开始自发地寻找着最微小的平衡。
我努力地控制着每一块肌肉,对抗着它们因为脱力而产生的剧烈颤抖。
双手捧着那只高跟鞋的姿势,在漫长的时间里,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
我甚至感觉,我的手掌,已经和那冰凉的皮革黏在了一起。
就在我感觉自己的意识即将彻底沉入黑暗的深渊时,一个声音,将我猛地拽了回来。
是脚步声。
声音很轻,来自厨房之外的客厅。
是林曼丽的拖鞋,踩在地板上发出不紧不慢的声响。
我的身体,瞬间绷紧到了极致。
我不敢回头。
我甚至不敢有丝毫多余的动作,连呼吸都下意识地屏住了。
我只能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维持身体的平衡上,捧着那只高跟鞋,如同捧着一个随时会爆炸的危险物
脚步声在厨房门口停顿了一下,然后走了进来。
她走到我的面前,停下了。
我能从视野的下方,看到她那双藕色的居家拖鞋。
那双鞋,与她此刻带给我的恐惧,形成了如此荒谬的对比。
我等待着。
等待着她的审判。
是觉得我跪得不够标准,要给我新的惩罚?
还是,这场漫长的折磨即将结束?
我不知道。
这种未知,比任何已知的痛苦都更加磨人。
接着,我看到她弯下了腰。
一股熟悉混杂着高级香水和沐浴露的清香,飘入了我的鼻腔。
她伸出了那只保养得宜的手。
那双手,指甲修剪得圆润光滑,皮肤细腻白皙,看起来温柔无害。
可就是这双手,刚刚才揪着我的头发,毫不留情地扇我耳光。
就是这双手,将那两个木头夹子,夹在了我身上最脆弱的地方。
她的指尖冰凉,捏住了我的下巴。
力道不大,却带着不容抗拒的意味。
她轻轻地向上抬起,强迫我扬起那张早已僵硬的脸,与她对视。
她的眼神很平静。
就像此刻窗外的夜色,深不见底,没有任何情绪的波澜。
她审视着我满是泪痕的脸。
审视着我因为长时间咬着而发白、破裂的嘴唇。
审视着我因为忍耐和痛苦而变得惨白的脸色。
最终,她的目光,落在了我的眼睛里,那深不见底纯粹的恐惧。
在她的注视下,我浑身抖得更厉害了。
牙齿不受控制地上下磕碰,发出了细微的“咯咯”声响。
我拼命地想从她那张脸上,读出一些信息。
满意?不耐烦?还是别的什么?
但我什么也读不到。
她的脸,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
在确认了我的状态,或者说,在欣赏够了我此刻的惨状之后,她终于松开了捏着我脸颊的手。
我的头,无力地垂了下去。
但她的手没有收回。
而是缓缓向下,移向了我胸前的位置。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的手指,轻轻触碰到了那个给我带来持续痛苦的木头夹子。
我全身的肌肉,再一次因为预感到即将到来的疼痛而瞬间绷紧。
她没有立刻取下它。
而是用她那涂着透明指甲油的指尖,在木头夹子上来回拨弄了两下。
每一次触碰,都让夹子更深地嵌入我的皮肉。
那是一种尖锐到极致的剧痛,仿佛要将我的灵魂都从身体里撕扯出来。
我的身体猛地一颤,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呜咽。
我死死地咬住自己的下唇,用新的疼痛去覆盖旧的疼痛,将那几乎要冲口而出的尖叫,硬生生吞回了肚子里。
我知道,她是在欣赏。
欣赏我在极致的痛苦中,依旧不敢反抗被彻底驯服的模样。
终于,在欣赏够了我的反应之后,她才用两根手指,捏住了夹子的尾端。
“啪嗒。”
她干脆利落地,将它从我的身体上摘了下来。
那瞬间的解脱,并没有带来任何快感,反而带来了另一种撕裂般的痛楚。
紧接着,是另一边。
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声音,同样的疼痛。
她随手将那两个沾染了我体温和痛苦的木头夹子,扔在了一旁的料理台上。
清脆的声响,在这死寂的厨房里,显得格外刺耳。
然后,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长记性了么?”
她的语气平淡,带着一丝审视的意味。
我拼命地点头,身体因为激动和恐惧而剧烈地摇晃着。
我张开嘴,想回答她,却发现自己的喉咙干涩嘶哑,几乎发不出任何声音。
“记……记住了……”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才从喉咙里挤出这几个破碎的音节。
“夫人……我……我记住了……”
我的声音里,带着无法掩饰的哭腔和浓浓的恐惧。
林曼丽对我这卑微至极的回答,似乎并不在意,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她只是像下达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指令那样,对我说道:
“把我鞋子放回鞋柜里。”
“今天可以休息了。”
说完,她甚至没有再多看我一眼,便直接转过身,迈着优雅的步子,走出了厨房。
我跪在原地,看着她那背影很快消失在了厨房口。
客厅里传来她走进卧室、然后关上房门的声音。
直到那最后一点声响也消失,我紧绷到极限的神经,才终于“啪”的一声,断掉了。
我颤抖着,想要立刻站起来,逃离这个地方。
但是,我的双腿,早已麻木得不属于自己。
我尝试着调动腿部的肌肉,却只能得到一阵阵更加剧烈如同无数蚂蚁在啃噬骨头的酸麻感。
我试了第一次,身体只是晃了晃,便无力地重新跪了回去。
我试了第二次,膝盖一软,整个人都向前扑倒,幸好及时用手撑住了地面,才没有让脸直接撞在地砖上。
那只被我捧了半夜的高跟鞋,也因为这个动作,从我手中滑落,“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这声响,让我瞬间吓出了一身冷汗,仿佛林曼丽会立刻从卧室里走出来一样。
最后,我只能先用已经同样酸软无力的手掌撑着地,将那只高跟鞋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放在一边。
然后,我扶着身边冰冷的橱柜柜门,一点一点地用一种极其缓慢而痛苦的姿势,让自己重新站立起来。
从跪姿到站立,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只需要一秒钟的动作,我却花费了将近一分钟。
当我终于直起身体时,眼前一阵发黑,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
我靠着橱柜,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等待着那阵眩晕过去。
然后,我弯下腰,捡起那只高跟鞋,几乎是拖着那两条已经快要失去知觉的腿,一步一步,艰难地向着玄关的方向挪去。
每走一步,膝盖都传来钻心的疼痛。
那感觉,就像是骨头碎裂了之后,又被强行黏合起来,每一次弯曲,都是一次新的碎裂。
短短的距离,我却走得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来到玄关,打开鞋柜的门,将那只被我捧了半天的高跟鞋,与它的另一只一起,整齐地摆放在了属于它的位置上。
做完这一切,我没有直接回房间。
我拐了个弯,走进了卫生间。
我打开灯,抬起头,看向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的人,陌生得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
那张脸,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左边的脸颊,还残留着被扇耳光留下的红肿。
嘴唇被我自己咬得发白、破裂,上面还有已经干涸的血迹。
而那双眼睛,空洞,黯淡,像一潭死水,看不到任何光亮。
我的目光,缓缓向下。
我看到了自己胸前,那两个被木夹子夹过的位置,已经变成了两个深紫红色的血点,周围的皮肤都因为长时间的压迫而微微肿起。
膝盖处,更是惨不忍睹。
大片的青紫,几乎覆盖了整个膝盖骨,在苍白的皮肤上,显得触目惊心。
我伸出手,轻轻地碰了一下,立刻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
我打开花洒,拧到温水的那一档。
温热的水流,冲刷着我冰冷的身体。
水流过那些地方时,带来一阵阵细密的刺痛。
我没有哭。
眼泪,似乎在那漫长的罚跪中,已经彻底流干了。
我只是低着头,拿着沐浴露,机械仔细地清洗着自己的每一寸皮肤。
仿佛,我清洗的不是我自己的身体,而是一件被弄脏了的物品。
洗漱完毕,我用浴巾擦干身体,轻手轻脚地走回我的客房。
我关上门,没有开灯,摸黑爬上了那张小小的床。
我躺在床上,身体的每一寸肌肉,都在疯狂地叫嚣着疼痛。
膝盖是钝痛,胸口是锐痛,手臂是酸痛,头皮是被拉扯过的隐痛。
这些痛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将我牢牢地困在其中。
我睡不着。
我只是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天花板。
黑暗中,林曼丽那句“长记性了么”,和她那平静到可怕的眼神,在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回放。
我当然记住了。
我用我的身体,我的尊严,我的痛苦,清清楚楚地记住了。
在这里,我不是人。
我只是一件会呼吸、会流泪、会感到痛苦的物品。
一件属于她们母女的,私有财产。
这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因为身体实在支撑不住,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但睡得并不安稳,噩梦一个接着一个。
我醒得很早,被生物钟准时叫醒。
我睁开眼,窗外的天光,已经微微泛白。
我忍着全身散架般的酸痛,慢慢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每一个动作,都牵扯着无数的伤口。
我为她们准备好了简单的早餐——热好的牛奶,烤好的吐司,还有切好的水果。
整个过程,我与起床后的林曼丽和白杨,没有任何交流。
我就像一个透明的幽灵,在她们身边穿梭,完成我应该做的工作。
她们也习惯了我的这种存在方式,视我如无物。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跪了多久。
时间的概念,在无尽的痛苦中早已变得模糊。
厨房里没有钟,只有顶灯投下的惨白光线,和窗外那片一成不变的深沉夜色。
起初,是刺骨的疼痛主宰着我的一切感官。
膝盖下的地砖冰冷。
坚硬的触感,透过薄薄的皮肤,直接硌在我的骨头上,每一秒都像是在加深一道烙印。
胸前,那两个被林曼丽亲手夹上的木头夹子,更是持续不断的锐痛来源。
它们死死地咬着我胸前最柔软的组织,力道大得惊人,仿佛要将那两点彻底从我身体上分离出去。
随着我每一次微弱的呼吸,胸口起伏,夹子便会晃动,带来一阵阵更加尖锐的摩擦与拉扯。
双臂因为长时间高举而产生的酸麻感,也几乎让我发疯。
从指尖开始,那股无力的酸软,顺着我的小臂,蔓延到大臂,最后汇聚在我的肩膀。
我感觉我的两条胳膊,已经不再是我自己的了,它们变成了两根沉重的木头,悬在空中,唯一的任务就是捧住那只高跟鞋。
渐渐地,这些泾渭分明的痛苦似乎融为了一体。
它们不再是独立的、可以分辨的信号,而是变成了一种无边无际麻木的背景音,包裹着我的整个意识。
我的大脑,为了保护自己,似乎选择性地屏蔽了一部分感知。
支撑着我没有倒下的,只剩下那条命令本身带来刻在骨子里的绝对恐惧。
鞋子掉了,就要跪到天亮。
这句话,像一个魔咒,在我混沌的脑海里反复回响。
我手中的那只黑色高跟鞋,不再是一件物品。
它是有生命的。
它是我能否获得片刻喘息的唯一评判标准。
我甚至不敢眨眼,死死地盯着鞋跟那一点幽暗的反光,仿佛它随时会变成一条毒蛇,给我致命一击。
我的意识,在清醒与混沌之间来回漂浮。
有时候,我会想起下午在白杨房间里发生的一切。
想起她踩在我胸部上的重量,想起她命令我舔舐她脚上口水的语气。
有时候,我会想起我那间属于自己的客房,想起书桌上摊开的习题册。
那些熟悉的公式和定理,在此刻显得那么遥远,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眼泪早已流干。
只在冰冷僵硬的脸颊上,留下了几道干涸紧绷的痕迹。
我的身体,在濒临极限的痛苦中,开始自发地寻找着最微小的平衡。
我努力地控制着每一块肌肉,对抗着它们因为脱力而产生的剧烈颤抖。
双手捧着那只高跟鞋的姿势,在漫长的时间里,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
我甚至感觉,我的手掌,已经和那冰凉的皮革黏在了一起。
就在我感觉自己的意识即将彻底沉入黑暗的深渊时,一个声音,将我猛地拽了回来。
是脚步声。
声音很轻,来自厨房之外的客厅。
是林曼丽的拖鞋,踩在地板上发出不紧不慢的声响。
我的身体,瞬间绷紧到了极致。
我不敢回头。
我甚至不敢有丝毫多余的动作,连呼吸都下意识地屏住了。
我只能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维持身体的平衡上,捧着那只高跟鞋,如同捧着一个随时会爆炸的危险物
脚步声在厨房门口停顿了一下,然后走了进来。
她走到我的面前,停下了。
我能从视野的下方,看到她那双藕色的居家拖鞋。
那双鞋,与她此刻带给我的恐惧,形成了如此荒谬的对比。
我等待着。
等待着她的审判。
是觉得我跪得不够标准,要给我新的惩罚?
还是,这场漫长的折磨即将结束?
我不知道。
这种未知,比任何已知的痛苦都更加磨人。
接着,我看到她弯下了腰。
一股熟悉混杂着高级香水和沐浴露的清香,飘入了我的鼻腔。
她伸出了那只保养得宜的手。
那双手,指甲修剪得圆润光滑,皮肤细腻白皙,看起来温柔无害。
可就是这双手,刚刚才揪着我的头发,毫不留情地扇我耳光。
就是这双手,将那两个木头夹子,夹在了我身上最脆弱的地方。
她的指尖冰凉,捏住了我的下巴。
力道不大,却带着不容抗拒的意味。
她轻轻地向上抬起,强迫我扬起那张早已僵硬的脸,与她对视。
她的眼神很平静。
就像此刻窗外的夜色,深不见底,没有任何情绪的波澜。
她审视着我满是泪痕的脸。
审视着我因为长时间咬着而发白、破裂的嘴唇。
审视着我因为忍耐和痛苦而变得惨白的脸色。
最终,她的目光,落在了我的眼睛里,那深不见底纯粹的恐惧。
在她的注视下,我浑身抖得更厉害了。
牙齿不受控制地上下磕碰,发出了细微的“咯咯”声响。
我拼命地想从她那张脸上,读出一些信息。
满意?不耐烦?还是别的什么?
但我什么也读不到。
她的脸,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
在确认了我的状态,或者说,在欣赏够了我此刻的惨状之后,她终于松开了捏着我脸颊的手。
我的头,无力地垂了下去。
但她的手没有收回。
而是缓缓向下,移向了我胸前的位置。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的手指,轻轻触碰到了那个给我带来持续痛苦的木头夹子。
我全身的肌肉,再一次因为预感到即将到来的疼痛而瞬间绷紧。
她没有立刻取下它。
而是用她那涂着透明指甲油的指尖,在木头夹子上来回拨弄了两下。
每一次触碰,都让夹子更深地嵌入我的皮肉。
那是一种尖锐到极致的剧痛,仿佛要将我的灵魂都从身体里撕扯出来。
我的身体猛地一颤,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呜咽。
我死死地咬住自己的下唇,用新的疼痛去覆盖旧的疼痛,将那几乎要冲口而出的尖叫,硬生生吞回了肚子里。
我知道,她是在欣赏。
欣赏我在极致的痛苦中,依旧不敢反抗被彻底驯服的模样。
终于,在欣赏够了我的反应之后,她才用两根手指,捏住了夹子的尾端。
“啪嗒。”
她干脆利落地,将它从我的身体上摘了下来。
那瞬间的解脱,并没有带来任何快感,反而带来了另一种撕裂般的痛楚。
紧接着,是另一边。
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声音,同样的疼痛。
她随手将那两个沾染了我体温和痛苦的木头夹子,扔在了一旁的料理台上。
清脆的声响,在这死寂的厨房里,显得格外刺耳。
然后,我听到了她的声音。
“长记性了么?”
她的语气平淡,带着一丝审视的意味。
我拼命地点头,身体因为激动和恐惧而剧烈地摇晃着。
我张开嘴,想回答她,却发现自己的喉咙干涩嘶哑,几乎发不出任何声音。
“记……记住了……”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才从喉咙里挤出这几个破碎的音节。
“夫人……我……我记住了……”
我的声音里,带着无法掩饰的哭腔和浓浓的恐惧。
林曼丽对我这卑微至极的回答,似乎并不在意,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她只是像下达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指令那样,对我说道:
“把我鞋子放回鞋柜里。”
“今天可以休息了。”
说完,她甚至没有再多看我一眼,便直接转过身,迈着优雅的步子,走出了厨房。
我跪在原地,看着她那背影很快消失在了厨房口。
客厅里传来她走进卧室、然后关上房门的声音。
直到那最后一点声响也消失,我紧绷到极限的神经,才终于“啪”的一声,断掉了。
我颤抖着,想要立刻站起来,逃离这个地方。
但是,我的双腿,早已麻木得不属于自己。
我尝试着调动腿部的肌肉,却只能得到一阵阵更加剧烈如同无数蚂蚁在啃噬骨头的酸麻感。
我试了第一次,身体只是晃了晃,便无力地重新跪了回去。
我试了第二次,膝盖一软,整个人都向前扑倒,幸好及时用手撑住了地面,才没有让脸直接撞在地砖上。
那只被我捧了半夜的高跟鞋,也因为这个动作,从我手中滑落,“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这声响,让我瞬间吓出了一身冷汗,仿佛林曼丽会立刻从卧室里走出来一样。
最后,我只能先用已经同样酸软无力的手掌撑着地,将那只高跟鞋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放在一边。
然后,我扶着身边冰冷的橱柜柜门,一点一点地用一种极其缓慢而痛苦的姿势,让自己重新站立起来。
从跪姿到站立,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只需要一秒钟的动作,我却花费了将近一分钟。
当我终于直起身体时,眼前一阵发黑,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
我靠着橱柜,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等待着那阵眩晕过去。
然后,我弯下腰,捡起那只高跟鞋,几乎是拖着那两条已经快要失去知觉的腿,一步一步,艰难地向着玄关的方向挪去。
每走一步,膝盖都传来钻心的疼痛。
那感觉,就像是骨头碎裂了之后,又被强行黏合起来,每一次弯曲,都是一次新的碎裂。
短短的距离,我却走得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来到玄关,打开鞋柜的门,将那只被我捧了半天的高跟鞋,与它的另一只一起,整齐地摆放在了属于它的位置上。
做完这一切,我没有直接回房间。
我拐了个弯,走进了卫生间。
我打开灯,抬起头,看向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的人,陌生得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
那张脸,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左边的脸颊,还残留着被扇耳光留下的红肿。
嘴唇被我自己咬得发白、破裂,上面还有已经干涸的血迹。
而那双眼睛,空洞,黯淡,像一潭死水,看不到任何光亮。
我的目光,缓缓向下。
我看到了自己胸前,那两个被木夹子夹过的位置,已经变成了两个深紫红色的血点,周围的皮肤都因为长时间的压迫而微微肿起。
膝盖处,更是惨不忍睹。
大片的青紫,几乎覆盖了整个膝盖骨,在苍白的皮肤上,显得触目惊心。
我伸出手,轻轻地碰了一下,立刻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
我打开花洒,拧到温水的那一档。
温热的水流,冲刷着我冰冷的身体。
水流过那些地方时,带来一阵阵细密的刺痛。
我没有哭。
眼泪,似乎在那漫长的罚跪中,已经彻底流干了。
我只是低着头,拿着沐浴露,机械仔细地清洗着自己的每一寸皮肤。
仿佛,我清洗的不是我自己的身体,而是一件被弄脏了的物品。
洗漱完毕,我用浴巾擦干身体,轻手轻脚地走回我的客房。
我关上门,没有开灯,摸黑爬上了那张小小的床。
我躺在床上,身体的每一寸肌肉,都在疯狂地叫嚣着疼痛。
膝盖是钝痛,胸口是锐痛,手臂是酸痛,头皮是被拉扯过的隐痛。
这些痛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将我牢牢地困在其中。
我睡不着。
我只是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天花板。
黑暗中,林曼丽那句“长记性了么”,和她那平静到可怕的眼神,在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回放。
我当然记住了。
我用我的身体,我的尊严,我的痛苦,清清楚楚地记住了。
在这里,我不是人。
我只是一件会呼吸、会流泪、会感到痛苦的物品。
一件属于她们母女的,私有财产。
这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因为身体实在支撑不住,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但睡得并不安稳,噩梦一个接着一个。
我醒得很早,被生物钟准时叫醒。
我睁开眼,窗外的天光,已经微微泛白。
我忍着全身散架般的酸痛,慢慢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每一个动作,都牵扯着无数的伤口。
我为她们准备好了简单的早餐——热好的牛奶,烤好的吐司,还有切好的水果。
整个过程,我与起床后的林曼丽和白杨,没有任何交流。
我就像一个透明的幽灵,在她们身边穿梭,完成我应该做的工作。
她们也习惯了我的这种存在方式,视我如无物。
lxhniuniu159发布于 2026-02-11 11:02
Re: 春风若有怜花意(女女,母女主,严厉高压)1.22,第36章
第三十八章
今天是周一,我们要去上学。
林曼丽开着她那辆黑色的奔驰S,车里放着舒缓的古典音乐。
白杨像往常一样,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戴着耳机,一边听歌,一边看着窗外的街景。
我一个人坐在宽敞的后排座位上,尽可能地将自己的身体缩在角落里,努力减少自己的存在感。
车内的气氛,安静而祥和。
如果不是我身上的疼痛还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我,我几乎要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我们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要去上学的家庭。
车子在离校门口还有一段距离的路边,缓缓停了下来。
这是林曼丽的习惯,她不希望自己的车太过引人注目。
白杨解开安全带,推开车门,准备下车。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着的林曼丽,忽然开了口。
她没有回头看我,只是从她那个精致的手包里,拿出了钱包。
她打开钱包,从里面抽出了五张一百元的钞票,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后递了过来。
我愣了一下,看着那几张簇新的还带着钱包里皮革气味的纸币,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我的手,停在半空中,有些迟疑。
“愣着干嘛?”
已经半个身子探出车外的白杨,有些不耐烦地回头看了我一眼,催促道。
“我妈给你的,拿着啊。”
我这才如梦初醒,连忙伸出手,接过了那五百块钱。
冰冷的指尖,触碰到那几张纸币,我却感觉像是被烫了一下。
“这周的生活费。”
林曼丽的声音,依旧是那么的平静,像是在交代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学校安分点。”
我攥着那五百块钱,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
“……谢谢夫人。”我低下头,用蚊子般大小的声音说道。
林曼丽没有再说话,白杨也已经下了车关上了车门。
五百块钱。
这是我近几个月来,见过最大的一笔钱。
它足以解决我所有的温饱问题,甚至还能让我偶尔奢侈一下,买一本新的习题册。
但这钱,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的手心生疼。
它不是薪水,不是报酬。
它是豢养一件宠物的开销。
它用一种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清晰地定义了我的价值。
一周,五百块。
这就是我,李盼男,现在的价格。
进入校园,白杨立刻就变成了那个光芒四射的中心。
她脸上的不耐烦和冷漠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开朗明媚恰到好处的笑容。
她会热情地和每一个跟她打招呼的同学回应,会亲昵地挽住她那几个小姐妹的胳膊,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周末新上映的电影。
而我,则自动切换到了“跟班”的角色。
她很自然地,将她的书包直接扔到了我的怀里。
“拿着。”
然后,她便两手空空,一身轻松地走在前面。
我沉默地跟在她的身后,抱着两个沉重的书包,低着头,尽可能不与任何人对视。
偶尔,我会感觉到一些目光落在我身上。
那些目光里,大多是同情,不解,或是一丝毫不掩饰的轻蔑。
在她们看来,这或许只是富家女和穷学生之间,一种常见的无伤大雅的权力游戏。
她们无法想象,也永远不会知道,这种校园里看似普通的“欺负”,在那个华丽的房子里,会演变成何等恐怖的模样。
白杨很享受这种巨大的反差。
在学校里,她需要扮演一个完美的受欢迎的女孩。
而我这个卑微沉默的“知情人”的存在,让她时刻都能感觉到自己隐藏在伪装之下更强大的权力。
她对我的每一次颐指气使,都是一种对那份权力的公开宣告。
也是一种对我无声的提醒:李盼男,别忘了你的身份。
午休的铃声刚刚响起,教室里瞬间变得嘈杂起来。
我正准备去食堂打饭。
坐在我斜前方的白杨,忽然走了过来,给了我一个眼神。
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沉默地站起身,跟在了她的身后。
她没有去食堂,也没有去小卖部,而是带着我,径直走向了教学楼的女厕所。
午休时间的厕所,人来人往。
白杨很有耐心地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直到里面的人都走光了。
然后,她拉着我的手腕,快步走了进去。
她径直将我拉到了最里面的一个隔断。
她把我推了进去,然后自己也闪身进来,随手将隔断的门从里面反锁了。
“咔哒”一声轻响,小小的门栓,隔绝了外面的世界。
狭小的空间里,顿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外面走廊里的喧闹声,被这扇薄薄的门板隔绝开,变得有些模糊。
厕所里那股特有的混杂着消毒水和秽物的气味,瞬间将我包围。
气氛,一下子变得压抑起来。
白杨靠在门板上,抱起双臂,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她的脸上,还带着一丝在教室里未曾褪去属于“公主”的甜美笑容。
但她的眼神,已经变了。
那里面,充满了戏谑,和一种毫不掩饰的不怀好意。
我垂着头,紧张地攥着自己的衣角,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
我不知道她想做什么。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隔断的地面上。
灰色的瓷砖地面上,有些脏,布满了各种深浅不一的鞋印。
角落里,还有一些潮湿的不明来源的水渍。
白杨忽然俯下身,凑到了我的耳边。
她的呼吸,带着温热的气息,吹拂在我的耳廓上,让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她用一种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听到带着气音的小恶魔般的语调,轻声说道:
“我脚出汗,有些痒。”
“小丫头,知道该怎么做么?”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当然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我无措地站在原地,低着头,一动也不敢动。
在家里,在那个完全属于她们私密的空间里,我已经习惯了执行各种各样侮辱性的命令。
但是这里……这里是学校。
是在这样一个肮脏而且随时都可能有人进出的公共厕所里。
我的内心,充满了强烈的抗拒和羞耻。
白杨见我没有反应,也不生气。
她只是好整以暇地直起身,背对着我,继续靠在隔板上。
然后,她俏皮地向后翘起一只脚,穿着那双干净的白色运动鞋的脚,在我的面前轻轻晃了晃。
她用鞋跟,勾了勾我的小腿,像是在逗弄一只不听话的小狗,示意我动手。
就在这时,我的心脏猛地一紧。
我清晰地听见,厕所的门被推开了,外面传来了几个女生说笑的脚步声。
“哎,你们听说了吗……”
“真的假的?太夸张了吧!”
她们的声音越来越近。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带着一丝祈求的目光,看向了白杨的侧脸,希望她能看在外面有人的份上,就此作罢。
白杨显然也听到了外面的声音。
她捕捉到了我眼神里的祈求,嘴角的戏谑弧度,反而更大了。
但她见我依旧僵持着不动,那份戏谑,很快就转变成了一丝不耐烦,和一抹熟悉的阴冷。
我认得这个眼神。
这个眼神意味着,她的耐心已经耗尽。
如果我现在不听从她的命令,那么回家之后,等待我的将是比昨天更加可怕的折磨。
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瞬间攫住了我的心脏,捏碎了我最后一丝的挣扎和羞耻。
我闭上了眼睛。
我的身体,因为极致的屈辱而微微颤抖着。
我期期艾艾地,在那片肮脏潮湿布满陌生人鞋印的地面上,缓缓地跪了下去。
我跪在地上,仰起头。
白杨那只穿着白色运动鞋的脚,就在我的面前。
我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干裂的嘴唇,然后张开嘴,用牙齿,轻轻地咬住了她的鞋跟。
鞋跟上,沾染着从操场和走廊里带来的灰尘与泥土,一股土腥味,瞬间充满了我的口腔。
我一点一点极其费力地将那只鞋子从她的脚上褪了下来。
我用手接过鞋子,不敢让它掉在地上发出声音,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一旁蹲便器的瓷砖台面上。
我刚刚抬起头,准备像在家里那样,用鼻子去闻她的脚。
她却忽然用那只穿着白色棉袜的脚尖,轻轻地点了点我的嘴唇。
这个动作,带着强烈的暗示意味。
我不解地抬头看她。
只见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朝着自己那只穿着袜子的脚,扬了扬下巴。
我瞬间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是要我用嘴,帮她把袜子也脱下来。
我的身体,彻底僵住了。
就在这时,隔壁的隔断,传来了开门和关门的声音,似乎是刚刚进来的某个同学,走进了我们旁边的位置。
我的动作猛地一顿,恐惧让我几乎停止了呼吸。
白杨感觉到了我的停顿。
她那穿着袜子的脚趾,忽然灵活地分开,不轻不重地,夹了一下我的鼻子,作为无声的警告。
我抬头,对上了她那双已经变得冰冷的眼睛。
那眼神里的意味很明确:继续。
我不敢再有任何迟疑。
我认命般地,再一次闭上了眼睛。
我将脸凑过去,把嘴探进了她那宽大的校服裤腿里。
我用牙齿和嘴唇,费力地咬住了袜子的边缘。
一股浓重的属于青春期少女的汗味,混合着棉布的味道,立刻霸道地充满了我的整个口腔和鼻腔。
我忍着强烈的恶心感,极其缓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地,将那只湿热的袜子,从她的脚上,一点一点地剥离下来。
然后,我将那只袜子,也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她的鞋子里。
终于,她那只白皙、秀气的脚,完全赤裸地呈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不敢耽搁,立刻将自己的鼻子贴了上去。
为了不发出声音,我尽量放缓了自己的动作,用鼻子在她的脚底轻轻地来回摩擦着。
白杨似乎觉得这样不过瘾。
她把脚翘得更高了一点,在空中晃了晃,示意我必须用手捧着。
我只能调整了一下姿势,以一个非常别扭的几乎要将上半身完全趴在地上的姿势,跪在地上,高高地举起双手,捧住她的脚。
她的脚趾,微微张开,像一朵盛开的花,停在我的鼻子前面。
我能清晰地闻到,那来自她脚趾缝隙深处混合着汗液与皮屑的独特酸味。
虽然不算特别浓重,但对于我来说,这股气味也绝不好闻。
我感到一阵生理性的恶心,胃里翻江倒海。
但我不敢表现出丝毫的嫌恶,只能努力地放缓自己呼吸的频率和声音,假装自己很投入。
我这细微强忍着恶心的反应,显然取悦了她。
我能感觉到,她的嘴角,一定勾起了一抹满意的笑容。
突然,她那张开的脚趾,猛地并拢,像一把钳子,死死地夹住了我的鼻子!
呼吸,瞬间被切断。
我猝不及防,刚想下意识地张开嘴喘气。
白杨冰冷刺骨的眼神,瞬间投了过来,像一盆零度以下的冰水,从我的头顶直直浇下。
那眼神,在警告我:把嘴闭上。
我只能死死地闭住嘴。
窒息的感觉,迅速地传来。
我的大脑,因为缺氧,开始阵阵发黑。
我的肺部,像一个被吹到极限的气球,灼热,刺痛,仿佛下一秒就要炸开。
我强行忍耐着这濒临死亡般的痛苦,身体因为缺氧而剧烈地颤抖起来。
我想张开嘴巴,哪怕只是吸入一小口空气。
但我不敢。
因为隔壁,就有同学。
任何一点异样的大口喘息声,都可能暴露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到时候,我不但会身败名裂,回家后,白杨和林曼丽,也绝对不会放过我。
白杨知道我有多难受。
她就是那么饶有兴致戏谑地看着我。
看着我因为痛苦和窒息而涨得通红、表情扭曲的脸。
她在等。
她在等我忍不住,等我出声向她求饶。
但我不敢求饶。
在这里,求饶的声音,和喘息的声音一样,都是致命的。
我只能用尽我全部的意志力,去忍耐。
窒息的痛苦,让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顺着我的脸颊,无声地滑落。
我的眼前,已经开始出现黑色的斑点,耳朵里也响起了尖锐的轰鸣声。
我感觉自己真的快要忍受不了,人体的保护本能即将让我下意识的张开嘴呼吸的时候。
那夹住我鼻子的力量,终于松开了。
新鲜的空气,涌入鼻腔的瞬间,我本能地贪婪地想要大口呼吸。
但我不敢。
在这个安静的气味并不好闻的厕所里,突兀的大口喘气声,会显得格外刺耳。
我只能拼命地压抑着身体的这种求生本能。
我用小口急促的、几乎听不见声音的方式,艰难地呼吸着,补充着肺部亏空的氧气。
白杨就这么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看着我想大口呼吸,却又拼命忍耐的样子。
我这种痛苦又小心翼翼狼狈不堪的模样,显然极大地取悦了她。
她没有着急进行下一次的折磨。
她只是那么看着我,看着我在她的脚下,拼命忍耐着身体的本能小口小口地急促喘息,继续用鼻子去闻她脚趾缝里的气味。
那是一种猫抓到老鼠后,并不急着吃掉,而是要先玩弄到最后一刻的残忍的快感。
而我,就是那只被玩弄的老鼠。
今天是周一,我们要去上学。
林曼丽开着她那辆黑色的奔驰S,车里放着舒缓的古典音乐。
白杨像往常一样,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戴着耳机,一边听歌,一边看着窗外的街景。
我一个人坐在宽敞的后排座位上,尽可能地将自己的身体缩在角落里,努力减少自己的存在感。
车内的气氛,安静而祥和。
如果不是我身上的疼痛还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我,我几乎要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我们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要去上学的家庭。
车子在离校门口还有一段距离的路边,缓缓停了下来。
这是林曼丽的习惯,她不希望自己的车太过引人注目。
白杨解开安全带,推开车门,准备下车。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着的林曼丽,忽然开了口。
她没有回头看我,只是从她那个精致的手包里,拿出了钱包。
她打开钱包,从里面抽出了五张一百元的钞票,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后递了过来。
我愣了一下,看着那几张簇新的还带着钱包里皮革气味的纸币,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我的手,停在半空中,有些迟疑。
“愣着干嘛?”
已经半个身子探出车外的白杨,有些不耐烦地回头看了我一眼,催促道。
“我妈给你的,拿着啊。”
我这才如梦初醒,连忙伸出手,接过了那五百块钱。
冰冷的指尖,触碰到那几张纸币,我却感觉像是被烫了一下。
“这周的生活费。”
林曼丽的声音,依旧是那么的平静,像是在交代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学校安分点。”
我攥着那五百块钱,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
“……谢谢夫人。”我低下头,用蚊子般大小的声音说道。
林曼丽没有再说话,白杨也已经下了车关上了车门。
五百块钱。
这是我近几个月来,见过最大的一笔钱。
它足以解决我所有的温饱问题,甚至还能让我偶尔奢侈一下,买一本新的习题册。
但这钱,却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的手心生疼。
它不是薪水,不是报酬。
它是豢养一件宠物的开销。
它用一种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清晰地定义了我的价值。
一周,五百块。
这就是我,李盼男,现在的价格。
进入校园,白杨立刻就变成了那个光芒四射的中心。
她脸上的不耐烦和冷漠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开朗明媚恰到好处的笑容。
她会热情地和每一个跟她打招呼的同学回应,会亲昵地挽住她那几个小姐妹的胳膊,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周末新上映的电影。
而我,则自动切换到了“跟班”的角色。
她很自然地,将她的书包直接扔到了我的怀里。
“拿着。”
然后,她便两手空空,一身轻松地走在前面。
我沉默地跟在她的身后,抱着两个沉重的书包,低着头,尽可能不与任何人对视。
偶尔,我会感觉到一些目光落在我身上。
那些目光里,大多是同情,不解,或是一丝毫不掩饰的轻蔑。
在她们看来,这或许只是富家女和穷学生之间,一种常见的无伤大雅的权力游戏。
她们无法想象,也永远不会知道,这种校园里看似普通的“欺负”,在那个华丽的房子里,会演变成何等恐怖的模样。
白杨很享受这种巨大的反差。
在学校里,她需要扮演一个完美的受欢迎的女孩。
而我这个卑微沉默的“知情人”的存在,让她时刻都能感觉到自己隐藏在伪装之下更强大的权力。
她对我的每一次颐指气使,都是一种对那份权力的公开宣告。
也是一种对我无声的提醒:李盼男,别忘了你的身份。
午休的铃声刚刚响起,教室里瞬间变得嘈杂起来。
我正准备去食堂打饭。
坐在我斜前方的白杨,忽然走了过来,给了我一个眼神。
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沉默地站起身,跟在了她的身后。
她没有去食堂,也没有去小卖部,而是带着我,径直走向了教学楼的女厕所。
午休时间的厕所,人来人往。
白杨很有耐心地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直到里面的人都走光了。
然后,她拉着我的手腕,快步走了进去。
她径直将我拉到了最里面的一个隔断。
她把我推了进去,然后自己也闪身进来,随手将隔断的门从里面反锁了。
“咔哒”一声轻响,小小的门栓,隔绝了外面的世界。
狭小的空间里,顿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外面走廊里的喧闹声,被这扇薄薄的门板隔绝开,变得有些模糊。
厕所里那股特有的混杂着消毒水和秽物的气味,瞬间将我包围。
气氛,一下子变得压抑起来。
白杨靠在门板上,抱起双臂,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她的脸上,还带着一丝在教室里未曾褪去属于“公主”的甜美笑容。
但她的眼神,已经变了。
那里面,充满了戏谑,和一种毫不掩饰的不怀好意。
我垂着头,紧张地攥着自己的衣角,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
我不知道她想做什么。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隔断的地面上。
灰色的瓷砖地面上,有些脏,布满了各种深浅不一的鞋印。
角落里,还有一些潮湿的不明来源的水渍。
白杨忽然俯下身,凑到了我的耳边。
她的呼吸,带着温热的气息,吹拂在我的耳廓上,让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她用一种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听到带着气音的小恶魔般的语调,轻声说道:
“我脚出汗,有些痒。”
“小丫头,知道该怎么做么?”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当然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我无措地站在原地,低着头,一动也不敢动。
在家里,在那个完全属于她们私密的空间里,我已经习惯了执行各种各样侮辱性的命令。
但是这里……这里是学校。
是在这样一个肮脏而且随时都可能有人进出的公共厕所里。
我的内心,充满了强烈的抗拒和羞耻。
白杨见我没有反应,也不生气。
她只是好整以暇地直起身,背对着我,继续靠在隔板上。
然后,她俏皮地向后翘起一只脚,穿着那双干净的白色运动鞋的脚,在我的面前轻轻晃了晃。
她用鞋跟,勾了勾我的小腿,像是在逗弄一只不听话的小狗,示意我动手。
就在这时,我的心脏猛地一紧。
我清晰地听见,厕所的门被推开了,外面传来了几个女生说笑的脚步声。
“哎,你们听说了吗……”
“真的假的?太夸张了吧!”
她们的声音越来越近。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带着一丝祈求的目光,看向了白杨的侧脸,希望她能看在外面有人的份上,就此作罢。
白杨显然也听到了外面的声音。
她捕捉到了我眼神里的祈求,嘴角的戏谑弧度,反而更大了。
但她见我依旧僵持着不动,那份戏谑,很快就转变成了一丝不耐烦,和一抹熟悉的阴冷。
我认得这个眼神。
这个眼神意味着,她的耐心已经耗尽。
如果我现在不听从她的命令,那么回家之后,等待我的将是比昨天更加可怕的折磨。
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瞬间攫住了我的心脏,捏碎了我最后一丝的挣扎和羞耻。
我闭上了眼睛。
我的身体,因为极致的屈辱而微微颤抖着。
我期期艾艾地,在那片肮脏潮湿布满陌生人鞋印的地面上,缓缓地跪了下去。
我跪在地上,仰起头。
白杨那只穿着白色运动鞋的脚,就在我的面前。
我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干裂的嘴唇,然后张开嘴,用牙齿,轻轻地咬住了她的鞋跟。
鞋跟上,沾染着从操场和走廊里带来的灰尘与泥土,一股土腥味,瞬间充满了我的口腔。
我一点一点极其费力地将那只鞋子从她的脚上褪了下来。
我用手接过鞋子,不敢让它掉在地上发出声音,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一旁蹲便器的瓷砖台面上。
我刚刚抬起头,准备像在家里那样,用鼻子去闻她的脚。
她却忽然用那只穿着白色棉袜的脚尖,轻轻地点了点我的嘴唇。
这个动作,带着强烈的暗示意味。
我不解地抬头看她。
只见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朝着自己那只穿着袜子的脚,扬了扬下巴。
我瞬间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是要我用嘴,帮她把袜子也脱下来。
我的身体,彻底僵住了。
就在这时,隔壁的隔断,传来了开门和关门的声音,似乎是刚刚进来的某个同学,走进了我们旁边的位置。
我的动作猛地一顿,恐惧让我几乎停止了呼吸。
白杨感觉到了我的停顿。
她那穿着袜子的脚趾,忽然灵活地分开,不轻不重地,夹了一下我的鼻子,作为无声的警告。
我抬头,对上了她那双已经变得冰冷的眼睛。
那眼神里的意味很明确:继续。
我不敢再有任何迟疑。
我认命般地,再一次闭上了眼睛。
我将脸凑过去,把嘴探进了她那宽大的校服裤腿里。
我用牙齿和嘴唇,费力地咬住了袜子的边缘。
一股浓重的属于青春期少女的汗味,混合着棉布的味道,立刻霸道地充满了我的整个口腔和鼻腔。
我忍着强烈的恶心感,极其缓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地,将那只湿热的袜子,从她的脚上,一点一点地剥离下来。
然后,我将那只袜子,也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她的鞋子里。
终于,她那只白皙、秀气的脚,完全赤裸地呈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不敢耽搁,立刻将自己的鼻子贴了上去。
为了不发出声音,我尽量放缓了自己的动作,用鼻子在她的脚底轻轻地来回摩擦着。
白杨似乎觉得这样不过瘾。
她把脚翘得更高了一点,在空中晃了晃,示意我必须用手捧着。
我只能调整了一下姿势,以一个非常别扭的几乎要将上半身完全趴在地上的姿势,跪在地上,高高地举起双手,捧住她的脚。
她的脚趾,微微张开,像一朵盛开的花,停在我的鼻子前面。
我能清晰地闻到,那来自她脚趾缝隙深处混合着汗液与皮屑的独特酸味。
虽然不算特别浓重,但对于我来说,这股气味也绝不好闻。
我感到一阵生理性的恶心,胃里翻江倒海。
但我不敢表现出丝毫的嫌恶,只能努力地放缓自己呼吸的频率和声音,假装自己很投入。
我这细微强忍着恶心的反应,显然取悦了她。
我能感觉到,她的嘴角,一定勾起了一抹满意的笑容。
突然,她那张开的脚趾,猛地并拢,像一把钳子,死死地夹住了我的鼻子!
呼吸,瞬间被切断。
我猝不及防,刚想下意识地张开嘴喘气。
白杨冰冷刺骨的眼神,瞬间投了过来,像一盆零度以下的冰水,从我的头顶直直浇下。
那眼神,在警告我:把嘴闭上。
我只能死死地闭住嘴。
窒息的感觉,迅速地传来。
我的大脑,因为缺氧,开始阵阵发黑。
我的肺部,像一个被吹到极限的气球,灼热,刺痛,仿佛下一秒就要炸开。
我强行忍耐着这濒临死亡般的痛苦,身体因为缺氧而剧烈地颤抖起来。
我想张开嘴巴,哪怕只是吸入一小口空气。
但我不敢。
因为隔壁,就有同学。
任何一点异样的大口喘息声,都可能暴露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到时候,我不但会身败名裂,回家后,白杨和林曼丽,也绝对不会放过我。
白杨知道我有多难受。
她就是那么饶有兴致戏谑地看着我。
看着我因为痛苦和窒息而涨得通红、表情扭曲的脸。
她在等。
她在等我忍不住,等我出声向她求饶。
但我不敢求饶。
在这里,求饶的声音,和喘息的声音一样,都是致命的。
我只能用尽我全部的意志力,去忍耐。
窒息的痛苦,让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顺着我的脸颊,无声地滑落。
我的眼前,已经开始出现黑色的斑点,耳朵里也响起了尖锐的轰鸣声。
我感觉自己真的快要忍受不了,人体的保护本能即将让我下意识的张开嘴呼吸的时候。
那夹住我鼻子的力量,终于松开了。
新鲜的空气,涌入鼻腔的瞬间,我本能地贪婪地想要大口呼吸。
但我不敢。
在这个安静的气味并不好闻的厕所里,突兀的大口喘气声,会显得格外刺耳。
我只能拼命地压抑着身体的这种求生本能。
我用小口急促的、几乎听不见声音的方式,艰难地呼吸着,补充着肺部亏空的氧气。
白杨就这么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看着我想大口呼吸,却又拼命忍耐的样子。
我这种痛苦又小心翼翼狼狈不堪的模样,显然极大地取悦了她。
她没有着急进行下一次的折磨。
她只是那么看着我,看着我在她的脚下,拼命忍耐着身体的本能小口小口地急促喘息,继续用鼻子去闻她脚趾缝里的气味。
那是一种猫抓到老鼠后,并不急着吃掉,而是要先玩弄到最后一刻的残忍的快感。
而我,就是那只被玩弄的老鼠。
a449291917发布于 2026-02-12 22:58
Re: 春风若有怜花意(女女,母女主,严厉高压)2.11,第38章
太少了,作者要奋斗啊
lxhniuniu159发布于 2026-02-12 23:53
Re: Re: 春风若有怜花意(女女,母女主,严厉高压)2.11,第38章
a449291917:↑太少了,作者要奋斗啊我就偶尔发发章节,全本俩月前就写完了
lxhniuniu159发布于 2026-02-20 15:52
Re: 春风若有怜花意(女女,母女主,严厉高压)2.11,第38章
第三十九章
温热的气流从我的鼻腔中呼出,拂过白杨的脚趾缝,似乎带去了一丝微痒。
她那几根秀气的脚趾,像是被惊扰的蝶翼,轻轻地晃动了几下。
那是一种近乎顽皮的动作,充满了猫捉老鼠般的戏谑。
紧接着,她的脚趾缝便在我的鼻尖上,极其缓慢地来回摩擦起来。
这个动作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挑逗与侮辱,每一次摩擦,都像是在用对待一件物品的方式,确认着我皮肤的触感,也像是在我的尊严上划过一刀。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脚趾缝里残留的因汗水而带来的湿热,以及那细腻皮肤下的纹理。
屈辱感再一次如同潮水般将我淹没。
就在我沉浸在这种屈辱的麻木中时,没有任何预兆,她的脚趾再一次猛地并拢,比上一次更加用力地,死死夹住了我的鼻子。
熟悉的窒息感瞬间涌来。
这一次,我有了心理准备,没有挣扎,只是默默地闭上了眼睛。
身体因为最原始的缺氧本能,再一次开始不受控制地轻微颤抖。
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不受控制地溢出眼眶,顺着脸颊无声滑落。
但我死死地咬住自己的嘴唇,不让自己发出任何一点求饶或痛苦的声音。
白杨一定很享受我这种无声绝望的忍耐。
这证明了她的规训是何等成功,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即使在极限的边缘,也绝不会违抗她命令的,一个“合格”的玩物。
就在我感觉肺部灼痛,意识即将彻底涣散,快要达到生理忍耐极限的时候,一个声音,将我从这濒死的幻觉中猛地拽了回来。
“哗啦——”
隔壁隔断,传来了清晰的冲水声。
这声音,对我而言不啻于天籁之音。
它既让我恐惧——怕被发现这惊世骇俗的一幕;又带来了一丝微弱的希望——这场折磨或许会因此而中断。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僵硬地维持着那个屈辱的姿势,一动也不敢动。
“吱呀”一声,隔壁的隔断门被拉开。
紧接着是门自动关闭时发出的“砰”的一声轻响,以及一阵逐渐远去的脚步声。
我能听出,那脚步声的主人,已经走出了卫生间,消失在了走廊的尽头。
白杨显然也听到了所有的声音。
我能感觉到,她夹住我鼻子的力量没有丝毫松懈,甚至因为这突发的状况,更添了一分难以言喻的兴奋。
她没有立刻松开我,而是侧着耳朵,仔细地倾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确认那脚步声已经完全消失。
在确认了绝对安全之后,她才仿佛仁慈施舍一般,松开了夹住我鼻子的脚趾。
鼻腔得到解放的瞬间,我立刻本能地拼命用鼻子大口呼吸着这间厕所里污浊的空气,喉咙里发出压抑不住的如同破旧风箱般急促喘息声。
白杨没有移开她的脚,就那么将它悬停在我的鼻子前方。
她的脚趾,随着我每一次急促的呼吸,一张一合,仿佛在玩弄着我的生命气息。
每一次吸气,都不可避免地吸入她脚上那股酸腐的气味;每一次呼气,又将温热的气息,喷在她的脚心。
我的呼吸,这一最基本的生存本能,此刻也完全被她所支配和观赏。
我感到极度的恶心与屈辱。
等到我的呼吸终于在她的注视下,一点点平稳下来,白杨转过身重新面对着我。
用她的脚底缓缓施加力道,将我那双原本捧着她脚的手,一点点踩在了肮脏潮湿的地面上。
冰冷坚硬的瓷砖,混合着不知名污水的湿滑感,透过我的手背,清晰地传来。
她的脚底板,稳稳地压着我的手,像是在我的手上,盖下了一个屈辱的印章。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下巴,朝着地面示意了一下。
我不敢违抗。
我只能顺从地,将整个上半身都趴了下去,脸颊被迫贴近她那只踩着我手的脚。
我就那么以一个跪趴在地毫无尊严的姿势,在肮脏的卫生间里,仔细地嗅闻着她脚上的每一寸气味,从脚跟,到脚心,再到脚趾。
闻了一会儿之后,她抬起了脚,用脚趾勾起了被我放在一旁鞋里她自己的那只白色棉袜。
她将袜子夹在脚趾之间,递到我的面前,我连忙伸出手将袜子接了过来。
然后,我听到了她那带着气音小恶魔般的命令。
“跪直了,捧着袜子闻。”
我不敢有丝毫犹豫,连忙依言照做。
我双手捧着那只还带着她的体温和汗味的袜子,慢慢地在狭小的空间里跪直了身体。
就在我跪直身体,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手上那只袜子上时,她的脚顺着我宽大的校服下摆伸了进去。
她的脚趾触碰到我温热的腹部肌肤,让我浑身控制不住地一颤。
她的脚并没有停下,而是继续向上探索,一路滑过我的小腹,最终停在了我的胸口。
我眼睁睁地看着也感受着,她的脚尖熟练地将我的胸罩向上拨弄,直到整个下摆都翻卷了上去,让我胸前最柔软的部分,完全暴露在她的脚趾之下。
紧接着,她那灵活的脚趾夹住了我左边的乳头。
一阵尖锐混杂着无尽羞耻的刺痛,猛地传来。
我的身体瞬间绷紧,牙关死死咬住,却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她就像一个发现了新奇玩具的孩子,用她的脚趾,反复地夹着、拨弄着、甚至轻轻地向外拉扯着那个对我而言无比敏感的部位。
她的动作并不重,甚至可以说很轻,但其带来的精神折磨,却远远超过了肉体上的痛苦。
我的身体,属于我自己的身体,此刻却成了她用脚就可以随意玩弄的物件。
我就那么屈辱地跪在这间肮脏的厕所隔断里,双手捧着她的脏袜子,被迫一下一下地呼吸着那股酸酸的味道,而我的胸部,则被她的脚趾肆意地玩弄着。
外面是正常属于同学们的校园世界,而在这个小小的封闭隔间里,我正经历着一场无人知晓无声的地狱。
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她似乎觉得无聊了,玩腻了,才终于将脚从我的衣服里抽了出来。
她将那只赤裸的脚伸到我的面前,用眼神示意我,给她穿好袜子和鞋。
我如蒙大赦,连忙放下手中的袜子,小心翼翼用最快的速度,将那只袜子重新套回到她的脚上,又伺候她穿好鞋子。
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卑微的深入骨髓的讨好。
她穿好鞋后站起身,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确认走廊上没有人之后,才面无表情地打开隔断门,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走了出去。
在白杨离开后,我在那狭小而肮脏的隔断里呆滞了许久,才终于扶着冰冷的隔板,艰难地从地面上站了起来。
膝盖因为长时间的跪地而酸痛麻木,我低头看去,校服裤子的膝盖处,已经蹭上了两块明显的混着水渍的黑色污垢。
我低下头,默默地将被她用脚拨乱的胸罩重新调整好,又用力地将已经变得皱巴巴的衣服下摆拽平整,试图抹去一切被侵犯过的痕迹,尽管我知道这只是徒劳。
我走出隔断,来到洗手池前,抬头看向镜子。
镜子里的那个人,脸色居然带着一丝莫名其妙的潮红。
我打开水龙头,用冰冷的水一遍又一遍地冲洗着自己的嘴和鼻子,仿佛这样就能洗掉那股刻在记忆里的屈辱气味,和口腔里残留的鞋底的土腥味。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是永远也洗不掉的。
我走进嘈杂的食堂,打了最便宜的饭菜,找到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坐了下来。
周围是同学们热闹的说笑声,讨论着周末的趣事和下午的考试,这一切都与我格格不入。
我默默地扒着碗里的饭,眼泪却不受控制一颗接着一颗地,砸进了饭菜里,溅起小小的水花。
我感到无比的屈辱和恶心。
但内心深处,另一个冰冷而理智的声音,在不断地告诫着自己:
“李盼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为了能继续读书,为了能考上大学,为了那个遥远但唯一的希望,你必须忍耐。”
“做她们母女的玩物,至少可以活下去,至少还有逃离的可能。这点屈辱,和你的未来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我把屈辱和眼泪,伴随着饭菜一起用力地吞进了肚子里。
吃完饭,我回到教室。
我看见白杨正坐在她的座位上,被几个要好的女孩子簇拥着,正笑语晏晏地讨论着什么,仿佛中午那场发生在厕所里的羞辱从来没有发生过。
她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没有了厕所里的阴冷和戏谑,只带着一丝了然于心的笑意,然后便立刻转回头,继续和她的朋友们热烈地聊天。
这个眼神,像一根无形的针,再一次狠狠地刺痛了我。
它在无声地提醒我,她掌握着我最卑贱、最狼狈的模样,这个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是她掌控我又一道坚不可摧的枷锁。
晚上放学,我收拾好自己的书包。
然后,我默默地走到教室门口,像一个最忠实的仆人一样,安静地等着她。
白杨和她的朋友们告别后,才施施然地走出教室。
她经过我身边时,甚至没有丝毫的停顿,只是极其自然地将她那沉重的书包,直接递到了我的怀里。
我也极其自然地伸出手接了过来,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谁都没有说话,沉默地走向公交车站。
她两手空空,步履轻快地走在前面,而我抱着她的书包低着头,像一个卑微的影子,沉默地跟在她的身后。
从教室到校门口,再到公交车站,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的同学和老师,看到的,或许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富家女与穷学生之间常见的校园常态。
没有人知道,这沉默的背后,隐藏着何等惊涛骇浪的屈辱与支配。
回到白杨家里,一关上门,隔绝了外界的一切视线,我立刻主动跪在了玄关的地垫上。
白杨站在我的面前,什么也不说,只是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熟练地用嘴咬住她的鞋跟,帮她脱下那双穿了一天的运动鞋,然后转身从鞋柜里,取来她那双白色居家拖鞋伺候她换上。
客厅里,林曼丽已经做好了晚饭,正在将菜肴一一端上餐桌。
她看到白杨回来,脸上立刻露出了慈爱的笑容,招呼她去洗手吃饭。
她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跪在地上正在给白杨整理鞋子的我,没有任何波澜仿佛我真的只是门口的一件摆设,一块地毯。
我将两个书包放好后,也默默地去卫生间洗了手。
走到餐桌旁,林曼丽已经为我盛好了一碗饭菜,就放在餐桌的一角。
我端起自己的碗,走到客厅的茶几边,将饭菜放在那张矮矮的茶几上。
然后,我在地毯上跪了下来,以跪着的姿态开始吃我的晚饭。
这是林曼丽为我定下的规矩,虽然不会在食物上苛待我,但我绝不可以和主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因为我的身份,是下人。
餐厅里,灯光明亮,母女二人边吃边聊着学校里的趣闻、美容院里贵妇们的八卦,气氛温馨而融洽。
而客厅里,只有我一个人跪在地上快速地扒着饭,与她们的世界格格不入。
仿佛有一道无形透明的墙,将我们彻底隔绝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快速地吃完自己的饭菜,立刻将碗拿到厨房,用最快的速度刷洗干净。
然后,我回到餐厅,跪在餐桌旁安静地一动不动等待着母女二人用餐结束。
在她们眼中,我仿佛就是空气。
她们的交谈,从未避讳过我,也从未将我纳入其中。
等她们终于吃完放下碗筷,我立刻上前将桌上所有的碗碟收拾好端到厨房,仔细地刷洗干净,并将厨房的台面和水池整理得一尘不染。
做完这一切后,白杨已经回到了她自己的卧室,大概是去写作业了。
林曼丽则慵懒地靠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敷着面膜一边看着电视里播放的无聊综艺。
我走到她的身边,安静地跪了下来,准备为她捏脚或者等待她下达任何新的命令。
她没有立刻说话,只是任由我跪着。
直到电视里插播广告,她才从屏幕上移开目光,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平静,淡漠。
“不用你伺候了,”她语气平静地说道,“回屋写作业去吧。”
这句话,对我来说,不啻于一种盛大的赦免。
我如蒙大赦,连忙深深地低下头,用极小的声音说道:“……谢谢夫人。”
我不敢奢求这是她突发的善意,我只知道,这或许是她今天心情不错,暂时不需要我这个“物件”,来为她提供任何服务。
我起身,轻手轻脚地回到了那间客房。
关上门,打开墙壁上的灯。
我从书包里,拿出今天下午刚发的数学卷子和练习本,小心翼翼地铺在桌子上。
我闭上眼,用力地甩了甩头,试图将一整天所有的屈辱、痛苦和恐惧,都从我的脑海里甩出去。
我拿起笔,眼神逐渐变得专注而坚定。
只有在这一刻,在面对这些冰冷、复杂却有规律可循的习题时,我才感觉自己不是那个任人践踏的“丫鬟李盼男”,而是那个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学生李盼男。
笔尖划过纸张时发出的“沙沙”声,是这片死寂的深渊里,唯一能回应我的声音。
也是我支撑着自己,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这是我的战争,也是我的救赎。
温热的气流从我的鼻腔中呼出,拂过白杨的脚趾缝,似乎带去了一丝微痒。
她那几根秀气的脚趾,像是被惊扰的蝶翼,轻轻地晃动了几下。
那是一种近乎顽皮的动作,充满了猫捉老鼠般的戏谑。
紧接着,她的脚趾缝便在我的鼻尖上,极其缓慢地来回摩擦起来。
这个动作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挑逗与侮辱,每一次摩擦,都像是在用对待一件物品的方式,确认着我皮肤的触感,也像是在我的尊严上划过一刀。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脚趾缝里残留的因汗水而带来的湿热,以及那细腻皮肤下的纹理。
屈辱感再一次如同潮水般将我淹没。
就在我沉浸在这种屈辱的麻木中时,没有任何预兆,她的脚趾再一次猛地并拢,比上一次更加用力地,死死夹住了我的鼻子。
熟悉的窒息感瞬间涌来。
这一次,我有了心理准备,没有挣扎,只是默默地闭上了眼睛。
身体因为最原始的缺氧本能,再一次开始不受控制地轻微颤抖。
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不受控制地溢出眼眶,顺着脸颊无声滑落。
但我死死地咬住自己的嘴唇,不让自己发出任何一点求饶或痛苦的声音。
白杨一定很享受我这种无声绝望的忍耐。
这证明了她的规训是何等成功,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即使在极限的边缘,也绝不会违抗她命令的,一个“合格”的玩物。
就在我感觉肺部灼痛,意识即将彻底涣散,快要达到生理忍耐极限的时候,一个声音,将我从这濒死的幻觉中猛地拽了回来。
“哗啦——”
隔壁隔断,传来了清晰的冲水声。
这声音,对我而言不啻于天籁之音。
它既让我恐惧——怕被发现这惊世骇俗的一幕;又带来了一丝微弱的希望——这场折磨或许会因此而中断。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僵硬地维持着那个屈辱的姿势,一动也不敢动。
“吱呀”一声,隔壁的隔断门被拉开。
紧接着是门自动关闭时发出的“砰”的一声轻响,以及一阵逐渐远去的脚步声。
我能听出,那脚步声的主人,已经走出了卫生间,消失在了走廊的尽头。
白杨显然也听到了所有的声音。
我能感觉到,她夹住我鼻子的力量没有丝毫松懈,甚至因为这突发的状况,更添了一分难以言喻的兴奋。
她没有立刻松开我,而是侧着耳朵,仔细地倾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确认那脚步声已经完全消失。
在确认了绝对安全之后,她才仿佛仁慈施舍一般,松开了夹住我鼻子的脚趾。
鼻腔得到解放的瞬间,我立刻本能地拼命用鼻子大口呼吸着这间厕所里污浊的空气,喉咙里发出压抑不住的如同破旧风箱般急促喘息声。
白杨没有移开她的脚,就那么将它悬停在我的鼻子前方。
她的脚趾,随着我每一次急促的呼吸,一张一合,仿佛在玩弄着我的生命气息。
每一次吸气,都不可避免地吸入她脚上那股酸腐的气味;每一次呼气,又将温热的气息,喷在她的脚心。
我的呼吸,这一最基本的生存本能,此刻也完全被她所支配和观赏。
我感到极度的恶心与屈辱。
等到我的呼吸终于在她的注视下,一点点平稳下来,白杨转过身重新面对着我。
用她的脚底缓缓施加力道,将我那双原本捧着她脚的手,一点点踩在了肮脏潮湿的地面上。
冰冷坚硬的瓷砖,混合着不知名污水的湿滑感,透过我的手背,清晰地传来。
她的脚底板,稳稳地压着我的手,像是在我的手上,盖下了一个屈辱的印章。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下巴,朝着地面示意了一下。
我不敢违抗。
我只能顺从地,将整个上半身都趴了下去,脸颊被迫贴近她那只踩着我手的脚。
我就那么以一个跪趴在地毫无尊严的姿势,在肮脏的卫生间里,仔细地嗅闻着她脚上的每一寸气味,从脚跟,到脚心,再到脚趾。
闻了一会儿之后,她抬起了脚,用脚趾勾起了被我放在一旁鞋里她自己的那只白色棉袜。
她将袜子夹在脚趾之间,递到我的面前,我连忙伸出手将袜子接了过来。
然后,我听到了她那带着气音小恶魔般的命令。
“跪直了,捧着袜子闻。”
我不敢有丝毫犹豫,连忙依言照做。
我双手捧着那只还带着她的体温和汗味的袜子,慢慢地在狭小的空间里跪直了身体。
就在我跪直身体,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手上那只袜子上时,她的脚顺着我宽大的校服下摆伸了进去。
她的脚趾触碰到我温热的腹部肌肤,让我浑身控制不住地一颤。
她的脚并没有停下,而是继续向上探索,一路滑过我的小腹,最终停在了我的胸口。
我眼睁睁地看着也感受着,她的脚尖熟练地将我的胸罩向上拨弄,直到整个下摆都翻卷了上去,让我胸前最柔软的部分,完全暴露在她的脚趾之下。
紧接着,她那灵活的脚趾夹住了我左边的乳头。
一阵尖锐混杂着无尽羞耻的刺痛,猛地传来。
我的身体瞬间绷紧,牙关死死咬住,却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她就像一个发现了新奇玩具的孩子,用她的脚趾,反复地夹着、拨弄着、甚至轻轻地向外拉扯着那个对我而言无比敏感的部位。
她的动作并不重,甚至可以说很轻,但其带来的精神折磨,却远远超过了肉体上的痛苦。
我的身体,属于我自己的身体,此刻却成了她用脚就可以随意玩弄的物件。
我就那么屈辱地跪在这间肮脏的厕所隔断里,双手捧着她的脏袜子,被迫一下一下地呼吸着那股酸酸的味道,而我的胸部,则被她的脚趾肆意地玩弄着。
外面是正常属于同学们的校园世界,而在这个小小的封闭隔间里,我正经历着一场无人知晓无声的地狱。
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她似乎觉得无聊了,玩腻了,才终于将脚从我的衣服里抽了出来。
她将那只赤裸的脚伸到我的面前,用眼神示意我,给她穿好袜子和鞋。
我如蒙大赦,连忙放下手中的袜子,小心翼翼用最快的速度,将那只袜子重新套回到她的脚上,又伺候她穿好鞋子。
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卑微的深入骨髓的讨好。
她穿好鞋后站起身,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确认走廊上没有人之后,才面无表情地打开隔断门,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走了出去。
在白杨离开后,我在那狭小而肮脏的隔断里呆滞了许久,才终于扶着冰冷的隔板,艰难地从地面上站了起来。
膝盖因为长时间的跪地而酸痛麻木,我低头看去,校服裤子的膝盖处,已经蹭上了两块明显的混着水渍的黑色污垢。
我低下头,默默地将被她用脚拨乱的胸罩重新调整好,又用力地将已经变得皱巴巴的衣服下摆拽平整,试图抹去一切被侵犯过的痕迹,尽管我知道这只是徒劳。
我走出隔断,来到洗手池前,抬头看向镜子。
镜子里的那个人,脸色居然带着一丝莫名其妙的潮红。
我打开水龙头,用冰冷的水一遍又一遍地冲洗着自己的嘴和鼻子,仿佛这样就能洗掉那股刻在记忆里的屈辱气味,和口腔里残留的鞋底的土腥味。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是永远也洗不掉的。
我走进嘈杂的食堂,打了最便宜的饭菜,找到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坐了下来。
周围是同学们热闹的说笑声,讨论着周末的趣事和下午的考试,这一切都与我格格不入。
我默默地扒着碗里的饭,眼泪却不受控制一颗接着一颗地,砸进了饭菜里,溅起小小的水花。
我感到无比的屈辱和恶心。
但内心深处,另一个冰冷而理智的声音,在不断地告诫着自己:
“李盼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为了能继续读书,为了能考上大学,为了那个遥远但唯一的希望,你必须忍耐。”
“做她们母女的玩物,至少可以活下去,至少还有逃离的可能。这点屈辱,和你的未来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我把屈辱和眼泪,伴随着饭菜一起用力地吞进了肚子里。
吃完饭,我回到教室。
我看见白杨正坐在她的座位上,被几个要好的女孩子簇拥着,正笑语晏晏地讨论着什么,仿佛中午那场发生在厕所里的羞辱从来没有发生过。
她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没有了厕所里的阴冷和戏谑,只带着一丝了然于心的笑意,然后便立刻转回头,继续和她的朋友们热烈地聊天。
这个眼神,像一根无形的针,再一次狠狠地刺痛了我。
它在无声地提醒我,她掌握着我最卑贱、最狼狈的模样,这个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是她掌控我又一道坚不可摧的枷锁。
晚上放学,我收拾好自己的书包。
然后,我默默地走到教室门口,像一个最忠实的仆人一样,安静地等着她。
白杨和她的朋友们告别后,才施施然地走出教室。
她经过我身边时,甚至没有丝毫的停顿,只是极其自然地将她那沉重的书包,直接递到了我的怀里。
我也极其自然地伸出手接了过来,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谁都没有说话,沉默地走向公交车站。
她两手空空,步履轻快地走在前面,而我抱着她的书包低着头,像一个卑微的影子,沉默地跟在她的身后。
从教室到校门口,再到公交车站,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的同学和老师,看到的,或许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富家女与穷学生之间常见的校园常态。
没有人知道,这沉默的背后,隐藏着何等惊涛骇浪的屈辱与支配。
回到白杨家里,一关上门,隔绝了外界的一切视线,我立刻主动跪在了玄关的地垫上。
白杨站在我的面前,什么也不说,只是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熟练地用嘴咬住她的鞋跟,帮她脱下那双穿了一天的运动鞋,然后转身从鞋柜里,取来她那双白色居家拖鞋伺候她换上。
客厅里,林曼丽已经做好了晚饭,正在将菜肴一一端上餐桌。
她看到白杨回来,脸上立刻露出了慈爱的笑容,招呼她去洗手吃饭。
她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跪在地上正在给白杨整理鞋子的我,没有任何波澜仿佛我真的只是门口的一件摆设,一块地毯。
我将两个书包放好后,也默默地去卫生间洗了手。
走到餐桌旁,林曼丽已经为我盛好了一碗饭菜,就放在餐桌的一角。
我端起自己的碗,走到客厅的茶几边,将饭菜放在那张矮矮的茶几上。
然后,我在地毯上跪了下来,以跪着的姿态开始吃我的晚饭。
这是林曼丽为我定下的规矩,虽然不会在食物上苛待我,但我绝不可以和主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因为我的身份,是下人。
餐厅里,灯光明亮,母女二人边吃边聊着学校里的趣闻、美容院里贵妇们的八卦,气氛温馨而融洽。
而客厅里,只有我一个人跪在地上快速地扒着饭,与她们的世界格格不入。
仿佛有一道无形透明的墙,将我们彻底隔绝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快速地吃完自己的饭菜,立刻将碗拿到厨房,用最快的速度刷洗干净。
然后,我回到餐厅,跪在餐桌旁安静地一动不动等待着母女二人用餐结束。
在她们眼中,我仿佛就是空气。
她们的交谈,从未避讳过我,也从未将我纳入其中。
等她们终于吃完放下碗筷,我立刻上前将桌上所有的碗碟收拾好端到厨房,仔细地刷洗干净,并将厨房的台面和水池整理得一尘不染。
做完这一切后,白杨已经回到了她自己的卧室,大概是去写作业了。
林曼丽则慵懒地靠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敷着面膜一边看着电视里播放的无聊综艺。
我走到她的身边,安静地跪了下来,准备为她捏脚或者等待她下达任何新的命令。
她没有立刻说话,只是任由我跪着。
直到电视里插播广告,她才从屏幕上移开目光,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平静,淡漠。
“不用你伺候了,”她语气平静地说道,“回屋写作业去吧。”
这句话,对我来说,不啻于一种盛大的赦免。
我如蒙大赦,连忙深深地低下头,用极小的声音说道:“……谢谢夫人。”
我不敢奢求这是她突发的善意,我只知道,这或许是她今天心情不错,暂时不需要我这个“物件”,来为她提供任何服务。
我起身,轻手轻脚地回到了那间客房。
关上门,打开墙壁上的灯。
我从书包里,拿出今天下午刚发的数学卷子和练习本,小心翼翼地铺在桌子上。
我闭上眼,用力地甩了甩头,试图将一整天所有的屈辱、痛苦和恐惧,都从我的脑海里甩出去。
我拿起笔,眼神逐渐变得专注而坚定。
只有在这一刻,在面对这些冰冷、复杂却有规律可循的习题时,我才感觉自己不是那个任人践踏的“丫鬟李盼男”,而是那个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学生李盼男。
笔尖划过纸张时发出的“沙沙”声,是这片死寂的深渊里,唯一能回应我的声音。
也是我支撑着自己,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这是我的战争,也是我的救赎。
BBlue4发布于 2026-02-22 15:05
Re: 春风若有怜花意(女女,母女主,严厉高压)2.20,第39章
作者写得真好。后面会有恋足和虐身体以外的调教吗
lxhniuniu159发布于 2026-02-24 21:55
Re: 春风若有怜花意(女女,母女主,严厉高压)2.20,第39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