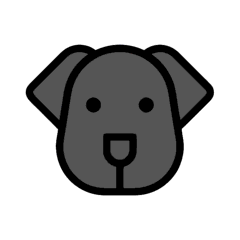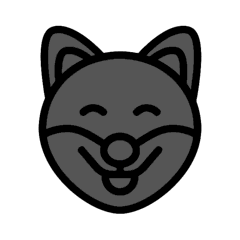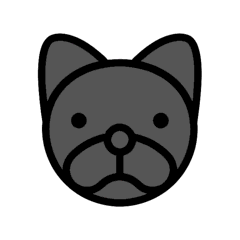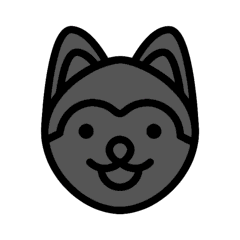【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在这充满罪恶、充满了流放的深渊, 这正是恶之花盛开的地方。全文42w字
连载中原创校园NTR绿奴体育生足控裸足袜控棉袜原味贞操锁臭脚运动鞋羞辱气味
Ankh发布于 ,编辑于 2025-12-23 23:09
【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在这充满罪恶、充满了流放的深渊, 这正是恶之花盛开的地方。全文42w字
第一章
京州的雨季总是来得毫无征兆,一旦开始,就像是某种漫长的、黏稠的刑罚,要把这座城市里所有活着的东西都腌入味。
已经是六月中旬了,空气里的湿度常年维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在这个巨大的、仿佛被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城市里,阳光成了一种奢侈的谎言。晾在男生宿舍阳台上的衣服永远带着一股未干透的馊味,课本的书页总是发软起皱,摸上去像是在摸一层死人的皮肤。就连人的骨头缝里,仿佛都正在长出一层看不见的青苔。
下午四点,京州大学图书馆的三楼阅览室里弥漫着一股令人昏昏欲睡的低气压。
中央空调似乎坏了,或者是因为这种尴尬的气温而被管理员关掉了。只有几扇半开的窗户里,偶尔吹进一阵带着土腥味的过堂风。这风并不能带来凉爽,反而把外面那股湿热的水汽卷了进来,混合着几百个学生呼出的二氧化碳、陈旧纸张的霉味,以及无数双被捂在运动鞋里的脚散发出的温热气息,在天花板下发酵成一种独特的、令人窒息的高校气味。
我坐在F区的最后一排,手里那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已经停留在第42页整整半个小时了。
角落里的阴影给了我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我叫沈言,中文系大二学生。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我是一块不起眼的背景板,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优衣库最基础款的灰色T恤,是那种帮室友带饭、帮同学占座、永远脾气温和的老好人。我就像这所大学里最常见的梧桐树叶,多一片不多,少一片不少。
但我有自己的秘密。或者说,我有自己长久以来观测的一颗恒星。
我的视线越过层层叠叠的书堆,穿过桌底昏暗的缝隙,熟练而贪婪地锁定在斜前方三排那个靠窗的位置上。
那是乔一。
其实她并不认识我。但我认识她,就像这所学校里很多暗恋她的男生一样。我知道她是体育学院羽毛球专业的王牌,知道她大一刚进校就拿了新生杯冠军,知道她喜欢喝食堂二楼最左边那家窗口的绿豆沙,不喜欢放糖。
她今天穿了一件宽松的灰色连帽卫衣,袖子随意地挽到手肘,露出一截白皙却紧致的小臂。因为长期挥拍,她的右小臂线条比左边稍微明显一些,那是日复一日在球场上扣杀、在极限状态下爆发出来的生命力。那不是健身房里吃蛋白粉练出来的死肉,而是蕴含着惊人爆发力的线条,像是一张随时拉满的弓。
下身是一条黑色的紧身运动裤,这种裤子对腿型的要求极高,但在她身上却像是第二层皮肤,完美地勾勒出大腿和小腿之间那种充满弹性的起伏。
她正在备战英语六级。桌上堆满了红宝书和真题集,手里那支黑色的签字笔在指尖飞快地旋转,发出沙沙的声响。
但我关注的不是她在看什么,甚至不是她那张即使素颜也足以让路人回头的脸。我的目光像是一只在阴沟里爬行的生物,顺着地砖的纹路,悄无声息地游走到她的脚下。
那是她的绝对领域。
她今天穿了一双白色的耐克AF1。
这双鞋应该穿了很久了。鞋面上的折痕深得像是岁月留下的刻痕,原本挺括的皮质已经变得软塌塌的,鞋底边缘泛着一圈洗不掉的焦黄色。鞋带系得很松,有些发灰,显然是为了穿脱方便。
对于乔一来说,这可能只是一双舒服的旧鞋。但对于我来说,这双鞋承载了她无数次的奔跑、急停和跳跃。它就像是一个忠诚的容器,收集了她所有的汗水和体温。
乔一似乎很焦躁。
这也难怪。这种阴湿闷热的天气,对于一个每天都要流几斤汗的体育特长生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皮肤层面的灾难。她的身体代谢率比普通人高得多,就像是一台大马力的发动机,即使在静止状态下也在源源不断地散发着热量。
我看得很清楚,她的双脚在桌子底下并不安分。
每隔几分钟,她的左脚就会无意识地在地上蹭两下。那种摩擦的频率很快,带着一种发泄式的急躁。
那是痒。
那种常年包裹在厚棉袜里的脚,在这个不透气的下午,被汗水、真菌和高温联合围剿了。那一层薄薄的皮肤下,无数个毛孔正在尖叫,渴望着呼吸。汗水顺着脚踝流进鞋子里,浸透了袜子,让原本干爽的棉织物变得黏腻、沉重。
我感觉我的喉咙有些发干,下意识地拿起手边的水杯喝了一口。温热的水滑过喉咙,却并没有解渴,反而让身体里的那股燥热更甚。
就在这时,乔一终于忍受不了那种隔靴搔痒的折磨。
她左右看了一眼,动作幅度很小,像是在确认周围有没有教导主任或者熟人。没人注意她,大家都在为了绩点和考证而焦头烂额。
于是,她做了一个极其自然的动作。
她用右脚的脚尖抵住左脚的脚后跟,轻轻一踩。
然后,把左脚从那只闷热的AF1里提了出来。
那只原本封闭的球鞋像是张开了嘴的贝壳,露出了一角隐秘的软肉。随着脚后跟的脱离,一抹白色暴露在空气中。
那是一只被白色中筒棉袜紧紧包裹的脚。因为长时间的行走和闷热,白色的棉袜已经不再是纯白,而是在脚底和后跟的位置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灰色。那是汗水洇透了棉织物后特有的质感,黏腻、潮湿,紧紧地贴在皮肤上,勾勒出脚踝骨那圆润的轮廓。
但这还不够解痒。
接下来的那一幕,让我握着书的手指瞬间收紧,指关节泛白。
乔一并没有把脚放回地上。她似乎觉得地面不够凉快,于是她抬起那只穿着半湿袜子的左脚,寻找着支点。
她的脚尖试探性地往前伸了伸,碰到了前排椅子的不锈钢横杠。
那是图书馆那种老式阅览椅特有的金属横杠,冰冷、坚硬。
她把脚心踩了上去。
然后,开始前后摩擦。
吱——嘎——
虽然声音很小,被周围的翻书声掩盖了,但我仿佛能听到那棉袜与金属摩擦时发出的细微声响。
她在用那根冰冷的横杠,去刮蹭她发痒的脚心。
一下,两下。
她的动作很有节奏。脚掌弓起,像是一只慵懒的猫在磨爪子。我看得到那灰色的袜底紧紧裹着横杠,随着她的动作,那根原本光亮的不锈钢管上,似乎留下了一层淡淡的、转瞬即逝的水雾。
那是她脚底的热气遇冷凝结成的痕迹。
我想象着那种触感。
冰冷的金属陷进温热的肉里,粗糙的棉袜纤维摩擦着娇嫩的足底皮肤。那种冷热交替的刺激,一定让她感到一阵战栗般的舒爽。因为我看到她的肩膀微微塌下来了一些,整个人放松地靠在了椅背上,手里转笔的速度也慢了下来。
我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
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我仿佛变成了一根那样冰冷的横杠,渴望着被她踩在脚下,渴望着感受那种带着体温的碾压。
啪嗒。
一声清脆的塑料撞击声,像是一记耳光,猛地把我从那种近乎病态的幻想中抽离出来。
乔一手中的那支签字笔掉了。
笔在地上弹跳了两下,像是一个不听话的小精灵,骨碌碌地滚到了过道中间,正好停在了距离我大概两米远的地方。
乔一下意识地想要弯腰去捡。
但因为阅览室的桌子太窄,或者是因为她那条紧身裤实在是太紧了,勒得她弯腰有些困难。她试着伸了伸手,指尖距离笔还有十几公分。
她叹了口气,手撑着桌子准备站起来。
我的心脏猛地跳漏了一拍。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只敢在梦里排练的机会。
几乎是身体比大脑先做出了反应,我猛地站起身。椅子在地板上划出滋啦一声轻响,但我根本顾不上周围人异样的目光。
“同学,我帮你。”
我快步走过去。声音比我想象中要平静,但我自己知道,那是紧绷到极致后的伪装。
乔一愣了一下,抬起头。
那是一张素面朝天的脸。没有化妆,皮肤白皙透亮,鼻尖上还挂着几颗细密的汗珠。几缕碎发因为静电贴在脸颊上,让她看起来少了几分球场上的凌厉,多了几分邻家女孩的娇憨。
“啊,谢谢。”她冲我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很淡,很客气,礼貌得就像是对待任何一个路过的陌生人。她显然不记得我是谁,不记得我们在食堂排队时曾经前后脚,不记得我在球场边捡过多少个她打飞的球。
我走到笔掉落的地方。
但我没有立刻蹲下去。
因为距离拉近了,我的视线不受控制地再次落在了她的脚下。
因为刚才想起身捡笔的动作,她的左脚已经完全从鞋里抽了出来,此刻正赤着脚踩在冰冷的水磨石地板上。
那只AF1孤零零地躺在一边,鞋舌外翻,鞋垫上甚至能看到一个深灰色的脚印轮廓,那是汗水长期浸泡留下的痕迹,像是一个黑色的幽灵。
而那只穿着灰袜子的脚,正无意识地蜷缩着脚趾。
那一刻,我离她只有不到一米。
一股极其微弱、但对我来说如同惊雷般的气息,钻进了我的鼻孔。
不是幻想中的酸臭,也不是令人作呕的异味。
而是一股热气。
一股湿漉漉的、带着体温的热气。
那是怎么形容呢?就像是夏天暴雨过后,从泥土里蒸腾起来的那种味道。带着一点点草腥气,一点点发酵的酸味,还有一种浓郁得化不开的甜。
那是少女特有的体香,混合了运动后的汗液,在封闭的鞋腔里酿造了一下午之后,终于重见天日。它有着惊人的穿透力,不像香水那样浮在表面,而是直接钻进你的毛孔,黏在你的肺泡上。
我的大脑在那一瞬间有些缺氧。
我慢慢蹲下来,手指触碰到了那支黑色的签字笔。
笔杆是温热的。甚至是有些潮湿的。
上面沾着她手心的汗水。
我握住那支笔,就像是握住了她的一根手指。
我并没有立刻站起来。我借着捡笔的动作,把头压得很低,鼻尖几乎贴到了地板上。
我在那个高度,屏住呼吸,然后极其克制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股从她脚底和鞋口散发出来的味道,瞬间充满了我的肺叶。
真好闻啊。
这就是活着的味道。
这就是乔一的味道。
我就像是一个即将渴死的旅人,在沙漠里遇到了一汪浑浊却甘甜的水。那味道顺着鼻腔直冲天灵盖,让我的脊椎骨都酥了一半,某种难以启齿的生理反应在瞬间被点燃。
但我必须克制。
我必须要把这头野兽关进笼子里。我是沈言,我是中文系的好学生,我不能在这里变成一个变态。
我咬了咬舌尖,用疼痛强迫自己清醒过来。
我迅速站起身,把笔递给她。
“没……没事。”我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的、有点书呆子气的男生,掩饰住眼底那近乎狂热的波动,“可能是低血糖,蹲久了有点晕。”
“哦,那你小心点,记得吃早饭。”
乔一接过笔。
在她手指碰到我的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一股电流。
她的手很热,指腹上有握拍磨出的茧子,粗糙而有力。
“谢了啊。”
她冲我摆摆手,那个动作随意而洒脱。然后她重新坐回位子上,继续和那本红宝书死磕。
她并没有把脚穿回鞋里。相反,她似乎觉得光脚踩在地板上那种冰凉的触感很舒服。她把右脚也脱了出来,两只穿着脏袜子的脚就这样大大方方地踩在地上,互相蹭了蹭。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一幕。
看着她脚踝上那根细细的青色血管。
看着袜子边缘那被勒出的一道浅浅的红印。
我的口袋里,那只刚才握过她笔的手,正死死地攥成拳头。指尖上,还残留着那支笔的温度,那是她手心的汗水。
我慢慢地走回自己的座位,拉开椅子坐下。
椅子的座面有些硬,硌得我很难受。但我没有调整姿势,而是保持着一种僵硬的坐姿,双腿在桌下紧紧并拢。那里传来的胀痛感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因为刚才那一瞬间的靠近和嗅闻,变得更加剧烈。布料摩擦着皮肤,每一次极微小的移动都是一种带着罪恶感的折磨。
但我没有动,更没有逃向厕所。
我重新翻开那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目光落在第42页那行密密麻麻的铅字上。
但我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我的右手——那只刚刚握过她笔的手,慢慢地抬了起来。
我假装推扶眼镜,手指极其自然地滑过鼻尖,然后停留在嘴唇上方。
我屏住呼吸,那是极其轻微的一吸。
很淡。
那是金属笔杆留下的铁锈味,混合着极其微弱的、几乎难以捕捉的咸湿气息。那是她手心汗水的味道,是她刚刚握着那支笔奋斗了一下午留下的体温。
这股味道像是一根看不见的线,瞬间将我和斜前方那个背影连接在了一起。
我看着乔一。
她依然保持着那个姿势,左脚的脚后跟踩在椅子的横杠上,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蹭着。那只脱了一半的AF1歪歪扭扭地躺在地上,像是个被遗弃的玩具。
过堂风又吹了进来,带着雨水的土腥味,但这股味道此刻在我的鼻腔里,已经完全被指尖那一抹若有若无的气息覆盖了。
我放下手,重新握住了书页。
这一次,我终于看清了书上的字,虽然我的心跳依然快得有些不正常。
窗外的雨还在下,淅淅沥沥地敲打着玻璃。图书馆里很安静,只有偶尔的翻书声和乔一那只笔旋转时发出的细微沙沙声。
我坐在阴影里,忍受着身体的胀痛,继续看着书。
只是每隔几分钟,我都会下意识地抬起手,用那根手指轻轻蹭过鼻尖。
仿佛那里还残留着整个夏天。
京州的雨季总是来得毫无征兆,一旦开始,就像是某种漫长的、黏稠的刑罚,要把这座城市里所有活着的东西都腌入味。
已经是六月中旬了,空气里的湿度常年维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在这个巨大的、仿佛被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城市里,阳光成了一种奢侈的谎言。晾在男生宿舍阳台上的衣服永远带着一股未干透的馊味,课本的书页总是发软起皱,摸上去像是在摸一层死人的皮肤。就连人的骨头缝里,仿佛都正在长出一层看不见的青苔。
下午四点,京州大学图书馆的三楼阅览室里弥漫着一股令人昏昏欲睡的低气压。
中央空调似乎坏了,或者是因为这种尴尬的气温而被管理员关掉了。只有几扇半开的窗户里,偶尔吹进一阵带着土腥味的过堂风。这风并不能带来凉爽,反而把外面那股湿热的水汽卷了进来,混合着几百个学生呼出的二氧化碳、陈旧纸张的霉味,以及无数双被捂在运动鞋里的脚散发出的温热气息,在天花板下发酵成一种独特的、令人窒息的高校气味。
我坐在F区的最后一排,手里那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已经停留在第42页整整半个小时了。
角落里的阴影给了我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我叫沈言,中文系大二学生。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我是一块不起眼的背景板,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优衣库最基础款的灰色T恤,是那种帮室友带饭、帮同学占座、永远脾气温和的老好人。我就像这所大学里最常见的梧桐树叶,多一片不多,少一片不少。
但我有自己的秘密。或者说,我有自己长久以来观测的一颗恒星。
我的视线越过层层叠叠的书堆,穿过桌底昏暗的缝隙,熟练而贪婪地锁定在斜前方三排那个靠窗的位置上。
那是乔一。
其实她并不认识我。但我认识她,就像这所学校里很多暗恋她的男生一样。我知道她是体育学院羽毛球专业的王牌,知道她大一刚进校就拿了新生杯冠军,知道她喜欢喝食堂二楼最左边那家窗口的绿豆沙,不喜欢放糖。
她今天穿了一件宽松的灰色连帽卫衣,袖子随意地挽到手肘,露出一截白皙却紧致的小臂。因为长期挥拍,她的右小臂线条比左边稍微明显一些,那是日复一日在球场上扣杀、在极限状态下爆发出来的生命力。那不是健身房里吃蛋白粉练出来的死肉,而是蕴含着惊人爆发力的线条,像是一张随时拉满的弓。
下身是一条黑色的紧身运动裤,这种裤子对腿型的要求极高,但在她身上却像是第二层皮肤,完美地勾勒出大腿和小腿之间那种充满弹性的起伏。
她正在备战英语六级。桌上堆满了红宝书和真题集,手里那支黑色的签字笔在指尖飞快地旋转,发出沙沙的声响。
但我关注的不是她在看什么,甚至不是她那张即使素颜也足以让路人回头的脸。我的目光像是一只在阴沟里爬行的生物,顺着地砖的纹路,悄无声息地游走到她的脚下。
那是她的绝对领域。
她今天穿了一双白色的耐克AF1。
这双鞋应该穿了很久了。鞋面上的折痕深得像是岁月留下的刻痕,原本挺括的皮质已经变得软塌塌的,鞋底边缘泛着一圈洗不掉的焦黄色。鞋带系得很松,有些发灰,显然是为了穿脱方便。
对于乔一来说,这可能只是一双舒服的旧鞋。但对于我来说,这双鞋承载了她无数次的奔跑、急停和跳跃。它就像是一个忠诚的容器,收集了她所有的汗水和体温。
乔一似乎很焦躁。
这也难怪。这种阴湿闷热的天气,对于一个每天都要流几斤汗的体育特长生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皮肤层面的灾难。她的身体代谢率比普通人高得多,就像是一台大马力的发动机,即使在静止状态下也在源源不断地散发着热量。
我看得很清楚,她的双脚在桌子底下并不安分。
每隔几分钟,她的左脚就会无意识地在地上蹭两下。那种摩擦的频率很快,带着一种发泄式的急躁。
那是痒。
那种常年包裹在厚棉袜里的脚,在这个不透气的下午,被汗水、真菌和高温联合围剿了。那一层薄薄的皮肤下,无数个毛孔正在尖叫,渴望着呼吸。汗水顺着脚踝流进鞋子里,浸透了袜子,让原本干爽的棉织物变得黏腻、沉重。
我感觉我的喉咙有些发干,下意识地拿起手边的水杯喝了一口。温热的水滑过喉咙,却并没有解渴,反而让身体里的那股燥热更甚。
就在这时,乔一终于忍受不了那种隔靴搔痒的折磨。
她左右看了一眼,动作幅度很小,像是在确认周围有没有教导主任或者熟人。没人注意她,大家都在为了绩点和考证而焦头烂额。
于是,她做了一个极其自然的动作。
她用右脚的脚尖抵住左脚的脚后跟,轻轻一踩。
然后,把左脚从那只闷热的AF1里提了出来。
那只原本封闭的球鞋像是张开了嘴的贝壳,露出了一角隐秘的软肉。随着脚后跟的脱离,一抹白色暴露在空气中。
那是一只被白色中筒棉袜紧紧包裹的脚。因为长时间的行走和闷热,白色的棉袜已经不再是纯白,而是在脚底和后跟的位置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灰色。那是汗水洇透了棉织物后特有的质感,黏腻、潮湿,紧紧地贴在皮肤上,勾勒出脚踝骨那圆润的轮廓。
但这还不够解痒。
接下来的那一幕,让我握着书的手指瞬间收紧,指关节泛白。
乔一并没有把脚放回地上。她似乎觉得地面不够凉快,于是她抬起那只穿着半湿袜子的左脚,寻找着支点。
她的脚尖试探性地往前伸了伸,碰到了前排椅子的不锈钢横杠。
那是图书馆那种老式阅览椅特有的金属横杠,冰冷、坚硬。
她把脚心踩了上去。
然后,开始前后摩擦。
吱——嘎——
虽然声音很小,被周围的翻书声掩盖了,但我仿佛能听到那棉袜与金属摩擦时发出的细微声响。
她在用那根冰冷的横杠,去刮蹭她发痒的脚心。
一下,两下。
她的动作很有节奏。脚掌弓起,像是一只慵懒的猫在磨爪子。我看得到那灰色的袜底紧紧裹着横杠,随着她的动作,那根原本光亮的不锈钢管上,似乎留下了一层淡淡的、转瞬即逝的水雾。
那是她脚底的热气遇冷凝结成的痕迹。
我想象着那种触感。
冰冷的金属陷进温热的肉里,粗糙的棉袜纤维摩擦着娇嫩的足底皮肤。那种冷热交替的刺激,一定让她感到一阵战栗般的舒爽。因为我看到她的肩膀微微塌下来了一些,整个人放松地靠在了椅背上,手里转笔的速度也慢了下来。
我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
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我仿佛变成了一根那样冰冷的横杠,渴望着被她踩在脚下,渴望着感受那种带着体温的碾压。
啪嗒。
一声清脆的塑料撞击声,像是一记耳光,猛地把我从那种近乎病态的幻想中抽离出来。
乔一手中的那支签字笔掉了。
笔在地上弹跳了两下,像是一个不听话的小精灵,骨碌碌地滚到了过道中间,正好停在了距离我大概两米远的地方。
乔一下意识地想要弯腰去捡。
但因为阅览室的桌子太窄,或者是因为她那条紧身裤实在是太紧了,勒得她弯腰有些困难。她试着伸了伸手,指尖距离笔还有十几公分。
她叹了口气,手撑着桌子准备站起来。
我的心脏猛地跳漏了一拍。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只敢在梦里排练的机会。
几乎是身体比大脑先做出了反应,我猛地站起身。椅子在地板上划出滋啦一声轻响,但我根本顾不上周围人异样的目光。
“同学,我帮你。”
我快步走过去。声音比我想象中要平静,但我自己知道,那是紧绷到极致后的伪装。
乔一愣了一下,抬起头。
那是一张素面朝天的脸。没有化妆,皮肤白皙透亮,鼻尖上还挂着几颗细密的汗珠。几缕碎发因为静电贴在脸颊上,让她看起来少了几分球场上的凌厉,多了几分邻家女孩的娇憨。
“啊,谢谢。”她冲我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很淡,很客气,礼貌得就像是对待任何一个路过的陌生人。她显然不记得我是谁,不记得我们在食堂排队时曾经前后脚,不记得我在球场边捡过多少个她打飞的球。
我走到笔掉落的地方。
但我没有立刻蹲下去。
因为距离拉近了,我的视线不受控制地再次落在了她的脚下。
因为刚才想起身捡笔的动作,她的左脚已经完全从鞋里抽了出来,此刻正赤着脚踩在冰冷的水磨石地板上。
那只AF1孤零零地躺在一边,鞋舌外翻,鞋垫上甚至能看到一个深灰色的脚印轮廓,那是汗水长期浸泡留下的痕迹,像是一个黑色的幽灵。
而那只穿着灰袜子的脚,正无意识地蜷缩着脚趾。
那一刻,我离她只有不到一米。
一股极其微弱、但对我来说如同惊雷般的气息,钻进了我的鼻孔。
不是幻想中的酸臭,也不是令人作呕的异味。
而是一股热气。
一股湿漉漉的、带着体温的热气。
那是怎么形容呢?就像是夏天暴雨过后,从泥土里蒸腾起来的那种味道。带着一点点草腥气,一点点发酵的酸味,还有一种浓郁得化不开的甜。
那是少女特有的体香,混合了运动后的汗液,在封闭的鞋腔里酿造了一下午之后,终于重见天日。它有着惊人的穿透力,不像香水那样浮在表面,而是直接钻进你的毛孔,黏在你的肺泡上。
我的大脑在那一瞬间有些缺氧。
我慢慢蹲下来,手指触碰到了那支黑色的签字笔。
笔杆是温热的。甚至是有些潮湿的。
上面沾着她手心的汗水。
我握住那支笔,就像是握住了她的一根手指。
我并没有立刻站起来。我借着捡笔的动作,把头压得很低,鼻尖几乎贴到了地板上。
我在那个高度,屏住呼吸,然后极其克制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股从她脚底和鞋口散发出来的味道,瞬间充满了我的肺叶。
真好闻啊。
这就是活着的味道。
这就是乔一的味道。
我就像是一个即将渴死的旅人,在沙漠里遇到了一汪浑浊却甘甜的水。那味道顺着鼻腔直冲天灵盖,让我的脊椎骨都酥了一半,某种难以启齿的生理反应在瞬间被点燃。
但我必须克制。
我必须要把这头野兽关进笼子里。我是沈言,我是中文系的好学生,我不能在这里变成一个变态。
我咬了咬舌尖,用疼痛强迫自己清醒过来。
我迅速站起身,把笔递给她。
“没……没事。”我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的、有点书呆子气的男生,掩饰住眼底那近乎狂热的波动,“可能是低血糖,蹲久了有点晕。”
“哦,那你小心点,记得吃早饭。”
乔一接过笔。
在她手指碰到我的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一股电流。
她的手很热,指腹上有握拍磨出的茧子,粗糙而有力。
“谢了啊。”
她冲我摆摆手,那个动作随意而洒脱。然后她重新坐回位子上,继续和那本红宝书死磕。
她并没有把脚穿回鞋里。相反,她似乎觉得光脚踩在地板上那种冰凉的触感很舒服。她把右脚也脱了出来,两只穿着脏袜子的脚就这样大大方方地踩在地上,互相蹭了蹭。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一幕。
看着她脚踝上那根细细的青色血管。
看着袜子边缘那被勒出的一道浅浅的红印。
我的口袋里,那只刚才握过她笔的手,正死死地攥成拳头。指尖上,还残留着那支笔的温度,那是她手心的汗水。
我慢慢地走回自己的座位,拉开椅子坐下。
椅子的座面有些硬,硌得我很难受。但我没有调整姿势,而是保持着一种僵硬的坐姿,双腿在桌下紧紧并拢。那里传来的胀痛感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因为刚才那一瞬间的靠近和嗅闻,变得更加剧烈。布料摩擦着皮肤,每一次极微小的移动都是一种带着罪恶感的折磨。
但我没有动,更没有逃向厕所。
我重新翻开那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目光落在第42页那行密密麻麻的铅字上。
但我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我的右手——那只刚刚握过她笔的手,慢慢地抬了起来。
我假装推扶眼镜,手指极其自然地滑过鼻尖,然后停留在嘴唇上方。
我屏住呼吸,那是极其轻微的一吸。
很淡。
那是金属笔杆留下的铁锈味,混合着极其微弱的、几乎难以捕捉的咸湿气息。那是她手心汗水的味道,是她刚刚握着那支笔奋斗了一下午留下的体温。
这股味道像是一根看不见的线,瞬间将我和斜前方那个背影连接在了一起。
我看着乔一。
她依然保持着那个姿势,左脚的脚后跟踩在椅子的横杠上,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蹭着。那只脱了一半的AF1歪歪扭扭地躺在地上,像是个被遗弃的玩具。
过堂风又吹了进来,带着雨水的土腥味,但这股味道此刻在我的鼻腔里,已经完全被指尖那一抹若有若无的气息覆盖了。
我放下手,重新握住了书页。
这一次,我终于看清了书上的字,虽然我的心跳依然快得有些不正常。
窗外的雨还在下,淅淅沥沥地敲打着玻璃。图书馆里很安静,只有偶尔的翻书声和乔一那只笔旋转时发出的细微沙沙声。
我坐在阴影里,忍受着身体的胀痛,继续看着书。
只是每隔几分钟,我都会下意识地抬起手,用那根手指轻轻蹭过鼻尖。
仿佛那里还残留着整个夏天。
513295987发布于 2025-12-18 03:35
Re: 【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
写的好棒!喜欢!楼主请继续!女体育生臭脚,天堂!
猴面包🏆笔下封神发布于 2025-12-18 19:18
Re: 【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
大佬还是一如既往强!不过大佬好多文开头第一段都是湿热的气候啊
Ankh发布于 ,编辑于 2025-12-19 09:39
Re: 【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
第二章
隔天下午的阳光并没有比前一日的暴雨可爱多少。京州的太阳带着一种湿漉漉的毒辣,像是要把地面上残留的水分全部蒸发成滚烫的蒸汽。
羽毛球馆里更是像一个巨大的、密封的高压锅。
数十双专业球鞋在地胶上急停、摩擦,发出那种尖锐得像是指甲刮过黑板的“吱吱”声。这种声音对于外人来说是噪音,但对于这里的人来说,是战斗的号角。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味道——橡胶受热后的焦糊味、止汗喷雾的薄荷味,以及最核心的、几十具年轻肉体剧烈运动后散发出的汗馊味。
我坐在看台最角落的蓝色塑料椅上,膝盖上摊着一本没怎么翻过的笔记本。
这里是我的另一个据点。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出现在体育学院的训练馆里其实有些突兀,但我总能找到理由——比如“来这里蹭空调写稿子”,或者“帮室友送水”。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惯了角落里有这么一个安静的、带着黑框眼镜的背景板。
我的视线穿过球网的方格,锁定在三号场地。
乔一正在打对抗赛。
她今天穿了一件亮黄色的无袖速干衣,下身是黑色的短裤。随着她起跳扣杀的动作,紧实的背部肌肉线条一览无余,像是一只展翅的鹰。汗水顺着她的发梢甩出去,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晶莹的弧线,然后重重地砸在地板上。
但我看得出来,她今天的状态不对。
她的步伐很沉。每一次上网扑球后的制动,她的眉头都会极其细微地皱一下。那不是体力透支的表现,而是疼痛。
视线下移。
她脚上穿的不是昨天那双旧的AF1,而是一双崭新的、白色的尤尼克斯专业羽毛球鞋。
那是赞助商刚发下来的新装备。白色的鞋面上印着亮银色的Logo,在灯光下反着光,看起来专业、昂贵、气派。但对于一双还没被驯服的脚来说,这种硬质皮革包裹的新鞋,往往意味着刑具。
“嘭!”
乔一一个反手挑球,球挂网了。
她落地时踉跄了一下,右脚着地,左脚不敢吃力地悬空了一瞬。
“暂停!”
她冲着对面的搭档摆了摆手,脸上带着压抑的烦躁,“不行了,歇会儿。”
她一瘸一拐地走到场边。没有去休息区的大长椅,而是径直走向了我所在的这个角落。因为这里离她的球包最近,也离我最近。
“水。”
她还没坐下,手已经伸到了我面前。
我拧开早就准备好的一瓶电解质饮料,递给她。瓶身外面裹着一层细密的水珠,那是从冰柜里拿出来后遇热凝结的冷凝水。
“谢了。”
乔一接过水,仰头灌了一大口。喉咙吞咽的动作带动着锁骨上的汗水滑落,滴进衣领深处。她的一口气喝掉了半瓶,然后长长地呼出一口热气。
“怎么了?”我明知故问,视线落在她的左脚上。
“脚废了。”
乔一骂了一句脏话,一屁股坐在我旁边的地上。她完全不顾及形象,或者说,在我面前她从来不需要顾及形象。
“这新鞋太硬了,跟穿了两块砖头似的。后跟那个内衬磨得我皮都快掉了。”
她一边抱怨,一边粗鲁地去解鞋带。
新鞋的包裹性太好了,脱起来很费劲。她用力蹬了两下,才把那只左脚从鞋里拔出来。
随着鞋子的脱离,一股浓烈的、带着热度的味道扑面而来。
那是不同于昨天在图书馆那种发酵了一整天的酸甜味。这是一种更具攻击性的味道——那是新鲜的、刚刚经过高强度运动激发的汗味,混合着新鞋特有的胶水味和皮革味。它热辣辣的,像是一股刚出炉的蒸汽。
我不动声色地吸了一口气,压抑住心底那股熟悉的颤栗。
乔一一把扯掉脚上的短袜。
白色的专业毛巾袜,厚实吸汗,此刻已经完全湿透了,变成了灰黄色。
随着袜子的剥离,伤口暴露在空气中。
在她的脚后跟位置,那块原本长着茧子的皮肤被磨破了。表皮被掀开,露出里面粉红色的、鲜嫩的真皮层,周围还有一圈被磨得透明的水泡。鲜红的血丝从伤口渗出来,混合着汗水,看起来触目惊心。
“破了?”我蹲下来,视线盯着那块血肉模糊的地方。
“嗯,疼死我了。”乔一吸着冷气,用手扇着风,试图给伤口降温,“张哲那个傻逼,非说这鞋支撑性好,让我赶紧适应。适应个屁,再穿半小时我跟腱都得磨断了。”
她嘴里骂着张哲,但语气里并没有真正的恶意,更多的是一种对“自己人”的吐槽。
“别动。”
我说。
我转身打开我的背包。
其实我并不需要找,因为那些东西就放在最外层的侧兜里。
一包医用棉签,一瓶凡士林,还有一个我是特意去便利店买的、此刻还在冒着冷气的冰袋。
我没有买创可贴。因为对于这种位置的运动损伤,创可贴一出汗就会掉,而且会卷边,反而会加重摩擦。
“把腿抬起来。”
我从包里拿出一条干净的毛巾,铺在塑料椅上。
“你要干嘛?”乔一看着我手里的冰袋,愣了一下,“你随身带这玩意儿干嘛?”
“刚才来的路上买可乐顺便买的,本来想自己冰敷一下膝盖。”我撒谎的时候面不改色,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先冰敷。消肿止痛,收缩血管。如果不先降温,你这脚脖子明天得肿成猪蹄。”
乔一犹豫了一下。
这里是训练馆,周围还有其他人。虽然大家都在忙着训练,但这么亲密的动作……
“快点,冰化了就没用了。”我催促道,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专业感。
乔一看了看自己红肿的脚后跟,又看了看我平静的脸。
“行吧。轻点啊。”
她不再矫情,转过身,把左腿抬起来,架在了铺着毛巾的椅子上。
那个高度,正好在我的胸口位置。
她的脚很烫。那是充血状态下的高温。脚掌因为刚才的跑动而微微发红,青色的血管在脚背上凸起,随着心跳一突一突的。
我撕开冰袋的包装。
并没有直接敷上去,那样会冻伤皮肤。我用毛巾把冰袋裹了一层,然后轻轻地贴在了她的跟腱和脚踝处。
“嘶——!”
乔一猛地缩了一下腿,脚趾瞬间扣紧,“好冰!”
“忍着。”
我伸出一只手,按住了她的脚背,制止了她的退缩,“冷热交替才能刺激循环。一开始是冰,过一会儿就舒服了。”
我的手掌覆盖在她的脚背上。
那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肌肤之亲。
她的皮肤滑腻湿润,上面全是汗水。掌心传来的触感是温热的、坚韧的。我能感觉到她骨骼的硬度,也能感觉到她皮肤下血液的流动。
那种触感顺着我的指尖传导回来,像是一把火,瞬间点燃了我的神经末梢。
我必须用极大的毅力,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手指不要去摩挲,不要去揉捏。
冰块在高温的皮肤上迅速融化。
冰水混合物顺着毛巾的缝隙渗出来,滴落在她的脚踝上,然后顺着足弓优美的弧线流下来,滴在地板上。
那种画面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
晶莹剔透的水珠划过她有些粗糙、甚至带着灰尘的皮肤,冲刷出一道道干净的痕迹。像是雨水冲刷着干涸的河床。
乔一慢慢适应了这种温度。紧绷的小腿肌肉松弛下来,她靠在椅背上,发出一声舒服的叹息。
“呼……活过来了。”她闭着眼睛说,“沈言,你这招还真管用。”
“还没完。”
我拿开已经化了一半的冰袋。
她的脚后跟已经被冻得有些发红,温度降了下来,痛感也被麻痹了不少。
我拧开凡士林的盖子。
那是无色无味的矿物脂,晶莹剔透,像是凝固的油脂。
“冰敷完,要涂这个。”
我用食指挖了一大块膏体。
“凡士林能减少摩擦,还能封闭伤口,隔绝汗水。比红花油那种又臭又辣的东西适合这种开放性伤口。”
我低下头。
那一刻,我离她的脚只有不到十公分的距离。
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她脚后跟上那些细小的纹路,看到伤口处翻卷的死皮。
那股混合着汗水和冰水的味道,直冲我的鼻腔。
我屏住呼吸,把手指伸了过去。
微凉的、滑腻的膏体,涂抹在那块滚烫的伤口上。
我的指尖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了她伤口周围完好的皮肤。
滑。
那是凡士林特有的质感。
我在她的脚后跟上轻轻打着圈,把膏体抹匀,形成一层厚厚的保护膜。
我的动作很慢,很细致。
与其说是在涂药,不如说是在进行某种神圣的仪式。
指尖感受着她皮肤的粗糙与细腻。每一次转动,都像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
“痒……”
乔一缩了缩脚,声音有些含混,“沈言,你涂个药怎么跟绣花似的。”
“涂匀了才有用。”
我声音沙哑,头也没抬,贪婪地享受着这合法的触碰时间。
“哟,这是干嘛呢?”
一个清脆却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突然在头顶响起。
我的手抖了一下,迅速收回来。
乔一也睁开了眼。
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林夏。
她是乔一的女双搭档,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手里拎着一只巨大的水壶。她正居高临下地看着蹲在地上的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让我心惊肉跳的审视。
“林夏,你也歇了?”乔一倒是很自然,甚至没把腿收回来。
“累了,喝口水。”林夏拧开水壶,咕咚咕咚灌了几口,然后用手背擦了擦嘴,目光依然粘在我身上,“我说沈大才子,你这业务范围挺广啊。我看张哲都没你伺候得这么周到。”
这句话像是一根针,精准地扎破了我和乔一之间那种模糊的氛围。
“正好带了药,顺手。”我站起来,抽出一张湿纸巾擦手。
手指上还残留着凡士林的油腻,以及乔一的体温。我擦得很慢,不想把那种感觉擦掉。
“是吗?”林夏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那你包里这冰袋还挺智能的,正好在乔一脚疼的时候还没化。”
我没说话。多说多错。林夏太敏锐了,她那种动物般的直觉总是能嗅出不对劲。
“哎呀你别阴阳怪气的。”乔一大大咧咧地帮我解围,把脚收了回来,试着踩了踩地,“沈言是我哥们儿,人家细心不行啊?哪像你们这帮大老粗。”
“行行行,你哥们儿。”林夏翻了个白眼,但并没有深究,“脚怎么样?下一局还能上吗?”
“应该行。”乔一穿上那只被汗水浸透的袜子,又皱着眉把脚塞进那只该死的尤尼克斯新鞋里,“有这层油润滑着,没刚才那么磨了。”
她站起来,用力跺了跺脚。
“谢了啊,沈言。”她冲我扬了扬下巴,“回头请你吃饭。”
“去吧。”我点点头。
乔一拿起球拍,重新跑回了场地。
林夏没有马上走。
她站在原地,看着乔一的背影,又转头看了看我。
“沈言。”她突然叫了我的名字。
“嗯?”
“乔一这人虽然大大咧咧的,但她不傻。”林夏看着我,眼神变得有些意味深长,“有些好,给多了就是负担。你自己悠着点。”
说完,她也没等我回答,转身跑向了球场。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们的背影。
林夏的话像是一记警钟,在嘈杂的球馆里回荡。
但我并不在乎。
或者是说,我已经停不下来了。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那张刚刚擦过手的湿纸巾。
上面沾着凡士林的油渍,还有一点点微不可见的、从乔一脚后跟上蹭下来的死皮。
还有那块裹过冰袋的毛巾。
此时它正湿漉漉地躺在椅子上,吸饱了融化的冰水和乔一脚上的汗水。
我左右看了看。
没人注意角落。
我拿起那块毛巾,并没有把它还给乔一,也没有把它扔进垃圾桶。
我把它叠好,哪怕它湿冷、沉重,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汗味。
我把它塞进了我背包的最深处,那个专门用来放“战利品”的夹层里。
然后,我重新坐下来。
手指放在鼻尖下。
那股凡士林的矿物味混合着少女脚踝处的咸湿气息,在我的指尖上形成了一层看不见的油膜。
这是我的标记。
也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
远处的球场上,乔一高高跃起,一记漂亮的扣杀。
“好球!”
欢呼声四起。
她在光里。
而我在阴影里,握着那块湿透的毛巾,感觉自己正在一点点融化,渗进这块看不见的地板缝隙里。
隔天下午的阳光并没有比前一日的暴雨可爱多少。京州的太阳带着一种湿漉漉的毒辣,像是要把地面上残留的水分全部蒸发成滚烫的蒸汽。
羽毛球馆里更是像一个巨大的、密封的高压锅。
数十双专业球鞋在地胶上急停、摩擦,发出那种尖锐得像是指甲刮过黑板的“吱吱”声。这种声音对于外人来说是噪音,但对于这里的人来说,是战斗的号角。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味道——橡胶受热后的焦糊味、止汗喷雾的薄荷味,以及最核心的、几十具年轻肉体剧烈运动后散发出的汗馊味。
我坐在看台最角落的蓝色塑料椅上,膝盖上摊着一本没怎么翻过的笔记本。
这里是我的另一个据点。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出现在体育学院的训练馆里其实有些突兀,但我总能找到理由——比如“来这里蹭空调写稿子”,或者“帮室友送水”。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惯了角落里有这么一个安静的、带着黑框眼镜的背景板。
我的视线穿过球网的方格,锁定在三号场地。
乔一正在打对抗赛。
她今天穿了一件亮黄色的无袖速干衣,下身是黑色的短裤。随着她起跳扣杀的动作,紧实的背部肌肉线条一览无余,像是一只展翅的鹰。汗水顺着她的发梢甩出去,在空中划出一道道晶莹的弧线,然后重重地砸在地板上。
但我看得出来,她今天的状态不对。
她的步伐很沉。每一次上网扑球后的制动,她的眉头都会极其细微地皱一下。那不是体力透支的表现,而是疼痛。
视线下移。
她脚上穿的不是昨天那双旧的AF1,而是一双崭新的、白色的尤尼克斯专业羽毛球鞋。
那是赞助商刚发下来的新装备。白色的鞋面上印着亮银色的Logo,在灯光下反着光,看起来专业、昂贵、气派。但对于一双还没被驯服的脚来说,这种硬质皮革包裹的新鞋,往往意味着刑具。
“嘭!”
乔一一个反手挑球,球挂网了。
她落地时踉跄了一下,右脚着地,左脚不敢吃力地悬空了一瞬。
“暂停!”
她冲着对面的搭档摆了摆手,脸上带着压抑的烦躁,“不行了,歇会儿。”
她一瘸一拐地走到场边。没有去休息区的大长椅,而是径直走向了我所在的这个角落。因为这里离她的球包最近,也离我最近。
“水。”
她还没坐下,手已经伸到了我面前。
我拧开早就准备好的一瓶电解质饮料,递给她。瓶身外面裹着一层细密的水珠,那是从冰柜里拿出来后遇热凝结的冷凝水。
“谢了。”
乔一接过水,仰头灌了一大口。喉咙吞咽的动作带动着锁骨上的汗水滑落,滴进衣领深处。她的一口气喝掉了半瓶,然后长长地呼出一口热气。
“怎么了?”我明知故问,视线落在她的左脚上。
“脚废了。”
乔一骂了一句脏话,一屁股坐在我旁边的地上。她完全不顾及形象,或者说,在我面前她从来不需要顾及形象。
“这新鞋太硬了,跟穿了两块砖头似的。后跟那个内衬磨得我皮都快掉了。”
她一边抱怨,一边粗鲁地去解鞋带。
新鞋的包裹性太好了,脱起来很费劲。她用力蹬了两下,才把那只左脚从鞋里拔出来。
随着鞋子的脱离,一股浓烈的、带着热度的味道扑面而来。
那是不同于昨天在图书馆那种发酵了一整天的酸甜味。这是一种更具攻击性的味道——那是新鲜的、刚刚经过高强度运动激发的汗味,混合着新鞋特有的胶水味和皮革味。它热辣辣的,像是一股刚出炉的蒸汽。
我不动声色地吸了一口气,压抑住心底那股熟悉的颤栗。
乔一一把扯掉脚上的短袜。
白色的专业毛巾袜,厚实吸汗,此刻已经完全湿透了,变成了灰黄色。
随着袜子的剥离,伤口暴露在空气中。
在她的脚后跟位置,那块原本长着茧子的皮肤被磨破了。表皮被掀开,露出里面粉红色的、鲜嫩的真皮层,周围还有一圈被磨得透明的水泡。鲜红的血丝从伤口渗出来,混合着汗水,看起来触目惊心。
“破了?”我蹲下来,视线盯着那块血肉模糊的地方。
“嗯,疼死我了。”乔一吸着冷气,用手扇着风,试图给伤口降温,“张哲那个傻逼,非说这鞋支撑性好,让我赶紧适应。适应个屁,再穿半小时我跟腱都得磨断了。”
她嘴里骂着张哲,但语气里并没有真正的恶意,更多的是一种对“自己人”的吐槽。
“别动。”
我说。
我转身打开我的背包。
其实我并不需要找,因为那些东西就放在最外层的侧兜里。
一包医用棉签,一瓶凡士林,还有一个我是特意去便利店买的、此刻还在冒着冷气的冰袋。
我没有买创可贴。因为对于这种位置的运动损伤,创可贴一出汗就会掉,而且会卷边,反而会加重摩擦。
“把腿抬起来。”
我从包里拿出一条干净的毛巾,铺在塑料椅上。
“你要干嘛?”乔一看着我手里的冰袋,愣了一下,“你随身带这玩意儿干嘛?”
“刚才来的路上买可乐顺便买的,本来想自己冰敷一下膝盖。”我撒谎的时候面不改色,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先冰敷。消肿止痛,收缩血管。如果不先降温,你这脚脖子明天得肿成猪蹄。”
乔一犹豫了一下。
这里是训练馆,周围还有其他人。虽然大家都在忙着训练,但这么亲密的动作……
“快点,冰化了就没用了。”我催促道,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专业感。
乔一看了看自己红肿的脚后跟,又看了看我平静的脸。
“行吧。轻点啊。”
她不再矫情,转过身,把左腿抬起来,架在了铺着毛巾的椅子上。
那个高度,正好在我的胸口位置。
她的脚很烫。那是充血状态下的高温。脚掌因为刚才的跑动而微微发红,青色的血管在脚背上凸起,随着心跳一突一突的。
我撕开冰袋的包装。
并没有直接敷上去,那样会冻伤皮肤。我用毛巾把冰袋裹了一层,然后轻轻地贴在了她的跟腱和脚踝处。
“嘶——!”
乔一猛地缩了一下腿,脚趾瞬间扣紧,“好冰!”
“忍着。”
我伸出一只手,按住了她的脚背,制止了她的退缩,“冷热交替才能刺激循环。一开始是冰,过一会儿就舒服了。”
我的手掌覆盖在她的脚背上。
那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肌肤之亲。
她的皮肤滑腻湿润,上面全是汗水。掌心传来的触感是温热的、坚韧的。我能感觉到她骨骼的硬度,也能感觉到她皮肤下血液的流动。
那种触感顺着我的指尖传导回来,像是一把火,瞬间点燃了我的神经末梢。
我必须用极大的毅力,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手指不要去摩挲,不要去揉捏。
冰块在高温的皮肤上迅速融化。
冰水混合物顺着毛巾的缝隙渗出来,滴落在她的脚踝上,然后顺着足弓优美的弧线流下来,滴在地板上。
那种画面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
晶莹剔透的水珠划过她有些粗糙、甚至带着灰尘的皮肤,冲刷出一道道干净的痕迹。像是雨水冲刷着干涸的河床。
乔一慢慢适应了这种温度。紧绷的小腿肌肉松弛下来,她靠在椅背上,发出一声舒服的叹息。
“呼……活过来了。”她闭着眼睛说,“沈言,你这招还真管用。”
“还没完。”
我拿开已经化了一半的冰袋。
她的脚后跟已经被冻得有些发红,温度降了下来,痛感也被麻痹了不少。
我拧开凡士林的盖子。
那是无色无味的矿物脂,晶莹剔透,像是凝固的油脂。
“冰敷完,要涂这个。”
我用食指挖了一大块膏体。
“凡士林能减少摩擦,还能封闭伤口,隔绝汗水。比红花油那种又臭又辣的东西适合这种开放性伤口。”
我低下头。
那一刻,我离她的脚只有不到十公分的距离。
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她脚后跟上那些细小的纹路,看到伤口处翻卷的死皮。
那股混合着汗水和冰水的味道,直冲我的鼻腔。
我屏住呼吸,把手指伸了过去。
微凉的、滑腻的膏体,涂抹在那块滚烫的伤口上。
我的指尖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了她伤口周围完好的皮肤。
滑。
那是凡士林特有的质感。
我在她的脚后跟上轻轻打着圈,把膏体抹匀,形成一层厚厚的保护膜。
我的动作很慢,很细致。
与其说是在涂药,不如说是在进行某种神圣的仪式。
指尖感受着她皮肤的粗糙与细腻。每一次转动,都像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
“痒……”
乔一缩了缩脚,声音有些含混,“沈言,你涂个药怎么跟绣花似的。”
“涂匀了才有用。”
我声音沙哑,头也没抬,贪婪地享受着这合法的触碰时间。
“哟,这是干嘛呢?”
一个清脆却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突然在头顶响起。
我的手抖了一下,迅速收回来。
乔一也睁开了眼。
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林夏。
她是乔一的女双搭档,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手里拎着一只巨大的水壶。她正居高临下地看着蹲在地上的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让我心惊肉跳的审视。
“林夏,你也歇了?”乔一倒是很自然,甚至没把腿收回来。
“累了,喝口水。”林夏拧开水壶,咕咚咕咚灌了几口,然后用手背擦了擦嘴,目光依然粘在我身上,“我说沈大才子,你这业务范围挺广啊。我看张哲都没你伺候得这么周到。”
这句话像是一根针,精准地扎破了我和乔一之间那种模糊的氛围。
“正好带了药,顺手。”我站起来,抽出一张湿纸巾擦手。
手指上还残留着凡士林的油腻,以及乔一的体温。我擦得很慢,不想把那种感觉擦掉。
“是吗?”林夏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那你包里这冰袋还挺智能的,正好在乔一脚疼的时候还没化。”
我没说话。多说多错。林夏太敏锐了,她那种动物般的直觉总是能嗅出不对劲。
“哎呀你别阴阳怪气的。”乔一大大咧咧地帮我解围,把脚收了回来,试着踩了踩地,“沈言是我哥们儿,人家细心不行啊?哪像你们这帮大老粗。”
“行行行,你哥们儿。”林夏翻了个白眼,但并没有深究,“脚怎么样?下一局还能上吗?”
“应该行。”乔一穿上那只被汗水浸透的袜子,又皱着眉把脚塞进那只该死的尤尼克斯新鞋里,“有这层油润滑着,没刚才那么磨了。”
她站起来,用力跺了跺脚。
“谢了啊,沈言。”她冲我扬了扬下巴,“回头请你吃饭。”
“去吧。”我点点头。
乔一拿起球拍,重新跑回了场地。
林夏没有马上走。
她站在原地,看着乔一的背影,又转头看了看我。
“沈言。”她突然叫了我的名字。
“嗯?”
“乔一这人虽然大大咧咧的,但她不傻。”林夏看着我,眼神变得有些意味深长,“有些好,给多了就是负担。你自己悠着点。”
说完,她也没等我回答,转身跑向了球场。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们的背影。
林夏的话像是一记警钟,在嘈杂的球馆里回荡。
但我并不在乎。
或者是说,我已经停不下来了。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那张刚刚擦过手的湿纸巾。
上面沾着凡士林的油渍,还有一点点微不可见的、从乔一脚后跟上蹭下来的死皮。
还有那块裹过冰袋的毛巾。
此时它正湿漉漉地躺在椅子上,吸饱了融化的冰水和乔一脚上的汗水。
我左右看了看。
没人注意角落。
我拿起那块毛巾,并没有把它还给乔一,也没有把它扔进垃圾桶。
我把它叠好,哪怕它湿冷、沉重,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汗味。
我把它塞进了我背包的最深处,那个专门用来放“战利品”的夹层里。
然后,我重新坐下来。
手指放在鼻尖下。
那股凡士林的矿物味混合着少女脚踝处的咸湿气息,在我的指尖上形成了一层看不见的油膜。
这是我的标记。
也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
远处的球场上,乔一高高跃起,一记漂亮的扣杀。
“好球!”
欢呼声四起。
她在光里。
而我在阴影里,握着那块湿透的毛巾,感觉自己正在一点点融化,渗进这块看不见的地板缝隙里。
chromaso发布于 2025-12-19 07:41
Re: 【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
上面这章好像重复了一遍(
Ankh发布于 2025-12-19 22:48
Re: 【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
第三章
离开羽毛球馆的时候,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路灯在潮湿的雾气中晕开一团团昏黄的光晕,像是浮在浑水里的油渍。我背着那个装着冰袋毛巾的包,感觉背脊发烫。那块毛巾虽然被裹在最深层的夹层里,但我总觉得它正在透过层层布料,向我的后背传递着某种只有我能感知的温度。
我没有直接回宿舍。现在的我,就像是一个刚偷吃了禁果的贼,还没办法立刻回到那种充满男生汗臭味和游戏喊叫声的集体生活中去。我需要一个地方,一个足够安静、足够阴暗的地方,来慢慢消化今天下午那种过载的触觉记忆。
我拐了个弯,走向了校园最北角的那栋老文科楼。
这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红砖楼,是京州大学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墙体上爬满了墨绿色的爬山虎,在这个雨季里,那些植物吸饱了水分,肥厚得像是无数只绿色的手掌,将整栋楼紧紧包裹。楼道里没有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微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木头腐朽味,混合着灰尘和某种不知名霉菌的气息。
这里是我的另一个世界。
推开三楼尽头那扇掉漆的木门,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
那是一股女式烟草混合着陈年旧书的味道。
“来了?”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窗边的阴影里传出来。
苏青正坐在那里。她没有开灯,整个人陷在一张破旧的单人沙发里。那是以前从教职工休息室淘汰下来的,弹簧都坏了,坐上去会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呀声。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真丝吊带长裙,外面随意地罩着一件男款的大号白衬衫。那衬衫太大了,袖口卷了好几道,下摆垂下来遮住了大腿,露出一双瘦削苍白的小腿。她的脚上没穿鞋,光着脚踩在满是烟灰的木地板上,脚趾甲涂成了深沉的酒红色,像是凝固的血。
“学姐。”
我随手关上门,把那个沉甸甸的背包放在门口的桌子上。
“怎么这副德行?”苏青吐出一口烟圈,借着窗外的月光打量了我一眼,“像只刚从水沟里爬出来的落水狗。”
“外面湿度太大。”我避开她的视线,走到书架前,假装翻找着上一期的社刊,“感觉都要长蘑菇了。”
苏青是文学院大四的学姐,也是我们这个半死不活的“流浪者文学社”的社长。她是个怪人。长得很美,是那种带有攻击性的、颓废的美,像是一朵开在坟墓边的罂粟。
在这个文学社里,我们不谈风花雪月,只谈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
“你身上有味道。”
苏青突然说。
我翻书的手顿了一下,心脏猛地缩紧。
“什么味道?”我故作镇定,但手指却下意识地抓紧了书脊。
“不是你平时的那种书呆子味。”苏青夹着烟的手指在空中画了个圈,然后指了指我的背包,“也不是雨水的味道。是一股……很热的、很躁动的味道。像是那种刚跑完五公里的动物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
她吸了吸鼻子,眼神变得玩味起来,“还有一股凡士林的味道。你去体育馆了?”
我沉默了。在苏青面前撒谎是没有意义的。她就像是一个拥有透视眼的巫师,总是能轻易地剥开我那层伪装的好学生外皮。
“嗯。”我承认道,“去帮忙送点东西。”
“送给那个打羽毛球的小学妹?”苏青轻笑了一声,那个笑声里带着一丝早已洞悉一切的嘲弄,“叫什么来着?乔一?”
“是。”
“还没死心呢?”苏青把烟头按灭在窗台上那个堆满了烟蒂的玻璃罐头瓶里,然后又从那个精致的烟盒里抽出一根,“沈言,你这人挺有意思。明明是个喜阴植物,偏偏喜欢那种光照强度最高的地方。你不怕被晒死?”
“不觉得。”我走到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看着她在黑暗中忽明忽暗的烟头,“正是因为刺眼,才想靠近。”
“靠近之后呢?”苏青盯着我,“摘下来?带回家?插在你的花瓶里?”
我摇了摇头。
“我养不活。”
我说得很平静。这不是自卑,而是一种经过精密计算后的现实认知。
“她那种人,需要很大的空间,很贵的肥料,还有……很多的关注。”我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因为常年握笔而有些苍白的手,“我这里只有阴影。如果把她摘下来,不出三天她就会枯萎。”
“所以你就打算这么看着?”苏青挑了挑眉,“做个偷窥狂?”
“不是偷窥。”我纠正道,尽管底气并不足,“是……守护。”
“噗——”
苏青没忍住,笑出了声。烟灰随着她的动作抖落在大腿上,她毫不在意地伸手拂去。
“守护?沈言,你能不能别把那个词用得这么恶心。”她把烟递到嘴边,深吸了一口,“守护是骑士干的事。骑士是要骑着马冲锋的,是要流血的。”
她站起来,光着脚走到我面前。那股浓烈的烟草味混合着她身上某种冷冽的香水味,直冲我的鼻腔。
“而你不是骑士。”她低下头,看着我的眼睛,“你的眼神里没有那种东西。你的眼神里只有贪婪。你想占有她,但你知道自己配不上,所以你退而求其次。”
她伸出一根手指,戳了戳我放在桌子上的那个背包。
“这里面装着什么?”
我下意识地伸手挡了一下。
“没什么。一些杂物。”
“杂物会让你这么紧张?”苏青冷笑了一声,“让我猜猜。是她喝剩的水瓶?还是擦过汗的纸巾?”
我没说话。
“沈言。”苏青的声音低了下来,带着一种诱导般的磁性,“承认吧。你根本不想当什么骑士。你也不想把她摘下来。你只是喜欢跟在她后面,捡她不要的东西。”
我不置可否。
但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烫。那种被剥光了游街的羞耻感,混合着一种被人理解的快感,在身体里交织。
“那又怎么样?”我声音沙哑,“这不犯法。”
“是不犯法。”苏青转过身,走回窗边,“但这很……下流。不过,也很美。”
她随手从沙发旁边的地上拿起一本书,扔给我。
那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第29首,《腐尸》。”她说,“念给我听。”
我接过那本已经被翻得起毛边的书。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翻到了那一页。
这首诗我很熟。每一个字都像是刻在我的脑子里。
我清了清嗓子,开始朗读。
“回忆吧,我的爱人,我们见到的东西,
在那温和而明媚的夏日清晨:
在小路拐弯处,一具丑恶的腐尸,
横卧在铺满石子的床上……”
我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
“它的双腿向上翘起,像个淫荡的女人,
热辣辣地喷发着毒气,
它随随便便地张开充满臭气的肚皮,
把无耻和这种调子连在一起。”
当我读到这里时,苏青突然转过头。
“停。”
她看着我,“你读这首诗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愣了一下。
“在想尸体。”我撒谎。
“骗子。”苏青毫不留情地拆穿我,“你在想那个打羽毛球的女孩。你在想她刚脱下来的鞋,想她满是汗水的脚,想那些别人觉得脏、但你觉得香的东西。”
她走过来,抽走了我手里的书。
“波德莱尔是个天才。他告诉我们,美不仅仅存在于鲜花里,也存在于腐烂里。甚至,腐烂才是更本质的生命力。”
她把书扔回沙发上,整个人靠在窗台上,背对着月光,脸庞隐没在阴影里。
“沈言,你知道为什么植物的根都要往地下钻吗?”
我看着她。
“因为上面太吵了。”苏青说,“阳光太烈,风太大,所有人都在争奇斗艳。只有地下是安静的。那里又黑,又湿,全是烂掉的叶子和动物的尸体。”
她停顿了一下,吐出最后一口烟雾。
“但只有在那里,你才能真正抱住她。在上面,你只能看着她。但在下面,你可以把她包裹起来。哪怕只是包裹住她的根。”
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包裹住她的根。
我想起了今天下午,我把凡士林涂在她脚后跟上的那一刻。我想起了那块此刻正躺在我包里的、吸饱了汗水的毛巾。
那种感觉……不就是包裹吗?
我不需要她知道我在那里。我不需要她对我感恩戴德。
我只需要在那里。
在她的脚下。
“懂了吗?”苏青把烟头弹向窗外。红色的火星在夜色中划出一道弧线,然后消失在茫茫的雨幕中。
“懂了。”我说。
“懂了就滚吧。”苏青挥了挥手,“你那一身的凡士林味儿,还有那种发情的味道,熏得我头疼。”
我站起来。
拿起那个沉甸甸的背包。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停下了脚步。
“学姐。”
“又怎么了?”
“这本书。”我指了指沙发上的《恶之花》,“虽然我读过很多遍,但我从来没买过。”
“想说什么?”
“我觉得……我可能活在那本书里。”
苏青没有回头。
她在黑暗中沉默了几秒,然后发出了一声极轻的叹息。
“那祝你在里面玩得开心。别把自己玩死了就行。”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推开那扇掉漆的木门,走出了那个充满了烟草味和霉味的房间。
随着门在我身后“吱呀”一声关上,苏青的世界被隔绝在了身后。楼道里没有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惨白月光,把台阶照得像是一排排森森的白骨。
我顺着楼梯往下走。
这栋老楼很空,脚步声在回廊里显得格外清晰。走到二楼转角风口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抬起手臂,闻了闻袖口。
那里沾染了苏青房间里浓烈的女式烟草味,但在那层辛辣之下,还顽固地残留着一股淡淡的、油腻的矿物脂味。那是我的味道,也是乔一的味道。
走出文科楼的时候,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被雨水浸泡后的腥气。路边的花坛里,那些白天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栀子花,被这场暴雨摧残得七零八落。
我停下脚步。
在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一朵被打落的栀子花正躺在泥水里。
它原本洁白的花瓣已经沾满了黑色的淤泥,边缘开始氧化发黄,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褐色,像是一张被揉皱了的废纸。
我弯下腰,鬼使神差地伸出手。
指尖触碰到花瓣的那一刻,传来一种湿冷、软烂的触感。
它已经脏了。散发着一股混合了浓烈甜香和腐败泥土的气息。
但我没有把它扔回花坛。
我把它捏在手心里,感受着那种黏腻的触感。
我拉开外套的口袋,把这朵沾着泥的残花放了进去。
它和那个装着毛巾的背包,只隔着一层薄薄的布料。
口袋沉甸甸的。
我拿出手机,按亮屏幕。
21:45。
微信置顶的头像依然安静,没有任何红点。
我盯着那个空白的界面看了一会儿,然后熄灭屏幕,把手机塞回了另一个口袋。
远处宿舍区的灯光把夜空映得发红,隐约能听到人群的喧嚣。
我紧了紧背包的带子,低下头,像个怀揣着赃物的窃贼,快步走进了那片浓重的夜色里。
雨后的风很凉。
但我口袋里的那朵烂花,正在慢慢变热。
离开羽毛球馆的时候,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路灯在潮湿的雾气中晕开一团团昏黄的光晕,像是浮在浑水里的油渍。我背着那个装着冰袋毛巾的包,感觉背脊发烫。那块毛巾虽然被裹在最深层的夹层里,但我总觉得它正在透过层层布料,向我的后背传递着某种只有我能感知的温度。
我没有直接回宿舍。现在的我,就像是一个刚偷吃了禁果的贼,还没办法立刻回到那种充满男生汗臭味和游戏喊叫声的集体生活中去。我需要一个地方,一个足够安静、足够阴暗的地方,来慢慢消化今天下午那种过载的触觉记忆。
我拐了个弯,走向了校园最北角的那栋老文科楼。
这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红砖楼,是京州大学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墙体上爬满了墨绿色的爬山虎,在这个雨季里,那些植物吸饱了水分,肥厚得像是无数只绿色的手掌,将整栋楼紧紧包裹。楼道里没有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微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木头腐朽味,混合着灰尘和某种不知名霉菌的气息。
这里是我的另一个世界。
推开三楼尽头那扇掉漆的木门,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
那是一股女式烟草混合着陈年旧书的味道。
“来了?”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窗边的阴影里传出来。
苏青正坐在那里。她没有开灯,整个人陷在一张破旧的单人沙发里。那是以前从教职工休息室淘汰下来的,弹簧都坏了,坐上去会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呀声。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真丝吊带长裙,外面随意地罩着一件男款的大号白衬衫。那衬衫太大了,袖口卷了好几道,下摆垂下来遮住了大腿,露出一双瘦削苍白的小腿。她的脚上没穿鞋,光着脚踩在满是烟灰的木地板上,脚趾甲涂成了深沉的酒红色,像是凝固的血。
“学姐。”
我随手关上门,把那个沉甸甸的背包放在门口的桌子上。
“怎么这副德行?”苏青吐出一口烟圈,借着窗外的月光打量了我一眼,“像只刚从水沟里爬出来的落水狗。”
“外面湿度太大。”我避开她的视线,走到书架前,假装翻找着上一期的社刊,“感觉都要长蘑菇了。”
苏青是文学院大四的学姐,也是我们这个半死不活的“流浪者文学社”的社长。她是个怪人。长得很美,是那种带有攻击性的、颓废的美,像是一朵开在坟墓边的罂粟。
在这个文学社里,我们不谈风花雪月,只谈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
“你身上有味道。”
苏青突然说。
我翻书的手顿了一下,心脏猛地缩紧。
“什么味道?”我故作镇定,但手指却下意识地抓紧了书脊。
“不是你平时的那种书呆子味。”苏青夹着烟的手指在空中画了个圈,然后指了指我的背包,“也不是雨水的味道。是一股……很热的、很躁动的味道。像是那种刚跑完五公里的动物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
她吸了吸鼻子,眼神变得玩味起来,“还有一股凡士林的味道。你去体育馆了?”
我沉默了。在苏青面前撒谎是没有意义的。她就像是一个拥有透视眼的巫师,总是能轻易地剥开我那层伪装的好学生外皮。
“嗯。”我承认道,“去帮忙送点东西。”
“送给那个打羽毛球的小学妹?”苏青轻笑了一声,那个笑声里带着一丝早已洞悉一切的嘲弄,“叫什么来着?乔一?”
“是。”
“还没死心呢?”苏青把烟头按灭在窗台上那个堆满了烟蒂的玻璃罐头瓶里,然后又从那个精致的烟盒里抽出一根,“沈言,你这人挺有意思。明明是个喜阴植物,偏偏喜欢那种光照强度最高的地方。你不怕被晒死?”
“不觉得。”我走到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看着她在黑暗中忽明忽暗的烟头,“正是因为刺眼,才想靠近。”
“靠近之后呢?”苏青盯着我,“摘下来?带回家?插在你的花瓶里?”
我摇了摇头。
“我养不活。”
我说得很平静。这不是自卑,而是一种经过精密计算后的现实认知。
“她那种人,需要很大的空间,很贵的肥料,还有……很多的关注。”我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因为常年握笔而有些苍白的手,“我这里只有阴影。如果把她摘下来,不出三天她就会枯萎。”
“所以你就打算这么看着?”苏青挑了挑眉,“做个偷窥狂?”
“不是偷窥。”我纠正道,尽管底气并不足,“是……守护。”
“噗——”
苏青没忍住,笑出了声。烟灰随着她的动作抖落在大腿上,她毫不在意地伸手拂去。
“守护?沈言,你能不能别把那个词用得这么恶心。”她把烟递到嘴边,深吸了一口,“守护是骑士干的事。骑士是要骑着马冲锋的,是要流血的。”
她站起来,光着脚走到我面前。那股浓烈的烟草味混合着她身上某种冷冽的香水味,直冲我的鼻腔。
“而你不是骑士。”她低下头,看着我的眼睛,“你的眼神里没有那种东西。你的眼神里只有贪婪。你想占有她,但你知道自己配不上,所以你退而求其次。”
她伸出一根手指,戳了戳我放在桌子上的那个背包。
“这里面装着什么?”
我下意识地伸手挡了一下。
“没什么。一些杂物。”
“杂物会让你这么紧张?”苏青冷笑了一声,“让我猜猜。是她喝剩的水瓶?还是擦过汗的纸巾?”
我没说话。
“沈言。”苏青的声音低了下来,带着一种诱导般的磁性,“承认吧。你根本不想当什么骑士。你也不想把她摘下来。你只是喜欢跟在她后面,捡她不要的东西。”
我不置可否。
但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烫。那种被剥光了游街的羞耻感,混合着一种被人理解的快感,在身体里交织。
“那又怎么样?”我声音沙哑,“这不犯法。”
“是不犯法。”苏青转过身,走回窗边,“但这很……下流。不过,也很美。”
她随手从沙发旁边的地上拿起一本书,扔给我。
那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第29首,《腐尸》。”她说,“念给我听。”
我接过那本已经被翻得起毛边的书。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翻到了那一页。
这首诗我很熟。每一个字都像是刻在我的脑子里。
我清了清嗓子,开始朗读。
“回忆吧,我的爱人,我们见到的东西,
在那温和而明媚的夏日清晨:
在小路拐弯处,一具丑恶的腐尸,
横卧在铺满石子的床上……”
我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
“它的双腿向上翘起,像个淫荡的女人,
热辣辣地喷发着毒气,
它随随便便地张开充满臭气的肚皮,
把无耻和这种调子连在一起。”
当我读到这里时,苏青突然转过头。
“停。”
她看着我,“你读这首诗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愣了一下。
“在想尸体。”我撒谎。
“骗子。”苏青毫不留情地拆穿我,“你在想那个打羽毛球的女孩。你在想她刚脱下来的鞋,想她满是汗水的脚,想那些别人觉得脏、但你觉得香的东西。”
她走过来,抽走了我手里的书。
“波德莱尔是个天才。他告诉我们,美不仅仅存在于鲜花里,也存在于腐烂里。甚至,腐烂才是更本质的生命力。”
她把书扔回沙发上,整个人靠在窗台上,背对着月光,脸庞隐没在阴影里。
“沈言,你知道为什么植物的根都要往地下钻吗?”
我看着她。
“因为上面太吵了。”苏青说,“阳光太烈,风太大,所有人都在争奇斗艳。只有地下是安静的。那里又黑,又湿,全是烂掉的叶子和动物的尸体。”
她停顿了一下,吐出最后一口烟雾。
“但只有在那里,你才能真正抱住她。在上面,你只能看着她。但在下面,你可以把她包裹起来。哪怕只是包裹住她的根。”
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包裹住她的根。
我想起了今天下午,我把凡士林涂在她脚后跟上的那一刻。我想起了那块此刻正躺在我包里的、吸饱了汗水的毛巾。
那种感觉……不就是包裹吗?
我不需要她知道我在那里。我不需要她对我感恩戴德。
我只需要在那里。
在她的脚下。
“懂了吗?”苏青把烟头弹向窗外。红色的火星在夜色中划出一道弧线,然后消失在茫茫的雨幕中。
“懂了。”我说。
“懂了就滚吧。”苏青挥了挥手,“你那一身的凡士林味儿,还有那种发情的味道,熏得我头疼。”
我站起来。
拿起那个沉甸甸的背包。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停下了脚步。
“学姐。”
“又怎么了?”
“这本书。”我指了指沙发上的《恶之花》,“虽然我读过很多遍,但我从来没买过。”
“想说什么?”
“我觉得……我可能活在那本书里。”
苏青没有回头。
她在黑暗中沉默了几秒,然后发出了一声极轻的叹息。
“那祝你在里面玩得开心。别把自己玩死了就行。”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推开那扇掉漆的木门,走出了那个充满了烟草味和霉味的房间。
随着门在我身后“吱呀”一声关上,苏青的世界被隔绝在了身后。楼道里没有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惨白月光,把台阶照得像是一排排森森的白骨。
我顺着楼梯往下走。
这栋老楼很空,脚步声在回廊里显得格外清晰。走到二楼转角风口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抬起手臂,闻了闻袖口。
那里沾染了苏青房间里浓烈的女式烟草味,但在那层辛辣之下,还顽固地残留着一股淡淡的、油腻的矿物脂味。那是我的味道,也是乔一的味道。
走出文科楼的时候,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被雨水浸泡后的腥气。路边的花坛里,那些白天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栀子花,被这场暴雨摧残得七零八落。
我停下脚步。
在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一朵被打落的栀子花正躺在泥水里。
它原本洁白的花瓣已经沾满了黑色的淤泥,边缘开始氧化发黄,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褐色,像是一张被揉皱了的废纸。
我弯下腰,鬼使神差地伸出手。
指尖触碰到花瓣的那一刻,传来一种湿冷、软烂的触感。
它已经脏了。散发着一股混合了浓烈甜香和腐败泥土的气息。
但我没有把它扔回花坛。
我把它捏在手心里,感受着那种黏腻的触感。
我拉开外套的口袋,把这朵沾着泥的残花放了进去。
它和那个装着毛巾的背包,只隔着一层薄薄的布料。
口袋沉甸甸的。
我拿出手机,按亮屏幕。
21:45。
微信置顶的头像依然安静,没有任何红点。
我盯着那个空白的界面看了一会儿,然后熄灭屏幕,把手机塞回了另一个口袋。
远处宿舍区的灯光把夜空映得发红,隐约能听到人群的喧嚣。
我紧了紧背包的带子,低下头,像个怀揣着赃物的窃贼,快步走进了那片浓重的夜色里。
雨后的风很凉。
但我口袋里的那朵烂花,正在慢慢变热。
513295987发布于 2025-12-20 01:48
Re: 【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
写文字有水平,我也曾经想过如何去表达对她脚臭的喜爱,但深度真不及楼主十分之一
Ankh发布于 2025-12-20 21:55
Re: 【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
第四章
周六的训练课比平时延长了一个小时。
虽然外面的雨暂时停了,但体育馆里的白炽灯依然亮得刺眼,把空气烤得焦躁不安。几十个排气扇在头顶轰鸣,却根本抽不走积聚在馆内的湿气。那是几十具年轻肉体在剧烈运动后散发出的热量,混合着橡胶地胶受热后的胶水味,在封闭的空间里发酵成一团看不见的、黏稠的雾。
我照例坐在看台最角落的阴影里,膝盖上放着那本《恶之花》,但书页很久没有翻动过。我的视线穿过球网的方格,有些失焦地落在三号场地的休息区。
那里似乎出了点状况。
“哎呀!学姐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
一个带着哭腔的女声尖锐地划破了球馆里原本只有击球声的背景音。
我皱了皱眉,推了一下鼻梁上下滑的眼镜,看清了那边的情况。
三号场地边,乔一正站在休息长椅旁,双手有些不知所措地张开,一脸错愕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胸口。
她身上那件白色的队服T恤——那是为了备战省赛刚发下来的新队服,面料挺括,白得刺眼——此刻已经面目全非。一大杯深褐色的液体从她的锁骨处一路泼洒下来,洇湿了大半个前胸,顺着布料的纹理迅速扩散,甚至连下身那条白色的运动短裤上都溅满了星星点点的褐色污渍。
空气中瞬间弥漫开一股甜腻得令人发指的味道。
是奶茶。而且闻起来像是那种加了厚重奶盖和黑糖的全糖奶茶。
站在她对面的,是一个身材娇小、扎着双马尾的大一新生。
陈瑶瑶。
我知道她。今年刚进校队的替补队员,长得是那种很符合直男审美的“初恋脸”,说话永远是软糯的叠词,在男生堆里很吃得开。她正手足无措地捏着那个已经空了的、还在滴着残液的塑料杯,眼圈红红的,仿佛受害者是她一样。
“刚才地太滑了……我想给乔一学姐递水,结果没站稳……”陈瑶瑶一边抽泣着,一边慌乱地从包里掏纸巾,想要伸手去帮乔一擦,“学姐你没事吧?烫不烫?”
“行了行了,别擦了!”
乔一猛地后退了一步,避开了陈瑶瑶的手。她的眉头紧锁,脸上带着极度压抑的烦躁和恶心。
对于一个常年运动、对身体清爽度有极高要求的人来说,这种黏糊糊的高糖液体倒在满是汗水的皮肤上,那种感觉比被人打了一巴掌还难受。汗水本来就是黏的,现在混合了糖浆和奶精,正在迅速风干成一层令人窒息的壳,把她的毛孔全部堵死。
“越擦越脏。这也太黏了。”乔一低头看着自己胸口那一大滩褐色的污渍,甚至能看到几颗黑色的珍珠黏在衣领上,像是什么恶心的虫卵。
周围的几个男生立刻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开始和稀泥。
“没事没事,学妹也不是故意的。”
“快去洗洗吧,应该能洗掉。”
“瑶瑶别哭了,乔一又没怪你。”
张哲不在,去跟教练组开会了。没人能真正镇得住场子,也没人看穿这场“意外”背后拙劣的演技。
只有我。
我坐在高处的看台上,视角刚刚好。
我捕捉到了陈瑶瑶低头擦眼泪时,嘴角那一闪而过的、极其微小的上扬弧度。
那不是愧疚,那是得逞后的快意。就像是在阴沟里爬行的老鼠,终于把那块高高在上的奶酪给弄脏了。那一瞬间,我甚至在她身上闻到了同类的气息——那种因为嫉妒而产生的酸腐味。
乔一显然没心思去分析这些微表情。她现在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自己黏糊糊的身体上。
“烦死了。”她低声骂了一句,抓起自己的运动包,“我去换衣服。”
她黑着脸,转身走向更衣室。陈瑶瑶还站在原地演着那出楚楚可怜的戏码,被一群男生众星捧月地安慰着。
我合上书,站起身,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看台,走向更衣室门口的通道。
十分钟后,乔一出来了。
她换上了便服——一件简单的黑色T恤和牛仔短裤。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显然是刚才冲了个澡,但脸色依然难看得要命。
她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透明塑料袋。
透过塑料袋的薄膜,能清晰地看到里面那团被揉成一团的、沾满了褐色污渍的白色队服。那曾经代表着荣耀和洁净的战袍,此刻像是一团被嚼烂了吐出来的口香糖。
“真倒霉。”
看到我站在通道口,乔一停下脚步,把手里的袋子往地上一扔,发出一声闷响。
“喝什么不好非喝全糖的,黏得我到现在都觉得身上有股奶精味。”她烦躁地抓了抓头发,“这衣服算是废了。那么大一片黑糖渍,还是白衣服,根本洗不出来。”
“陈瑶瑶故意的?”我靠在墙边,低声问了一句。
乔一愣了一下,随即苦笑:“不知道。就算是故意的又能怎么样?人家都哭成那样了,我要是再计较,显得我这个主力学姐多欺负替补似的。这哑巴亏我是吃定了。”
她叹了口气,用脚尖踢了踢地上的袋子。
“烦死了,不想洗。这一身糖水味儿混合着汗味,闻着就想吐。我想直接扔了。”
我的视线落在那团衣物上。
塑料袋没有系紧。透过袋口,我能看到那件被浸透的白色T恤,还有被压在T恤下面的……那双换下来的球袜。
因为是周六的大运动量训练,那双袜子依然是灰黑色的,袜筒边沿卷曲着,像是两块吸饱了水的海绵。那是她这一周最脏、最狼狈、也最真实的代谢产物,现在正和那些虚伪的奶茶渍混在一起。
“别扔。”
我开口了,声音很稳,没有暴露出一丝一毫的贪婪,“队服是定制的,扔了还得重新向队里申请补订,流程挺麻烦的,还得被教练骂一顿丢三落四。”
“那怎么办?拿回宿舍洗?”乔一皱着眉,“这一身糖味儿,还没走到水房就要招蚂蚁了。而且我宿舍没强力去渍液,手搓都搓不掉。”
“给我吧。”
我弯下腰,自然地捡起那个袋子。
入手沉甸甸的。那是布料吸饱了液体后的重量,湿润、软烂,隔着塑料袋传来一丝冰凉的触感。
“我那儿有专门去渍的工业洗衣液,之前为了刷鞋买的。我拿回去帮你处理一下,先泡一晚上,应该能洗掉。实在洗不干净再扔。”
乔一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变成了感激。
“沈言,你是不是有点太贤惠了?”她半开玩笑地说,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这种脏活你都揽?里面可是还有……”
她指了指袋子底部。
“还有我的臭袜子和护膝。这你也洗?”
“顺手的事。”我面不改色,推了推眼镜,“反正我积了一周的衣服也要洗,洗衣机一转就完事了。”
“行,你是好人,大好人。”乔一松了口气,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就拜托你了!这周末请你吃大餐,必须吃顿好的!”
她并没有多想。在她眼里,我就是那个永远靠谱、永远不嫌麻烦、甚至有点洁癖的老好人沈言。她怎么会想到,一个正常男生会主动要求去洗女生的脏袜子?
“走了,我得回宿舍再洗一遍澡,总觉得头发上还有味儿。”
乔一冲我挥挥手,转身走出了体育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
手里那个塑料袋的提手勒得我的手指有些发白。
我低下头,看了一眼袋子里的东西。褐色的奶茶渍在白色的布料上显得格外刺眼,像是一种暴力的侵犯,一种肮脏的涂鸦。
陈瑶瑶弄脏了她。
但我会把她洗干净。
回到男生宿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半。
推开302的门,一股混合着红烧牛肉面、陈年脚臭和劣质烟草的浑浊空气扑面而来。那是独属于男生宿舍的味道,粗鲁、直接、令人窒息。
我的室友老周正光着膀子,只穿一条大裤衩,把两条毛茸茸的腿架在桌子上。他戴着耳机,对着电脑屏幕狂吼,屏幕上是某个衣着暴露的女主播正在扭动腰肢。
“老沈回来了?饭呢?”老周摘下一只耳机,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迷离。
“忘买了。”
我冷冷地回了一句,径直走向阳台。
“靠,你也太不靠谱了……饿死爹了。”老周骂骂咧咧地嘟囔了一句,又戴上耳机,继续沉浸在他的虚拟温柔乡里。
我走进阳台,反手拉上了落地门,并极其轻微地扣上了插销。
这里是这间脏乱差的宿舍里,唯一相对私密的领地。
阳台上堆满了杂物,挂着几件还没干的男生内裤,滴着水,散发着潮气。水槽里积着一层黄色的垢。
我把那个沉甸甸的塑料袋放在水槽里。
并没有像我对乔一承诺的那样扔进洗衣机。洗衣机那种冰冷的机械运动,无法体会我的快乐,也洗不干净那种恶意的污渍。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只属于我的仪式。
我打开水龙头,放了半盆清水。
然后,我解开了塑料袋的死结。
一股复杂的味道瞬间在这个狭小的阳台扩散开来,甚至盖过了外面老周那碗泡面的味道。
那是全糖奶茶的甜腻味,混合着汗水发酵后的酸味。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极其诡异的嗅觉冲击。甜得发腻,酸得刺鼻。
我先把那件沾满了奶茶渍的T恤拿出来。
那上面还残留着乔一的体温,湿漉漉的。褐色的污渍在白布上显得格外刺眼,摸上去黏糊糊的,像是一层干涸的糖浆壳。
我把T恤扔进盆里。
但我没有急着洗它。
我的手伸向了袋子的最底部。
那里躺着两只团在一起的球袜。
因为被上面的湿衣服压了一路,这两只袜子已经变得潮湿沉重,像两块吸饱了水的面团。白色的棉袜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袜底是深灰色的,那是鞋垫脱色和灰尘混合的结果。脚后跟和前脚掌的位置,因为长期高强度的摩擦,起了一层细小的毛球,摸上去像砂纸一样粗糙。
我把它们拿出来,摊在手心里。
这才是重头戏。
T恤上的奶茶是陈瑶瑶的恶意,但这双袜子上的汗水,是乔一的全部。
我背对着阳台门,挡住了可能投来的视线。
我弯下腰。
把脸埋进了那双手心里的袜子里。
深深地吸了一气。
轰——
那是一种怎样的味道啊。
没有了奶茶那种虚伪的甜腻干扰,这里只有最纯粹的、高浓度的生物气息。
酸。
极度的酸。
那是乳酸在无氧环境下发酵的味道,像是放久了的酸面团,又像是梅雨季节里发霉的柠檬。
咸。
那是汗水结晶的味道。
还有一股只有贴着皮肤才能闻到的、淡淡的肉味。
那是乔一的味道。是那个在球场上高高跃起、在领奖台上光彩照人、在所有人面前都必须保持完美的女神,脱下伪装后最真实、最底层的味道。
它并不香,甚至对于普通人来说是臭的,是令人作呕的。
但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氧气。
我闭着眼睛,大口大口地吞咽着这股空气。我的鼻尖蹭过粗糙的袜底,那种砂纸般的触感摩擦着我的皮肤,引起一阵阵战栗。
我甚至伸出了舌头。
轻轻地,舔了一下袜子脚后跟的位置。
苦的。咸的。涩的。
还带着一点点布料纤维的粗糙感。
这是她走过的路。这是她流过的汗。这是她身体里排出的多余的水分和盐分。
现在,它们都在我的嘴里。
我想象着这双袜子几小时前还包裹着那一双温热的脚,想象着她的脚趾在里面蜷缩、舒展,想象着汗水是如何一点点浸透棉纱。
“老沈!你干嘛呢?放个水放半天?”
老周的声音突然隔着玻璃门传来,吓得我猛地一抖。
“洗衣服!”
我声音有些哑,迅速把袜子扔进水盆里,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像是要撞破胸腔。
“快点啊,我要去尿尿,别把阳台门锁死!”
“知道了,马上。”
我看着水盆。
袜子沉入水中,迅速把那一盆清水染成了淡淡的灰色。
我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呼吸。
我挤了一泵洗衣液。
蓝色的粘稠液体在水中化开,散发出廉价的薰衣草香精味,试图掩盖那股属于乔一的原始气息。
我开始用力地搓洗。
白色的泡沫在我的指缝间炸裂。
我洗得很认真,很用力。
我想象着我的手不仅仅是在洗一双袜子,而是在抚摸她的脚,抚摸她的每一寸皮肤。
我在帮她清理污秽。
我在帮她洗掉陈瑶瑶泼在她身上的恶意。
也在洗掉她身上那些不属于我的、属于这个世界的杂质。
当这盆水变得浑浊不堪的时候,我的心里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洁净。
我是她的清洁工。
我是她的过滤器。
只要经过我的手,她就可以重新变回那个一尘不染的乔一。而那些脏东西,那些她不要的、嫌弃的、甚至觉得恶心的东西,我都留下了。
它们留在了我的肺里,留在了我的胃里,留在了我这个见不得光的灵魂里。
半小时后。
我把洗好的衣服和袜子拧干。
那件T恤上的奶茶渍已经被我完全洗掉了,恢复了原本的洁白。那双袜子也被搓洗得干干净净,只有袜底还残留着一点点洗不掉的灰色印记。
我把它们挂在衣架上。
它们和其他男生那些灰扑扑、散发着汗臭味的衣服挂在一起,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它们那么娇小,那么白得刺眼,在夜风中轻轻晃动。
阳台外面的雨又开始下了。
淅淅沥沥的雨声掩盖了宿舍里的游戏声。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双随风摆动的白袜子。
我推了推眼镜,嘴角勾起一抹满足的弧度。
第一件收藏品,虽然只是暂时的,但已经在那一瞬间,永久地属于过我了。
我拿起那瓶还没倒完的洗衣液,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薰衣草的味道。
不。
在这一刻,它就是乔一的味道。
“晚安。”
我对着那双袜子轻声说。
然后拉开阳台门,重新走进了那个充满浑浊空气的现实世界。
周六的训练课比平时延长了一个小时。
虽然外面的雨暂时停了,但体育馆里的白炽灯依然亮得刺眼,把空气烤得焦躁不安。几十个排气扇在头顶轰鸣,却根本抽不走积聚在馆内的湿气。那是几十具年轻肉体在剧烈运动后散发出的热量,混合着橡胶地胶受热后的胶水味,在封闭的空间里发酵成一团看不见的、黏稠的雾。
我照例坐在看台最角落的阴影里,膝盖上放着那本《恶之花》,但书页很久没有翻动过。我的视线穿过球网的方格,有些失焦地落在三号场地的休息区。
那里似乎出了点状况。
“哎呀!学姐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
一个带着哭腔的女声尖锐地划破了球馆里原本只有击球声的背景音。
我皱了皱眉,推了一下鼻梁上下滑的眼镜,看清了那边的情况。
三号场地边,乔一正站在休息长椅旁,双手有些不知所措地张开,一脸错愕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胸口。
她身上那件白色的队服T恤——那是为了备战省赛刚发下来的新队服,面料挺括,白得刺眼——此刻已经面目全非。一大杯深褐色的液体从她的锁骨处一路泼洒下来,洇湿了大半个前胸,顺着布料的纹理迅速扩散,甚至连下身那条白色的运动短裤上都溅满了星星点点的褐色污渍。
空气中瞬间弥漫开一股甜腻得令人发指的味道。
是奶茶。而且闻起来像是那种加了厚重奶盖和黑糖的全糖奶茶。
站在她对面的,是一个身材娇小、扎着双马尾的大一新生。
陈瑶瑶。
我知道她。今年刚进校队的替补队员,长得是那种很符合直男审美的“初恋脸”,说话永远是软糯的叠词,在男生堆里很吃得开。她正手足无措地捏着那个已经空了的、还在滴着残液的塑料杯,眼圈红红的,仿佛受害者是她一样。
“刚才地太滑了……我想给乔一学姐递水,结果没站稳……”陈瑶瑶一边抽泣着,一边慌乱地从包里掏纸巾,想要伸手去帮乔一擦,“学姐你没事吧?烫不烫?”
“行了行了,别擦了!”
乔一猛地后退了一步,避开了陈瑶瑶的手。她的眉头紧锁,脸上带着极度压抑的烦躁和恶心。
对于一个常年运动、对身体清爽度有极高要求的人来说,这种黏糊糊的高糖液体倒在满是汗水的皮肤上,那种感觉比被人打了一巴掌还难受。汗水本来就是黏的,现在混合了糖浆和奶精,正在迅速风干成一层令人窒息的壳,把她的毛孔全部堵死。
“越擦越脏。这也太黏了。”乔一低头看着自己胸口那一大滩褐色的污渍,甚至能看到几颗黑色的珍珠黏在衣领上,像是什么恶心的虫卵。
周围的几个男生立刻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开始和稀泥。
“没事没事,学妹也不是故意的。”
“快去洗洗吧,应该能洗掉。”
“瑶瑶别哭了,乔一又没怪你。”
张哲不在,去跟教练组开会了。没人能真正镇得住场子,也没人看穿这场“意外”背后拙劣的演技。
只有我。
我坐在高处的看台上,视角刚刚好。
我捕捉到了陈瑶瑶低头擦眼泪时,嘴角那一闪而过的、极其微小的上扬弧度。
那不是愧疚,那是得逞后的快意。就像是在阴沟里爬行的老鼠,终于把那块高高在上的奶酪给弄脏了。那一瞬间,我甚至在她身上闻到了同类的气息——那种因为嫉妒而产生的酸腐味。
乔一显然没心思去分析这些微表情。她现在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自己黏糊糊的身体上。
“烦死了。”她低声骂了一句,抓起自己的运动包,“我去换衣服。”
她黑着脸,转身走向更衣室。陈瑶瑶还站在原地演着那出楚楚可怜的戏码,被一群男生众星捧月地安慰着。
我合上书,站起身,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看台,走向更衣室门口的通道。
十分钟后,乔一出来了。
她换上了便服——一件简单的黑色T恤和牛仔短裤。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显然是刚才冲了个澡,但脸色依然难看得要命。
她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透明塑料袋。
透过塑料袋的薄膜,能清晰地看到里面那团被揉成一团的、沾满了褐色污渍的白色队服。那曾经代表着荣耀和洁净的战袍,此刻像是一团被嚼烂了吐出来的口香糖。
“真倒霉。”
看到我站在通道口,乔一停下脚步,把手里的袋子往地上一扔,发出一声闷响。
“喝什么不好非喝全糖的,黏得我到现在都觉得身上有股奶精味。”她烦躁地抓了抓头发,“这衣服算是废了。那么大一片黑糖渍,还是白衣服,根本洗不出来。”
“陈瑶瑶故意的?”我靠在墙边,低声问了一句。
乔一愣了一下,随即苦笑:“不知道。就算是故意的又能怎么样?人家都哭成那样了,我要是再计较,显得我这个主力学姐多欺负替补似的。这哑巴亏我是吃定了。”
她叹了口气,用脚尖踢了踢地上的袋子。
“烦死了,不想洗。这一身糖水味儿混合着汗味,闻着就想吐。我想直接扔了。”
我的视线落在那团衣物上。
塑料袋没有系紧。透过袋口,我能看到那件被浸透的白色T恤,还有被压在T恤下面的……那双换下来的球袜。
因为是周六的大运动量训练,那双袜子依然是灰黑色的,袜筒边沿卷曲着,像是两块吸饱了水的海绵。那是她这一周最脏、最狼狈、也最真实的代谢产物,现在正和那些虚伪的奶茶渍混在一起。
“别扔。”
我开口了,声音很稳,没有暴露出一丝一毫的贪婪,“队服是定制的,扔了还得重新向队里申请补订,流程挺麻烦的,还得被教练骂一顿丢三落四。”
“那怎么办?拿回宿舍洗?”乔一皱着眉,“这一身糖味儿,还没走到水房就要招蚂蚁了。而且我宿舍没强力去渍液,手搓都搓不掉。”
“给我吧。”
我弯下腰,自然地捡起那个袋子。
入手沉甸甸的。那是布料吸饱了液体后的重量,湿润、软烂,隔着塑料袋传来一丝冰凉的触感。
“我那儿有专门去渍的工业洗衣液,之前为了刷鞋买的。我拿回去帮你处理一下,先泡一晚上,应该能洗掉。实在洗不干净再扔。”
乔一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变成了感激。
“沈言,你是不是有点太贤惠了?”她半开玩笑地说,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这种脏活你都揽?里面可是还有……”
她指了指袋子底部。
“还有我的臭袜子和护膝。这你也洗?”
“顺手的事。”我面不改色,推了推眼镜,“反正我积了一周的衣服也要洗,洗衣机一转就完事了。”
“行,你是好人,大好人。”乔一松了口气,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就拜托你了!这周末请你吃大餐,必须吃顿好的!”
她并没有多想。在她眼里,我就是那个永远靠谱、永远不嫌麻烦、甚至有点洁癖的老好人沈言。她怎么会想到,一个正常男生会主动要求去洗女生的脏袜子?
“走了,我得回宿舍再洗一遍澡,总觉得头发上还有味儿。”
乔一冲我挥挥手,转身走出了体育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
手里那个塑料袋的提手勒得我的手指有些发白。
我低下头,看了一眼袋子里的东西。褐色的奶茶渍在白色的布料上显得格外刺眼,像是一种暴力的侵犯,一种肮脏的涂鸦。
陈瑶瑶弄脏了她。
但我会把她洗干净。
回到男生宿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半。
推开302的门,一股混合着红烧牛肉面、陈年脚臭和劣质烟草的浑浊空气扑面而来。那是独属于男生宿舍的味道,粗鲁、直接、令人窒息。
我的室友老周正光着膀子,只穿一条大裤衩,把两条毛茸茸的腿架在桌子上。他戴着耳机,对着电脑屏幕狂吼,屏幕上是某个衣着暴露的女主播正在扭动腰肢。
“老沈回来了?饭呢?”老周摘下一只耳机,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迷离。
“忘买了。”
我冷冷地回了一句,径直走向阳台。
“靠,你也太不靠谱了……饿死爹了。”老周骂骂咧咧地嘟囔了一句,又戴上耳机,继续沉浸在他的虚拟温柔乡里。
我走进阳台,反手拉上了落地门,并极其轻微地扣上了插销。
这里是这间脏乱差的宿舍里,唯一相对私密的领地。
阳台上堆满了杂物,挂着几件还没干的男生内裤,滴着水,散发着潮气。水槽里积着一层黄色的垢。
我把那个沉甸甸的塑料袋放在水槽里。
并没有像我对乔一承诺的那样扔进洗衣机。洗衣机那种冰冷的机械运动,无法体会我的快乐,也洗不干净那种恶意的污渍。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只属于我的仪式。
我打开水龙头,放了半盆清水。
然后,我解开了塑料袋的死结。
一股复杂的味道瞬间在这个狭小的阳台扩散开来,甚至盖过了外面老周那碗泡面的味道。
那是全糖奶茶的甜腻味,混合着汗水发酵后的酸味。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极其诡异的嗅觉冲击。甜得发腻,酸得刺鼻。
我先把那件沾满了奶茶渍的T恤拿出来。
那上面还残留着乔一的体温,湿漉漉的。褐色的污渍在白布上显得格外刺眼,摸上去黏糊糊的,像是一层干涸的糖浆壳。
我把T恤扔进盆里。
但我没有急着洗它。
我的手伸向了袋子的最底部。
那里躺着两只团在一起的球袜。
因为被上面的湿衣服压了一路,这两只袜子已经变得潮湿沉重,像两块吸饱了水的面团。白色的棉袜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袜底是深灰色的,那是鞋垫脱色和灰尘混合的结果。脚后跟和前脚掌的位置,因为长期高强度的摩擦,起了一层细小的毛球,摸上去像砂纸一样粗糙。
我把它们拿出来,摊在手心里。
这才是重头戏。
T恤上的奶茶是陈瑶瑶的恶意,但这双袜子上的汗水,是乔一的全部。
我背对着阳台门,挡住了可能投来的视线。
我弯下腰。
把脸埋进了那双手心里的袜子里。
深深地吸了一气。
轰——
那是一种怎样的味道啊。
没有了奶茶那种虚伪的甜腻干扰,这里只有最纯粹的、高浓度的生物气息。
酸。
极度的酸。
那是乳酸在无氧环境下发酵的味道,像是放久了的酸面团,又像是梅雨季节里发霉的柠檬。
咸。
那是汗水结晶的味道。
还有一股只有贴着皮肤才能闻到的、淡淡的肉味。
那是乔一的味道。是那个在球场上高高跃起、在领奖台上光彩照人、在所有人面前都必须保持完美的女神,脱下伪装后最真实、最底层的味道。
它并不香,甚至对于普通人来说是臭的,是令人作呕的。
但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氧气。
我闭着眼睛,大口大口地吞咽着这股空气。我的鼻尖蹭过粗糙的袜底,那种砂纸般的触感摩擦着我的皮肤,引起一阵阵战栗。
我甚至伸出了舌头。
轻轻地,舔了一下袜子脚后跟的位置。
苦的。咸的。涩的。
还带着一点点布料纤维的粗糙感。
这是她走过的路。这是她流过的汗。这是她身体里排出的多余的水分和盐分。
现在,它们都在我的嘴里。
我想象着这双袜子几小时前还包裹着那一双温热的脚,想象着她的脚趾在里面蜷缩、舒展,想象着汗水是如何一点点浸透棉纱。
“老沈!你干嘛呢?放个水放半天?”
老周的声音突然隔着玻璃门传来,吓得我猛地一抖。
“洗衣服!”
我声音有些哑,迅速把袜子扔进水盆里,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像是要撞破胸腔。
“快点啊,我要去尿尿,别把阳台门锁死!”
“知道了,马上。”
我看着水盆。
袜子沉入水中,迅速把那一盆清水染成了淡淡的灰色。
我深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呼吸。
我挤了一泵洗衣液。
蓝色的粘稠液体在水中化开,散发出廉价的薰衣草香精味,试图掩盖那股属于乔一的原始气息。
我开始用力地搓洗。
白色的泡沫在我的指缝间炸裂。
我洗得很认真,很用力。
我想象着我的手不仅仅是在洗一双袜子,而是在抚摸她的脚,抚摸她的每一寸皮肤。
我在帮她清理污秽。
我在帮她洗掉陈瑶瑶泼在她身上的恶意。
也在洗掉她身上那些不属于我的、属于这个世界的杂质。
当这盆水变得浑浊不堪的时候,我的心里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洁净。
我是她的清洁工。
我是她的过滤器。
只要经过我的手,她就可以重新变回那个一尘不染的乔一。而那些脏东西,那些她不要的、嫌弃的、甚至觉得恶心的东西,我都留下了。
它们留在了我的肺里,留在了我的胃里,留在了我这个见不得光的灵魂里。
半小时后。
我把洗好的衣服和袜子拧干。
那件T恤上的奶茶渍已经被我完全洗掉了,恢复了原本的洁白。那双袜子也被搓洗得干干净净,只有袜底还残留着一点点洗不掉的灰色印记。
我把它们挂在衣架上。
它们和其他男生那些灰扑扑、散发着汗臭味的衣服挂在一起,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它们那么娇小,那么白得刺眼,在夜风中轻轻晃动。
阳台外面的雨又开始下了。
淅淅沥沥的雨声掩盖了宿舍里的游戏声。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双随风摆动的白袜子。
我推了推眼镜,嘴角勾起一抹满足的弧度。
第一件收藏品,虽然只是暂时的,但已经在那一瞬间,永久地属于过我了。
我拿起那瓶还没倒完的洗衣液,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薰衣草的味道。
不。
在这一刻,它就是乔一的味道。
“晚安。”
我对着那双袜子轻声说。
然后拉开阳台门,重新走进了那个充满浑浊空气的现实世界。
Ankh发布于 2025-12-21 01:04
Re: 【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
第五章
周日的清晨并没有带来往常的宁静。
我是被热醒的。才早上六点半,宿舍里的空气就已经黏稠得像是一锅煮开的浆糊。老周那台用了三年的杂牌小风扇在床头艰难地转动着,发出濒死般的嘎吱声,吹出来的风全是热浪。
我从上铺坐起来,浑身是汗。T恤黏在后背上,稍微一动就扯得皮肤生疼。
老周还在下铺打雷般地打着呼噜,一条腿伸出蚊帐,上面全是蚊子叮的包。空气里弥漫着昨晚他没吃完的泡面馊味,混合着四个人一整夜呼出的二氧化碳,让人窒息。
我轻手轻脚地爬下床,没有开灯,径直走向阳台。
拉开落地门的那一刻,一股更沉闷的热浪扑面而来。外面的天空是一种病态的灰黄色,云层压得极低,仿佛触手可及。没有风,树叶纹丝不动,整个世界都被封印在一个巨大的蒸笼里。
我的目光第一时间落在了晾衣绳上。
那件白色的队服T恤和那双球袜已经干了。
经过一夜的晾晒,棉质面料变得有些发硬,直挺挺地挂在那里。T恤胸口那块曾经触目惊心的褐色奶茶渍已经完全消失不见,恢复了雪一般的洁白。那双被我用手一点点搓洗出来的袜子,也褪去了灰暗的底色,在昏暗的晨光中泛着干净的光泽。
我走过去,并没有立刻把它们收下来。
我凑近那件T恤,鼻尖几乎贴上布料。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没有了汗味,没有了奶茶的甜腻味,也没有了乔一身上那种独特的、带着生命力的酸味。
只剩下廉价而浓郁的薰衣草洗衣液残留的香精味。
那种味道太工业、太虚假了,就像是商场里喷洒的空气清新剂,掩盖了一切真实的痕迹。
我有些失望,但更多的是一种隐秘的满足感。
因为这股味道,是我留下的。
现在,这件衣服干净了,它不再属于昨天那个狼狈不堪的乔一。它经过了我的手,经过了我的净化,盖上了我的印章。
我小心翼翼地把T恤和袜子取下来。
回到书桌前,我把老周桌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游戏手办和空饮料瓶推到一边,清理出一块干净的区域。
我开始叠衣服。
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陌生的事。平时对待自己的衣服,我都是胡乱揉成一团塞进衣柜。但此刻,我的动作慢得像是在折叠一面国旗。
我把T恤摊平,抚平上面的每一道褶皱。然后按照标准的叠衣法,将两只袖子向内折叠,再对折。
接着是袜子。
那两只白色的小东西躺在我的手心里。因为晒干了,摸起来有些粗糙拉手。
我把它们叠在一起,然后把袜口翻过来,整整齐齐地团成一个结实的小球。
做完这一切,我找来一个干净的透明自封袋,把叠好的衣物放了进去,挤出多余的空气,封好口。
完美。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件刚从商店里买回来的新商品。
我把它放进我的背包里。
七点半,老周被热醒了。
“操,这什么鬼天气。”他迷迷糊糊地坐起来,抓着胸口浓密的胸毛,骂骂咧咧地看了一眼手机,“天气预报说台风今天要登陆?怪不得这么闷,老子感觉都要熟了。”
“嗯,说是这几年最大的一次。”我一边换鞋一边说,“学校可能会停课。”
“真的假的?那太爽了!”老周瞬间精神了,“正好把昨晚没通关的那个副本打了。哎老沈,你这么早去哪儿?”
“去图书馆还书。”我撒谎道。
“神经病啊,这种天气还去图书馆。”老周翻了个白眼,重新躺回凉席上,“帮我带俩包子回来,要肉的。”
“知道了。”
我背上包,走出了充满男人汗臭味的宿舍。
外面的世界比宿舍里更让人难以忍受。空气湿度大到了极点,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咽温水。身上刚换的干T恤不出五分钟就又湿透了,黏在身上极其难受。
校园里人很少。大家都被这可怕的天气吓退了,躲在一切有空调的地方。
我和乔一约在二食堂门口见面。那里离她们女生宿舍区比较近。
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那儿了。
她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oversize大T恤,下面是一条牛仔热裤,露出两条修长结实的大腿。脚上踩着一双人字拖,脚指甲涂成了亮眼的宝蓝色。
她看起来心情不错,显然已经从昨天的不愉快中恢复过来了。手里依然拿着一杯冰美式,杯壁上全是冷凝水。
“早啊田螺姑娘!”
看到我,乔一远远地就冲我挥手,用了一个让我有些尴尬的称呼。
我走过去,把背包里的那个自封袋拿出来递给她。
“洗好了。你检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印子。”
乔一接过袋子,隔着透明塑料看了一眼,眼睛瞬间瞪大了。
“我靠,沈言你可以啊!”她惊呼道,“这哪是洗衣服,你这是变魔术吧?跟新的一样!”
她打开自封袋。
一股浓郁的薰衣草香味瞬间飘了出来。
乔一凑过去闻了闻,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
“真香。比我那瓶洗衣液好闻多了。”她把T恤拿出来,在身上比划了一下,确认那块巨大的污渍真的完全消失了,“你怎么洗的?我本来都打算扔了。”
“先用温水化开爆炸盐泡了一晚上,然后手搓的。”我面不改色地编造着流程,省略了中间最关键的、不可告人的步骤,“那袜子也洗了,在下面。”
“谢了谢了,真的太感谢了!”乔一重新把衣服塞回袋子,抬头看着我,眼神里全是真诚的感激,“你不知道那件队服多难订。沈言,你真是我的救星。”
她伸出手,大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好的大餐肯定跑不了。等这台风过去了,地方随你挑!”
我笑了笑,推了推眼镜掩饰住眼底的波澜。
“小事。举手之劳。”
“对了,你看新闻了吗?”乔一指了指天空,“这台风好像挺猛的。我们教练刚在群里发通知,说下午和晚上的训练全部取消了,让大家待在宿舍别乱跑,还要储备点干粮和水。”
“嗯,听说了。那你赶紧回去吧,别在外面晃了。”
“行,那我先撤了。我还得去超市抢点泡面呢,去晚了估计连渣都不剩了。”
乔一冲我摆摆手,踩着人字拖吧嗒吧嗒地跑远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
她的步伐轻快,马尾辫在脑后一甩一甩的。她根本不知道,就在几个小时前,她视若珍宝的那双脚曾经包裹过的袜子,被我怎样亵渎过。
她现在手里拎着的那个袋子里,装着的不再是她的衣服,而是我的作品。
我抬起手,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指尖上还残留着那股薰衣草的味道。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真好。
现在,我和她身上,有着同样的味道了。
这就像是一个隐秘的标记。在未来的某一天,当她穿着那件T恤,那双袜子在球场上奔跑的时候,那股薰衣草的味道会混合着她的汗水重新散发出来。
没人知道那股味道的源头是我。
只有我知道。
这种掌控感让我有些上瘾。
我没有去图书馆。那种地方在这种天气里只会更加闷热。
我去了学校的小超市。
超市里已经人满为患。恐慌情绪在蔓延,货架上的方便面、火腿肠、矿泉水正在被疯抢。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末日来临般的焦虑和兴奋。
我挤在人群里,随波逐流地拿了几包我不喜欢吃的红烧牛肉面,又拿了两大瓶水。
结账的队伍排到了门外。
空气里全是汗臭味、廉价香水味和超市特有的那种生鲜区的腥味。大家都在抱怨天气,抱怨学校的后勤,抱怨插队的人。
我站在队伍里,感觉自己像是一条被挤在沙丁鱼罐头里的死鱼。
但我并不焦虑。相反,我甚至有点期待。
我期待这场台风。
我期待秩序的崩坏。当狂风暴雨把所有人都困在那个小小的宿舍里,当外面的世界变得一片混乱,当文明的外壳被剥离……
也许,有些平时见不得光的东西,就能找到缝隙钻出来了。
回到宿舍的时候,老周正在阳台上加固窗户。
“老沈你可算回来了!快来搭把手!”他用透明胶带在玻璃上贴着米字格,“宿管阿姨刚在楼下喊,说这次是超强台风,让大家一定要把阳台上的东西收进来。”
我放下东西,过去帮他。
我们把那些万年不收的烂球鞋、生锈的晾衣架全都搬进了屋里。原本就拥挤不堪的宿舍瞬间变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这鬼天气,真是让人暴躁。”老周擦了一把汗,一屁股坐在那堆杂物上,“哎,老沈,你那包里是啥?一股娘们儿唧唧的香味。”
我心里一紧。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顺手把那个装脏衣服的塑料袋塞进了书包侧兜,忘了拿出来。那里面还残留着洗衣服时的味道。
“刚去超市买的洗衣液,可能盖子没拧紧漏了一点。”我面不改色地撒谎。
“哦,我还以为你小子终于开窍了,搞了个女朋友回来呢。”老周也没多想,拿起手机继续刷着台风路径图,“你看这台风眼,擦着咱们京州过。这次真要发大水了。”
我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
时间接近中午十二点。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像是一块巨大的、吸饱了墨汁的黑布罩在城市上空。
起风了。
一开始只是树叶的沙沙声,然后变成了呼啸。路边的景观树开始剧烈地摇晃,像是在跳一场疯狂的舞蹈。一些没关好的窗户在风中发出砰砰的巨响。
“来了。”老周嘟囔了一句。
第一滴雨砸在窗户玻璃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紧接着,暴雨倾盆而至。
那不是在下雨,简直就像是天空裂开了一道口子,整条天河的水都倾泻了下来。天地间瞬间拉起了一道白茫茫的雨幕,能见度不足十米。
风声夹杂着雨声,像是有无数头野兽在窗外嘶吼。
宿舍楼里响起一片惊呼声和关窗户的声音。
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末日景象。玻璃上全是蜿蜒的水痕,把外面的世界扭曲得光怪陆离。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身体里那股被压抑了许久的燥热,随着窗外的狂风暴雨,开始蠢蠢欲动。
那种低气压带来的窒息感终于找到了宣泄口。
我拿出手机。
班级群、社团群、各种群都在疯狂地刷屏,大家都在讨论这场台风,分享着窗外的视频和照片。
我点开乔一的头像。
她的朋友圈刚刚更新了一条动态。
是一张照片。她宿舍的窗台上摆着好几桶泡面和零食,配文是:“粮草充足,坐等看海。希望不要停电啊啊啊!”
照片的角落里,我看到了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色T恤,正搭在她的床头。
我盯着那个角落看了很久。
外面的风声越来越大,宿舍的窗户被吹得嗡嗡作响,仿佛随时都会碎裂。
我伸出手,隔着玻璃,按在了外面那个狂暴的世界核心。
台风来了。
周日的清晨并没有带来往常的宁静。
我是被热醒的。才早上六点半,宿舍里的空气就已经黏稠得像是一锅煮开的浆糊。老周那台用了三年的杂牌小风扇在床头艰难地转动着,发出濒死般的嘎吱声,吹出来的风全是热浪。
我从上铺坐起来,浑身是汗。T恤黏在后背上,稍微一动就扯得皮肤生疼。
老周还在下铺打雷般地打着呼噜,一条腿伸出蚊帐,上面全是蚊子叮的包。空气里弥漫着昨晚他没吃完的泡面馊味,混合着四个人一整夜呼出的二氧化碳,让人窒息。
我轻手轻脚地爬下床,没有开灯,径直走向阳台。
拉开落地门的那一刻,一股更沉闷的热浪扑面而来。外面的天空是一种病态的灰黄色,云层压得极低,仿佛触手可及。没有风,树叶纹丝不动,整个世界都被封印在一个巨大的蒸笼里。
我的目光第一时间落在了晾衣绳上。
那件白色的队服T恤和那双球袜已经干了。
经过一夜的晾晒,棉质面料变得有些发硬,直挺挺地挂在那里。T恤胸口那块曾经触目惊心的褐色奶茶渍已经完全消失不见,恢复了雪一般的洁白。那双被我用手一点点搓洗出来的袜子,也褪去了灰暗的底色,在昏暗的晨光中泛着干净的光泽。
我走过去,并没有立刻把它们收下来。
我凑近那件T恤,鼻尖几乎贴上布料。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没有了汗味,没有了奶茶的甜腻味,也没有了乔一身上那种独特的、带着生命力的酸味。
只剩下廉价而浓郁的薰衣草洗衣液残留的香精味。
那种味道太工业、太虚假了,就像是商场里喷洒的空气清新剂,掩盖了一切真实的痕迹。
我有些失望,但更多的是一种隐秘的满足感。
因为这股味道,是我留下的。
现在,这件衣服干净了,它不再属于昨天那个狼狈不堪的乔一。它经过了我的手,经过了我的净化,盖上了我的印章。
我小心翼翼地把T恤和袜子取下来。
回到书桌前,我把老周桌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游戏手办和空饮料瓶推到一边,清理出一块干净的区域。
我开始叠衣服。
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陌生的事。平时对待自己的衣服,我都是胡乱揉成一团塞进衣柜。但此刻,我的动作慢得像是在折叠一面国旗。
我把T恤摊平,抚平上面的每一道褶皱。然后按照标准的叠衣法,将两只袖子向内折叠,再对折。
接着是袜子。
那两只白色的小东西躺在我的手心里。因为晒干了,摸起来有些粗糙拉手。
我把它们叠在一起,然后把袜口翻过来,整整齐齐地团成一个结实的小球。
做完这一切,我找来一个干净的透明自封袋,把叠好的衣物放了进去,挤出多余的空气,封好口。
完美。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件刚从商店里买回来的新商品。
我把它放进我的背包里。
七点半,老周被热醒了。
“操,这什么鬼天气。”他迷迷糊糊地坐起来,抓着胸口浓密的胸毛,骂骂咧咧地看了一眼手机,“天气预报说台风今天要登陆?怪不得这么闷,老子感觉都要熟了。”
“嗯,说是这几年最大的一次。”我一边换鞋一边说,“学校可能会停课。”
“真的假的?那太爽了!”老周瞬间精神了,“正好把昨晚没通关的那个副本打了。哎老沈,你这么早去哪儿?”
“去图书馆还书。”我撒谎道。
“神经病啊,这种天气还去图书馆。”老周翻了个白眼,重新躺回凉席上,“帮我带俩包子回来,要肉的。”
“知道了。”
我背上包,走出了充满男人汗臭味的宿舍。
外面的世界比宿舍里更让人难以忍受。空气湿度大到了极点,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咽温水。身上刚换的干T恤不出五分钟就又湿透了,黏在身上极其难受。
校园里人很少。大家都被这可怕的天气吓退了,躲在一切有空调的地方。
我和乔一约在二食堂门口见面。那里离她们女生宿舍区比较近。
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那儿了。
她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oversize大T恤,下面是一条牛仔热裤,露出两条修长结实的大腿。脚上踩着一双人字拖,脚指甲涂成了亮眼的宝蓝色。
她看起来心情不错,显然已经从昨天的不愉快中恢复过来了。手里依然拿着一杯冰美式,杯壁上全是冷凝水。
“早啊田螺姑娘!”
看到我,乔一远远地就冲我挥手,用了一个让我有些尴尬的称呼。
我走过去,把背包里的那个自封袋拿出来递给她。
“洗好了。你检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印子。”
乔一接过袋子,隔着透明塑料看了一眼,眼睛瞬间瞪大了。
“我靠,沈言你可以啊!”她惊呼道,“这哪是洗衣服,你这是变魔术吧?跟新的一样!”
她打开自封袋。
一股浓郁的薰衣草香味瞬间飘了出来。
乔一凑过去闻了闻,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
“真香。比我那瓶洗衣液好闻多了。”她把T恤拿出来,在身上比划了一下,确认那块巨大的污渍真的完全消失了,“你怎么洗的?我本来都打算扔了。”
“先用温水化开爆炸盐泡了一晚上,然后手搓的。”我面不改色地编造着流程,省略了中间最关键的、不可告人的步骤,“那袜子也洗了,在下面。”
“谢了谢了,真的太感谢了!”乔一重新把衣服塞回袋子,抬头看着我,眼神里全是真诚的感激,“你不知道那件队服多难订。沈言,你真是我的救星。”
她伸出手,大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好的大餐肯定跑不了。等这台风过去了,地方随你挑!”
我笑了笑,推了推眼镜掩饰住眼底的波澜。
“小事。举手之劳。”
“对了,你看新闻了吗?”乔一指了指天空,“这台风好像挺猛的。我们教练刚在群里发通知,说下午和晚上的训练全部取消了,让大家待在宿舍别乱跑,还要储备点干粮和水。”
“嗯,听说了。那你赶紧回去吧,别在外面晃了。”
“行,那我先撤了。我还得去超市抢点泡面呢,去晚了估计连渣都不剩了。”
乔一冲我摆摆手,踩着人字拖吧嗒吧嗒地跑远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
她的步伐轻快,马尾辫在脑后一甩一甩的。她根本不知道,就在几个小时前,她视若珍宝的那双脚曾经包裹过的袜子,被我怎样亵渎过。
她现在手里拎着的那个袋子里,装着的不再是她的衣服,而是我的作品。
我抬起手,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指尖上还残留着那股薰衣草的味道。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真好。
现在,我和她身上,有着同样的味道了。
这就像是一个隐秘的标记。在未来的某一天,当她穿着那件T恤,那双袜子在球场上奔跑的时候,那股薰衣草的味道会混合着她的汗水重新散发出来。
没人知道那股味道的源头是我。
只有我知道。
这种掌控感让我有些上瘾。
我没有去图书馆。那种地方在这种天气里只会更加闷热。
我去了学校的小超市。
超市里已经人满为患。恐慌情绪在蔓延,货架上的方便面、火腿肠、矿泉水正在被疯抢。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末日来临般的焦虑和兴奋。
我挤在人群里,随波逐流地拿了几包我不喜欢吃的红烧牛肉面,又拿了两大瓶水。
结账的队伍排到了门外。
空气里全是汗臭味、廉价香水味和超市特有的那种生鲜区的腥味。大家都在抱怨天气,抱怨学校的后勤,抱怨插队的人。
我站在队伍里,感觉自己像是一条被挤在沙丁鱼罐头里的死鱼。
但我并不焦虑。相反,我甚至有点期待。
我期待这场台风。
我期待秩序的崩坏。当狂风暴雨把所有人都困在那个小小的宿舍里,当外面的世界变得一片混乱,当文明的外壳被剥离……
也许,有些平时见不得光的东西,就能找到缝隙钻出来了。
回到宿舍的时候,老周正在阳台上加固窗户。
“老沈你可算回来了!快来搭把手!”他用透明胶带在玻璃上贴着米字格,“宿管阿姨刚在楼下喊,说这次是超强台风,让大家一定要把阳台上的东西收进来。”
我放下东西,过去帮他。
我们把那些万年不收的烂球鞋、生锈的晾衣架全都搬进了屋里。原本就拥挤不堪的宿舍瞬间变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这鬼天气,真是让人暴躁。”老周擦了一把汗,一屁股坐在那堆杂物上,“哎,老沈,你那包里是啥?一股娘们儿唧唧的香味。”
我心里一紧。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顺手把那个装脏衣服的塑料袋塞进了书包侧兜,忘了拿出来。那里面还残留着洗衣服时的味道。
“刚去超市买的洗衣液,可能盖子没拧紧漏了一点。”我面不改色地撒谎。
“哦,我还以为你小子终于开窍了,搞了个女朋友回来呢。”老周也没多想,拿起手机继续刷着台风路径图,“你看这台风眼,擦着咱们京州过。这次真要发大水了。”
我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
时间接近中午十二点。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像是一块巨大的、吸饱了墨汁的黑布罩在城市上空。
起风了。
一开始只是树叶的沙沙声,然后变成了呼啸。路边的景观树开始剧烈地摇晃,像是在跳一场疯狂的舞蹈。一些没关好的窗户在风中发出砰砰的巨响。
“来了。”老周嘟囔了一句。
第一滴雨砸在窗户玻璃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紧接着,暴雨倾盆而至。
那不是在下雨,简直就像是天空裂开了一道口子,整条天河的水都倾泻了下来。天地间瞬间拉起了一道白茫茫的雨幕,能见度不足十米。
风声夹杂着雨声,像是有无数头野兽在窗外嘶吼。
宿舍楼里响起一片惊呼声和关窗户的声音。
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末日景象。玻璃上全是蜿蜒的水痕,把外面的世界扭曲得光怪陆离。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身体里那股被压抑了许久的燥热,随着窗外的狂风暴雨,开始蠢蠢欲动。
那种低气压带来的窒息感终于找到了宣泄口。
我拿出手机。
班级群、社团群、各种群都在疯狂地刷屏,大家都在讨论这场台风,分享着窗外的视频和照片。
我点开乔一的头像。
她的朋友圈刚刚更新了一条动态。
是一张照片。她宿舍的窗台上摆着好几桶泡面和零食,配文是:“粮草充足,坐等看海。希望不要停电啊啊啊!”
照片的角落里,我看到了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色T恤,正搭在她的床头。
我盯着那个角落看了很久。
外面的风声越来越大,宿舍的窗户被吹得嗡嗡作响,仿佛随时都会碎裂。
我伸出手,隔着玻璃,按在了外面那个狂暴的世界核心。
台风来了。
hahahabf发布于 2025-12-21 01:20
Re: 【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
心理描写太棒了!
Ankh发布于 2025-12-21 22:28
Re: 【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
第六章
下午三点,京州的天空彻底死了。
那不再是阴天,而是一块巨大的、沉重的铅板,直接压在了头顶上。窗外的世界已经失去了原本的颜色,只剩下灰与黑的混沌。狂风裹挟着暴雨,像是一万台高压水枪同时对着宿舍楼扫射,玻璃窗在框里疯狂颤抖,发出那种濒临破碎的“嗡嗡”声,听得人牙根发酸。
302宿舍里一片死寂,只有老周打游戏的机械键盘声还在噼里啪啦地响,那是他对这场末日唯一的反抗。
突然,“啪”的一声。
世界黑了。
原本昏暗的宿舍瞬间陷入了彻底的黑暗,老周电脑屏幕上的微光也随之熄灭。与此同时,走廊里传来一阵此起彼伏的哀嚎和咒骂声。
“操!停电了!”
“老子的排位赛啊!”
“有没有搞错,这种时候停电?”
空调停止了运作。原本就被密封在室内的闷热空气,瞬间像是失去了枷锁的野兽,开始肆虐。湿度表上的指针早就爆表了,空气里全是汗味、霉味和那种令人窒息的静电感。
我坐在黑暗中,没有出声。
我拿出手机。信号格在两格和无服务之间疯狂跳动。
屏幕的光照亮了我半张脸。我点开微信,班级群里已经炸锅了。
辅导员发了一条标红的全员通知:「@所有人 接学校紧急通知,受超强台风“海葵”影响,校内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电力设施受损。请所有同学待在宿舍,严禁外出!严禁外出!注意安全!」
下面是一连串的“收到”和抱怨。
有人发了几张照片。
那是学校的北门和老校区。黄褐色的泥水已经漫过了路沿石,垃圾桶翻倒在水里,白色的快餐盒和黑色的塑料袋像是一群死鱼,漂浮在水面上。
那是真正的浑浊。
下水道里的秽物、泥土里的腐殖质、城市角落里的垃圾,全都被这场暴雨翻了出来,搅拌在一起。
我盯着那些照片,心里却莫名地感到一种平静。
这不就是世界的本质吗?平时光鲜亮丽,只要一场雨,底下的烂泥就会翻涌上来。
就在这时,手机震动了一下。
不是群消息。
是一个私聊。
我看清那个头像的瞬间,呼吸猛地一滞。
是乔一。
只有一条语音。
我点开,把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
背景音是一片嘈杂的风雨声,大得吓人,几乎盖过了人声。
“……沈言……你在宿舍吗?我有急事……我被困在老体育馆了……水涨得好快……我怕……”
她的声音在发抖。那种平时在球场上大杀四方的霸气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无助女孩的惊恐。
老体育馆。
那是京大最老的一栋建筑,地势极低,就在人工湖旁边。因为设施陈旧,平时很少有人去,只有一些想偷懒不训练的学生会去那里躲着。
她去那儿干什么?
我没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我在。”
我飞快地回了两个字,手指都在颤抖。
“别怕,找个高的地方待着。我马上来。”
发完这条消息,我把手机塞进防水袋里,挂在脖子上。
“老沈,你去哪儿?”
黑暗中,老周的声音带着一丝惊恐,“辅导员刚说严禁外出,外面水都到小腿了!”
“我去买点蜡烛。”
我随口编了个理由,声音冷静得让自己都觉得可怕。
“你有病啊!这时候买什么蜡烛!”
我不理会身后的叫喊,抓起一件一次性雨衣,推门冲进了黑暗的走廊。
楼道里全是乱窜的学生,手电筒的光束乱晃。我逆着人流,冲下了楼梯。
推开宿舍大门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撞上了一堵墙。
那不是风,那是实体化的空气。狂风夹杂着雨点,像是一把把小刀子,狠狠地割在脸上。
积水已经漫上了台阶。
我一步踏进去。
冷。
刺骨的冷。
那浑浊的黄泥水瞬间灌满了我的鞋子,那是怎样一种触感啊。黏稠、滑腻、带着一股浓烈的下水道腥臭味。枯枝烂叶缠绕在我的脚踝上,像是一只只水鬼的手。
但我没有停。
我就像是一条回到了沼泽的鳄鱼,这种肮脏的环境反而让我感到如鱼得水。
我压低重心,顶着狂风,向着老体育馆的方向艰难跋涉。
路很难走。平时熟悉的校园此刻变成了一片汪洋。路灯都熄灭了,只有时不时划过天际的闪电,能瞬间照亮这片末日般的景象。
树倒了。巨大的梧桐树被连根拔起,横亘在路中间,树根带起一大团黑色的泥土,像是一个个张开的伤口。
我绕过断树,趟过齐膝深的积水。
那个方向没有人。所有人都躲在安全的宿舍里。
只有我。
我在暴雨中狂奔,或者说是在泥水里挪动。
越靠近老体育馆,水越深。
到了人工湖附近,水已经漫到了我的大腿根。这里地势最低,湖水倒灌,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湖。
“乔一!”
我大喊了一声。
声音瞬间被风声吞没。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眯着眼睛,借着下一道闪电的光,看向前方。
老体育馆那扇斑驳的铁门开着。
门口的积水已经快要没过那几级台阶了。
我冲进去。
馆内一片漆黑。因为停电,这里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风从破损的窗户灌进来,发出凄厉的呜咽声。
“乔一!”
我又喊了一声,这次声音在空旷的馆内有了回音。
“沈言?!是你吗?”
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从看台上方传来。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光束扫向声音的来源。
在那排最高层的木质看台上,蜷缩着一个身影。
乔一。
她浑身都湿透了,像是一只落汤鸡。那件我也有一件同款的黑色大T恤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她发抖的身体曲线。她手里紧紧抱着一个防水的球包,那是她的命根子。
看到我的那一刻,她原本紧绷的肩膀瞬间垮了下来,眼泪夺眶而出。
“沈言……我以为我要淹死在这儿了……”
我趟着水,快步走到看台下。
馆内的积水也很深,混杂着淤泥和不知哪里冲来的垃圾。
“没事了。”
我仰起头,看着她。手电筒的光照亮了她苍白的脸。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我昨天把最贵的那把拍子落在这儿了,我想趁着台风没来拿回去,结果……结果水涨得太快了,我出不去了……”
她指了指下面黑黝黝的水面,“下面好像有东西……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撞了我的腿……”
她的眼神里满是恐惧。对于一个在陆地上称王的运动员来说,这种浑浊、未知、淹没一切的水,是最可怕的噩梦。
“别怕,是漂浮的木头或者垃圾。”
我伸出手,“下来。”
乔一犹豫了一下,看着那浑浊的水面,缩了缩脚。
“水太深了……而且好脏……”
她穿着那双宝蓝色指甲油的人字拖,脚趾紧紧扣着台阶的边缘。
“我背你。”
我说。
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
我转过身,背对着她,弯下腰。
“上来。我带你出去。”
乔一愣了一下。
此时此刻,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孤岛里,在这个黑暗、寒冷、充满恐惧的时刻,我是她唯一的救命稻草。
她没有别的选择。
“那……麻烦你了。”
我感觉到身后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
然后,一具温热的、湿漉漉的躯体,贴上了我的后背。
那是怎样的一种触感啊。
虽然隔着湿透的T恤和雨衣,但我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她的体温。
她的双臂环过我的脖子,有些发抖。她的胸口紧紧贴着我的肩胛骨,我甚至能感受到她剧烈的心跳。
咚、咚、咚。
和我的心跳重叠在一起。
“抓紧了。”
我双手向后,托住了她的腿弯。
入手是一片滑腻。
那是大腿内侧细腻的皮肤,混合着冰冷的雨水。那一瞬间,我的手指不受控制地陷进了那柔软的肉里。
但我没有心猿意马。或者说,这种极致的亲密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欲望,变成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我深吸一口气,腰部发力,把她稳稳地背了起来。
她比我想象中要重一些。那是长期力量训练带来的肌肉密度。但这重量压在我的身上,却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
就像是蜗牛背上了它的壳。
就像是泥土抱住了它的树。
“走了。”
我低声说了一句,然后迈步走进了那片浑浊的脏水里。
水很冷,已经没过了我的大腿。
但我感觉不到冷。
因为我的背上背着一个小火炉。乔一呼出的热气喷洒在我的脖颈处,痒痒的,热热的。
“沈言……”她在我的耳边小声说,“对不起啊,这么大雨还把你叫出来。”
“没事。”
我在水里艰难地挪动着步子,每一步都要试探水下的虚实,以免踩空或者被杂物绊倒。
“你怎么这么傻啊。”她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声音闷闷的,“万一你也出不去怎么办?”
“出得去。”
我看着前方漆黑的雨幕,语气平静,“只要你在我背上,我就能出去。”
这句话有些暧昧,甚至有些越界。
但在这种环境下,乔一并没有多想。她只是把它当成了患难与共的安慰。
她把手臂收得更紧了一些。
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慢慢放松,那种僵硬的恐惧感正在消退。她开始依赖这个宽阔的背,开始信任这个平日里不起眼的老好人。
我们走出了老体育馆。
外面的风更大了。暴雨打在脸上,几乎睁不开眼。
但我走得很稳。
哪怕脚下的淤泥吸附着我的鞋底,哪怕水里的垃圾撞击着我的小腿,哪怕那股下水道的腥臭味直冲脑门。
我都不在乎。
我甚至享受这种行走。
我在脏水里。而她在我的背上,干干净净,离地三尺。
我是她的底座。
“沈言,你身上好热。”乔一突然说。
“是吗?”
“嗯。像个暖宝宝。”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都快冻僵了。”
说着,她无意识地蹭了蹭我的脖子。
那一瞬间,我的脊椎骨窜过一阵电流。
我想起了苏青的话。
“泥土是没有嘴的。你只能在下面,包裹着她。”
现在,我就在包裹着她。
我托着她大腿的手指,悄悄地用了点力。那紧致的肌肉触感,透过雨水传遍我的全身。
“那个……沈言。”
乔一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或者只是单纯地想要找个话题来驱散恐惧。
“我们要去哪儿?宿舍肯定回不去了,那边地势更低,估计淹得更惨。”
我想了想。
确实,现在的校园就是一片汪洋泽国。女生宿舍在一楼,现在估计已经可以养鱼了。
“去我那儿吧。”
我说。
“我不住校内宿舍。我在西门那边租了个小房子,在二楼。那边地势高,应该没淹。”
这是实话。也是我蓄谋已久的一个念头。
乔一沉默了几秒。
在这个台风夜,孤男寡女,去一个男生的出租屋。
这意味着什么,成年人都懂。
但她看了一眼四周茫茫的黑水,又看了一眼天上不断劈下的闪电。
她没有选择。
“好。”
她把脸贴在我的后背上,声音很轻。
“听你的。”
听到这两个字,我的嘴角在黑暗中不可抑制地上扬。
暴雨还在下。
但我已经感觉不到冷了。
我背着她,背着我的全世界,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那个属于我的、阴暗潮湿的巢穴。
下午三点,京州的天空彻底死了。
那不再是阴天,而是一块巨大的、沉重的铅板,直接压在了头顶上。窗外的世界已经失去了原本的颜色,只剩下灰与黑的混沌。狂风裹挟着暴雨,像是一万台高压水枪同时对着宿舍楼扫射,玻璃窗在框里疯狂颤抖,发出那种濒临破碎的“嗡嗡”声,听得人牙根发酸。
302宿舍里一片死寂,只有老周打游戏的机械键盘声还在噼里啪啦地响,那是他对这场末日唯一的反抗。
突然,“啪”的一声。
世界黑了。
原本昏暗的宿舍瞬间陷入了彻底的黑暗,老周电脑屏幕上的微光也随之熄灭。与此同时,走廊里传来一阵此起彼伏的哀嚎和咒骂声。
“操!停电了!”
“老子的排位赛啊!”
“有没有搞错,这种时候停电?”
空调停止了运作。原本就被密封在室内的闷热空气,瞬间像是失去了枷锁的野兽,开始肆虐。湿度表上的指针早就爆表了,空气里全是汗味、霉味和那种令人窒息的静电感。
我坐在黑暗中,没有出声。
我拿出手机。信号格在两格和无服务之间疯狂跳动。
屏幕的光照亮了我半张脸。我点开微信,班级群里已经炸锅了。
辅导员发了一条标红的全员通知:「@所有人 接学校紧急通知,受超强台风“海葵”影响,校内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电力设施受损。请所有同学待在宿舍,严禁外出!严禁外出!注意安全!」
下面是一连串的“收到”和抱怨。
有人发了几张照片。
那是学校的北门和老校区。黄褐色的泥水已经漫过了路沿石,垃圾桶翻倒在水里,白色的快餐盒和黑色的塑料袋像是一群死鱼,漂浮在水面上。
那是真正的浑浊。
下水道里的秽物、泥土里的腐殖质、城市角落里的垃圾,全都被这场暴雨翻了出来,搅拌在一起。
我盯着那些照片,心里却莫名地感到一种平静。
这不就是世界的本质吗?平时光鲜亮丽,只要一场雨,底下的烂泥就会翻涌上来。
就在这时,手机震动了一下。
不是群消息。
是一个私聊。
我看清那个头像的瞬间,呼吸猛地一滞。
是乔一。
只有一条语音。
我点开,把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
背景音是一片嘈杂的风雨声,大得吓人,几乎盖过了人声。
“……沈言……你在宿舍吗?我有急事……我被困在老体育馆了……水涨得好快……我怕……”
她的声音在发抖。那种平时在球场上大杀四方的霸气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无助女孩的惊恐。
老体育馆。
那是京大最老的一栋建筑,地势极低,就在人工湖旁边。因为设施陈旧,平时很少有人去,只有一些想偷懒不训练的学生会去那里躲着。
她去那儿干什么?
我没时间思考这个问题。
“我在。”
我飞快地回了两个字,手指都在颤抖。
“别怕,找个高的地方待着。我马上来。”
发完这条消息,我把手机塞进防水袋里,挂在脖子上。
“老沈,你去哪儿?”
黑暗中,老周的声音带着一丝惊恐,“辅导员刚说严禁外出,外面水都到小腿了!”
“我去买点蜡烛。”
我随口编了个理由,声音冷静得让自己都觉得可怕。
“你有病啊!这时候买什么蜡烛!”
我不理会身后的叫喊,抓起一件一次性雨衣,推门冲进了黑暗的走廊。
楼道里全是乱窜的学生,手电筒的光束乱晃。我逆着人流,冲下了楼梯。
推开宿舍大门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撞上了一堵墙。
那不是风,那是实体化的空气。狂风夹杂着雨点,像是一把把小刀子,狠狠地割在脸上。
积水已经漫上了台阶。
我一步踏进去。
冷。
刺骨的冷。
那浑浊的黄泥水瞬间灌满了我的鞋子,那是怎样一种触感啊。黏稠、滑腻、带着一股浓烈的下水道腥臭味。枯枝烂叶缠绕在我的脚踝上,像是一只只水鬼的手。
但我没有停。
我就像是一条回到了沼泽的鳄鱼,这种肮脏的环境反而让我感到如鱼得水。
我压低重心,顶着狂风,向着老体育馆的方向艰难跋涉。
路很难走。平时熟悉的校园此刻变成了一片汪洋。路灯都熄灭了,只有时不时划过天际的闪电,能瞬间照亮这片末日般的景象。
树倒了。巨大的梧桐树被连根拔起,横亘在路中间,树根带起一大团黑色的泥土,像是一个个张开的伤口。
我绕过断树,趟过齐膝深的积水。
那个方向没有人。所有人都躲在安全的宿舍里。
只有我。
我在暴雨中狂奔,或者说是在泥水里挪动。
越靠近老体育馆,水越深。
到了人工湖附近,水已经漫到了我的大腿根。这里地势最低,湖水倒灌,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湖。
“乔一!”
我大喊了一声。
声音瞬间被风声吞没。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眯着眼睛,借着下一道闪电的光,看向前方。
老体育馆那扇斑驳的铁门开着。
门口的积水已经快要没过那几级台阶了。
我冲进去。
馆内一片漆黑。因为停电,这里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风从破损的窗户灌进来,发出凄厉的呜咽声。
“乔一!”
我又喊了一声,这次声音在空旷的馆内有了回音。
“沈言?!是你吗?”
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从看台上方传来。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光束扫向声音的来源。
在那排最高层的木质看台上,蜷缩着一个身影。
乔一。
她浑身都湿透了,像是一只落汤鸡。那件我也有一件同款的黑色大T恤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她发抖的身体曲线。她手里紧紧抱着一个防水的球包,那是她的命根子。
看到我的那一刻,她原本紧绷的肩膀瞬间垮了下来,眼泪夺眶而出。
“沈言……我以为我要淹死在这儿了……”
我趟着水,快步走到看台下。
馆内的积水也很深,混杂着淤泥和不知哪里冲来的垃圾。
“没事了。”
我仰起头,看着她。手电筒的光照亮了她苍白的脸。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我昨天把最贵的那把拍子落在这儿了,我想趁着台风没来拿回去,结果……结果水涨得太快了,我出不去了……”
她指了指下面黑黝黝的水面,“下面好像有东西……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撞了我的腿……”
她的眼神里满是恐惧。对于一个在陆地上称王的运动员来说,这种浑浊、未知、淹没一切的水,是最可怕的噩梦。
“别怕,是漂浮的木头或者垃圾。”
我伸出手,“下来。”
乔一犹豫了一下,看着那浑浊的水面,缩了缩脚。
“水太深了……而且好脏……”
她穿着那双宝蓝色指甲油的人字拖,脚趾紧紧扣着台阶的边缘。
“我背你。”
我说。
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
我转过身,背对着她,弯下腰。
“上来。我带你出去。”
乔一愣了一下。
此时此刻,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孤岛里,在这个黑暗、寒冷、充满恐惧的时刻,我是她唯一的救命稻草。
她没有别的选择。
“那……麻烦你了。”
我感觉到身后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
然后,一具温热的、湿漉漉的躯体,贴上了我的后背。
那是怎样的一种触感啊。
虽然隔着湿透的T恤和雨衣,但我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她的体温。
她的双臂环过我的脖子,有些发抖。她的胸口紧紧贴着我的肩胛骨,我甚至能感受到她剧烈的心跳。
咚、咚、咚。
和我的心跳重叠在一起。
“抓紧了。”
我双手向后,托住了她的腿弯。
入手是一片滑腻。
那是大腿内侧细腻的皮肤,混合着冰冷的雨水。那一瞬间,我的手指不受控制地陷进了那柔软的肉里。
但我没有心猿意马。或者说,这种极致的亲密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欲望,变成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我深吸一口气,腰部发力,把她稳稳地背了起来。
她比我想象中要重一些。那是长期力量训练带来的肌肉密度。但这重量压在我的身上,却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
就像是蜗牛背上了它的壳。
就像是泥土抱住了它的树。
“走了。”
我低声说了一句,然后迈步走进了那片浑浊的脏水里。
水很冷,已经没过了我的大腿。
但我感觉不到冷。
因为我的背上背着一个小火炉。乔一呼出的热气喷洒在我的脖颈处,痒痒的,热热的。
“沈言……”她在我的耳边小声说,“对不起啊,这么大雨还把你叫出来。”
“没事。”
我在水里艰难地挪动着步子,每一步都要试探水下的虚实,以免踩空或者被杂物绊倒。
“你怎么这么傻啊。”她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声音闷闷的,“万一你也出不去怎么办?”
“出得去。”
我看着前方漆黑的雨幕,语气平静,“只要你在我背上,我就能出去。”
这句话有些暧昧,甚至有些越界。
但在这种环境下,乔一并没有多想。她只是把它当成了患难与共的安慰。
她把手臂收得更紧了一些。
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慢慢放松,那种僵硬的恐惧感正在消退。她开始依赖这个宽阔的背,开始信任这个平日里不起眼的老好人。
我们走出了老体育馆。
外面的风更大了。暴雨打在脸上,几乎睁不开眼。
但我走得很稳。
哪怕脚下的淤泥吸附着我的鞋底,哪怕水里的垃圾撞击着我的小腿,哪怕那股下水道的腥臭味直冲脑门。
我都不在乎。
我甚至享受这种行走。
我在脏水里。而她在我的背上,干干净净,离地三尺。
我是她的底座。
“沈言,你身上好热。”乔一突然说。
“是吗?”
“嗯。像个暖宝宝。”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都快冻僵了。”
说着,她无意识地蹭了蹭我的脖子。
那一瞬间,我的脊椎骨窜过一阵电流。
我想起了苏青的话。
“泥土是没有嘴的。你只能在下面,包裹着她。”
现在,我就在包裹着她。
我托着她大腿的手指,悄悄地用了点力。那紧致的肌肉触感,透过雨水传遍我的全身。
“那个……沈言。”
乔一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或者只是单纯地想要找个话题来驱散恐惧。
“我们要去哪儿?宿舍肯定回不去了,那边地势更低,估计淹得更惨。”
我想了想。
确实,现在的校园就是一片汪洋泽国。女生宿舍在一楼,现在估计已经可以养鱼了。
“去我那儿吧。”
我说。
“我不住校内宿舍。我在西门那边租了个小房子,在二楼。那边地势高,应该没淹。”
这是实话。也是我蓄谋已久的一个念头。
乔一沉默了几秒。
在这个台风夜,孤男寡女,去一个男生的出租屋。
这意味着什么,成年人都懂。
但她看了一眼四周茫茫的黑水,又看了一眼天上不断劈下的闪电。
她没有选择。
“好。”
她把脸贴在我的后背上,声音很轻。
“听你的。”
听到这两个字,我的嘴角在黑暗中不可抑制地上扬。
暴雨还在下。
但我已经感觉不到冷了。
我背着她,背着我的全世界,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那个属于我的、阴暗潮湿的巢穴。
Ankh发布于 2025-12-22 01:16
Re: 【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
第七章
西门外的城中村地势确实比较高。
当我们终于爬上二楼,站在我那间出租屋的防盗门前时,外面的积水“只”淹到了脚踝。
“到了。”
我把你乔一放下来。
她双脚落地的瞬间,摇晃了一下,下意识地抓住了我的胳膊。长时间的蜷缩和寒冷让她的小腿有些抽筋。
“哎哟……腿软了。”她苦笑了一下,牙齿还在打架,发出细微的咯咯声。
我没说话,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手因为冻僵了有些不听使唤,插了两次才插进锁孔。
“咔哒”。
门开了。
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那是一种长久没人居住的尘封味,混合着老房子特有的潮气和书纸味。对于此刻的我们来说,这股味道意味着“干燥”和“安全”。
“进去吧。”
我推开门,把她让了进去。
屋里一片漆黑。停电的范围显然也波及到了这里。
我关上门,反锁。
那一瞬间,呼啸的风雨声被隔绝在了一层薄薄的铁门之外,变得闷闷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回响。屋里安静得只能听到我们两个沉重的呼吸声,以及衣服上雨水滴落地板的“滴答”声。
“有光吗?”乔一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很脆弱。
“有。”
我摸索着走到书桌旁,拉开抽屉。
作为这里的主人,我对每一件物品的位置都了如指掌。
“擦。”
火柴划燃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脆。
一团橘黄色的小火苗跳了出来,随即点燃了一根白色的蜡烛。
光晕荡开。
昏黄的烛光并不明亮,只能照亮这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单间。墙壁上贴着几张泛黄的电影海报,一张单人床,一张堆满书的桌子,还有一个简易的布衣柜。
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射在墙上,随着烛火的摇曳而晃动。
我转过身,看向乔一。
她站在门口,浑身湿透,头发贴在脸上,狼狈不堪。那双平时充满活力的眼睛此刻有些失神,那是应激反应后的疲惫。她的脚——那双穿着人字拖的脚,此刻糊满了黑色的淤泥,甚至小腿上还挂着几根不知从哪儿沾来的水草。
“先换衣服。”
我打破了沉默。
我走到衣柜前,拿出一件我平时当睡衣穿的纯棉T恤,还有一条宽松的大裤衩。
“新的内裤没有。你……先挂空挡吧。”我说这话的时候,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像是在讨论天气,“反正这衣服够大,能遮住。”
乔一接过衣服,脸在烛光下微微红了一下,但并没有矫情。
“谢谢。这救命之恩我记下了。”
“卫生间在那边。”我指了指角落里那扇磨砂玻璃门,“但我估计没热水,电热水器用不了。”
“没事,擦擦就行。我现在只想把这身湿衣服扒下来。”
乔一拿着衣服钻进了卫生间。
很快,里面传来了悉悉索索的脱衣声,还有拧毛巾的水声。
我站在原地,听着那些声音。
每一声都像是某种暗示。
但我没有动。我转身去阳台那个小角落改造的厨房。虽然没电,但我这里有个户外的卡式炉。
“啪。”
我打着火。蓝色的火苗舔舐着不锈钢水壶的底部。
我想烧点热水。
这种天气,不泡个脚,寒气会入骨。对于运动员来说,身体是本钱,这一双腿要是受凉废了,比杀了她还难受。
十分钟后。
卫生间的门开了。
乔一走了出来。
她穿着我的灰色T恤。那衣服穿在我身上也就是合身,但在她身上就像是一条裙子,下摆一直垂到了大腿中部。那是纯棉的面料,已经被我洗得发白,软软地贴在她刚刚擦干的皮肤上。
她光着脚。
那双人字拖被她扔在了卫生间门口。
“沈言,你这儿有吃的吗?我快饿晕了。”她一边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走到床边坐下。
“有泡面。”
我也把水烧好了。
我先把泡面泡上,盖上书压好。
然后,我端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脸盆走了过来。盆里冒着热气,那是刚刚烧开的水兑了凉水,温度正好。
“先别吃。”
我把盆放在她脚边。
“把脚洗了。”
乔一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缩了缩脚。
“我自己来就行……”
“你手上有伤。”我指了指她的手背。那里有一道划痕,大概是在老体育馆爬看台时被什么东西刮破的,刚才在烛光下不明显,现在看来还在往外渗血珠。
“别沾水了,感染了麻烦。”
我蹲下来。
在这个狭小的、只有烛光的房间里,我的姿态放得很低。
“抬脚。”
乔一犹豫了两秒,看了看自己那双在泥水里泡过的、脏兮兮的脚,又看了看我平静的脸。
在这个台风夜,在她最狼狈的时候,所有的防备似乎都显得多余。
她慢慢地抬起左脚。
我伸出手,托住她的脚踝。
入手冰凉。
那是失温的触感。皮肤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泥沙,摸起来粗糙、硌手。
我把她的脚放进热水里。
“嘶……”
乔一发出一声舒服的叹息,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一样,软软地靠在了床头的墙上,“好暖和……”
我没有说话。
我挽起袖子,把手伸进浑浊的水里。
指尖触碰到她冰冷的脚背。
我开始帮她清洗。
动作很轻,很慢。
我的大拇指推过她的脚弓,那里因为长期训练而紧绷的肌肉此刻在热水中慢慢松弛下来。
我摸到了她脚底的老茧。
那层薄薄的、淡黄色的角质层,在热水的浸泡下变得有些发软。我用指腹轻轻摩挲着那里,感受着那种粗糙的纹理。
那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水很快就变脏了。
原本清澈的热水,变成了黑褐色。那是京州的泥土,是老体育馆积水里的污垢,现在都溶解在了这盆水里。
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脏。
相反,我觉得这是一种……融合。
“沈言。”
乔一突然开口,声音有些哑,“你以前……给别人洗过脚吗?”
我的手顿了一下。
“没有。”
“那你怎么这么熟练?”她低头看着我,眼神在烛光下显得有些迷离,“感觉像是练过一样。”
“因为是你。”
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
说出来之后,空气凝固了一秒。
但我并没有慌张。在这个特殊的夜晚,在这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空间里,这句话可以被解读为暧昧,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单纯的、极致的友谊。
果然,乔一笑了。
“够义气。”她动了动脚趾,在我的手心里挠了一下,“没白交你这个朋友。”
朋友。
这个词像是一道安全的屏障,把所有的越界都挡在了外面。
我没反驳。
我继续洗着她的右脚。
洗掉泥沙,洗掉水草,洗掉那些属于外部世界的肮脏。
当我把她的脚从水里捞出来的时候,它们已经恢复了原本的颜色。白皙,透着淡淡的粉红,因为热水的浸泡而冒着热气。
我拿过一条干净的干毛巾。
把她的脚放在我的膝盖上。
细致地擦干每一滴水。脚趾缝,脚踝窝,每一个褶皱都不放过。
这一刻,我是虔诚的。
就像是一个工匠在擦拭他最得意的作品。
“好了。”
我松开手,把毛巾扔进脏水盆里。
“面应该泡好了,吃吧。”
乔一收回脚,盘腿坐在床上,端起那碗红烧牛肉面。
“真香啊……”
她大口大口地吃着,毫无吃相。热气熏蒸着她的脸,让她的脸颊泛起健康的红晕。
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看着她。
看着她穿着我的T恤,光着脚,坐在我的床上,吃着我的泡面。
这一幕,比任何春梦都要让我满足。
因为这是真实的。
她是真实的。
她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女神,而是一个会饿、会冷、脚上会有泥的活人。
而我,是那个把她从泥潭里背出来,又把她洗干净的人。
“沈言,今晚我睡哪儿?”
吃完面,乔一打了个饱嗝,有些困倦地揉了揉眼睛。
“你睡床。”
我指了指地板,“我打地铺。”
“那多不好意思……”
“没事,我有防潮垫。”
我站起来,开始收拾地上的残局。
我端起那盆洗脚水。
水很浑,很黑,还在冒着微弱的热气。
我走向卫生间。
但在倒掉它之前,我停下了脚步。
我在黑暗的卫生间里,低头看着那一盆浑水。
水面上漂浮着一层淡淡的油花,那是凡士林被热水融化后的痕迹。
还有那股味道。
泥土味,汗味,还有……她的味道。
我没有倒掉它。
我把它放在了马桶边。
今晚,这盆水也会留在这里。
回到房间时,乔一已经躺下了。她太累了,几乎是沾枕头就睡着了。
烛光还在摇曳。
我吹灭了蜡烛。
房间陷入了彻底的黑暗。
我躺在硬邦邦的地板上,听着外面狂暴的风雨声,听着床上乔一均匀的呼吸声。
那是世界上最动听的二重奏。
我伸出手,在虚空中描绘着那个躺在床上的人的轮廓。
这个只有二十平米的出租屋,今晚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这里藏着一朵花,和一堆心满意足的泥土。
西门外的城中村地势确实比较高。
当我们终于爬上二楼,站在我那间出租屋的防盗门前时,外面的积水“只”淹到了脚踝。
“到了。”
我把你乔一放下来。
她双脚落地的瞬间,摇晃了一下,下意识地抓住了我的胳膊。长时间的蜷缩和寒冷让她的小腿有些抽筋。
“哎哟……腿软了。”她苦笑了一下,牙齿还在打架,发出细微的咯咯声。
我没说话,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手因为冻僵了有些不听使唤,插了两次才插进锁孔。
“咔哒”。
门开了。
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那是一种长久没人居住的尘封味,混合着老房子特有的潮气和书纸味。对于此刻的我们来说,这股味道意味着“干燥”和“安全”。
“进去吧。”
我推开门,把她让了进去。
屋里一片漆黑。停电的范围显然也波及到了这里。
我关上门,反锁。
那一瞬间,呼啸的风雨声被隔绝在了一层薄薄的铁门之外,变得闷闷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回响。屋里安静得只能听到我们两个沉重的呼吸声,以及衣服上雨水滴落地板的“滴答”声。
“有光吗?”乔一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很脆弱。
“有。”
我摸索着走到书桌旁,拉开抽屉。
作为这里的主人,我对每一件物品的位置都了如指掌。
“擦。”
火柴划燃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脆。
一团橘黄色的小火苗跳了出来,随即点燃了一根白色的蜡烛。
光晕荡开。
昏黄的烛光并不明亮,只能照亮这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单间。墙壁上贴着几张泛黄的电影海报,一张单人床,一张堆满书的桌子,还有一个简易的布衣柜。
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射在墙上,随着烛火的摇曳而晃动。
我转过身,看向乔一。
她站在门口,浑身湿透,头发贴在脸上,狼狈不堪。那双平时充满活力的眼睛此刻有些失神,那是应激反应后的疲惫。她的脚——那双穿着人字拖的脚,此刻糊满了黑色的淤泥,甚至小腿上还挂着几根不知从哪儿沾来的水草。
“先换衣服。”
我打破了沉默。
我走到衣柜前,拿出一件我平时当睡衣穿的纯棉T恤,还有一条宽松的大裤衩。
“新的内裤没有。你……先挂空挡吧。”我说这话的时候,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像是在讨论天气,“反正这衣服够大,能遮住。”
乔一接过衣服,脸在烛光下微微红了一下,但并没有矫情。
“谢谢。这救命之恩我记下了。”
“卫生间在那边。”我指了指角落里那扇磨砂玻璃门,“但我估计没热水,电热水器用不了。”
“没事,擦擦就行。我现在只想把这身湿衣服扒下来。”
乔一拿着衣服钻进了卫生间。
很快,里面传来了悉悉索索的脱衣声,还有拧毛巾的水声。
我站在原地,听着那些声音。
每一声都像是某种暗示。
但我没有动。我转身去阳台那个小角落改造的厨房。虽然没电,但我这里有个户外的卡式炉。
“啪。”
我打着火。蓝色的火苗舔舐着不锈钢水壶的底部。
我想烧点热水。
这种天气,不泡个脚,寒气会入骨。对于运动员来说,身体是本钱,这一双腿要是受凉废了,比杀了她还难受。
十分钟后。
卫生间的门开了。
乔一走了出来。
她穿着我的灰色T恤。那衣服穿在我身上也就是合身,但在她身上就像是一条裙子,下摆一直垂到了大腿中部。那是纯棉的面料,已经被我洗得发白,软软地贴在她刚刚擦干的皮肤上。
她光着脚。
那双人字拖被她扔在了卫生间门口。
“沈言,你这儿有吃的吗?我快饿晕了。”她一边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走到床边坐下。
“有泡面。”
我也把水烧好了。
我先把泡面泡上,盖上书压好。
然后,我端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脸盆走了过来。盆里冒着热气,那是刚刚烧开的水兑了凉水,温度正好。
“先别吃。”
我把盆放在她脚边。
“把脚洗了。”
乔一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缩了缩脚。
“我自己来就行……”
“你手上有伤。”我指了指她的手背。那里有一道划痕,大概是在老体育馆爬看台时被什么东西刮破的,刚才在烛光下不明显,现在看来还在往外渗血珠。
“别沾水了,感染了麻烦。”
我蹲下来。
在这个狭小的、只有烛光的房间里,我的姿态放得很低。
“抬脚。”
乔一犹豫了两秒,看了看自己那双在泥水里泡过的、脏兮兮的脚,又看了看我平静的脸。
在这个台风夜,在她最狼狈的时候,所有的防备似乎都显得多余。
她慢慢地抬起左脚。
我伸出手,托住她的脚踝。
入手冰凉。
那是失温的触感。皮肤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泥沙,摸起来粗糙、硌手。
我把她的脚放进热水里。
“嘶……”
乔一发出一声舒服的叹息,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一样,软软地靠在了床头的墙上,“好暖和……”
我没有说话。
我挽起袖子,把手伸进浑浊的水里。
指尖触碰到她冰冷的脚背。
我开始帮她清洗。
动作很轻,很慢。
我的大拇指推过她的脚弓,那里因为长期训练而紧绷的肌肉此刻在热水中慢慢松弛下来。
我摸到了她脚底的老茧。
那层薄薄的、淡黄色的角质层,在热水的浸泡下变得有些发软。我用指腹轻轻摩挲着那里,感受着那种粗糙的纹理。
那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水很快就变脏了。
原本清澈的热水,变成了黑褐色。那是京州的泥土,是老体育馆积水里的污垢,现在都溶解在了这盆水里。
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脏。
相反,我觉得这是一种……融合。
“沈言。”
乔一突然开口,声音有些哑,“你以前……给别人洗过脚吗?”
我的手顿了一下。
“没有。”
“那你怎么这么熟练?”她低头看着我,眼神在烛光下显得有些迷离,“感觉像是练过一样。”
“因为是你。”
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
说出来之后,空气凝固了一秒。
但我并没有慌张。在这个特殊的夜晚,在这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空间里,这句话可以被解读为暧昧,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单纯的、极致的友谊。
果然,乔一笑了。
“够义气。”她动了动脚趾,在我的手心里挠了一下,“没白交你这个朋友。”
朋友。
这个词像是一道安全的屏障,把所有的越界都挡在了外面。
我没反驳。
我继续洗着她的右脚。
洗掉泥沙,洗掉水草,洗掉那些属于外部世界的肮脏。
当我把她的脚从水里捞出来的时候,它们已经恢复了原本的颜色。白皙,透着淡淡的粉红,因为热水的浸泡而冒着热气。
我拿过一条干净的干毛巾。
把她的脚放在我的膝盖上。
细致地擦干每一滴水。脚趾缝,脚踝窝,每一个褶皱都不放过。
这一刻,我是虔诚的。
就像是一个工匠在擦拭他最得意的作品。
“好了。”
我松开手,把毛巾扔进脏水盆里。
“面应该泡好了,吃吧。”
乔一收回脚,盘腿坐在床上,端起那碗红烧牛肉面。
“真香啊……”
她大口大口地吃着,毫无吃相。热气熏蒸着她的脸,让她的脸颊泛起健康的红晕。
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看着她。
看着她穿着我的T恤,光着脚,坐在我的床上,吃着我的泡面。
这一幕,比任何春梦都要让我满足。
因为这是真实的。
她是真实的。
她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女神,而是一个会饿、会冷、脚上会有泥的活人。
而我,是那个把她从泥潭里背出来,又把她洗干净的人。
“沈言,今晚我睡哪儿?”
吃完面,乔一打了个饱嗝,有些困倦地揉了揉眼睛。
“你睡床。”
我指了指地板,“我打地铺。”
“那多不好意思……”
“没事,我有防潮垫。”
我站起来,开始收拾地上的残局。
我端起那盆洗脚水。
水很浑,很黑,还在冒着微弱的热气。
我走向卫生间。
但在倒掉它之前,我停下了脚步。
我在黑暗的卫生间里,低头看着那一盆浑水。
水面上漂浮着一层淡淡的油花,那是凡士林被热水融化后的痕迹。
还有那股味道。
泥土味,汗味,还有……她的味道。
我没有倒掉它。
我把它放在了马桶边。
今晚,这盆水也会留在这里。
回到房间时,乔一已经躺下了。她太累了,几乎是沾枕头就睡着了。
烛光还在摇曳。
我吹灭了蜡烛。
房间陷入了彻底的黑暗。
我躺在硬邦邦的地板上,听着外面狂暴的风雨声,听着床上乔一均匀的呼吸声。
那是世界上最动听的二重奏。
我伸出手,在虚空中描绘着那个躺在床上的人的轮廓。
这个只有二十平米的出租屋,今晚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这里藏着一朵花,和一堆心满意足的泥土。
Ankh发布于 2025-12-22 22:19
Re: 【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
第八章
台风过境后的清晨,京州的天空呈现出一种被漂白过度后的惨淡青灰色。
我是被一种极度细微的声音吵醒的。那是屋檐上积聚的雨水,顺着生锈的排水管滴落在楼下铁皮雨棚上的声音。节奏单调,却像是在给这个劫后余生的城市进行某种催眠。
我睁开眼,视线有些模糊。发霉的天花板上,几块剥落的墙皮在微风中摇摇欲坠。空气里依然弥漫着那种潮湿到能拧出水来的水汽,但已经没有了昨晚那种令人窒息的低气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暴雨洗刷过后的、带着泥腥味的清冽。
地板很硬,防潮垫并没有起到太大的缓冲作用,我的脊背有些发酸。但我没有动,甚至连呼吸的频率都不敢改变。
因为我听到了床上的动静。
在那张铺着淡蓝色床单的单人床上,乔一还在睡。
她侧身向外,半张脸埋在那个有些塌陷的枕头里,呼吸绵长而均匀。昨晚那件灰色的宽大T恤随着她的睡姿卷上去了一些,露出了一截柔韧紧致的腰线,皮肤在清晨微弱的光线下泛着瓷白色的光泽。
被子被她踢掉了一半,一条修长的小腿悬在床边。
那是她的左脚。
昨晚在昏暗摇曳的烛光下,我并没有看真切。而此刻,在清晨这种毫无修饰的自然光下,这双脚就像是一件静置在展台上的艺术品,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我的视野里。
38码,并不算小,但因为足弓极高,整个脚型被拉得修长而挺拔。从脚踝到脚尖的线条流畅得惊人,像是一张蓄势待发的弓。脚背上的皮肤很薄,能清晰地看到淡青色的血管蜿蜒其下,那是生命力在流动的证明。
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脚趾。
那一抹亮眼的宝蓝色,在有些昏暗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妖冶。
那是她在台风来临前涂的指甲油。经过了昨晚泥水的浸泡和刷洗,边缘处已经微微有些剥落,露出了一点点底下原本的指甲颜色。但这种残缺感并没有破坏美感,反而带着一种经历过风雨后的真实。
那一抹深邃的蓝,衬得她的脚背更加白皙,也更加具有一种隐秘的色气。
我微微侧过头,视线贪婪地在她的脚底游走。
在前脚掌和脚后跟的着力点,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硬皮。那不是我想象中发黄的老茧,而是一层像是精心烧制的透明釉质。它们紧紧贴合在红润的肌理上,在晨光下泛着一点点柔和的哑光。
这层薄茧就像是战士的铠甲,保护着她那双能在球场上飞翔的脚。
我看着那微微内扣的小脚趾,看着那抹残缺的宝蓝色。
一股强烈的冲动在我的指尖蔓延。
我想伸出手,用手指去触碰那层半透明的薄茧。我想知道那种触感是不是像我想象中那样,带着一点点丝绸背面的阻尼感?我想知道那里的温度是不是比其他地方更热一些?
我的手在防潮垫上慢慢移动,像一只潜行的蜘蛛,一点点靠近床沿。
五厘米。三厘米。
就在我的指尖即将触碰到她悬在半空中的脚后跟时。
“嗯……”
床上的人突然翻了个身。
乔一发出了一声慵懒的鼻音,整个人缩成了一团,那只带着宝蓝色趾甲的脚也随之收回了被子里。
我触电般地缩回手,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撞击着,仿佛要跳出嗓子眼。
好险。
如果刚才碰到了,如果她醒了,昨晚建立起来的一切默契和信任,可能会在那一瞬间崩塌。
我闭上眼,强迫自己平复呼吸,装作还在熟睡的样子。
几分钟后,床板发出一声轻响。
乔一醒了。
我听到她伸懒腰时关节发出的轻微脆响,听到她迷迷糊糊地嘟囔着“几点了”,听到她赤脚踩在地板上的声音。
啪嗒,啪嗒。
那声音很轻,带着一种令人心痒的私密感。
她似乎走到了我身边,停顿了几秒。我能感觉到一道视线落在我的脸上,带着探究,或许还有一丝昨晚残留的温情。
但我没敢睁眼。
接着是卫生间门被推开的声音,马桶冲水的声音,水龙头流水的哗哗声。
这些平时听起来极其琐碎、甚至有些粗俗的生活噪音,此刻在这个狭小的出租屋里,却交织成了一种让人沉溺的亲密幻觉。
这就好像……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很久一样。
等到卫生间的水声停止,我才假装刚刚醒来,揉着眼睛坐起身。
“醒了?”
乔一正站在镜子前整理头发。她依然穿着我那件大T恤,下摆遮住了大腿根部,露出的两条腿笔直修长。她的脸上还带着刚洗完脸的水珠,素颜干净得让人挪不开眼。
“嗯。早。”
我的声音有些沙哑,不知道是因为没睡好,还是因为刚才那场未遂的偷袭。
“早个屁,都九点了。”乔一转过头,冲我咧嘴一笑,笑容里没有丝毫的尴尬,“你这儿连把梳子都没有,我这头发都快成鸡窝了。”
“我有把酒店带回来的一次性梳子,你要吗?”我从抽屉里翻出一把白色的塑料梳子。
“凑合用吧。”
她接过梳子,随意地梳了几下,然后把长发扎成了一个高马尾。
那个动作露出了她修长的脖颈和锁骨。T恤的领口有些大,随着她的动作滑落向一边,露出一大片雪白的皮肤。
我迅速移开视线,低头去收拾地上的防潮垫。
“饿死了,走,回学校吃饭去。”乔一拍了拍肚子,“昨晚那碗泡面根本不顶饿。”
回学校的路并不好走。
虽然积水已经退去,但西门外的这条小路依然泥泞不堪。黑色的淤泥混合着烂菜叶、断树枝,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
乔一换回了她昨天的衣服——那条牛仔短裤和黑T恤。但鞋子还是那双人字拖。
她走得很小心。
那双刚刚洗干净的脚,此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泥泞中寻找落脚点。那十个涂着宝蓝色指甲油的脚趾紧紧扣着人字拖的底板,在灰暗的泥路上显得格外醒目。
“小心。”
在一个积水坑前,我自然地伸出手。
乔一也没有矫情,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她的手心很热,很有力。借着我的力道,她轻盈地跳过了那个水坑。
“谢了。”
她松开手,但并没有完全拉开距离。
我们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走着。路很窄,偶尔有积水的车驶过,我会下意识地把她拉到里侧,用身体挡住飞溅的泥点。
这种沉默的互动一直持续到宿舍楼下。
女生宿舍楼门口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热闹。进进出出的女生们都在讨论着这场台风,宿管阿姨正在大声指挥着清理门口的淤泥。
“那个……”
乔一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
她的眼神有些闪烁,似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衣服我洗干净了再还你。”她指了指身上套在外面的那件黑色T恤,那是她昨天自己的衣服,而我的那件灰色睡衣此刻正穿在她里面。
“不急。”我说,“那件灰色的你留着当睡衣也行。”
乔一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想得美,那是你的味道,我穿着睡觉算怎么回事。”
这句话一出口,我们两个都愣住了。
空气中那种暧昧的张力瞬间拉满。
乔一的耳根迅速红了。她有些慌乱地拨弄了一下刘海,掩饰着刚才那句过于亲密的玩笑。
“那个……晚上有空吗?”她赶紧转移话题。
“有。”
“晚上八点,操场见?我想去跑跑步,出出汗。这两天闷在屋里都要发霉了。”
“好。我等你。”
“那……拜拜。”
她冲我挥挥手,转身跑进了宿舍楼。那双宝蓝色指甲油的脚在台阶上一闪而过,像是一尾灵活的鱼。
回到男生宿舍,老周正在阳台上对着那一堆重新搬回来的杂物发愁。
“老沈你昨晚死哪儿去了?电话也打不通,我都以为你被冲走了。”老周看到我,立刻开始抱怨。
“去避难了。”
我把背包扔在床上,整个人瘫倒在凉席上。
身体很累,脊背酸痛,但精神却处于一种极其亢奋的状态。
我的鼻尖仿佛还残留着清晨那种潮湿的空气味,指尖还残留着她手腕的温度。
我闭上眼。
脑海里全是那一双在晨光下泛着微光的脚,以及那一抹妖冶的宝蓝色。
今晚。
一定要再看一次。
晚上八点,北操场。
因为刚下过雨,塑胶跑道还是湿漉漉的,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橡胶味。但这并不妨碍那些憋了两天的情侣们出来透气。看台的阴影里,跑道的角落里,到处都是依偎在一起的身影。
我和乔一并肩走在最外圈的跑道上。
她换回了平时的打扮,不再是那双不跟脚的人字拖,而是穿回了那双熟悉的、旧旧的白色AF1。上身是一件修身的白色运动短袖,下身是黑色的紧身运动裤。
头发扎成了丸子头,露出光洁的额头。
我们走得很慢。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聊台风,聊被淹的老体育馆,聊这周即将恢复的训练。
但我知道,我们都在等。
等一个契机,等一个突破口。
走到操场那个光线最昏暗的弯道处时,乔一突然停了下来。
“哎呀。”
她低呼了一声,脚步踉跄了一下。
“怎么了?”我立刻紧张地看向她。
“鞋带开了。”
她指了指自己的左脚。
那只AF1的鞋带不知何时散开了,长长的鞋带拖在湿漉漉的塑胶跑道上,已经沾满了黑色的橡胶颗粒和积水。
“别动。”
这两个字几乎是没经过大脑思考就说了出来。
还没等她弯腰,我已经极其自然地、顺从地蹲了下去。
在这个姿势下,我又回到了我最熟悉、也最舒适的位置——她的脚下。
我单膝跪在湿漉漉的跑道上。膝盖处的布料瞬间被积水浸透,传来一阵冰凉的触感。
但我根本不在乎。
我的视线平齐于她的鞋面。
那双白色的AF1就在我眼前。鞋面的折痕里藏着细微的灰尘,那是她走过的路的证明。
我伸出手,捏起那根沾了水的鞋带。
湿湿的,凉凉的,还带着一点橡胶的涩感。
我小心翼翼地把上面的黑色颗粒抖掉。
我的动作很慢,慢得像是在进行某种精密的拆弹作业。
我能感觉到乔一正低着头看我。她的目光像是有重量一样,落在我的发顶,落在我的后颈。
我把鞋带交叉,拉紧。
透过鞋舌并没有完全闭合的缝隙,我隐约能看到里面白色的棉袜。
我想象着在那层棉袜之下,就是那双有着宝蓝色指甲的脚。此刻,它们正被包裹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温热、柔软、充满生机。
我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但我没有立刻站起来。
我依然保持着单膝跪地的姿势,双手轻轻搭在她的鞋面上。
指腹传来皮革微凉而粗糙的触感。
那一瞬间,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想要低下头,把脸贴在那个鞋面上的冲动。
但我克制住了。
我抬起头。
逆着操场边路灯昏黄的光晕,我看不清乔一的表情。但我能看到她的眼睛,那双平日里总是神采飞扬的眼睛,此刻正亮得惊人,里面倒映着我卑微的身影。
“沈言。”
她的声音很轻,被晚风吹得有些破碎。
“嗯?”
“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这么好?”
这个问题,她终于问出口了。
为什么帮我洗那双恶心的奶茶袜?为什么冒着台风背我趟过脏水?为什么像现在这样,毫无怨言地跪在泥水里帮我系鞋带?
我看着她。
我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露出一个我练习过无数次的、温和无害的笑容。
“因为不想看你摔跤。”
这句回答很简单。
但对于刚刚经历过那场暴雨、在那座孤岛上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乔一来说,这就够了。
她愣了一下。
下一秒,她突然弯下腰。
一阵带着柠檬草香气的风扑面而来。
那是她洗发水的味道,也是她身上那种干净、热烈、混合着淡淡汗味的少女气息。
柔软的触感印在了我的嘴唇上。
是一个吻。
很轻,很快,像是一只蝴蝶停在了花瓣上。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周围操场上的喧嚣声、远处广播台的音乐声、脚下积水的声音,在这一刻全部消失了。
世界只剩下嘴唇上那一点残留的温度,以及那一瞬间,她发梢扫过我脸颊时的微痒。
她亲了我。
在我跪在她脚边,手里还捏着她鞋带的时候。
这个吻没有任何的情欲色彩,甚至算不上是接吻,只是嘴唇与嘴唇的一次触碰。
但它像是一个烙印。
乔一迅速直起腰,脸红得像是熟透的番茄。她在夜色中显得有些慌乱,不敢看我的眼睛,手足无措地抓了抓衣角。
“那个……算是……昨晚的利息!”
她结结巴巴地丢下这句话,声音都在抖。
然后转身就跑。
“快点跟上!别傻跪着了!冷死了!”
她跑出几米远,又回过头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羞涩和欢快。
“来了。”
我撑着膝盖站起来,湿透的裤管冰冷地贴在腿上,随着动作滴答滴答地往下淌水。
那是刚才跪在积水里的代价。
但我并不觉得难受。我抬起手,指尖无意识地碰了一下嘴唇。那里已经凉了,但那股柠檬草的香气似乎还固执地停留在鼻尖,并没有被操场上的橡胶味盖过去。
前方,乔一已经跑进了路灯的光晕里。
那双白色的AF1在湿漉漉的跑道上起起落落,每一步都溅起细小的水花。她的马尾辫在脑后一甩一甩的,整个人像是要融化在那些昏黄的光线里。
我迈开步子,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
我没有试图追上她并肩而行,也没有刻意拉开距离。
我只是盯着地面,看着她被路灯拉得长长的影子投射在积水上。
我踩着那个影子的头部,一步,两步。
脚下的积水发出“啪嗒、啪嗒”的轻响,正好和前面那个轻快的脚步声重叠在一起。
操场上的风很大,吹干了我额头上的汗。
我插着兜,就这样跟在那个白色的背影后面,在这个潮湿的夜晚,一直走到了灯光最暗的地方。
台风过境后的清晨,京州的天空呈现出一种被漂白过度后的惨淡青灰色。
我是被一种极度细微的声音吵醒的。那是屋檐上积聚的雨水,顺着生锈的排水管滴落在楼下铁皮雨棚上的声音。节奏单调,却像是在给这个劫后余生的城市进行某种催眠。
我睁开眼,视线有些模糊。发霉的天花板上,几块剥落的墙皮在微风中摇摇欲坠。空气里依然弥漫着那种潮湿到能拧出水来的水汽,但已经没有了昨晚那种令人窒息的低气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暴雨洗刷过后的、带着泥腥味的清冽。
地板很硬,防潮垫并没有起到太大的缓冲作用,我的脊背有些发酸。但我没有动,甚至连呼吸的频率都不敢改变。
因为我听到了床上的动静。
在那张铺着淡蓝色床单的单人床上,乔一还在睡。
她侧身向外,半张脸埋在那个有些塌陷的枕头里,呼吸绵长而均匀。昨晚那件灰色的宽大T恤随着她的睡姿卷上去了一些,露出了一截柔韧紧致的腰线,皮肤在清晨微弱的光线下泛着瓷白色的光泽。
被子被她踢掉了一半,一条修长的小腿悬在床边。
那是她的左脚。
昨晚在昏暗摇曳的烛光下,我并没有看真切。而此刻,在清晨这种毫无修饰的自然光下,这双脚就像是一件静置在展台上的艺术品,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我的视野里。
38码,并不算小,但因为足弓极高,整个脚型被拉得修长而挺拔。从脚踝到脚尖的线条流畅得惊人,像是一张蓄势待发的弓。脚背上的皮肤很薄,能清晰地看到淡青色的血管蜿蜒其下,那是生命力在流动的证明。
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脚趾。
那一抹亮眼的宝蓝色,在有些昏暗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妖冶。
那是她在台风来临前涂的指甲油。经过了昨晚泥水的浸泡和刷洗,边缘处已经微微有些剥落,露出了一点点底下原本的指甲颜色。但这种残缺感并没有破坏美感,反而带着一种经历过风雨后的真实。
那一抹深邃的蓝,衬得她的脚背更加白皙,也更加具有一种隐秘的色气。
我微微侧过头,视线贪婪地在她的脚底游走。
在前脚掌和脚后跟的着力点,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硬皮。那不是我想象中发黄的老茧,而是一层像是精心烧制的透明釉质。它们紧紧贴合在红润的肌理上,在晨光下泛着一点点柔和的哑光。
这层薄茧就像是战士的铠甲,保护着她那双能在球场上飞翔的脚。
我看着那微微内扣的小脚趾,看着那抹残缺的宝蓝色。
一股强烈的冲动在我的指尖蔓延。
我想伸出手,用手指去触碰那层半透明的薄茧。我想知道那种触感是不是像我想象中那样,带着一点点丝绸背面的阻尼感?我想知道那里的温度是不是比其他地方更热一些?
我的手在防潮垫上慢慢移动,像一只潜行的蜘蛛,一点点靠近床沿。
五厘米。三厘米。
就在我的指尖即将触碰到她悬在半空中的脚后跟时。
“嗯……”
床上的人突然翻了个身。
乔一发出了一声慵懒的鼻音,整个人缩成了一团,那只带着宝蓝色趾甲的脚也随之收回了被子里。
我触电般地缩回手,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撞击着,仿佛要跳出嗓子眼。
好险。
如果刚才碰到了,如果她醒了,昨晚建立起来的一切默契和信任,可能会在那一瞬间崩塌。
我闭上眼,强迫自己平复呼吸,装作还在熟睡的样子。
几分钟后,床板发出一声轻响。
乔一醒了。
我听到她伸懒腰时关节发出的轻微脆响,听到她迷迷糊糊地嘟囔着“几点了”,听到她赤脚踩在地板上的声音。
啪嗒,啪嗒。
那声音很轻,带着一种令人心痒的私密感。
她似乎走到了我身边,停顿了几秒。我能感觉到一道视线落在我的脸上,带着探究,或许还有一丝昨晚残留的温情。
但我没敢睁眼。
接着是卫生间门被推开的声音,马桶冲水的声音,水龙头流水的哗哗声。
这些平时听起来极其琐碎、甚至有些粗俗的生活噪音,此刻在这个狭小的出租屋里,却交织成了一种让人沉溺的亲密幻觉。
这就好像……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很久一样。
等到卫生间的水声停止,我才假装刚刚醒来,揉着眼睛坐起身。
“醒了?”
乔一正站在镜子前整理头发。她依然穿着我那件大T恤,下摆遮住了大腿根部,露出的两条腿笔直修长。她的脸上还带着刚洗完脸的水珠,素颜干净得让人挪不开眼。
“嗯。早。”
我的声音有些沙哑,不知道是因为没睡好,还是因为刚才那场未遂的偷袭。
“早个屁,都九点了。”乔一转过头,冲我咧嘴一笑,笑容里没有丝毫的尴尬,“你这儿连把梳子都没有,我这头发都快成鸡窝了。”
“我有把酒店带回来的一次性梳子,你要吗?”我从抽屉里翻出一把白色的塑料梳子。
“凑合用吧。”
她接过梳子,随意地梳了几下,然后把长发扎成了一个高马尾。
那个动作露出了她修长的脖颈和锁骨。T恤的领口有些大,随着她的动作滑落向一边,露出一大片雪白的皮肤。
我迅速移开视线,低头去收拾地上的防潮垫。
“饿死了,走,回学校吃饭去。”乔一拍了拍肚子,“昨晚那碗泡面根本不顶饿。”
回学校的路并不好走。
虽然积水已经退去,但西门外的这条小路依然泥泞不堪。黑色的淤泥混合着烂菜叶、断树枝,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
乔一换回了她昨天的衣服——那条牛仔短裤和黑T恤。但鞋子还是那双人字拖。
她走得很小心。
那双刚刚洗干净的脚,此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泥泞中寻找落脚点。那十个涂着宝蓝色指甲油的脚趾紧紧扣着人字拖的底板,在灰暗的泥路上显得格外醒目。
“小心。”
在一个积水坑前,我自然地伸出手。
乔一也没有矫情,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她的手心很热,很有力。借着我的力道,她轻盈地跳过了那个水坑。
“谢了。”
她松开手,但并没有完全拉开距离。
我们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走着。路很窄,偶尔有积水的车驶过,我会下意识地把她拉到里侧,用身体挡住飞溅的泥点。
这种沉默的互动一直持续到宿舍楼下。
女生宿舍楼门口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热闹。进进出出的女生们都在讨论着这场台风,宿管阿姨正在大声指挥着清理门口的淤泥。
“那个……”
乔一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
她的眼神有些闪烁,似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衣服我洗干净了再还你。”她指了指身上套在外面的那件黑色T恤,那是她昨天自己的衣服,而我的那件灰色睡衣此刻正穿在她里面。
“不急。”我说,“那件灰色的你留着当睡衣也行。”
乔一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想得美,那是你的味道,我穿着睡觉算怎么回事。”
这句话一出口,我们两个都愣住了。
空气中那种暧昧的张力瞬间拉满。
乔一的耳根迅速红了。她有些慌乱地拨弄了一下刘海,掩饰着刚才那句过于亲密的玩笑。
“那个……晚上有空吗?”她赶紧转移话题。
“有。”
“晚上八点,操场见?我想去跑跑步,出出汗。这两天闷在屋里都要发霉了。”
“好。我等你。”
“那……拜拜。”
她冲我挥挥手,转身跑进了宿舍楼。那双宝蓝色指甲油的脚在台阶上一闪而过,像是一尾灵活的鱼。
回到男生宿舍,老周正在阳台上对着那一堆重新搬回来的杂物发愁。
“老沈你昨晚死哪儿去了?电话也打不通,我都以为你被冲走了。”老周看到我,立刻开始抱怨。
“去避难了。”
我把背包扔在床上,整个人瘫倒在凉席上。
身体很累,脊背酸痛,但精神却处于一种极其亢奋的状态。
我的鼻尖仿佛还残留着清晨那种潮湿的空气味,指尖还残留着她手腕的温度。
我闭上眼。
脑海里全是那一双在晨光下泛着微光的脚,以及那一抹妖冶的宝蓝色。
今晚。
一定要再看一次。
晚上八点,北操场。
因为刚下过雨,塑胶跑道还是湿漉漉的,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橡胶味。但这并不妨碍那些憋了两天的情侣们出来透气。看台的阴影里,跑道的角落里,到处都是依偎在一起的身影。
我和乔一并肩走在最外圈的跑道上。
她换回了平时的打扮,不再是那双不跟脚的人字拖,而是穿回了那双熟悉的、旧旧的白色AF1。上身是一件修身的白色运动短袖,下身是黑色的紧身运动裤。
头发扎成了丸子头,露出光洁的额头。
我们走得很慢。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聊台风,聊被淹的老体育馆,聊这周即将恢复的训练。
但我知道,我们都在等。
等一个契机,等一个突破口。
走到操场那个光线最昏暗的弯道处时,乔一突然停了下来。
“哎呀。”
她低呼了一声,脚步踉跄了一下。
“怎么了?”我立刻紧张地看向她。
“鞋带开了。”
她指了指自己的左脚。
那只AF1的鞋带不知何时散开了,长长的鞋带拖在湿漉漉的塑胶跑道上,已经沾满了黑色的橡胶颗粒和积水。
“别动。”
这两个字几乎是没经过大脑思考就说了出来。
还没等她弯腰,我已经极其自然地、顺从地蹲了下去。
在这个姿势下,我又回到了我最熟悉、也最舒适的位置——她的脚下。
我单膝跪在湿漉漉的跑道上。膝盖处的布料瞬间被积水浸透,传来一阵冰凉的触感。
但我根本不在乎。
我的视线平齐于她的鞋面。
那双白色的AF1就在我眼前。鞋面的折痕里藏着细微的灰尘,那是她走过的路的证明。
我伸出手,捏起那根沾了水的鞋带。
湿湿的,凉凉的,还带着一点橡胶的涩感。
我小心翼翼地把上面的黑色颗粒抖掉。
我的动作很慢,慢得像是在进行某种精密的拆弹作业。
我能感觉到乔一正低着头看我。她的目光像是有重量一样,落在我的发顶,落在我的后颈。
我把鞋带交叉,拉紧。
透过鞋舌并没有完全闭合的缝隙,我隐约能看到里面白色的棉袜。
我想象着在那层棉袜之下,就是那双有着宝蓝色指甲的脚。此刻,它们正被包裹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温热、柔软、充满生机。
我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但我没有立刻站起来。
我依然保持着单膝跪地的姿势,双手轻轻搭在她的鞋面上。
指腹传来皮革微凉而粗糙的触感。
那一瞬间,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想要低下头,把脸贴在那个鞋面上的冲动。
但我克制住了。
我抬起头。
逆着操场边路灯昏黄的光晕,我看不清乔一的表情。但我能看到她的眼睛,那双平日里总是神采飞扬的眼睛,此刻正亮得惊人,里面倒映着我卑微的身影。
“沈言。”
她的声音很轻,被晚风吹得有些破碎。
“嗯?”
“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这么好?”
这个问题,她终于问出口了。
为什么帮我洗那双恶心的奶茶袜?为什么冒着台风背我趟过脏水?为什么像现在这样,毫无怨言地跪在泥水里帮我系鞋带?
我看着她。
我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露出一个我练习过无数次的、温和无害的笑容。
“因为不想看你摔跤。”
这句回答很简单。
但对于刚刚经历过那场暴雨、在那座孤岛上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乔一来说,这就够了。
她愣了一下。
下一秒,她突然弯下腰。
一阵带着柠檬草香气的风扑面而来。
那是她洗发水的味道,也是她身上那种干净、热烈、混合着淡淡汗味的少女气息。
柔软的触感印在了我的嘴唇上。
是一个吻。
很轻,很快,像是一只蝴蝶停在了花瓣上。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周围操场上的喧嚣声、远处广播台的音乐声、脚下积水的声音,在这一刻全部消失了。
世界只剩下嘴唇上那一点残留的温度,以及那一瞬间,她发梢扫过我脸颊时的微痒。
她亲了我。
在我跪在她脚边,手里还捏着她鞋带的时候。
这个吻没有任何的情欲色彩,甚至算不上是接吻,只是嘴唇与嘴唇的一次触碰。
但它像是一个烙印。
乔一迅速直起腰,脸红得像是熟透的番茄。她在夜色中显得有些慌乱,不敢看我的眼睛,手足无措地抓了抓衣角。
“那个……算是……昨晚的利息!”
她结结巴巴地丢下这句话,声音都在抖。
然后转身就跑。
“快点跟上!别傻跪着了!冷死了!”
她跑出几米远,又回过头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羞涩和欢快。
“来了。”
我撑着膝盖站起来,湿透的裤管冰冷地贴在腿上,随着动作滴答滴答地往下淌水。
那是刚才跪在积水里的代价。
但我并不觉得难受。我抬起手,指尖无意识地碰了一下嘴唇。那里已经凉了,但那股柠檬草的香气似乎还固执地停留在鼻尖,并没有被操场上的橡胶味盖过去。
前方,乔一已经跑进了路灯的光晕里。
那双白色的AF1在湿漉漉的跑道上起起落落,每一步都溅起细小的水花。她的马尾辫在脑后一甩一甩的,整个人像是要融化在那些昏黄的光线里。
我迈开步子,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
我没有试图追上她并肩而行,也没有刻意拉开距离。
我只是盯着地面,看着她被路灯拉得长长的影子投射在积水上。
我踩着那个影子的头部,一步,两步。
脚下的积水发出“啪嗒、啪嗒”的轻响,正好和前面那个轻快的脚步声重叠在一起。
操场上的风很大,吹干了我额头上的汗。
我插着兜,就这样跟在那个白色的背影后面,在这个潮湿的夜晚,一直走到了灯光最暗的地方。
没吃晚饭发布于 2025-12-22 22:41
Re: 【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
xie de zhen hao
xalalsss发布于 2025-12-23 00:03
Re: 【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
写的很牛逼,目前还没看出绿奴在哪
Ankh发布于 2025-12-23 22:59
Re: 【恋足/绿奴/虐心】恶之花
第九章
台风“海葵”彻底离开了京州。
那个狂暴、混乱、充满了水汽和越界冲动的夜晚,像是一个不真实的梦,随着积水的退去而被蒸发到了空气里。取而代之的,是京州特有的那种高远而刺眼的蓝天。
阳光毫无遮拦地泼洒下来,把柏油马路晒得微微发软,空气里弥漫着悬铃木叶片被暴晒后散发出的那种干燥的焦香。
我和乔一,在一起了。
这件事并没有我想象中那种轰轰烈烈的昭告天下,也没有什么仪式感极强的官宣文案。它发生得很自然,就像是两股水流汇合在了一起,静静地流淌。
早上七点半,二食堂。
人声鼎沸,热气腾腾。不锈钢餐盘碰撞的声音、阿姨打饭的吆喝声、学生们的交谈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大学生活最原本的底色。
我端着餐盘,穿过拥挤的人群。盘子里是两碗热腾腾的豆腐脑,一碗加辣一碗加糖,两根刚出锅的油条,还有两个茶叶蛋。
我在靠窗的位置找到了乔一。
她今天穿了一件浅黄色的修身针织短袖,领口有些低,露出一字型的锁骨和一小片晒成小麦色的皮肤。下身是一条浅蓝色的牛仔短裤,那双修长有力的腿随意地伸展着,脚上依然是那双白色的AF1。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侧脸上,那一层细细的绒毛在光晕里清晰可见。
“给。”
我把餐盘放下,把那碗加了红油和香菜的咸豆腐脑推到她面前,“茶叶蛋剥好了,把蛋黄吃了,别挑食。”
乔一正低头回消息,听到声音抬起头,冲我灿烂地一笑。
“谢啦沈言!饿死我了。”
她接过勺子,毫无顾忌地大口吃了起来。红色的辣油沾在她的嘴唇上,让那里看起来更加红润饱满。
“慢点吃。”我抽出一张纸巾,自然地伸过去,擦掉了她嘴角的油渍。
动作熟练得仿佛我们已经这样做过无数次。
旁边的几个体院男生路过,看到这一幕,发出了意味深长的起哄声。
“哟,乔姐,这就开始虐狗了?”
“沈后勤转正了啊?恭喜恭喜!”
以前听到这些话,乔一总是会把筷子扔过去骂一句“滚蛋”。但今天,她只是咬着勺子,脸颊微微泛红,眉眼弯弯地骂了一句:“吃你们的饭去,废话真多。”
没有否认。
那一瞬间,我握着豆浆杯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
一种巨大的、不真实的眩晕感击中了我。
我是她的男朋友了。
我,沈言,一个像苔藓一样生活在阴暗角落里的人,竟然真的拥有了这轮太阳。
“想什么呢?傻乎乎的。”
桌子底下,有什么东西碰了碰我的小腿。
我低下头。
是乔一的脚。
她不知什么时候把那只左脚从鞋里抽了出来,隔着桌布的遮挡,轻轻地蹭着我的牛仔裤管。
白色的棉袜包裹着那双我无比熟悉的脚,袜底因为在鞋里闷了一早上,带着一点温热的潮气。那层薄薄的织物摩擦着我的小腿皮肤,带来一种过电般的酥麻感。
她在调情。
用一种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方式,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这个充满了饭菜味和喧嚣声的食堂里,向我传递着一种私密的亲昵。
我抬起头,看到她正一脸坏笑地看着我,眼神里闪烁着狡黠的光。
我伸出手,在桌子底下,准确地握住了她的脚踝。
她的脚颤了一下,但没有躲。
拇指的指腹轻轻摩挲着她的脚踝骨。那是跟腱连接的地方,坚硬、紧致,充满了爆发力。
“快吃。”我哑着嗓子说,“一会儿还有课。”
“遵命,男朋友。”
她眨了眨眼,把脚收了回去,重新塞进那只微温的球鞋里。
那一整天,我都觉得自己在飘。
我就像是一个突然暴富的穷光蛋,揣着巨额支票走在大街上,看谁都觉得亲切,又看谁都觉得在觊觎我的财富。
下午没课,我陪她去图书馆自习。
图书馆里很安静,只有翻书的声音和键盘的敲击声。中央空调的冷气开得很足,空气里弥漫着书纸特有的陈旧味道。
我们选了一个角落的位置。
乔一其实坐不住,她对着那本《运动解剖学》愁眉苦脸,没看两页就开始在草稿纸上画乌龟。
我坐在她旁边,看着手里的《西方文学批评》,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我的注意力全在放在桌下的那只手上。
我们就这样牵着手。
我的手心很容易出汗,湿漉漉的。而她的手干燥、温暖,掌心和指根处有着长期握拍留下的硬茧。
那些茧子粗糙、坚硬,磨砺着我柔软的手心。
这就是三十七度。
这是正常人的体温,是恋人的体温,是活生生的、不加修饰的生命力。
我侧过头看她。
她大概是看累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脸颊压在书页上,挤出一团软肉。呼吸轻轻地吹动着额前的碎发。
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她的脸上投下一道道斑驳的光影。
我看着她毫无防备的睡颜,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酸涩的温柔。
我想保护她。
我想用我的一切,去守护这份光亮。哪怕我是泥土,我也要成为最肥沃的那一堆,让她这朵花开得更艳。
但我不知道的是,泥土再肥沃,也只能在地下腐烂。
晚上,我们没有回学校。
我们在学校后街吃了顿麻辣烫,然后心照不宣地走向了西门外的那片城中村。
那间狭小的、只有二十平米的出租屋,在那个台风夜之后,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
推开门,屋里依然是一股淡淡的霉味,混合着还没散去的潮气。
“累死我了……”
一进门,乔一就甩掉了背包,整个人毫无形象地瘫倒在那张单人床上。
“今天教练简直是变态,那个折返跑练得我腿都快断了。”她把头埋在枕头里,声音闷闷的,“沈言,我想喝冰可乐。”
“不行。”
我关上门,打开那盏昏黄的落地灯,“刚出完汗不能喝冰的,对肺不好。我给你倒杯温水。”
“哎呀你像个老头子一样……”
她翻了个身,仰面躺在床上,看着正在倒水的我,嘴角却挂着笑。
我把水杯递给她。
她喝了一口,然后冲我伸出双臂,“抱抱。”
我走过去,坐在床边,轻轻地抱住了她。
她的身上有一股好闻的味道。那是沐浴露残留的柠檬草香,混合着今天在图书馆沾染的书纸味,还有一点点淡淡的汗味。
那是活着的气息。
我们接吻了。
这不是操场上那个蜻蜓点水般的吻。这是一个真正的、深长的、带着一点点试探和急切的吻。
她的嘴唇很软,舌尖带着一点点甜味。她的手臂环住我的脖子,手指插进我的头发里,用力地把我向下压。
我们的呼吸交缠在一起,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升温、发酵。
我的身体起了反应。
那是作为一个正常男性的本能冲动。但我立刻压制住了它。我不敢。在这份刚刚开始的、过于美好的感情面前,我有一种近乎卑微的虔诚,生怕任何一点粗鲁的举动会亵渎了她。
“沈言……”
她松开我,眼睛湿漉漉的,脸颊绯红,“我脚疼。”
这句话像是一个开关,瞬间把我们从那种意乱情迷的氛围中拉回了熟悉的轨道。
“哪儿疼?”我立刻紧张起来。
“足弓。今天穿那双新鞋跑太久了,酸得不行。”她撒娇似地把腿抬起来,搁在我的大腿上。
那是她的左脚。
白色的棉袜袜口有些松了,软软地堆在脚踝处。
我不需要任何指令,身体已经做出了最自然的反应。
我的手握住了她的脚。
隔着棉袜,我能感受到里面的温度。那是比三十七度稍微高一点的温度,是运动过后的充血和热量。
“脱了吧。”我说,声音有些哑,“穿着袜子捏不准穴位。”
乔一听话地用另一只脚踩住袜头,轻轻一蹭。
袜子被脱了下来,掉在地板上。
那一瞬间,一股浓郁而熟悉的气味在空气中散开。
那是汗液发酵后的酸味,是皮脂的咸味,是棉织物受潮后的霉味,还有那双尤尼克斯球鞋里特有的橡胶味。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可能是臭味。
但对于我来说,这是费洛蒙。是她在向我敞开最私密、最真实的一面。
她的脚暴露在昏黄的灯光下。
38码,修长,足弓高高隆起。脚背上的血管在皮肤下微微跳动。
那层薄薄的、半透明的茧子,分布在前脚掌和后跟处,像是一层天然的釉质。
还有那十个脚趾。
那一抹妖艳的宝蓝色,虽然边缘已经有些磨损,露出了一点点指甲原本的颜色,但在灯光下依然显得格外醒目。
那是我们定情的颜色。
我低下头,把这双脚放在我的膝盖上。
我的手指开始工作。
拇指按压在涌泉穴上,缓缓用力。
“嗯……”
乔一发出一声舒服的叹息,头向后仰去,露出了修长的脖颈,“就是那里……好酸……”
我加大了力度。
我的手掌包裹着她的脚背,指尖顺着脚趾的缝隙滑过。
那里的皮肤很嫩,有些湿润。
我一点点揉捏着她僵硬的足底筋膜,感受着那层薄茧在我的掌纹上摩擦。那种极其细微的粗糙感,像是一把小刷子,刷过我的心脏。
这是一种合法的占有。
我是她的男朋友。我现在在帮她按摩。这是一件多么正当、多么体贴的事情。
但我知道,我的内心在咆哮。
我想把这双脚塞进嘴里。我想用舌头去舔舐那层带着咸味的薄茧。我想把鼻子埋进那双脚趾缝里,吸干每一滴汗水。
但我不能。
至少现在不能。
我只能把这种变态的欲望,转化为指尖的温柔。
“沈言。”
乔一闭着眼睛,声音慵懒,“你手艺真好。以后我要是退役了,你就去开个足疗店养我吧。”
“好啊。”
我低着头,视线死死地盯着她大脚趾上那块微微翘起的蓝色甲油,“我养你。只要你不嫌弃。”
“傻瓜。”
她睁开眼,突然坐起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捧起我的脸,在我的额头上用力亲了一口。
“这辈子赖上你了。”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里面全是信任和依赖。
我看着她。
在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但我又觉得恐惧。
因为这种幸福太满、太亮了。它照亮了我内心深处那些阴暗的角落,让我无处遁形。
夜深了。
那张单人床很窄,只够两个人侧着身,像是两把勺子一样紧紧叠在一起。
我们没有做那最后一步。她太累了,我也太珍惜了。
不久后,乔一的呼吸变得绵长而均匀。她侧身缩在我的怀里,一条修长的腿习惯性地搭在我的腰上。那只左脚的脚心正好抵在我的小腹处,隔着薄薄的棉质睡裤,那种温热、坚实的触感一丝一丝地传导进来。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老旧冰箱压缩机偶尔发出的嗡嗡声,和窗外偶尔驶过的车轮碾压过井盖的“哐当”声。
我没有睡。
我睁着眼睛,借着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的月光,看着这个拥挤而昏暗的空间。
光束斜斜地打在地板上。
那里躺着两只被她随手脱下的白色棉袜。
因为脱得急,它们并没有被展平,而是皱巴巴地团在一起,一只压着另一只,袜口还翻卷着。在冷白色的月光下,那两团白色的织物看起来像是一对在这个房间里窒息的小兽,又像是两朵开败了、枯萎在泥里的白玉兰。
即使隔着一段距离,我也仿佛能闻到那上面残留的、属于她的酸涩气味。
那是她今天一整天的痕迹。
我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搭在我小腹上的那只脚微微动了动,脚趾无意识地抓挠了一下我的布料。
我伸出手,在黑暗中悬停了片刻,似乎是想去够地上的那双袜子。
但最后,我收回了手。
我把手轻轻覆在了她搭在我腰间的那条腿上,掌心贴着她膝盖处的皮肤。
很热。
三十七度。
我闭上眼睛,把脸埋进她的颈窝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双被月光照亮的脏袜子,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地板上,陪着我们度过了这一整夜。
台风“海葵”彻底离开了京州。
那个狂暴、混乱、充满了水汽和越界冲动的夜晚,像是一个不真实的梦,随着积水的退去而被蒸发到了空气里。取而代之的,是京州特有的那种高远而刺眼的蓝天。
阳光毫无遮拦地泼洒下来,把柏油马路晒得微微发软,空气里弥漫着悬铃木叶片被暴晒后散发出的那种干燥的焦香。
我和乔一,在一起了。
这件事并没有我想象中那种轰轰烈烈的昭告天下,也没有什么仪式感极强的官宣文案。它发生得很自然,就像是两股水流汇合在了一起,静静地流淌。
早上七点半,二食堂。
人声鼎沸,热气腾腾。不锈钢餐盘碰撞的声音、阿姨打饭的吆喝声、学生们的交谈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大学生活最原本的底色。
我端着餐盘,穿过拥挤的人群。盘子里是两碗热腾腾的豆腐脑,一碗加辣一碗加糖,两根刚出锅的油条,还有两个茶叶蛋。
我在靠窗的位置找到了乔一。
她今天穿了一件浅黄色的修身针织短袖,领口有些低,露出一字型的锁骨和一小片晒成小麦色的皮肤。下身是一条浅蓝色的牛仔短裤,那双修长有力的腿随意地伸展着,脚上依然是那双白色的AF1。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侧脸上,那一层细细的绒毛在光晕里清晰可见。
“给。”
我把餐盘放下,把那碗加了红油和香菜的咸豆腐脑推到她面前,“茶叶蛋剥好了,把蛋黄吃了,别挑食。”
乔一正低头回消息,听到声音抬起头,冲我灿烂地一笑。
“谢啦沈言!饿死我了。”
她接过勺子,毫无顾忌地大口吃了起来。红色的辣油沾在她的嘴唇上,让那里看起来更加红润饱满。
“慢点吃。”我抽出一张纸巾,自然地伸过去,擦掉了她嘴角的油渍。
动作熟练得仿佛我们已经这样做过无数次。
旁边的几个体院男生路过,看到这一幕,发出了意味深长的起哄声。
“哟,乔姐,这就开始虐狗了?”
“沈后勤转正了啊?恭喜恭喜!”
以前听到这些话,乔一总是会把筷子扔过去骂一句“滚蛋”。但今天,她只是咬着勺子,脸颊微微泛红,眉眼弯弯地骂了一句:“吃你们的饭去,废话真多。”
没有否认。
那一瞬间,我握着豆浆杯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
一种巨大的、不真实的眩晕感击中了我。
我是她的男朋友了。
我,沈言,一个像苔藓一样生活在阴暗角落里的人,竟然真的拥有了这轮太阳。
“想什么呢?傻乎乎的。”
桌子底下,有什么东西碰了碰我的小腿。
我低下头。
是乔一的脚。
她不知什么时候把那只左脚从鞋里抽了出来,隔着桌布的遮挡,轻轻地蹭着我的牛仔裤管。
白色的棉袜包裹着那双我无比熟悉的脚,袜底因为在鞋里闷了一早上,带着一点温热的潮气。那层薄薄的织物摩擦着我的小腿皮肤,带来一种过电般的酥麻感。
她在调情。
用一种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方式,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这个充满了饭菜味和喧嚣声的食堂里,向我传递着一种私密的亲昵。
我抬起头,看到她正一脸坏笑地看着我,眼神里闪烁着狡黠的光。
我伸出手,在桌子底下,准确地握住了她的脚踝。
她的脚颤了一下,但没有躲。
拇指的指腹轻轻摩挲着她的脚踝骨。那是跟腱连接的地方,坚硬、紧致,充满了爆发力。
“快吃。”我哑着嗓子说,“一会儿还有课。”
“遵命,男朋友。”
她眨了眨眼,把脚收了回去,重新塞进那只微温的球鞋里。
那一整天,我都觉得自己在飘。
我就像是一个突然暴富的穷光蛋,揣着巨额支票走在大街上,看谁都觉得亲切,又看谁都觉得在觊觎我的财富。
下午没课,我陪她去图书馆自习。
图书馆里很安静,只有翻书的声音和键盘的敲击声。中央空调的冷气开得很足,空气里弥漫着书纸特有的陈旧味道。
我们选了一个角落的位置。
乔一其实坐不住,她对着那本《运动解剖学》愁眉苦脸,没看两页就开始在草稿纸上画乌龟。
我坐在她旁边,看着手里的《西方文学批评》,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我的注意力全在放在桌下的那只手上。
我们就这样牵着手。
我的手心很容易出汗,湿漉漉的。而她的手干燥、温暖,掌心和指根处有着长期握拍留下的硬茧。
那些茧子粗糙、坚硬,磨砺着我柔软的手心。
这就是三十七度。
这是正常人的体温,是恋人的体温,是活生生的、不加修饰的生命力。
我侧过头看她。
她大概是看累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脸颊压在书页上,挤出一团软肉。呼吸轻轻地吹动着额前的碎发。
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她的脸上投下一道道斑驳的光影。
我看着她毫无防备的睡颜,心里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酸涩的温柔。
我想保护她。
我想用我的一切,去守护这份光亮。哪怕我是泥土,我也要成为最肥沃的那一堆,让她这朵花开得更艳。
但我不知道的是,泥土再肥沃,也只能在地下腐烂。
晚上,我们没有回学校。
我们在学校后街吃了顿麻辣烫,然后心照不宣地走向了西门外的那片城中村。
那间狭小的、只有二十平米的出租屋,在那个台风夜之后,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
推开门,屋里依然是一股淡淡的霉味,混合着还没散去的潮气。
“累死我了……”
一进门,乔一就甩掉了背包,整个人毫无形象地瘫倒在那张单人床上。
“今天教练简直是变态,那个折返跑练得我腿都快断了。”她把头埋在枕头里,声音闷闷的,“沈言,我想喝冰可乐。”
“不行。”
我关上门,打开那盏昏黄的落地灯,“刚出完汗不能喝冰的,对肺不好。我给你倒杯温水。”
“哎呀你像个老头子一样……”
她翻了个身,仰面躺在床上,看着正在倒水的我,嘴角却挂着笑。
我把水杯递给她。
她喝了一口,然后冲我伸出双臂,“抱抱。”
我走过去,坐在床边,轻轻地抱住了她。
她的身上有一股好闻的味道。那是沐浴露残留的柠檬草香,混合着今天在图书馆沾染的书纸味,还有一点点淡淡的汗味。
那是活着的气息。
我们接吻了。
这不是操场上那个蜻蜓点水般的吻。这是一个真正的、深长的、带着一点点试探和急切的吻。
她的嘴唇很软,舌尖带着一点点甜味。她的手臂环住我的脖子,手指插进我的头发里,用力地把我向下压。
我们的呼吸交缠在一起,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升温、发酵。
我的身体起了反应。
那是作为一个正常男性的本能冲动。但我立刻压制住了它。我不敢。在这份刚刚开始的、过于美好的感情面前,我有一种近乎卑微的虔诚,生怕任何一点粗鲁的举动会亵渎了她。
“沈言……”
她松开我,眼睛湿漉漉的,脸颊绯红,“我脚疼。”
这句话像是一个开关,瞬间把我们从那种意乱情迷的氛围中拉回了熟悉的轨道。
“哪儿疼?”我立刻紧张起来。
“足弓。今天穿那双新鞋跑太久了,酸得不行。”她撒娇似地把腿抬起来,搁在我的大腿上。
那是她的左脚。
白色的棉袜袜口有些松了,软软地堆在脚踝处。
我不需要任何指令,身体已经做出了最自然的反应。
我的手握住了她的脚。
隔着棉袜,我能感受到里面的温度。那是比三十七度稍微高一点的温度,是运动过后的充血和热量。
“脱了吧。”我说,声音有些哑,“穿着袜子捏不准穴位。”
乔一听话地用另一只脚踩住袜头,轻轻一蹭。
袜子被脱了下来,掉在地板上。
那一瞬间,一股浓郁而熟悉的气味在空气中散开。
那是汗液发酵后的酸味,是皮脂的咸味,是棉织物受潮后的霉味,还有那双尤尼克斯球鞋里特有的橡胶味。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可能是臭味。
但对于我来说,这是费洛蒙。是她在向我敞开最私密、最真实的一面。
她的脚暴露在昏黄的灯光下。
38码,修长,足弓高高隆起。脚背上的血管在皮肤下微微跳动。
那层薄薄的、半透明的茧子,分布在前脚掌和后跟处,像是一层天然的釉质。
还有那十个脚趾。
那一抹妖艳的宝蓝色,虽然边缘已经有些磨损,露出了一点点指甲原本的颜色,但在灯光下依然显得格外醒目。
那是我们定情的颜色。
我低下头,把这双脚放在我的膝盖上。
我的手指开始工作。
拇指按压在涌泉穴上,缓缓用力。
“嗯……”
乔一发出一声舒服的叹息,头向后仰去,露出了修长的脖颈,“就是那里……好酸……”
我加大了力度。
我的手掌包裹着她的脚背,指尖顺着脚趾的缝隙滑过。
那里的皮肤很嫩,有些湿润。
我一点点揉捏着她僵硬的足底筋膜,感受着那层薄茧在我的掌纹上摩擦。那种极其细微的粗糙感,像是一把小刷子,刷过我的心脏。
这是一种合法的占有。
我是她的男朋友。我现在在帮她按摩。这是一件多么正当、多么体贴的事情。
但我知道,我的内心在咆哮。
我想把这双脚塞进嘴里。我想用舌头去舔舐那层带着咸味的薄茧。我想把鼻子埋进那双脚趾缝里,吸干每一滴汗水。
但我不能。
至少现在不能。
我只能把这种变态的欲望,转化为指尖的温柔。
“沈言。”
乔一闭着眼睛,声音慵懒,“你手艺真好。以后我要是退役了,你就去开个足疗店养我吧。”
“好啊。”
我低着头,视线死死地盯着她大脚趾上那块微微翘起的蓝色甲油,“我养你。只要你不嫌弃。”
“傻瓜。”
她睁开眼,突然坐起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捧起我的脸,在我的额头上用力亲了一口。
“这辈子赖上你了。”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里面全是信任和依赖。
我看着她。
在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但我又觉得恐惧。
因为这种幸福太满、太亮了。它照亮了我内心深处那些阴暗的角落,让我无处遁形。
夜深了。
那张单人床很窄,只够两个人侧着身,像是两把勺子一样紧紧叠在一起。
我们没有做那最后一步。她太累了,我也太珍惜了。
不久后,乔一的呼吸变得绵长而均匀。她侧身缩在我的怀里,一条修长的腿习惯性地搭在我的腰上。那只左脚的脚心正好抵在我的小腹处,隔着薄薄的棉质睡裤,那种温热、坚实的触感一丝一丝地传导进来。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老旧冰箱压缩机偶尔发出的嗡嗡声,和窗外偶尔驶过的车轮碾压过井盖的“哐当”声。
我没有睡。
我睁着眼睛,借着窗帘缝隙里漏进来的月光,看着这个拥挤而昏暗的空间。
光束斜斜地打在地板上。
那里躺着两只被她随手脱下的白色棉袜。
因为脱得急,它们并没有被展平,而是皱巴巴地团在一起,一只压着另一只,袜口还翻卷着。在冷白色的月光下,那两团白色的织物看起来像是一对在这个房间里窒息的小兽,又像是两朵开败了、枯萎在泥里的白玉兰。
即使隔着一段距离,我也仿佛能闻到那上面残留的、属于她的酸涩气味。
那是她今天一整天的痕迹。
我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搭在我小腹上的那只脚微微动了动,脚趾无意识地抓挠了一下我的布料。
我伸出手,在黑暗中悬停了片刻,似乎是想去够地上的那双袜子。
但最后,我收回了手。
我把手轻轻覆在了她搭在我腰间的那条腿上,掌心贴着她膝盖处的皮肤。
很热。
三十七度。
我闭上眼睛,把脸埋进她的颈窝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双被月光照亮的脏袜子,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地板上,陪着我们度过了这一整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