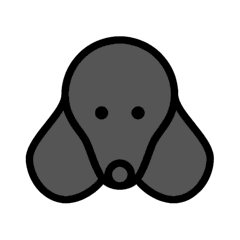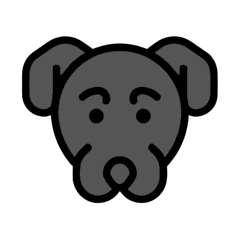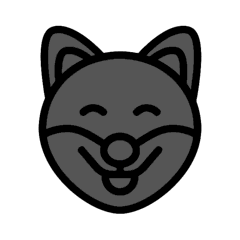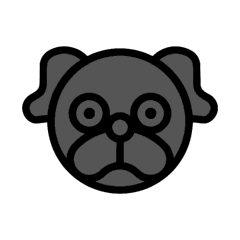[轻度克系][人外][超短篇]田螺姑娘,但哪里不对
短篇原创奇幻魔物娘榨精裸足催眠灵异
林远把那东西从公园人工湖的泥岸边捞起来时,还以为是什么废弃的装饰品。
直径三十厘米左右,浑圆如球,通体墨黑,表面光滑得不可思议。它沉甸甸的,抱在怀里像一块打磨过的玄武岩,却又轻得有些不对劲——仿佛外壳之下是空的。林远翻来覆去看了半天,看不出是什么螺,只觉形状优雅得像某种现代雕塑,线条流畅得近乎不真实。边缘处有一圈极细的螺纹,螺旋状向内收缩,颜色比本体略浅,近乎深紫。
“这么大,要是田螺……”他自嘲地笑了,想起小时候读过的民间故事,“总不会真有什么田螺姑娘吧。”
他租住的老公寓在三楼,一室一厅,采光很差。客厅角落有个闲置的陶瓷鱼缸,原主人留下的,半米高,底部积了层薄灰。林远把黑螺放进去,注满清水。螺壳沉底,稳稳定住,黑色在水波折射下泛出幽幽的暗光,竟有种奇异的庄严感。他盯着看了会儿,摇摇头,转身去厨房煮泡面。
生活是重复的:早上七点半起床,挤地铁,在广告公司做设计,加班,回家,点外卖,刷手机,睡觉。三十岁,存款不多,恋爱谈过几次,都无疾而终。父母在老家催婚,他总敷衍说“快了快了”。有时深夜惊醒,看着天花板渗水留下的黄渍,会觉得自己像缸里那枚螺——困在壳中,动弹不得。
变化是第四天开始的。
那天他加班到九点,拖着疲惫的身子开门,一股异香扑面而来。不是外卖那种重油重盐的气味,而是……家常菜香,混合着米饭刚蒸熟的蒸汽。他愣在玄关。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散落的杂志叠好,脏衣服不见了,地板擦过,泛着微光。餐桌上摆着两菜一汤:青椒肉丝,油光润泽,肉丝切得均匀;清炒空心菜,碧绿清脆;番茄蛋汤,红黄相间,飘着几粒葱花。电饭煲亮着保温灯。
林远第一反应是进贼了——哪有贼还做饭的?他小心检查每个房间,窗户锁着,门锁完好,什么都没少。回到餐桌前,肚子不争气地叫起来。他犹豫了五分钟,拿起筷子。
好吃。异常好吃。
肉丝嫩滑,带着恰到好处的酱香;空心菜火候精准,爽脆微甜;汤的酸度温和,蛋花蓬松。每一口都让他想起童年时母亲做的饭菜,却又多了一层说不清的、勾人食欲的鲜味。他狼吞虎咽,把饭菜扫得精光,连汤汁都拌了饭。吃完后,一股暖流从胃部扩散到四肢,疲惫感奇迹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轻微的兴奋。他坐在椅子上,思绪飘忽,脑子里闪过各种不着边际的念头:要是天天有人这么做饭该多好;这手艺开餐馆肯定火;做这饭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接下来的三天,天天如此。
他试过早起埋伏,但每次刚过七点就困得睁不开眼,醒来已是八点半,家里空无一人,早餐却准备好了——粥、煎蛋、小菜。他检查过门窗,装过摄像头(第二天就坏了),甚至故意在门口撒了面粉,却只看到自己的脚印。饭菜依旧出现,味道依旧迷人,吃完后依旧有种奇异的愉悦感,像微醺,又像服用了温和的兴奋剂。他开始期待回家,上班时心不在焉,琢磨今晚会吃什么。
第七天,他请了半天假。
中午十二点,他悄悄回到公寓楼下,躲在对面便利店的角落。一点十分,他看见一个女孩走进单元门——身形高挑,皮肤是健康的深麦色,穿着宽大的白色T恤(他认出那是自己丢在洗衣篮里的一件),下身是牛仔短裤,露出惹火的长腿,赤脚踩着人字拖。长发披散,看不清脸。她手里拎着个装着各色食材的帆布袋子,步履缓慢,有种慵懒的韵律。
林远的心脏狂跳。他等了五分钟,轻手轻脚上楼,钥匙插进锁孔时屏住呼吸。
门开了条缝。
客厅里没人,但厨房有动静。水声,切菜声,锅铲碰撞声。他脱了鞋,穿着袜子踩在地板上,悄无声息地挪到厨房门口,侧身窥视。
她背对着他,正在炒菜。
T恤下摆刚盖住臀线,恰好暗示出腿线的顶点,双腿虽笔直修长,却因臀与大腿过度的饱满圆润,而显现出一种肉感,肤色是均匀的深蜜色,在午后的光线里泛着柔和的光泽。赤脚踩在瓷砖上,脚踝浑圆,连脚背胖胖的有些肉,但足弓却格外高耸优美,让整只脚丝毫不显得臃肿。脚趾圆润,指甲是健康的淡粉色。她动作不疾不徐,翻炒,调味,关火,每一个动作都带着某种黏稠的节奏感,仿佛时间在她周围流淌得慢了一些。
然后她转过身。
林远屏住呼吸。
那是一张极具冲击力的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皙美人,却有种妖异的吸引力。皮肤是深麦色,光滑无瑕,像打磨过的黑檀木。五官分明:眉骨略高,眼窝深邃,眼睛是深褐色,瞳孔在光线下近乎黑色,眼神慵懒,半眯着,像刚睡醒。鼻梁挺直,嘴唇有些厚,饱满如丹参花,唇色是自然的深红,嘴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长发乌黑,微卷,散在肩头,发梢沾着些许水汽。
T恤领口宽大,露出一侧锁骨和圆润的肩头。胸部丰腴,在棉质布料下显出饱满的曲线,随着呼吸轻轻起伏。腰肢纤细,与臀胯形成夸张的对比,身体线条像一道流畅的波浪。她抬手捋了捋头发,手臂肌肉紧实,线条柔和。
“看够了吗?”她开口,声音低沉沙哑,带着黏腻的鼻音,像裹了蜜糖。
林远僵在原地。
她笑了笑,不急不缓地走过来,赤脚踩在地板上,几乎没发出声音。距离拉近,林远闻到一股气味——水腥气,混合着某种甜腻的香气,像熟透的水果。她比他矮半个头,仰脸看他,睫毛很长,在眼睑投下阴影。
“饭快好了。”她说,伸手轻抚他的脸颊。指尖微凉,触感异常柔软。
“你……是谁?”林远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
“你的螺。”她笑了,眼角弯起,“你不是总念叨田螺姑娘么?”
“那是开玩笑……”
“可我是真的。”她靠得更近,身体几乎贴着他。体温偏低,但透过薄薄的T恤,他能感觉到柔软的肌肤。“不喜欢我做的饭?”
“喜欢……”林远大脑一片空白,“但为什么?”
“因为你把我带回来了呀。”她踮起脚,嘴唇凑到他耳边,气息温热,“缸里太闷了。”
她的手臂环上他的脖子,身体重量压过来。林远下意识抱住她,手掌触到她后背,T恤下的肌肤光滑细腻,像浸过油的丝绸。她的身体异常柔软,仿佛没有骨头,可以任意弯曲贴合。她仰头吻他,嘴唇湿润,舌尖探入,带着淡淡的甜味,像他每天吃到的饭菜里那种鲜味的来源。
林远残存的理智在挣扎,但身体已经投降。他把她抵在墙上,手从T恤下摆伸进去,掌心覆上她丰满的胸部。皮肤温热,乳头挺立,在他掌心跳动。她发出低低的哼声,不像是愉悦,更像某种慵懒的回应。
他们跌跌撞撞挪到卧室,倒在床上。她帮他脱衣服,动作缓慢,手指划过他胸口时,带来一阵战栗。她脱掉T恤,赤裸的身体展露无遗——深色的皮肤在昏暗光线里像某种稀有金属,曲线夸张得近乎不真实,小腹线条健康地微微隆起,如安格尔画作中的女子,臀胯更加丰腴饱满。她跪坐在他身上,低头看他,长发垂落,扫过他胸口。
“别怕。”她轻声说,俯身吻他。
她的身体沉下来时,林远倒抽一口气。太紧了,湿滑,温热,内壁像有无数细小的吸盘,蠕动,收缩,紧紧包裹住他。她开始缓慢地动,节奏黏腻,每一次起伏都带出细微的水声。她闭着眼,表情迷离,嘴唇微张,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声音拖得很长,像在哼唱某种古老的歌谣。
林远抓住她的腰,手感绵软,像握住一团有弹性的胶质。他试图加快节奏,但她总能把他拉回那种缓慢的韵律里。时间变得模糊,空气里弥漫着那股甜腻的水腥气。她的身体越来越软,仿佛在融化,皮肤渗出细密的汗珠,在深色肌理上闪闪发光。
高潮来得猝不及防。
林远绷紧身体,精液喷射的瞬间,他感觉到某种异样——她体内深处,有什么东西松动了,涌出,顺着他的阴茎流下来。他低头看,愣住。
粉色的。一团团,一簇簇,黏稠的半透明颗粒,裹在他勃起的器官上,像一串畸形的葡萄。每一颗里都有极细微,针尖大小的黑点,排列整齐,密密麻麻,像……
卵。
林远的大脑尖叫着“危险”,但身体却沉浸在余韵里,软绵绵的,提不起力气。恐惧感像隔着毛玻璃,模糊不清。他想抽身,却发现她的下体紧紧箍着他,那些粉色物质还在不断涌出,越来越多,仿佛有生命般蠕动着,刺激着他最敏感的位置,又顺着两人交合处滴落,在床单上积成一滩。
“别动……”她喃喃,手臂环住他,把他拉进怀里。她的身体真的在软化——皮肤变得像温热的蜡,缓慢地包裹住他的胸膛、手臂。林远挣扎,但力道微弱,仿佛全身力气都被抽空了。随着她的拥抱,他的阴茎滑出了她的身体,却仍然被蠕动的卵块包裹着,又一次勃起、射精。
“不……”他含糊地说。
她吻他,舌头探入他口腔,带着那股熟悉的鲜甜味。与此同时,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她身体两侧延伸出来——柔软,湿滑,像触手,缠绕上他的大腿,腰腹,胸口。一条触手绕上他仍在抽搐的阴茎顶端,轻轻摩擦铃口;另一条撬开他的嘴唇,探入口腔,抵住上颚。
他瞪大眼睛,想喊,却发不出声音。触手尖端挟着一颗粉红色的卵,在他嘴里挤压,膨胀,裂开,喷射出黏稠的液体——正是他每天在饭菜里尝到的、让人欲罢不能的鲜味。液体滑入喉咙,温暖,甘甜,带着淡淡的腥气。他的意识进一步模糊,像沉入温水,下沉,下沉……
触手缠绕得更紧,把他完全包裹。他最后看到的是她的脸——那双深褐色的眼睛温柔地看着他,嘴角噙着笑意,仿佛在哄一个任性的孩子。
然后黑暗降临。
---
三个月后,林远结婚了。
婚礼在城郊一家小酒店举行,只摆了五桌。横幅上写着林远、罗晓芙新婚志喜。
新郎穿着不甚合身的西装,笑容满面,但眼神有些空洞。新娘美得惊人——肤色黝黑,身材火辣,一袭很衬肤色的淡蓝色婚纱裙,勾勒出夸张的曲线。她挽着林远的手臂,对来宾微笑,眼神慵懒,嘴角永远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新娘是哪里人呀?”有亲戚问。
“外地人,孤儿。”林远回答,语气平稳,“我们一见钟情。”
确实没有女方亲友。问起父母,林远就说都过世了;问起籍贯,他就说南方某个小城,名字含糊不清。新娘话很少,大部分时间只是安静地坐着,偶尔为林远夹菜,动作缓慢优雅。她赤脚穿一双淡蓝色高跟鞋——这是林远坚持的,说新娘脚踝有旧伤,穿不了太久。
敬酒时,有人起哄让新娘喝一杯。她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随即皱眉,低声对林远说了句什么。林远立刻接过杯子,一饮而尽,笑道:“她酒精过敏,我代劳。”
宴席规模实在很小,连林远敬完了酒也能坐下来吃上几口。新娘给他夹菜,他吃得很香。有人调侃:“以后有口福了!”林远笑着点头,看向新娘,眼神温柔得有些过头。
婚礼结束,两人回到公寓。鱼缸还在角落,黑螺静静地沉在水底,旁边多了几枚小一些的螺,外壳是浅粉色。
新娘——现在该叫妻子了——脱掉高跟鞋,赤脚走到鱼缸边,手指轻点水面。林远从背后抱住她,脸埋在她颈间,深深吸气。
“今天累吗?”她问,声音黏腻。
“不累。”林远说,手探进她裙摆,“我们……要不要……”
她转过身,吻他。嘴唇相触的瞬间,林远身体微颤,像触了电。他急切地脱掉她的衣服,把她压在沙发上,动作近乎粗暴。她任由他摆布,手臂环住他脖子,双腿缠上他的腰,像某种柔韧的藤蔓。
事后,林远瘫在她怀里,眼神涣散。她轻抚他的头发,哼着不成调的歌谣。窗外夜色渐深,鱼缸里,黑色的螺壳在月光下泛着幽暗的光。
---
周一,林远照常上班。
同事发现他瘦了些,但精神很好,总是带着幸福的微笑。中午,他打开便当盒——米饭,青椒肉丝,清炒空心菜,番茄蛋汤。和以前一样。
“你老婆手艺真好。”邻座同事羡慕地说。
“是啊。”林远夹起一筷子肉丝,放进嘴里,细细咀嚼,眼睛微微眯起,像品尝什么珍馐。“特别好吃。”
他吃得干干净净,只在饭盒角落里,挨着几粒残米,有一小块瘪瘪的、无色透明的东西,像玉米粒的表皮。
吃完后,他靠在椅背上,闭眼休息,嘴角挂着满足的笑意。下午的工作效率奇高,他设计出一套让客户赞不绝口的方案,得到主管表扬。
下班时,他拎着空便当盒,脚步轻快地走向地铁站。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头部微微隆起,形状有些怪异,像背着什么沉重的东西。
但他没有回头。
公寓里,妻子站在厨房,正在准备晚餐。她赤着脚,穿着林远的旧T恤,哼着歌,动作缓慢优雅。鱼缸里,黑色的螺静静沉在水底,周围粉色的小螺又多了几枚,紧紧吸附在缸壁上,像一串怪异的装饰。
窗外,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
又是一天。

直径三十厘米左右,浑圆如球,通体墨黑,表面光滑得不可思议。它沉甸甸的,抱在怀里像一块打磨过的玄武岩,却又轻得有些不对劲——仿佛外壳之下是空的。林远翻来覆去看了半天,看不出是什么螺,只觉形状优雅得像某种现代雕塑,线条流畅得近乎不真实。边缘处有一圈极细的螺纹,螺旋状向内收缩,颜色比本体略浅,近乎深紫。
“这么大,要是田螺……”他自嘲地笑了,想起小时候读过的民间故事,“总不会真有什么田螺姑娘吧。”
他租住的老公寓在三楼,一室一厅,采光很差。客厅角落有个闲置的陶瓷鱼缸,原主人留下的,半米高,底部积了层薄灰。林远把黑螺放进去,注满清水。螺壳沉底,稳稳定住,黑色在水波折射下泛出幽幽的暗光,竟有种奇异的庄严感。他盯着看了会儿,摇摇头,转身去厨房煮泡面。
生活是重复的:早上七点半起床,挤地铁,在广告公司做设计,加班,回家,点外卖,刷手机,睡觉。三十岁,存款不多,恋爱谈过几次,都无疾而终。父母在老家催婚,他总敷衍说“快了快了”。有时深夜惊醒,看着天花板渗水留下的黄渍,会觉得自己像缸里那枚螺——困在壳中,动弹不得。
变化是第四天开始的。
那天他加班到九点,拖着疲惫的身子开门,一股异香扑面而来。不是外卖那种重油重盐的气味,而是……家常菜香,混合着米饭刚蒸熟的蒸汽。他愣在玄关。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散落的杂志叠好,脏衣服不见了,地板擦过,泛着微光。餐桌上摆着两菜一汤:青椒肉丝,油光润泽,肉丝切得均匀;清炒空心菜,碧绿清脆;番茄蛋汤,红黄相间,飘着几粒葱花。电饭煲亮着保温灯。
林远第一反应是进贼了——哪有贼还做饭的?他小心检查每个房间,窗户锁着,门锁完好,什么都没少。回到餐桌前,肚子不争气地叫起来。他犹豫了五分钟,拿起筷子。
好吃。异常好吃。
肉丝嫩滑,带着恰到好处的酱香;空心菜火候精准,爽脆微甜;汤的酸度温和,蛋花蓬松。每一口都让他想起童年时母亲做的饭菜,却又多了一层说不清的、勾人食欲的鲜味。他狼吞虎咽,把饭菜扫得精光,连汤汁都拌了饭。吃完后,一股暖流从胃部扩散到四肢,疲惫感奇迹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轻微的兴奋。他坐在椅子上,思绪飘忽,脑子里闪过各种不着边际的念头:要是天天有人这么做饭该多好;这手艺开餐馆肯定火;做这饭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接下来的三天,天天如此。
他试过早起埋伏,但每次刚过七点就困得睁不开眼,醒来已是八点半,家里空无一人,早餐却准备好了——粥、煎蛋、小菜。他检查过门窗,装过摄像头(第二天就坏了),甚至故意在门口撒了面粉,却只看到自己的脚印。饭菜依旧出现,味道依旧迷人,吃完后依旧有种奇异的愉悦感,像微醺,又像服用了温和的兴奋剂。他开始期待回家,上班时心不在焉,琢磨今晚会吃什么。
第七天,他请了半天假。
中午十二点,他悄悄回到公寓楼下,躲在对面便利店的角落。一点十分,他看见一个女孩走进单元门——身形高挑,皮肤是健康的深麦色,穿着宽大的白色T恤(他认出那是自己丢在洗衣篮里的一件),下身是牛仔短裤,露出惹火的长腿,赤脚踩着人字拖。长发披散,看不清脸。她手里拎着个装着各色食材的帆布袋子,步履缓慢,有种慵懒的韵律。
林远的心脏狂跳。他等了五分钟,轻手轻脚上楼,钥匙插进锁孔时屏住呼吸。
门开了条缝。
客厅里没人,但厨房有动静。水声,切菜声,锅铲碰撞声。他脱了鞋,穿着袜子踩在地板上,悄无声息地挪到厨房门口,侧身窥视。
她背对着他,正在炒菜。
T恤下摆刚盖住臀线,恰好暗示出腿线的顶点,双腿虽笔直修长,却因臀与大腿过度的饱满圆润,而显现出一种肉感,肤色是均匀的深蜜色,在午后的光线里泛着柔和的光泽。赤脚踩在瓷砖上,脚踝浑圆,连脚背胖胖的有些肉,但足弓却格外高耸优美,让整只脚丝毫不显得臃肿。脚趾圆润,指甲是健康的淡粉色。她动作不疾不徐,翻炒,调味,关火,每一个动作都带着某种黏稠的节奏感,仿佛时间在她周围流淌得慢了一些。
然后她转过身。
林远屏住呼吸。
那是一张极具冲击力的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皙美人,却有种妖异的吸引力。皮肤是深麦色,光滑无瑕,像打磨过的黑檀木。五官分明:眉骨略高,眼窝深邃,眼睛是深褐色,瞳孔在光线下近乎黑色,眼神慵懒,半眯着,像刚睡醒。鼻梁挺直,嘴唇有些厚,饱满如丹参花,唇色是自然的深红,嘴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长发乌黑,微卷,散在肩头,发梢沾着些许水汽。
T恤领口宽大,露出一侧锁骨和圆润的肩头。胸部丰腴,在棉质布料下显出饱满的曲线,随着呼吸轻轻起伏。腰肢纤细,与臀胯形成夸张的对比,身体线条像一道流畅的波浪。她抬手捋了捋头发,手臂肌肉紧实,线条柔和。
“看够了吗?”她开口,声音低沉沙哑,带着黏腻的鼻音,像裹了蜜糖。
林远僵在原地。
她笑了笑,不急不缓地走过来,赤脚踩在地板上,几乎没发出声音。距离拉近,林远闻到一股气味——水腥气,混合着某种甜腻的香气,像熟透的水果。她比他矮半个头,仰脸看他,睫毛很长,在眼睑投下阴影。
“饭快好了。”她说,伸手轻抚他的脸颊。指尖微凉,触感异常柔软。
“你……是谁?”林远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
“你的螺。”她笑了,眼角弯起,“你不是总念叨田螺姑娘么?”
“那是开玩笑……”
“可我是真的。”她靠得更近,身体几乎贴着他。体温偏低,但透过薄薄的T恤,他能感觉到柔软的肌肤。“不喜欢我做的饭?”
“喜欢……”林远大脑一片空白,“但为什么?”
“因为你把我带回来了呀。”她踮起脚,嘴唇凑到他耳边,气息温热,“缸里太闷了。”
她的手臂环上他的脖子,身体重量压过来。林远下意识抱住她,手掌触到她后背,T恤下的肌肤光滑细腻,像浸过油的丝绸。她的身体异常柔软,仿佛没有骨头,可以任意弯曲贴合。她仰头吻他,嘴唇湿润,舌尖探入,带着淡淡的甜味,像他每天吃到的饭菜里那种鲜味的来源。
林远残存的理智在挣扎,但身体已经投降。他把她抵在墙上,手从T恤下摆伸进去,掌心覆上她丰满的胸部。皮肤温热,乳头挺立,在他掌心跳动。她发出低低的哼声,不像是愉悦,更像某种慵懒的回应。
他们跌跌撞撞挪到卧室,倒在床上。她帮他脱衣服,动作缓慢,手指划过他胸口时,带来一阵战栗。她脱掉T恤,赤裸的身体展露无遗——深色的皮肤在昏暗光线里像某种稀有金属,曲线夸张得近乎不真实,小腹线条健康地微微隆起,如安格尔画作中的女子,臀胯更加丰腴饱满。她跪坐在他身上,低头看他,长发垂落,扫过他胸口。
“别怕。”她轻声说,俯身吻他。
她的身体沉下来时,林远倒抽一口气。太紧了,湿滑,温热,内壁像有无数细小的吸盘,蠕动,收缩,紧紧包裹住他。她开始缓慢地动,节奏黏腻,每一次起伏都带出细微的水声。她闭着眼,表情迷离,嘴唇微张,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声音拖得很长,像在哼唱某种古老的歌谣。
林远抓住她的腰,手感绵软,像握住一团有弹性的胶质。他试图加快节奏,但她总能把他拉回那种缓慢的韵律里。时间变得模糊,空气里弥漫着那股甜腻的水腥气。她的身体越来越软,仿佛在融化,皮肤渗出细密的汗珠,在深色肌理上闪闪发光。
高潮来得猝不及防。
林远绷紧身体,精液喷射的瞬间,他感觉到某种异样——她体内深处,有什么东西松动了,涌出,顺着他的阴茎流下来。他低头看,愣住。
粉色的。一团团,一簇簇,黏稠的半透明颗粒,裹在他勃起的器官上,像一串畸形的葡萄。每一颗里都有极细微,针尖大小的黑点,排列整齐,密密麻麻,像……
卵。
林远的大脑尖叫着“危险”,但身体却沉浸在余韵里,软绵绵的,提不起力气。恐惧感像隔着毛玻璃,模糊不清。他想抽身,却发现她的下体紧紧箍着他,那些粉色物质还在不断涌出,越来越多,仿佛有生命般蠕动着,刺激着他最敏感的位置,又顺着两人交合处滴落,在床单上积成一滩。
“别动……”她喃喃,手臂环住他,把他拉进怀里。她的身体真的在软化——皮肤变得像温热的蜡,缓慢地包裹住他的胸膛、手臂。林远挣扎,但力道微弱,仿佛全身力气都被抽空了。随着她的拥抱,他的阴茎滑出了她的身体,却仍然被蠕动的卵块包裹着,又一次勃起、射精。
“不……”他含糊地说。
她吻他,舌头探入他口腔,带着那股熟悉的鲜甜味。与此同时,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她身体两侧延伸出来——柔软,湿滑,像触手,缠绕上他的大腿,腰腹,胸口。一条触手绕上他仍在抽搐的阴茎顶端,轻轻摩擦铃口;另一条撬开他的嘴唇,探入口腔,抵住上颚。
他瞪大眼睛,想喊,却发不出声音。触手尖端挟着一颗粉红色的卵,在他嘴里挤压,膨胀,裂开,喷射出黏稠的液体——正是他每天在饭菜里尝到的、让人欲罢不能的鲜味。液体滑入喉咙,温暖,甘甜,带着淡淡的腥气。他的意识进一步模糊,像沉入温水,下沉,下沉……
触手缠绕得更紧,把他完全包裹。他最后看到的是她的脸——那双深褐色的眼睛温柔地看着他,嘴角噙着笑意,仿佛在哄一个任性的孩子。
然后黑暗降临。
---
三个月后,林远结婚了。
婚礼在城郊一家小酒店举行,只摆了五桌。横幅上写着林远、罗晓芙新婚志喜。
新郎穿着不甚合身的西装,笑容满面,但眼神有些空洞。新娘美得惊人——肤色黝黑,身材火辣,一袭很衬肤色的淡蓝色婚纱裙,勾勒出夸张的曲线。她挽着林远的手臂,对来宾微笑,眼神慵懒,嘴角永远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新娘是哪里人呀?”有亲戚问。
“外地人,孤儿。”林远回答,语气平稳,“我们一见钟情。”
确实没有女方亲友。问起父母,林远就说都过世了;问起籍贯,他就说南方某个小城,名字含糊不清。新娘话很少,大部分时间只是安静地坐着,偶尔为林远夹菜,动作缓慢优雅。她赤脚穿一双淡蓝色高跟鞋——这是林远坚持的,说新娘脚踝有旧伤,穿不了太久。
敬酒时,有人起哄让新娘喝一杯。她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随即皱眉,低声对林远说了句什么。林远立刻接过杯子,一饮而尽,笑道:“她酒精过敏,我代劳。”
宴席规模实在很小,连林远敬完了酒也能坐下来吃上几口。新娘给他夹菜,他吃得很香。有人调侃:“以后有口福了!”林远笑着点头,看向新娘,眼神温柔得有些过头。
婚礼结束,两人回到公寓。鱼缸还在角落,黑螺静静地沉在水底,旁边多了几枚小一些的螺,外壳是浅粉色。
新娘——现在该叫妻子了——脱掉高跟鞋,赤脚走到鱼缸边,手指轻点水面。林远从背后抱住她,脸埋在她颈间,深深吸气。
“今天累吗?”她问,声音黏腻。
“不累。”林远说,手探进她裙摆,“我们……要不要……”
她转过身,吻他。嘴唇相触的瞬间,林远身体微颤,像触了电。他急切地脱掉她的衣服,把她压在沙发上,动作近乎粗暴。她任由他摆布,手臂环住他脖子,双腿缠上他的腰,像某种柔韧的藤蔓。
事后,林远瘫在她怀里,眼神涣散。她轻抚他的头发,哼着不成调的歌谣。窗外夜色渐深,鱼缸里,黑色的螺壳在月光下泛着幽暗的光。
---
周一,林远照常上班。
同事发现他瘦了些,但精神很好,总是带着幸福的微笑。中午,他打开便当盒——米饭,青椒肉丝,清炒空心菜,番茄蛋汤。和以前一样。
“你老婆手艺真好。”邻座同事羡慕地说。
“是啊。”林远夹起一筷子肉丝,放进嘴里,细细咀嚼,眼睛微微眯起,像品尝什么珍馐。“特别好吃。”
他吃得干干净净,只在饭盒角落里,挨着几粒残米,有一小块瘪瘪的、无色透明的东西,像玉米粒的表皮。
吃完后,他靠在椅背上,闭眼休息,嘴角挂着满足的笑意。下午的工作效率奇高,他设计出一套让客户赞不绝口的方案,得到主管表扬。
下班时,他拎着空便当盒,脚步轻快地走向地铁站。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头部微微隆起,形状有些怪异,像背着什么沉重的东西。
但他没有回头。
公寓里,妻子站在厨房,正在准备晚餐。她赤着脚,穿着林远的旧T恤,哼着歌,动作缓慢优雅。鱼缸里,黑色的螺静静沉在水底,周围粉色的小螺又多了几枚,紧紧吸附在缸壁上,像一串怪异的装饰。
窗外,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
又是一天。

Harry_sec发布于 2026-01-04 14:13
Re: [轻度克系][人外][超短篇]田螺姑娘,但哪里不对
好文\( ͯω ͯ)/

19
1944774669发布于 2026-01-04 14:59
Re: [轻度克系][人外][超短篇]田螺姑娘,但哪里不对
福寿螺姑娘是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lemonaid发布于 2026-01-04 16:45
Re: [轻度克系][人外][超短篇]田螺姑娘,但哪里不对
好色!怎么不直接插尿道里产卵
1944774669:↑福寿螺姑娘是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对,其实最后我贴图了,但镜像不翻墙看不见图。福寿螺真的是一种克系的动物。看见它那卵我就不好了。
z3929507447发布于 2026-01-04 23:09
Re: [轻度克系][人外][超短篇]田螺姑娘,但哪里不对
硬了,又吓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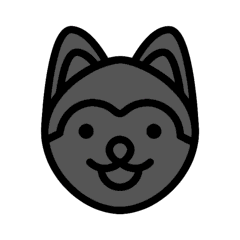
Na
Napoleon0726发布于 2026-01-04 23:17
Re: [轻度克系][人外][超短篇]田螺姑娘,但哪里不对
男主是被榨干日益消瘦了吗😱
海米发布于 2026-01-04 23:20
Re: [轻度克系][人外][超短篇]田螺姑娘,但哪里不对
那叫母体给后代繁衍找的寄生的宿主
abc1233123发布于 2026-01-05 10:39
Re: [轻度克系][人外][超短篇]田螺姑娘,但哪里不对
看到克系就進來了,突然想寫點怪東西了

Be
believeral最佳读者发布于 2026-01-05 23:23
Re: [轻度克系][人外][超短篇]田螺姑娘,但哪里不对
这种略带诡异的人外很戳我😍😍😍😍😍
Harry_sec发布于 2026-01-05 23:41
Re: [轻度克系][人外][超短篇]田螺姑娘,但哪里不对
多来点克系,莫多莫多~🥰🥰
_zhenC发布于 2026-01-06 00:36
Re: [轻度克系][人外][超短篇]田螺姑娘,但哪里不对
感觉功底很深啊,文字很凝炼。(克系还是太对胃口了)
68799426发布于 2026-01-06 23:53
Re: [轻度克系][人外][超短篇]田螺姑娘,但哪里不对
好文,但是感觉催眠的元素不太够,感觉螺类的可以用外壳的螺旋表达视角上的催眠,克系很可以,爱了爱了🥰
XL751发布于 2026-01-08 01:03
Re: [轻度克系][人外][超短篇]田螺姑娘,但哪里不对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