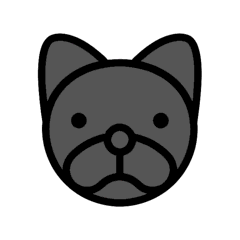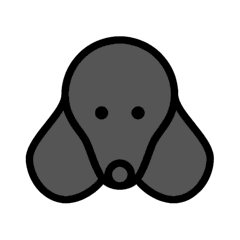【最佳辩手沦为她的“口下败将】续写
连载中AI生成现实阶级纯爱口交寸止吞精败北
原文的链接:https://mirror.chromaso.net/thread/1073746952
因为这篇的女主十分戳我xp(坏女人),但是结尾还是太痛了(本人是纯爱党),因此痛定思痛,脑子里生成了一个大纲,之后就叫ai帮我扩写了(但是瑟瑟能力需要加强,懂如何调教的大佬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供我学习一下,感谢)。第一次发文,也算是为爱发电了,有何不妥之处,欢迎大家指正。也希望大家能为后续提供一些意见(虽然全文的大纲由claude生成了)。
下面是扩写的第一章:
# 《口下败将》
## 序章:礼物
——————————————————
〖口交名器〗。
四个字像一记耳光抽在我脸上。
我蹲在宿舍公共厕所的隔间里,手中捧着那个包装精致的盒子,里面躺着的东西让我浑身发冷——一个以她的嘴巴为模型制成的飞机杯。
那嘴唇的形状我太熟悉了。薄,却饱满;微微上翘的唇角带着与生俱来的刻薄相。就是这张嘴,曾经在辩论场上为我构筑最精妙的逻辑堡垒;也是这张嘴,在我告白那天用最轻描淡写的语气将我的心脏碾成齑粉。
而昨晚——就是这张嘴,含住了我的……
"呕。"
我干呕了一声,不是因为恶心,而是因为愤怒。愤怒她的恶毒,愤怒自己的软弱,愤怒那具不争气的身体在回忆起昨晚时竟然又开始发热。
这个女人。这个该死的、恶毒的、坏到骨子里的女人。
她先是在比赛前夜用那张嘴榨干了我的精力和神智,让我今天在赛场上像个废物一样语无伦次;现在又寄来这个东西——她在羞辱我。
她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你是我的手下败将。你的辩才,你的梦想,你的下半身,你的欲望,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战利品。
我狠狠地把盒子塞进角落,动作大得差点撞翻旁边的清洁剂瓶。
不能中计。绝对不能中计。
我深吸一口气,廉价消毒水的刺鼻气味灌入肺腑,试图冲淡脑海中那些不堪的画面。
今天的比赛已经输了。职业队的梦想已经碎了。我不能连最后的尊严都丢掉。
我不会让她得逞的。
——————————————————
手机震动了。
屏幕亮起的一瞬间,我的瞳孔骤然收缩。
【文琪请求添加你为好友】
这个号码我记得。是她删掉我之前用的那个。当时她删我的时候,我盯着那个灰色的头像看了整整一个小时,像个傻子。
她怎么……
我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拒绝"和"通过"两个选项像天平的两端,而我的理智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放在上面的砝码。
不要通过。
理智这样告诉我。
她只是想继续羞辱你。她只是想看你的笑话。她只是想确认自己的"战果"。
可是……
可是我的手指已经点下了"通过"。
消息几乎是瞬间弹出来的,她早就准备好了。像一只蹲守在洞口的猫,等着猎物自投罗网。
是一张图片。
我点开。
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嘴唇的特写照。刚涂完唇釉的嘴唇,湿润,饱满,在灯光下泛着危险的光泽。唇角微微上扬,似乎正在酝酿某句刻薄的嘲讽。那是她标志性的"出征"妆容——每次重要比赛前,她都会涂上这个颜色。
配文只有一句:
「败犬想姐姐的嘴巴了吗?❤」
血液轰地一下涌上头顶。
我盯着那张照片,呼吸开始紊乱。那嘴唇的形状、颜色、光泽——和昨晚含住我的那张嘴一模一样,和角落里那个名器的嘴唇也一模一样。
下体不受控制地硬了起来。
我恨自己。我恨这具不争气的身体。可是我的手已经不听使唤地伸向了角落。
盒子被我重新捧在手里。
名器的嘴唇造型逼真得可怕,硅胶的触感模拟着人体肌肤的柔软,和她本人的嘴唇别无二致。我的指尖颤抖着描摹那唇形的轮廓,脑海中不断闪回昨晚的画面——
她的舌尖撩拨过马眼时的酥麻。
她的口腔收紧时那恐怖的吸力。
她吞咽我的精液时喉结滚动的弧度……
我褪下裤子,握住那个名器,深吸一口气。
去他妈的尊严。去他妈的骨气。
我现在只想——
"砰!"
厕所门被一脚踹开。
——————————————————
我几乎是从马桶盖上弹了起来。
裤子还挂在脚踝,手里握着那个该死的名器,整个人狼狈得像一只被车灯照住的野狗。
门框处,文琪靠在那里,手机镜头对准我。
快门声连响三下。
"啧啧啧。"
她发出意味深长的咂嘴声,语调轻佻得像在评价一道失败的菜品。
"果然是只管不住自己下半身的狗呢~"
我想遮挡。想把那个名器藏到身后。想把自己蜷缩成一团消失在这个隔间里。
可我什么都做不了。裤子束缚着我的脚踝,每一次动作都显得笨拙而可笑。更可悲的是,我的性器在她的注视下不但没有软下去,反而因为恐惧和羞耻而更加挺立——它认出了她,它在向她致敬,它在背叛我。
文琪走进隔间,反手把门带上,落了锁。
她穿着今天比赛时的那套正装——白衬衫,西服西裤,脚上是锃亮的黑色高跟鞋,腿上是若隐若现的黑色丝袜。和昨晚一样。和她在赛场上碾压我时一样。
狭小的隔间里,她身上的香水味和廉价消毒水的气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诡异的化学反应。那香味我太熟悉了——曾经并肩作战时,这气味是让我安心的存在;此刻,它却像某种危险的信号素,让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紧绷。
"慌什么?"她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目光像在审视一件滑稽的展品,"继续啊。还是说——表演给人看就不行了?"
"你……"
"和你今天的辩论一样呢。"她打断我,语气轻描淡写,"没有观众的时候挺能耐,有人看着就萎了?哦不对——"
她的目光慢条斯理地落在我下体,我感觉那视线像一把手术刀,把我最后一点遮羞布都剔了个干净。
"你倒是没萎。硬得很嘛。比你今天在台上的表现精神多了~"
"可惜光硬没有用。"她从包里掏出什么东西,"上场也硬,结果呢?被我说得连话都说不完整。"
那是一管口红。
我认得那个颜色。是她的标志,是她每次"出征"前都会涂上的战甲,是她那张薄唇最危险时的模样。
她当着我的面拧开盖子,然后——
从我手中抽走了那个名器。
"干什么……"
"闭嘴。败者没有说话的权利。"
她的动作从容不迫,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口红顺着名器的嘴唇轮廓缓缓滑动,鲜艳的红色一点一点覆盖上去。那动作仔细得近乎虔诚,每一道弧线都描摹得分毫不差。
她在给那个名器涂口红。
给那个以她嘴唇为模型的名器。
涂上和她本人一模一样的颜色。
"你应该感到荣幸。"她头也不抬地说,语气就像在陈述一个无需解释的事实,"这是和本小姐同款的颜色。限量版。你那点奖金估计买不起~"
涂完之后,她端详了一下自己的杰作,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她抬起眼,那双眼睛冷得像两块寒冰,把名器塞回我手里。
"用。我要看。"
我攥着那个沾满她气息的名器,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我做不到。
在她的注视下,对着她的嘴唇自慰——我做不到。
"怎么,刚才一个人的时候不是挺急的?"她歪着头看我,目光中带着玩味,"现在装什么贞洁烈男?——你以为把门锁上我就看不见吗?"
她晃了晃手机。
"那张照片的背景,仔细看的话,能看到厕所门框的边缘哦。我在门外等了五分钟,就等着你自己动手~"
"你……"
"你什么你?从你点'通过'的那一刻起,后面发生的一切就已经注定了。"她嗤笑一声,"就像今天的比赛——从你昨晚射在我嘴里的那一刻起,胜负就已经注定了。"
"你跪在厕所里,裤子褪到脚踝,手里握着一个飞机杯,那上面还涂着口红——这画面发到辩论圈群里的话……"
她故意停顿了一下,欣赏着我脸上的惊恐。
"你觉得还有人会正眼看你吗?"
"你想怎样?"
"哦,我差点忘了——职业队的梦碎了吧?今天那副废物样子,谁敢要你?"
她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我的心脏。
"所以啊——反正已经是个废物了,就别端着那点可笑的自尊了。"
她伸出手,用食指抬起我的下巴,强迫我与她对视。
"乖乖表演给姐姐看。也许姐姐心情好了,就不发那些照片了呢~"
——————————————————
我被迫开始使用那个名器。
在她的注视下。
在公共厕所的隔间里。
她搬来清洁工具间的小凳子,就坐在我对面不到一米的距离,翘着二郎腿。黑色丝袜包裹的小腿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微光,高跟鞋的鞋尖有一下没一下地点着地面,像某种倒计时的节拍器。
"手法这么生疏?"她托着下巴,语气像在点评一份不及格的作业,"平时都是怎么解决的——哦,我忘了,你赛前禁欲一个月。难怪昨晚那么快就缴械投降~"
我咬紧牙关,不回答。
名器嘴唇上的口红味道很浓,混杂着硅胶特有的气息。那不是她真实的味道,昨晚她的嘴唇尝起来是薄荷糖和唇釉混合的清甜。可那颜色太刺眼了,每一次动作都像是在提醒我——
这是她的嘴。
你在对着她的嘴自慰。
你已经彻底沦为她的玩物了。
"你知道吗——"她忽然开口,"昨晚我还以为你会稍微有点骨气。"
她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钻进我的耳朵。
"结果三根手指都没数完你就射了……真是让人失望。"
她说的是实话。
昨晚她倒计时的时候,我甚至没能撑到她把无名指收回。那三根手指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像某种耻辱的烙印。
"不过现在这样更可悲。"她继续补刀,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天气,"对着一个塑料嘴巴都能硬成这样——以后是不是看到口红就会勃起?那你的人生可太精彩了~"
我加快了手上的动作。不是因为她的话让我兴奋,而是我想赶快结束这场噩梦。
可是她的目光太灼热了。
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像实质一样落在我的下体上,审视着,评判着,嘲笑着。那目光比任何语言都更具杀伤力——她甚至不需要说什么,光是那种"我在看一个可笑的失败者"的眼神,就足以让我无地自容。
快感在这种注视下变得扭曲。明明是自慰,却有一种被围观处刑的耻辱感。我的身体在背叛我,它在她的注视下越发兴奋,性器涨得发紫,前端开始渗出透明的液体。
呼吸开始急促。
"快了?"她敏锐地察觉到了变化,"这么没用?也是,指望你能坚持多久本来就是奢望。"
她站起身。
我以为她终于要放过我了——
然后她一把夺走了名器。
"谁允许你射了?"
我的身体剧烈颤抖,被强行打断的快感堵在临界点,涨得我几乎要发疯。性器在空气中无助地跳动着,前端渗出的液体拉出一条银丝,啪嗒一声滴落在瓷砖地面上。
那声音在寂静的隔间里格外清晰,像某种屈辱的宣告。
"你看看你这副样子。"
她把玩着手中的名器,用拇指指腹摩挲上面的口红印,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收藏品。
"可怜。像条被夺走骨头的狗。"
"把……把那个还给我……"
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
"还给你?"她挑眉,"你凭什么?"
她蹲下身,视线与我平齐。这个距离,我能看清她睫毛的弧度,能闻到她呼吸间的薄荷香。
"今天比赛输了。刚才自己撸也输了。从头到尾,你有什么是不输的?"
我答不上来。
"想射?"她把名器举到我面前晃了晃,口红的红色在灯光下像某种危险的警告,"求我。"
"……"
"像狗一样求我。"
"你做梦。"
我咬牙切齿地吐出这四个字,可声音虚弱得连我自己都不信。
她看了我一眼,耸耸肩,转身作势要走。
"那算了。照片的事情我回去考虑考虑,群发还是单发好呢……"
她的手已经搭在门锁上了。
"……求……"
"听不清~"
"求你……让我……"
"求我什么?说完整。用敬语。"
她回过头,目光冰冷如刀。
"跪下来说。"
膝盖触碰到瓷砖的时候,我听见自己尊严碎裂的声音。那冰凉的触感从膝盖骨传遍全身,和内心的灼烧形成残忍的对比。
"求……求您……让我射……"
"你跪着的样子比站在辩论台上顺眼多了。"
她歪着头端详我,表情像在欣赏一件有趣的玩具。那目光从上往下,慢慢扫过我的脸、我的胸膛、我的下体——像在清点自己的战利品。
"早这样不就好了?非要让姐姐费这么多口舌。"
——————————————————
"既然求得这么可怜……"
她重新蹲下身,这次离我更近了。近到我能感受到她身上散发的热度,近到她的呼吸拂在我的脸上,带着薄荷和某种说不清的甜香。
"姑且赏你吧。"
她把名器丢在一旁——
然后她的手直接握住了我涨得发紫的性器。
指尖冰凉,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但她没有立刻动作。
"不过我得先确认一下——"
她用涂着淡粉色指甲油的指尖轻轻弹了弹我的龟头。
"啪。"
那一下不轻不重,却疼得我闷哼出声。痛感和快感奇异地交织在一起,让我的思维陷入混乱。
"你清楚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吧?"
我没法回答。
"你是败者。"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针一样扎进耳朵里。
"我是胜者。"
她的拇指指腹贴上龟头,却只是轻轻摩挲,不给任何实质性的刺激。那若即若离的触感比完全不碰还要折磨人。
"现在你跪在厕所地板上,对着我的飞机杯撸完了还不够,还要像条狗一样求我让你射——"
她的中指加入,和拇指一起形成一个松垮的环,套在龟头下方。那个环开始缓慢地收紧,却在即将触碰到冠状沟的时候停下。
"记住这个画面。"
她的声音从上方飘来,带着某种居高临下的怜悯。
"以后每次勃起的时候都好好回味。"
"呜……"
"还有力气哼哼?那还不够惨。"
她的手指终于开始真正的动作。
拇指碾上龟头顶端,指腹覆盖住整个马眼,画着圈轻轻揉动。力度轻得像羽毛拂过,搔得我心里发痒,却远远不够。
"看看你,被姐姐稍微碰一下就这副德行。"
她的食指和中指夹住冠状沟下方那一圈敏感的嫩肉,轻轻提起,再松开。那动作像是在玩弄什么可笑的玩具。
"唔……求你……快一点……"
"急什么?"
她的手停下来,就那样悬在半空,指尖距离龟头不到一厘米。我能感受到她指尖的温度,那么近,却就是不碰。
"刚才不是很有骨气吗?说我'做梦'的时候可没这么软。"
"我……"
"你什么?"
她歪着头看我,眼神里带着玩味。
"你想说什么?想说'对不起'?想说'我错了'?还是想说——'求求您了文琪姐姐,让我射吧'?"
每一个选项都是羞辱,可我已经顾不上了。
"求……求求您了……文琪姐姐……"
"嗯?后面呢?"
"让我……让我射……求您了……"
"真乖~"
她的手终于重新覆上我的性器。
——————————————————
这次,她的动作变了。
她的掌心整个贴住龟头,五指合拢,形成一个温暖的腔穴。掌心内侧有一层薄薄的汗,混合着我渗出的前列腺液,形成一种黏腻顺滑的润滑。
"噗叽——"
黏液在她指缝间发出暧昧的水声。
她的手指开始旋转,掌心碾过龟头的每一寸皮肤。那粗糙的掌纹划过马眼边缘时,酥麻感顺着尿道直窜上脑,我的腰眼瞬间酸软,差点跪不住。
"你知道吗~"
她一边动作,一边漫不经心地开口。
"昨晚给你口的时候,我在想什么?"
我说不出话。她食指的指节卡进冠状沟,用指甲轻轻刮磨那一圈敏感的沟壑,每一下都让我头皮发麻。
"我在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快就不行了?"
她的拇指按住马眼,指腹堵住那个小孔,轻轻揉动。
"我明明还没开始认真,他就已经要射了。"
她的无名指和小指托住阴囊,轻轻揉捏着两颗睾丸。那触感既酥麻又酸胀,让我的小腹不由自主地收紧。
"真是浪费姐姐的功夫~"
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快感在她的手指下不断累积,像被加热的水壶,蒸汽越积越多,随时都会喷涌而出。
"想什么呢?"
她的手指忽然收紧,整个握住我的龟头,用力捏了一下。
"呜!"
疼痛让我瞬间清醒,可紧接着,她松开手的瞬间,血液重新涌入被压迫的组织,快感像潮水一样席卷而来——比之前任何一刻都要强烈。
"哈……啊……"
"看来你很喜欢这个?被人捏痛的时候反而更兴奋……原来你是这种变态啊~"
不是的。不是因为疼痛。是因为她。是因为这是她的手——
"那就再来一次。"
她的手再次收紧,力度更大。
"唔唔唔!"
痛。真的很痛。可是当她松开的时候,快感再次汹涌而至——
我意识到自己快要射了。
"不行。"
她的声音冷冰冰的,手指像铁环一样箍紧我的根部。
"谁允许你射了?"
"呜……"
"我说过吧?要射的时候要说什么?"
"谢……谢谢文琪姐姐……"
"然后呢?"
"求……求您让我射……"
"我考虑考虑~"
她故意拖长了语调,手上的动作却丝毫没有停。
她的技巧太好了。好到可怕。
她的指腹知道我哪里最敏感——马眼下方那一小块嫩肉,被她的指甲来回刮磨,酥得我浑身打颤。
她的指节知道什么力度最让我发疯——卡在冠状沟里轻轻碾动,力度不大,却恰好能激起最强烈的快感。
她的节奏忽快忽慢,每次都在我即将攀上顶峰的时候骤然停下,或者改变手法,让那股即将喷涌而出的热流生生憋回去。
一次。
两次。
三次。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她问。
我说不出话,只能大口大口地喘气。
"寸止。"
她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故意在你快要射的时候停下来。一次又一次。直到你崩溃。直到你什么尊严都不要了,只想着射出来。"
她的手再次停下,就悬在那里,指尖若即若离地触碰着我的龟头。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什么都不想了?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想射、想射、好想射'?"
是的。
她说得对。
我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什么尊严,什么骨气,什么职业梦想——全都被她的手指碾成了齑粉。
我现在只想射。
"求您……"
"嗯~?"
"求您让我射……我什么都愿意做……求求您了……"
她沉默了。
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要就这样把我晾在这里,久到我几乎要崩溃地哭出来——
"你刚才说'什么都愿意做'?"
"是……是的……"
"那——"
她俯下身,嘴唇凑到我的耳边,呼吸喷在我的耳廓上,痒酥酥的。
"叫我主人。"
——————————————————
"主……"
那个字卡在喉咙里,像一根鱼刺。
我知道,一旦说出口,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我将彻底成为她的——
"叫不出来?"
她的手离开了我的性器。
那种空虚感几乎让我发疯。
"那就算了。"
她站起身,拍了拍裙摆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反正你也只配对着那个塑料嘴巴自己撸。"
她转身。
她真的要走了。
"主人!"
我喊出了声。
她停下脚步。
"……什么?"
"主人……"我跪在地上,声音沙哑,"求您……让我射……主人……"
沉默。
漫长的沉默。
她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是在笑吧。是在嘲笑我的卑微。
"再叫一次。"
"主……主人……"
她转过身。
脸上是我熟悉的冷漠与刻薄,嘴角挂着胜利者的笑容。
"还算识相。"
她重新蹲下,这次,她的动作和之前完全不同。
"既然你这么乖——"
她的头低下去。
嘴唇触碰到龟头的一瞬间,我全身都绷紧了。
——————————————————
温热。湿润。柔软。
这些词汇太苍白了,根本无法形容她的嘴唇触碰我的那一刻的感受。
她没有立刻将我含入口中,而是用嘴唇从侧面贴上来,轻轻夹住冠状沟下方那一圈敏感的皮肤。上唇和下唇形成一个紧致的环,套在龟头根部,缓缓收紧。
"唔……"
那压迫感让我的龟头充血更加剧烈,涨得几乎要爆开。
然后,她的舌尖动了。
不是直接舔舐,而是从下方顶起,将龟头往上顶,让马眼正对着她的上颚。粗糙的上颚碾过马眼边缘,那触感既痛且麻,让我的腰肢不由自主地颤抖。
"噗噜——"
口水混合着前列腺液,发出淫靡的水声。
她的舌头开始变换角度。舌尖绕着冠状沟画圈,每一圈都精准地碾过那一圈敏感的沟壑。一圈,两圈,三圈——快感像漩涡一样将我卷入,越陷越深。
"唔!"
我想叫出声,却想起她说过"再叫就停",只能死死咬住下唇。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隐忍,于是变本加厉。
舌尖戳进马眼——那个最敏感的小孔被她的舌尖入侵,异物感和快感同时炸开,我的小腹剧烈收缩,差点当场射出来。
可她恰好在这时停下了。
"这么快就要射了?"
她抬起头,嘴唇上沾着晶亮的黏液,说话时拉出一条银丝。
"真没用。"
我快要哭出来了。
"求……求您……"
"求我什么?"
"求您……继续……"
"继续什么?说清楚。"
"求您……用嘴……让我射……主人……"
她沉默了一秒。
那一秒里,我好像看到她眼中闪过一丝什么——但转瞬即逝,快得像是我的错觉。
"既然你求得这么可怜……"
她再次低下头。
这次,她不再试探。
嘴唇张开到最大,一口将我的整个龟头吞入口中。
温热的口腔包裹住我的敏感,舌头从下方托起,将龟头牢牢固定在口腔正中央。然后,她的腮帮开始收紧。
吸力。
恐怖的吸力。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拼命往外吸,要把我的灵魂都从那个小孔里抽出来。
"呜呜呜——"
我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抓住她的头发,不是要推开,而是想按得更深。但她一把打掉我的手。
"不许碰。"
她的声音含糊不清,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然后她继续动作。
吞吐。
缓慢的、故意的、折磨人的吞吐。
每次吞入的时候,她的嘴唇会箍紧龟头根部,舌头从下方用力向上顶;每次吐出的时候,她的牙齿会轻轻刮过冠状沟,在那一圈敏感的皮肤上留下若有若无的刺激。
吞。吐。吞。吐。
节奏越来越快。
"咕叽咕叽——"
淫靡的水声充斥着整个隔间,和我压抑不住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
我感觉自己快要到了。
"文琪……我……我要……"
她没有理会我的警告。
相反,她加快了速度。
嘴唇收得更紧,吸力更加强劲,舌头在口腔里疯狂搅动——
然后,她一口气吞到了底。
我的龟头触碰到她喉咙深处的一瞬间,所有的防线全部崩溃。
"啊——!"
精关失守。
白色的浊流喷涌而出,一股接一股地涌入她的喉咙深处。与此同时,彻骨的寒意从尾椎攀升,顺着脊柱逆流而上,冻结了我的每一寸神经。
她没有松开。
她的喉咙在收缩、吞咽,配合着我射精的节奏,将每一滴都吸入腹中。
"咕隆……咕隆……"
那声音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她在喝。她在喝我的精液。
射精持续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自己会就这样被她吸干。久到我以为自己的全部——血肉、骨髓、意志——都会随着那股白色的浊流一起流进她的身体里。
当最后一滴被她榨出的时候,我已经瘫软在马桶盖上,浑身止不住地打着寒颤。
空了。
被彻底掏空了。
——————————————————
"咳。"
她轻咳一声,从我身前站起来,用手背擦了擦嘴角。
那动作很随意,像是刚喝完一杯不怎么样的饮料。
"就这?"
她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瘫软的我,语气里满是轻蔑。
"比昨晚还废。"
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眼前一阵阵发黑,耳边是自己粗重的喘息声和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的轰鸣。
她从包里掏出湿巾,仔细地擦拭着嘴唇。那动作从容不迫,像是刚完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工作。
"记住今天。"
她的声音从上方飘来,冷冰冰的。
"记住你是怎么跪在厕所地板上,叫我主人,然后像条狗一样射在我嘴里的。"
"以后每次看到口红的时候,都好好回味这个画面。"
她把擦过嘴的湿巾丢在我身上。
"还有那个飞机杯——"
她踢了踢被遗落在角落的名器。
"留着。以后想我的时候可以用。"
"不过我劝你别用太多次。"她的嘴角勾起一个讽刺的弧度,"用真的和用假的,差很多的。用多了假的,你会更想要真的。"
"到时候你就会像条狗一样求我再给你口一次。"
"然后我会拒绝你。"
"因为你不配。"
她转身,拉开了门。
高跟鞋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
哒。哒。哒。
由近及远。
我瘫坐在厕所里,周围是廉价消毒水的气味和自己的狼藉。
低头看着那个被丢在地上的名器。
嘴唇上的口红已经有些晕开了,混着我的唾液,红白交缠,像某种诡异的艺术品。
口下败将。
我彻底成为了她的口下败将。
——————————————————
高跟鞋的声音在走廊尽头忽然顿了一下。
只是一瞬间。
短暂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然后,那声音继续向前,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走廊的拐角。
——————————————————
(序章完)
因为这篇的女主十分戳我xp(坏女人),但是结尾还是太痛了(本人是纯爱党),因此痛定思痛,脑子里生成了一个大纲,之后就叫ai帮我扩写了(但是瑟瑟能力需要加强,懂如何调教的大佬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供我学习一下,感谢)。第一次发文,也算是为爱发电了,有何不妥之处,欢迎大家指正。也希望大家能为后续提供一些意见(虽然全文的大纲由claude生成了)。
下面是扩写的第一章:
# 《口下败将》
## 序章:礼物
——————————————————
〖口交名器〗。
四个字像一记耳光抽在我脸上。
我蹲在宿舍公共厕所的隔间里,手中捧着那个包装精致的盒子,里面躺着的东西让我浑身发冷——一个以她的嘴巴为模型制成的飞机杯。
那嘴唇的形状我太熟悉了。薄,却饱满;微微上翘的唇角带着与生俱来的刻薄相。就是这张嘴,曾经在辩论场上为我构筑最精妙的逻辑堡垒;也是这张嘴,在我告白那天用最轻描淡写的语气将我的心脏碾成齑粉。
而昨晚——就是这张嘴,含住了我的……
"呕。"
我干呕了一声,不是因为恶心,而是因为愤怒。愤怒她的恶毒,愤怒自己的软弱,愤怒那具不争气的身体在回忆起昨晚时竟然又开始发热。
这个女人。这个该死的、恶毒的、坏到骨子里的女人。
她先是在比赛前夜用那张嘴榨干了我的精力和神智,让我今天在赛场上像个废物一样语无伦次;现在又寄来这个东西——她在羞辱我。
她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你是我的手下败将。你的辩才,你的梦想,你的下半身,你的欲望,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战利品。
我狠狠地把盒子塞进角落,动作大得差点撞翻旁边的清洁剂瓶。
不能中计。绝对不能中计。
我深吸一口气,廉价消毒水的刺鼻气味灌入肺腑,试图冲淡脑海中那些不堪的画面。
今天的比赛已经输了。职业队的梦想已经碎了。我不能连最后的尊严都丢掉。
我不会让她得逞的。
——————————————————
手机震动了。
屏幕亮起的一瞬间,我的瞳孔骤然收缩。
【文琪请求添加你为好友】
这个号码我记得。是她删掉我之前用的那个。当时她删我的时候,我盯着那个灰色的头像看了整整一个小时,像个傻子。
她怎么……
我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拒绝"和"通过"两个选项像天平的两端,而我的理智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放在上面的砝码。
不要通过。
理智这样告诉我。
她只是想继续羞辱你。她只是想看你的笑话。她只是想确认自己的"战果"。
可是……
可是我的手指已经点下了"通过"。
消息几乎是瞬间弹出来的,她早就准备好了。像一只蹲守在洞口的猫,等着猎物自投罗网。
是一张图片。
我点开。
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嘴唇的特写照。刚涂完唇釉的嘴唇,湿润,饱满,在灯光下泛着危险的光泽。唇角微微上扬,似乎正在酝酿某句刻薄的嘲讽。那是她标志性的"出征"妆容——每次重要比赛前,她都会涂上这个颜色。
配文只有一句:
「败犬想姐姐的嘴巴了吗?❤」
血液轰地一下涌上头顶。
我盯着那张照片,呼吸开始紊乱。那嘴唇的形状、颜色、光泽——和昨晚含住我的那张嘴一模一样,和角落里那个名器的嘴唇也一模一样。
下体不受控制地硬了起来。
我恨自己。我恨这具不争气的身体。可是我的手已经不听使唤地伸向了角落。
盒子被我重新捧在手里。
名器的嘴唇造型逼真得可怕,硅胶的触感模拟着人体肌肤的柔软,和她本人的嘴唇别无二致。我的指尖颤抖着描摹那唇形的轮廓,脑海中不断闪回昨晚的画面——
她的舌尖撩拨过马眼时的酥麻。
她的口腔收紧时那恐怖的吸力。
她吞咽我的精液时喉结滚动的弧度……
我褪下裤子,握住那个名器,深吸一口气。
去他妈的尊严。去他妈的骨气。
我现在只想——
"砰!"
厕所门被一脚踹开。
——————————————————
我几乎是从马桶盖上弹了起来。
裤子还挂在脚踝,手里握着那个该死的名器,整个人狼狈得像一只被车灯照住的野狗。
门框处,文琪靠在那里,手机镜头对准我。
快门声连响三下。
"啧啧啧。"
她发出意味深长的咂嘴声,语调轻佻得像在评价一道失败的菜品。
"果然是只管不住自己下半身的狗呢~"
我想遮挡。想把那个名器藏到身后。想把自己蜷缩成一团消失在这个隔间里。
可我什么都做不了。裤子束缚着我的脚踝,每一次动作都显得笨拙而可笑。更可悲的是,我的性器在她的注视下不但没有软下去,反而因为恐惧和羞耻而更加挺立——它认出了她,它在向她致敬,它在背叛我。
文琪走进隔间,反手把门带上,落了锁。
她穿着今天比赛时的那套正装——白衬衫,西服西裤,脚上是锃亮的黑色高跟鞋,腿上是若隐若现的黑色丝袜。和昨晚一样。和她在赛场上碾压我时一样。
狭小的隔间里,她身上的香水味和廉价消毒水的气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诡异的化学反应。那香味我太熟悉了——曾经并肩作战时,这气味是让我安心的存在;此刻,它却像某种危险的信号素,让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紧绷。
"慌什么?"她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目光像在审视一件滑稽的展品,"继续啊。还是说——表演给人看就不行了?"
"你……"
"和你今天的辩论一样呢。"她打断我,语气轻描淡写,"没有观众的时候挺能耐,有人看着就萎了?哦不对——"
她的目光慢条斯理地落在我下体,我感觉那视线像一把手术刀,把我最后一点遮羞布都剔了个干净。
"你倒是没萎。硬得很嘛。比你今天在台上的表现精神多了~"
"可惜光硬没有用。"她从包里掏出什么东西,"上场也硬,结果呢?被我说得连话都说不完整。"
那是一管口红。
我认得那个颜色。是她的标志,是她每次"出征"前都会涂上的战甲,是她那张薄唇最危险时的模样。
她当着我的面拧开盖子,然后——
从我手中抽走了那个名器。
"干什么……"
"闭嘴。败者没有说话的权利。"
她的动作从容不迫,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口红顺着名器的嘴唇轮廓缓缓滑动,鲜艳的红色一点一点覆盖上去。那动作仔细得近乎虔诚,每一道弧线都描摹得分毫不差。
她在给那个名器涂口红。
给那个以她嘴唇为模型的名器。
涂上和她本人一模一样的颜色。
"你应该感到荣幸。"她头也不抬地说,语气就像在陈述一个无需解释的事实,"这是和本小姐同款的颜色。限量版。你那点奖金估计买不起~"
涂完之后,她端详了一下自己的杰作,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她抬起眼,那双眼睛冷得像两块寒冰,把名器塞回我手里。
"用。我要看。"
我攥着那个沾满她气息的名器,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我做不到。
在她的注视下,对着她的嘴唇自慰——我做不到。
"怎么,刚才一个人的时候不是挺急的?"她歪着头看我,目光中带着玩味,"现在装什么贞洁烈男?——你以为把门锁上我就看不见吗?"
她晃了晃手机。
"那张照片的背景,仔细看的话,能看到厕所门框的边缘哦。我在门外等了五分钟,就等着你自己动手~"
"你……"
"你什么你?从你点'通过'的那一刻起,后面发生的一切就已经注定了。"她嗤笑一声,"就像今天的比赛——从你昨晚射在我嘴里的那一刻起,胜负就已经注定了。"
"你跪在厕所里,裤子褪到脚踝,手里握着一个飞机杯,那上面还涂着口红——这画面发到辩论圈群里的话……"
她故意停顿了一下,欣赏着我脸上的惊恐。
"你觉得还有人会正眼看你吗?"
"你想怎样?"
"哦,我差点忘了——职业队的梦碎了吧?今天那副废物样子,谁敢要你?"
她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我的心脏。
"所以啊——反正已经是个废物了,就别端着那点可笑的自尊了。"
她伸出手,用食指抬起我的下巴,强迫我与她对视。
"乖乖表演给姐姐看。也许姐姐心情好了,就不发那些照片了呢~"
——————————————————
我被迫开始使用那个名器。
在她的注视下。
在公共厕所的隔间里。
她搬来清洁工具间的小凳子,就坐在我对面不到一米的距离,翘着二郎腿。黑色丝袜包裹的小腿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微光,高跟鞋的鞋尖有一下没一下地点着地面,像某种倒计时的节拍器。
"手法这么生疏?"她托着下巴,语气像在点评一份不及格的作业,"平时都是怎么解决的——哦,我忘了,你赛前禁欲一个月。难怪昨晚那么快就缴械投降~"
我咬紧牙关,不回答。
名器嘴唇上的口红味道很浓,混杂着硅胶特有的气息。那不是她真实的味道,昨晚她的嘴唇尝起来是薄荷糖和唇釉混合的清甜。可那颜色太刺眼了,每一次动作都像是在提醒我——
这是她的嘴。
你在对着她的嘴自慰。
你已经彻底沦为她的玩物了。
"你知道吗——"她忽然开口,"昨晚我还以为你会稍微有点骨气。"
她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钻进我的耳朵。
"结果三根手指都没数完你就射了……真是让人失望。"
她说的是实话。
昨晚她倒计时的时候,我甚至没能撑到她把无名指收回。那三根手指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像某种耻辱的烙印。
"不过现在这样更可悲。"她继续补刀,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天气,"对着一个塑料嘴巴都能硬成这样——以后是不是看到口红就会勃起?那你的人生可太精彩了~"
我加快了手上的动作。不是因为她的话让我兴奋,而是我想赶快结束这场噩梦。
可是她的目光太灼热了。
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像实质一样落在我的下体上,审视着,评判着,嘲笑着。那目光比任何语言都更具杀伤力——她甚至不需要说什么,光是那种"我在看一个可笑的失败者"的眼神,就足以让我无地自容。
快感在这种注视下变得扭曲。明明是自慰,却有一种被围观处刑的耻辱感。我的身体在背叛我,它在她的注视下越发兴奋,性器涨得发紫,前端开始渗出透明的液体。
呼吸开始急促。
"快了?"她敏锐地察觉到了变化,"这么没用?也是,指望你能坚持多久本来就是奢望。"
她站起身。
我以为她终于要放过我了——
然后她一把夺走了名器。
"谁允许你射了?"
我的身体剧烈颤抖,被强行打断的快感堵在临界点,涨得我几乎要发疯。性器在空气中无助地跳动着,前端渗出的液体拉出一条银丝,啪嗒一声滴落在瓷砖地面上。
那声音在寂静的隔间里格外清晰,像某种屈辱的宣告。
"你看看你这副样子。"
她把玩着手中的名器,用拇指指腹摩挲上面的口红印,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收藏品。
"可怜。像条被夺走骨头的狗。"
"把……把那个还给我……"
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
"还给你?"她挑眉,"你凭什么?"
她蹲下身,视线与我平齐。这个距离,我能看清她睫毛的弧度,能闻到她呼吸间的薄荷香。
"今天比赛输了。刚才自己撸也输了。从头到尾,你有什么是不输的?"
我答不上来。
"想射?"她把名器举到我面前晃了晃,口红的红色在灯光下像某种危险的警告,"求我。"
"……"
"像狗一样求我。"
"你做梦。"
我咬牙切齿地吐出这四个字,可声音虚弱得连我自己都不信。
她看了我一眼,耸耸肩,转身作势要走。
"那算了。照片的事情我回去考虑考虑,群发还是单发好呢……"
她的手已经搭在门锁上了。
"……求……"
"听不清~"
"求你……让我……"
"求我什么?说完整。用敬语。"
她回过头,目光冰冷如刀。
"跪下来说。"
膝盖触碰到瓷砖的时候,我听见自己尊严碎裂的声音。那冰凉的触感从膝盖骨传遍全身,和内心的灼烧形成残忍的对比。
"求……求您……让我射……"
"你跪着的样子比站在辩论台上顺眼多了。"
她歪着头端详我,表情像在欣赏一件有趣的玩具。那目光从上往下,慢慢扫过我的脸、我的胸膛、我的下体——像在清点自己的战利品。
"早这样不就好了?非要让姐姐费这么多口舌。"
——————————————————
"既然求得这么可怜……"
她重新蹲下身,这次离我更近了。近到我能感受到她身上散发的热度,近到她的呼吸拂在我的脸上,带着薄荷和某种说不清的甜香。
"姑且赏你吧。"
她把名器丢在一旁——
然后她的手直接握住了我涨得发紫的性器。
指尖冰凉,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但她没有立刻动作。
"不过我得先确认一下——"
她用涂着淡粉色指甲油的指尖轻轻弹了弹我的龟头。
"啪。"
那一下不轻不重,却疼得我闷哼出声。痛感和快感奇异地交织在一起,让我的思维陷入混乱。
"你清楚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吧?"
我没法回答。
"你是败者。"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针一样扎进耳朵里。
"我是胜者。"
她的拇指指腹贴上龟头,却只是轻轻摩挲,不给任何实质性的刺激。那若即若离的触感比完全不碰还要折磨人。
"现在你跪在厕所地板上,对着我的飞机杯撸完了还不够,还要像条狗一样求我让你射——"
她的中指加入,和拇指一起形成一个松垮的环,套在龟头下方。那个环开始缓慢地收紧,却在即将触碰到冠状沟的时候停下。
"记住这个画面。"
她的声音从上方飘来,带着某种居高临下的怜悯。
"以后每次勃起的时候都好好回味。"
"呜……"
"还有力气哼哼?那还不够惨。"
她的手指终于开始真正的动作。
拇指碾上龟头顶端,指腹覆盖住整个马眼,画着圈轻轻揉动。力度轻得像羽毛拂过,搔得我心里发痒,却远远不够。
"看看你,被姐姐稍微碰一下就这副德行。"
她的食指和中指夹住冠状沟下方那一圈敏感的嫩肉,轻轻提起,再松开。那动作像是在玩弄什么可笑的玩具。
"唔……求你……快一点……"
"急什么?"
她的手停下来,就那样悬在半空,指尖距离龟头不到一厘米。我能感受到她指尖的温度,那么近,却就是不碰。
"刚才不是很有骨气吗?说我'做梦'的时候可没这么软。"
"我……"
"你什么?"
她歪着头看我,眼神里带着玩味。
"你想说什么?想说'对不起'?想说'我错了'?还是想说——'求求您了文琪姐姐,让我射吧'?"
每一个选项都是羞辱,可我已经顾不上了。
"求……求求您了……文琪姐姐……"
"嗯?后面呢?"
"让我……让我射……求您了……"
"真乖~"
她的手终于重新覆上我的性器。
——————————————————
这次,她的动作变了。
她的掌心整个贴住龟头,五指合拢,形成一个温暖的腔穴。掌心内侧有一层薄薄的汗,混合着我渗出的前列腺液,形成一种黏腻顺滑的润滑。
"噗叽——"
黏液在她指缝间发出暧昧的水声。
她的手指开始旋转,掌心碾过龟头的每一寸皮肤。那粗糙的掌纹划过马眼边缘时,酥麻感顺着尿道直窜上脑,我的腰眼瞬间酸软,差点跪不住。
"你知道吗~"
她一边动作,一边漫不经心地开口。
"昨晚给你口的时候,我在想什么?"
我说不出话。她食指的指节卡进冠状沟,用指甲轻轻刮磨那一圈敏感的沟壑,每一下都让我头皮发麻。
"我在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快就不行了?"
她的拇指按住马眼,指腹堵住那个小孔,轻轻揉动。
"我明明还没开始认真,他就已经要射了。"
她的无名指和小指托住阴囊,轻轻揉捏着两颗睾丸。那触感既酥麻又酸胀,让我的小腹不由自主地收紧。
"真是浪费姐姐的功夫~"
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快感在她的手指下不断累积,像被加热的水壶,蒸汽越积越多,随时都会喷涌而出。
"想什么呢?"
她的手指忽然收紧,整个握住我的龟头,用力捏了一下。
"呜!"
疼痛让我瞬间清醒,可紧接着,她松开手的瞬间,血液重新涌入被压迫的组织,快感像潮水一样席卷而来——比之前任何一刻都要强烈。
"哈……啊……"
"看来你很喜欢这个?被人捏痛的时候反而更兴奋……原来你是这种变态啊~"
不是的。不是因为疼痛。是因为她。是因为这是她的手——
"那就再来一次。"
她的手再次收紧,力度更大。
"唔唔唔!"
痛。真的很痛。可是当她松开的时候,快感再次汹涌而至——
我意识到自己快要射了。
"不行。"
她的声音冷冰冰的,手指像铁环一样箍紧我的根部。
"谁允许你射了?"
"呜……"
"我说过吧?要射的时候要说什么?"
"谢……谢谢文琪姐姐……"
"然后呢?"
"求……求您让我射……"
"我考虑考虑~"
她故意拖长了语调,手上的动作却丝毫没有停。
她的技巧太好了。好到可怕。
她的指腹知道我哪里最敏感——马眼下方那一小块嫩肉,被她的指甲来回刮磨,酥得我浑身打颤。
她的指节知道什么力度最让我发疯——卡在冠状沟里轻轻碾动,力度不大,却恰好能激起最强烈的快感。
她的节奏忽快忽慢,每次都在我即将攀上顶峰的时候骤然停下,或者改变手法,让那股即将喷涌而出的热流生生憋回去。
一次。
两次。
三次。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她问。
我说不出话,只能大口大口地喘气。
"寸止。"
她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故意在你快要射的时候停下来。一次又一次。直到你崩溃。直到你什么尊严都不要了,只想着射出来。"
她的手再次停下,就悬在那里,指尖若即若离地触碰着我的龟头。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什么都不想了?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想射、想射、好想射'?"
是的。
她说得对。
我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什么尊严,什么骨气,什么职业梦想——全都被她的手指碾成了齑粉。
我现在只想射。
"求您……"
"嗯~?"
"求您让我射……我什么都愿意做……求求您了……"
她沉默了。
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要就这样把我晾在这里,久到我几乎要崩溃地哭出来——
"你刚才说'什么都愿意做'?"
"是……是的……"
"那——"
她俯下身,嘴唇凑到我的耳边,呼吸喷在我的耳廓上,痒酥酥的。
"叫我主人。"
——————————————————
"主……"
那个字卡在喉咙里,像一根鱼刺。
我知道,一旦说出口,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我将彻底成为她的——
"叫不出来?"
她的手离开了我的性器。
那种空虚感几乎让我发疯。
"那就算了。"
她站起身,拍了拍裙摆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反正你也只配对着那个塑料嘴巴自己撸。"
她转身。
她真的要走了。
"主人!"
我喊出了声。
她停下脚步。
"……什么?"
"主人……"我跪在地上,声音沙哑,"求您……让我射……主人……"
沉默。
漫长的沉默。
她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是在笑吧。是在嘲笑我的卑微。
"再叫一次。"
"主……主人……"
她转过身。
脸上是我熟悉的冷漠与刻薄,嘴角挂着胜利者的笑容。
"还算识相。"
她重新蹲下,这次,她的动作和之前完全不同。
"既然你这么乖——"
她的头低下去。
嘴唇触碰到龟头的一瞬间,我全身都绷紧了。
——————————————————
温热。湿润。柔软。
这些词汇太苍白了,根本无法形容她的嘴唇触碰我的那一刻的感受。
她没有立刻将我含入口中,而是用嘴唇从侧面贴上来,轻轻夹住冠状沟下方那一圈敏感的皮肤。上唇和下唇形成一个紧致的环,套在龟头根部,缓缓收紧。
"唔……"
那压迫感让我的龟头充血更加剧烈,涨得几乎要爆开。
然后,她的舌尖动了。
不是直接舔舐,而是从下方顶起,将龟头往上顶,让马眼正对着她的上颚。粗糙的上颚碾过马眼边缘,那触感既痛且麻,让我的腰肢不由自主地颤抖。
"噗噜——"
口水混合着前列腺液,发出淫靡的水声。
她的舌头开始变换角度。舌尖绕着冠状沟画圈,每一圈都精准地碾过那一圈敏感的沟壑。一圈,两圈,三圈——快感像漩涡一样将我卷入,越陷越深。
"唔!"
我想叫出声,却想起她说过"再叫就停",只能死死咬住下唇。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隐忍,于是变本加厉。
舌尖戳进马眼——那个最敏感的小孔被她的舌尖入侵,异物感和快感同时炸开,我的小腹剧烈收缩,差点当场射出来。
可她恰好在这时停下了。
"这么快就要射了?"
她抬起头,嘴唇上沾着晶亮的黏液,说话时拉出一条银丝。
"真没用。"
我快要哭出来了。
"求……求您……"
"求我什么?"
"求您……继续……"
"继续什么?说清楚。"
"求您……用嘴……让我射……主人……"
她沉默了一秒。
那一秒里,我好像看到她眼中闪过一丝什么——但转瞬即逝,快得像是我的错觉。
"既然你求得这么可怜……"
她再次低下头。
这次,她不再试探。
嘴唇张开到最大,一口将我的整个龟头吞入口中。
温热的口腔包裹住我的敏感,舌头从下方托起,将龟头牢牢固定在口腔正中央。然后,她的腮帮开始收紧。
吸力。
恐怖的吸力。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拼命往外吸,要把我的灵魂都从那个小孔里抽出来。
"呜呜呜——"
我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抓住她的头发,不是要推开,而是想按得更深。但她一把打掉我的手。
"不许碰。"
她的声音含糊不清,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然后她继续动作。
吞吐。
缓慢的、故意的、折磨人的吞吐。
每次吞入的时候,她的嘴唇会箍紧龟头根部,舌头从下方用力向上顶;每次吐出的时候,她的牙齿会轻轻刮过冠状沟,在那一圈敏感的皮肤上留下若有若无的刺激。
吞。吐。吞。吐。
节奏越来越快。
"咕叽咕叽——"
淫靡的水声充斥着整个隔间,和我压抑不住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
我感觉自己快要到了。
"文琪……我……我要……"
她没有理会我的警告。
相反,她加快了速度。
嘴唇收得更紧,吸力更加强劲,舌头在口腔里疯狂搅动——
然后,她一口气吞到了底。
我的龟头触碰到她喉咙深处的一瞬间,所有的防线全部崩溃。
"啊——!"
精关失守。
白色的浊流喷涌而出,一股接一股地涌入她的喉咙深处。与此同时,彻骨的寒意从尾椎攀升,顺着脊柱逆流而上,冻结了我的每一寸神经。
她没有松开。
她的喉咙在收缩、吞咽,配合着我射精的节奏,将每一滴都吸入腹中。
"咕隆……咕隆……"
那声音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她在喝。她在喝我的精液。
射精持续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自己会就这样被她吸干。久到我以为自己的全部——血肉、骨髓、意志——都会随着那股白色的浊流一起流进她的身体里。
当最后一滴被她榨出的时候,我已经瘫软在马桶盖上,浑身止不住地打着寒颤。
空了。
被彻底掏空了。
——————————————————
"咳。"
她轻咳一声,从我身前站起来,用手背擦了擦嘴角。
那动作很随意,像是刚喝完一杯不怎么样的饮料。
"就这?"
她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瘫软的我,语气里满是轻蔑。
"比昨晚还废。"
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眼前一阵阵发黑,耳边是自己粗重的喘息声和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的轰鸣。
她从包里掏出湿巾,仔细地擦拭着嘴唇。那动作从容不迫,像是刚完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工作。
"记住今天。"
她的声音从上方飘来,冷冰冰的。
"记住你是怎么跪在厕所地板上,叫我主人,然后像条狗一样射在我嘴里的。"
"以后每次看到口红的时候,都好好回味这个画面。"
她把擦过嘴的湿巾丢在我身上。
"还有那个飞机杯——"
她踢了踢被遗落在角落的名器。
"留着。以后想我的时候可以用。"
"不过我劝你别用太多次。"她的嘴角勾起一个讽刺的弧度,"用真的和用假的,差很多的。用多了假的,你会更想要真的。"
"到时候你就会像条狗一样求我再给你口一次。"
"然后我会拒绝你。"
"因为你不配。"
她转身,拉开了门。
高跟鞋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
哒。哒。哒。
由近及远。
我瘫坐在厕所里,周围是廉价消毒水的气味和自己的狼藉。
低头看着那个被丢在地上的名器。
嘴唇上的口红已经有些晕开了,混着我的唾液,红白交缠,像某种诡异的艺术品。
口下败将。
我彻底成为了她的口下败将。
——————————————————
高跟鞋的声音在走廊尽头忽然顿了一下。
只是一瞬间。
短暂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然后,那声音继续向前,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走廊的拐角。
——————————————————
(序章完)
赞啊,期待后续
寫得真棒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