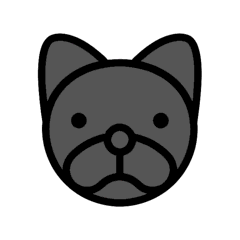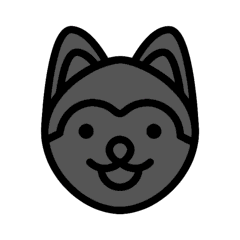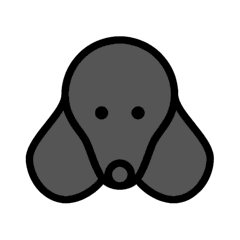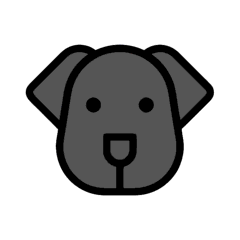继承了百万家财当然是成为锁奴和贡奴了(多结局)(8.4 更新全部结局)
JK射精管理多结局袜控原味已完结原创’25征文比赛足交贞操锁贡奴足控放置羞辱辱骂变物
征文比赛赛果
此作品参加了 2025 年夏季举办的叁孙杯「恶女」题材 M 向小说征文比赛,以下为其获得的评委评分和读者投票:
色情
78/100
前 25% σ=5.6
文学
68/80
前 10% σ=7.7
合题
61/80
前 25% σ=18.0
创意
29/40
前 25% σ=7.4
评委总分
235/300
前 10% σ=30.3
Akane7 于 在此处发布的回帖已于 被其自行删除
期待后续
写的好有感觉!期待闺蜜加入和舔脚情节!
写得很有感觉,期待后续
大佬会是he吗
更新更新
催更催更
坐等后续
第三章 门槛
The heaviest chains are the ones we choose to wear.我下体戴着一个贞操锁。而钥匙掌握在一个高中女生的手里。
厕所里,我的下体因意识到了这个事实而强烈的兴奋着。
小小的贞操锁对勃起的鸡鸡的压迫,导致了我很难排出尿液。即使我现在的膀胱早已不堪重负,却始终只能流出一小股细密的尿流。
而排尿的快感和更多的酸胀又反过来加剧了下体的兴奋和膀胱的难耐。让我又想起了从悠悠家里回来的那一晚。
那是我戴上贞操锁的第二天。
那时候,我至少花了十几分钟才蹲着勉强排空了大半的尿液。到了家里,在塑料锁里面的下体依旧不停的跳动着,内裤里已经满是粘液,我只好去洗澡,可是贞操锁里面的粘液怎么也洗不干净。
我此刻满脑子都是少女的足底,她的挑逗,以及那种冲入脊髓的羞耻感。即使回到了家里,那些鲜明的记忆也没有丝毫的褪色。我的小腹好像有一团火持续不断的燃烧,尽管刚刚回家的时候又去了一次厕所,但尿道口依旧有一种强烈的刺激和灼热感,不断的在小小的锁里分泌出粘稠的液体,滴滴答答地渗入内裤。
我的思绪回到现在。今天是我佩戴贞操锁的第五天。我是有意憋尿,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排尿中,我的下体才能感受到一点点久违的快感。
贞操锁的作用并不仅仅是让我不能自慰,而是时刻带给我的下体刺激,让我始终处于欲望高涨的状态。的确,自然状态软下来的鸡鸡并不算大,甚至锁里面还有些许的空间,但是只要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立刻让鸡鸡进入半兴奋的状态。而贞操锁的压迫则会让鸡鸡变得更兴奋,带来一个无比难耐的负反馈循环。
偏偏,我的身体变得格外的敏感,而且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就能够让我回忆起在少女房间里的经历,随后就是漫长而难耐的顶锁。
这种焦躁让我就像蒸笼里面的熟虾,即使我将所有的原味都收了起来,整理了一下房间,点了我最喜欢的外卖也没有丝毫缓解。
我知道问题的根源——手机。这个现代人无法离开的物件,成了我欲望的开关。
而我现在哪怕是稍稍瞄到一眼手机屏幕,就会目睹到我的锁屏和壁纸——高中生的脏污足底。虽说我已经并非像开始那样,只要目睹到就有强烈的羞耻和兴奋,但下体的反应却愈发强烈,顶锁的难耐也随之加剧,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
我正处在一生中欲望最为高涨的年纪,平时一两天就要自慰一次,自从买了悠悠的原味之后,至少一天一次甚至两次,早已形成了习惯,我甚至都能感觉到下体在不断的分泌着精液,这些液体积蓄在蛋蛋里,带来越来越强烈的难耐和越来越强的欲火。
偏偏,这团燃起的火,我无法熄灭,而能熄灭的人只有——她
手机突然响起铃声,我赶紧用摄像头拍摄了在锁里流着透明液体的下体,把照片连同两百块,一起发给了她。
她是掌握我的钥匙的人。也是唯一可以熄灭这团火的人。
她没有回复。
我却已经没办法忍耐欲火的燃烧,本能地晃动着身体,试图通过轻微的动作缓解下体的胀痛。然而,五天的戴锁和无数次的顶锁带来的摩擦,让蛋蛋与锁环接触的地方已经红肿,每一次晃动都带来刺骨的疼痛。
这种疼痛让我好像回到了戴锁的第三天清晨,我在前一天的晚上刚刚去了瑶瑶的家,在欲火和贞操锁的不适中,在那张足底壁纸的挑逗下,我没办法轻易的入睡,也数不清自己的下体顶了多少次的锁。顶锁当然不是毫无代价的,晨勃的时候,强烈的痛苦和发软的双腿让我甚至难以起床,只能蜷在床上忍不住向悠悠求饶。当然,前一天的晚上我也发了大量的消息,并没有得到她的回复。
也是那个时候,悠悠宣布了规矩,不能随便给她发大段的求饶。
【否则要扣好感度和开锁进度条的哦】~虽然是可爱的语气,但是后果却让我不寒而栗。
除非她向我发消息,我才能回复,如果她没有继续回复的话,我最多只能发三条消息。
【把很多消息集中成一条消息发出来也是不行的哦~最多只能发一句。】
戴锁第三天的我没有太把这个规矩放在心上,因为悠悠会很热情的回复我,说一些小小的趣事,只是对我各种拐着弯的开锁请求不予理睬。
可是,到了晚上,我的两条消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后来我忍不住又发了几条消息,悠悠说自己在上课被打扰了,我第一次见到她没有用可爱的语气说话,一下子慌了手脚,被迫答应了“不平等条约”,也正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只要没有得到回复,我又还要发新消息的话,就要付门槛费,费用是用水印相机拍摄的当前戴锁的照片,以及两百块。
【这也是哥哥汇报自己的状况哦~汇报的越多,开锁的进度条和好感度说不定会上涨呢~】
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的悠悠显得有些冷淡。这种冷淡让我格外的慌张,好像又找回了当年初恋的感觉,甚至比初恋还要更加提心吊胆,以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等待和在意一个人的消息。
虽然她偶尔会讲校园的话题,或者轻轻挑逗我一下,显得很温柔。有时候也会和我聊的火热,但是总是会在聊得开心的时候突然消失,回来之后就是一句轻飘飘的有点事情。
【秒回也会涨好感度哦~】她曾说过这样的话,于是每次手机响起,我都会立刻抓起来看,期待是她的消息,期待她能给我一丝释放的希望。
但是她的消息并不总是会响起,很多时候,我知只是打开手机,再次目睹壁纸上悠悠的脏污足底,划掉一条无用的消息,在下体不断的顶锁和难耐中坐立不安。
悠悠几个小时不回复,我就会开始想,是不是她又不开心了,是不是需要交门槛费哄她了,最开始,两百块的转账会让我觉得会有些心疼,需要咬牙。但刚刚我非常自然的给她转了账,甚至下体因为这个变得更加兴奋。
过了很久,她终于回复了,只有一个字,乖。我却如释重负,赶紧将准备好的话题发出去,试图延续这场对话。
然而,她又一次没了回应。失落与焦躁交织,夹杂着一丝兴奋和希望,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我的心逐渐被这个高中生牵乱,变得患得患失,而她所依靠的,仅仅是我下体的一把小锁。
每当我为了聊天,拍下我上锁的,丑丑的鸡鸡照片并转钱时,我都能感觉到一种来自地位差距的卑微感和羞耻,以及随之而来的下体强烈的兴奋。兴奋和快感,在这几天的时间里不断的上升。
我赶紧自己已经不再是为了哄她开心,忍辱负重的哄她,让她把锁解开。而是切实的跟她有了地位的差别。两百块只是为了换说两句话,任谁都会说一句不值,而我却逐渐变得对此习以为常乃至甘之如饴。
甚至每次拍摄自己戴锁的照片并发出去时,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感都会让我全身颤抖。
我开始不敢出门。首先,隨著戴锁时间延长,下体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些气味,淡淡的,却让我羞耻不已。其次,手机壁纸我担心被别人看到。更重要的是,街上任何一个女性的鞋袜——无论是高跟鞋的轻叩和黑丝,还是运动鞋露出的一抹抹白色,都会让我陷入漫长而难耐的顶锁。更可怕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大街上的其他男人都可以站着尿尿和舒服的射精,但我却不可以。这种羞耻和卑微感会带给我更强烈的快感,也让我有些恐惧。
悠悠的原味也被我收起来了,积累了五天的蛋蛋已经变得鼓胀,变得这么强烈的刺激,我感觉整个人已经开始逼近极限。
这个时候,手机响起了提示音,我拿起手机,壁纸里的足底再次让我弓下腰,而这一次,是悠悠的消息。
【哥哥,现在立刻出发,开车到一中门口等人家哦~】
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泵动的心脏和下体。
【帮人家搬个快递】
而接下来的一句话,又泼了我一盆冷水,压住了我的兴奋。就像这样,我怎么能够斗得过这个小恶魔呢?我只好带着期待以及灼热的下体立刻动身。
快递出乎意料地沉重,我费力地将它塞进后座,蛋蛋处的疼痛变得难以抑制、额头处的汗珠也已经汇成了细流。
正当我靠着车门喘气时,悠悠的身影才从校门口出现。此时应该距离放学过去了很长时间,校门口已经没有学生出入了。
她今天没有穿了一双纯白的及膝长袜,棉质的纹理清晰可见。或许是走了太多路,袜筒有些松垮,滑落了一些,堆在了纤细的脚踝处,形成一圈圈柔软的褶皱。脚上则是一双基础款的白色帆布鞋,鞋面和侧边都有些灰尘和污渍,鞋带松散地系着,其中一边的末端甚至在地面上轻轻拖沓,显得十分随意。我忍不住想着鞋内包裹着的足底,忍受着下体在锁里跳动带来的疼痛。
她走到车前,我这才注意到她的脸,脸上的妆容似乎刚补过,粉底在鼻翼两侧有些许不匀,白衬衫的袖口处还带着一抹淡淡的污渍和灰尘。她看到我满头大汗的搬东西的样子,非但没有半分心疼,反而停下脚步,歪着头打量我。接着,她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熟悉的略带戏谑,却又甜美的的笑容,然后才拉开车门,轻快地跳上了副驾。
“哥哥,我们,去你家吧~”当我坐上车,刚刚打算说点什么,盘算着怎样尝试拿回钥匙的时候,悠悠用她那标志性的、尾音微微上扬的语调说出了这句话。
我正握着方向盘的手猛地一紧。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怀疑是自己的幻听。接着是下体强烈的悸动,疯狂的顶着小小的锁,我就在这样的兴奋中,超速,只用了十分钟就开回了家。
“把东西都搬上去,”她用下巴点了点后座那个巨大的纸箱,脸上是一种琢磨不透的笑容,“这都是悠悠送给哥哥的礼物哦。”
“礼物”这个词,像一个开关,让我下体积蓄了五天的火焰开锁熊熊燃烧。即使我知道,这可能又是个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想出的一个坏心眼的游戏,但我依旧兴奋无比。
我尽可能快的将那个沉重的箱子搬进电梯,再拖进我的家里。
这间屋子藏在复杂的资产关系后面,是律师为我选择的安全屋,是没有被那些所谓的“亲戚”知道的,我最后的安全的堡垒。
当然。在悠悠踏入的那一刻,便宣告失守。
悠悠似乎在环顾着我的楼道,马尾的细发扫过我的脖颈,带来少女的清甜气息。
“不愧是高档小区呢,真整洁~”她没有脱鞋就进了我的屋子,像个巡视领地的女王,毫不客气地在我的沙发上坐下,两条包裹着白色及膝袜的小腿随意地交叠晃动着。被灰尘包裹着的鞋底让我感到一阵阵的兴奋。
“快,拆开它。”她命令道。
我划开胶带,里面露出的,是一根根泛着冷光的钢管,以及一卷卷黑色的皮革绑带和金属卡扣。是一个拘束床,我的心沉了一下,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更加强烈的兴奋。
“悠悠,这就是我的礼物吗?”我忍不住张嘴问,没有敢于直接像她讨要贞操锁的钥匙,但她却好像看穿了我的心,回答道:“对啊,悠悠今晚要施展魔法,哥哥的钥匙才会变出来哦~”
她居高临下的坐在沙发上,露出了甜美的微笑,眼神中满是得意,还俏皮地拍了拍自己的口袋,摊开手,“你看,身上没有哦~”
那空无一物的手掌,吸走了我最后一丝侥幸心理。
“哥哥要先把这些组装起来,”她用穿着帆布鞋的脚尖踢了踢地上的说明书,“然后,让悠悠把你捆好,才能进行下一步哦~”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照着说明书开始了漫长的安装过程。客厅里回荡着金属部件碰撞的、清脆而空洞的声响。
我将一根根钢管拧紧、固定,亲手建造着自己的受刑架。
悠悠就坐在沙发上,晃着腿,一边喝着我冰箱里的酸奶,一边用那种监督功课的老师般的语气,不时吩咐我一两句,让我跑前跑后,给她那拿些东西。或者让我喝水。
胀痛的下体和蛋蛋让我当然没办法反抗她的命令。
过了一会,她开始时不时随意翻翻我家里的东西,调侃我几句。没有一点拘谨,好像这里理所当然的是她的领地。
终于,当我把自己灌了一个水饱的时候,我终于在一间空余的卧室里安装好了那张床。
与其说是床、不如说是一个精巧的刑具,她满意地点了点头。“哥哥,快点,躺上去。”
我顺从地躺下,冰凉的皮革激得我皮肤一阵战栗。
衣服都要脱掉哦~ 我无法反抗,只好红着脸,在少女的目光中脱掉衣服,露出了被小小的塑料贞操锁包裹的,不断流出透明粘稠液体的下体。
“哥哥羞什么呀,明明已经主动把这里的照片发给了人家那么多次~”
她一边说着让我脸涨红的话,一边拿起一根皮质的束缚带,熟练地绕过我的手腕。金属卡扣“咔哒”一声锁上。与上一次戴手铐时候的猝不及防不同,这是一种极为缓慢的体验。
我慢慢见证着身上的每一个关节被逐步、巧妙地固定住,手腕、脚踝、腰部、甚至脖颈,每一个能够发力的位置,都被皮革温柔而牢固地包裹、收紧,连接在冰冷的钢架上。
悠悠的动作很轻,她的胳膊细细的,看起来也没什么力气。但她只用了一句话就压制住了我。
“想要开锁的话,只能乖乖听话,对吧,不许动哦~”
我不能,不想,当然也不敢挣扎。
过了不知道多久,我猛然意识到,自己真的已经完全动不了了,哪怕手指,也只能无力的轻微弯曲。我被牢牢地捆在这张床上,以一个完全敞开、毫无防备的姿态,像待宰的羔羊。
“为了给哥哥买这些,悠悠可是花了很多钱哦,”她一边检查着每一处绑带的松紧,一边用轻松的语气说,手指有意无意地划过我腰间的皮肤,激起一阵强烈的刺痒。我本能的想要躲避,当然,没有任何余地和空间。
紧接着,她拿起我的手机,一只手放在耳廓,做出了一副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的样子。
“哇,真的要给悠悠报销账单呀~哥哥真好~”
紧接,是递过来的,已经到了faceid付款界面的手机。
此时的我已经没有什么损失金钱的实感。在短暂的心痛后,更多的是对自己陷入任凭一个坏心眼的高中生宰割的,无力处境的兴奋。
“好了,到了给哥哥喂水的时间了,”她终于放下了手机,不知从哪拿来一大瓶矿泉水
“水是生命之源哦~快,一口气喝下去。”
她拧开瓶盖,将冰凉的瓶口凑到我的嘴边。我只能顺从地、大口地吞咽着,冰冷的液体滑过喉咙,涌入我那早已因为刚刚的灌水而变得鼓胀的胃,一下子就带来了一股沉重的尿意,好像直接向着我的膀胱灌水。
当我喝下大半瓶,因为喘不过气就要喷出来时,她却放下了水瓶。然后,她缓缓地脱下了那双已经不算干净的帆布鞋,露出来了那双纯白的及膝袜。一股强烈的味道涌了出来,甚至遮住了少女清甜的体香。我只能看到那双袜子的足背部分,但是已经可以隐隐的目睹到有些泛黄。
“诶,”她用足尖,轻轻地、试探性地,碰了碰我胯下那个锁具周围,因长久积蓄而肿胀、敏感的部位。
一股无法形容的、混杂着剧痛与快感的电流,从接触点瞬间贯穿我的全身。我无法抑制地浑身一颤,浑身变得有些麻,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呜咽。
小小的锁因这突如其来的刺激,而更加疯狂地挤压着我的下体,换句话说,我在疯狂的顶锁。
“只是用足底轻轻碰了碰,哥哥的反应怎么这么大呀?”她似乎对我的反应很满意,微笑着,足尖开始更进一步地、带着戏谑的意味,轻轻地、反复地拨弄、碾压我的蛋蛋,带来一阵阵无比难耐又火热的感觉,好像蛋蛋里面积蓄好几天的液体被她的动作激活了,一股难耐的憋胀感逐渐蔓延我的全身。
“难道说~这几天,哥哥一直在噗嗤噗呲地顶锁?”她俯下身,温热的呼吸喷在我的脸上,用灼灼的眼神盯着我,好像要把我的一切都看破。
“噗~好羞耻呀。难道,每次看到悠悠的消息都会这样?”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能感受到她足尖带来的、如同烙铁般的骤热和强烈触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把我淹没的羞耻与快感。
“不会~~一看到锁屏界面,看到悠悠的足底,就会有下跪磕头的冲动吧~变态哥哥~”
她的脚趾灵活地蜷曲,夹住我的一直蛋蛋,然后缓缓施力。强烈的压迫感伴随着羞耻传来,我能感觉到兴奋的下体占满了小小的锁的每一寸空间,甚至把很多肉挤了出来,透明、黏稠、温热的液体,正不受控制地从锁具的缝隙中渗出。
“流出了好多黏黏的液体呢,”她用一种发现新奇玩具的语气说道,“被高中女生用脏脏的足底欺负,还能兴奋成这个样子。哥哥的喜好,真是无可救药了呢~”
“求你……开锁……”我几乎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才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她停下了动作,歪着头看着我,脸上那甜美的笑容第一次完全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些冰冷的戏谑。
“诶?求我开锁?”她轻笑出声,“悠悠可没说过,交了钱、听了话,就会给哥哥开锁哦~对吧~”
我的心脏瞬间沉入了谷底。
“噗嗤~”她又笑了,又变回了那种天真烂漫的模样,好像刚才的那一幕只是我的错觉。“哥哥这张脸,看上去就让人好想欺负一下呢。”
她轻轻捏了捏我的脸,柔软的触感让我下体一颤,站起身,伸了个懒腰,仿佛刚刚完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好了,悠悠要去施展魔法,把哥哥的钥匙变出来了~哥哥在这里乖乖地等我。”
她顿了顿,又补充道:“当然了,悠悠说过的,钥匙不在我身上。要去闺蜜家里取哦~可能要晚一点。”
我的心中燃起一丝微弱的希望,但立刻就被她接下来的动作彻底扑灭。她走到我的衣柜前,拉开抽屉,将我之前藏起来的、她那些“原味”的袜子,一件件拿了出来。明明,我没有告诉过她这些东西在哪里。
“当然,不会让哥哥寂寞的哦~”她举起一双粉色、袜底已经变成满是泛黄汗渍的棉袜,在我眼前晃了晃,“悠悠的袜袜们,会陪着你的。”
“哥哥居然把它们都偷偷收起来了呀~明明是花了那么多钱买来的~”她啧啧称奇,脸上带着刻意的、夸张的惊讶,“难不成,只要看到这些,哥哥就会无可救药地顶锁和发情”
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有些免疫了她的调侃,但这句话还是让我的脸彻底的烫了起来,这个女孩......不,这个小恶魔好像有着读心术,能把我藏在心底的羞耻想法一一看破。
她将那瓶剩下小半瓶的水拿了过来,把这些袜子里面最脏的两只向我展示了一下,接着毫不犹豫的塞进了瓶口,毫不犹豫地塞了进去。水,立刻变得有些浑浊。
她将剩下的那些袜子,一件一件地,丢在我的脸上、胸口上。那混合着她的体味、汗水和灰尘的气味,在我的眼前编制成了一张网,将我眼前的一切彻底笼罩、吞噬。
“好了,”她将一根吸管插进瓶口,然后温柔地放进我的嘴里,“在悠悠回来之前,要乖乖地把瓶子里面的水喝光哦~”
她的声音再次变得甜美而轻柔,像在哄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毕竟,这可是用悠悠的袜子,亲手为哥哥泡的‘茶’呢。要是不喝掉的话,悠悠会伤心的哦。没准伤心到手一滑,把钥匙……不小心掉到马桶里冲走,也说不定呢~”
我惊恐地瞪大了眼睛,身体因为恐惧而剧烈地颤抖起来,带动着整个金属床架发出了轻微的“咯吱”声。
“开玩笑嘛,”她咯咯地笑了起来,再次用足尖轻轻的点了一下我的蛋蛋,“哥哥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呀。好了,一会见哦,哥哥~”
她转身,脚步轻快地走向门口。门被打开,又被关上。她的鞋轻轻的踢在门槛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咔哒”一声,门锁落上。
这个曾是我的堡垒也安静了下来。只剩下我被捆绑在这个冰冷的刑台上,嘴里含着那根屈辱的吸管,被少女的强烈味道毫无缝隙的包裹着。我闭上眼,羞耻地、兴奋地、难耐地开始吸吮那瓶“茶”。时间,在极度的焦躁、膀胱的无比酸胀、强烈的足底气息包裹、无止境的顶锁和间歇性的昏沉中,失去了意义。
不知过了多久,当房间里最后一丝天光也被黑暗吞噬时,门锁再次转动。
她回来了。
脚步声轻快,带着一点哼唱的小调,灯开了,我眯着眼适应着光亮,看到她已经换下了一中那身的校服,穿上了一件粉色的、带着蕾丝花边的可爱长裙,长发随意地披散着,脸上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
“哥哥,等很久了吧~”
她走到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目光扫过床边那个空空如也的矿泉水瓶,眼睛里闪过一丝刻意的惊讶,随即化为淡淡的戏谑。
“明明是悠悠洗袜袜的水,哥哥居然真的全部喝掉了呀,诶呀呀~”她用一种故意夸张的、难以置信的咏叹调说道。此刻,我的下体早已变得灼热无比,连同我鼓胀的小腹一起,让我难于去发出什么声音。
长时间的忍耐和等待让我无力回答,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丝微弱的呜咽,脸颊再次烧了起来。
“不会还是在~”她俯下身,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脸颊,“一边噗呲噗呲的顶锁~一边闻着悠悠脏袜子的情况下,喝下去的吧~”
我羞耻得浑身颤抖,而下体不受控制的悸动,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她突然向我敏感的耳道里吹来一阵热风,强烈的刺激让我一下麻了半边脸,如果不是被绑着,一定跳了起来。
“看来哥哥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呢,”她咯咯地笑着,脱下了穿着的小皮鞋,一股强烈的味道随之传来,哪怕已经被少女的原味包裹了几个小时,那股味道还是强烈得让我一下子有些发昏,她抬起足底,在我眼前晃了晃。是一双白色的棉袜,但已经不能称之为白色了——袜底板结着黑灰色的硬块,整个袜身都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黄褐色,被汗水浸透后又风干的痕迹清晰可见。
她顿了顿,看着我因震惊而微微睁大的眼睛,嘴角的弧度咧得更开了,补充道:“之所以刚刚走进屋子里没有脱鞋,就是因为担心这个的味道太大,一下子就把哥哥吓跑了呢。不过现在就不用担心了,”
她用一种无比甜美的、却又无比残忍的语气说,“因为哥哥……完全❤跑不掉了呢~”
那一瞬间,一股几乎是固态的、浓烈到极致的气味,如同挣脱囚笼的猛兽,轰然炸开,霸道地侵占了房间里的每一寸空气。那不再是单纯的酸臭,而是一种复杂的、充满层次感的混合物——汗液被反复风干后发酵的酸,混杂着尘土的腥气,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少女本身的、被腌入味了的甜。这气味像一堵无形的墙,狠狠地撞在我的脸上,让我一阵眩晕。
“不过,看哥哥的反应~可一点点都不像是排斥呢~”悠悠蹲下身,好整以暇地欣赏着我的表情,她的目光肆意的在我身上每一寸颤抖的皮肤上游走。
“特别是哥哥的下面,”她的视线缓缓下移,落在我那早已被欲望支配的、不堪的身体上,“还在拼命地顶锁哦。难道说,连这么脏污和这么臭的袜子,也会让哥哥这样的发情吗?真是难以想象呢~”
“难不成,”她歪着头,用一种天真烂漫的语气,提出了一个最恶毒的猜想,“如果悠悠现在走了,哥哥还会对着这个脏污的袜子,在地上‘咚咚咚’地磕头?噗呲~”
我的脸颊滚烫,羞耻感让我恨不得立刻死去,但身体的反应却背道而驰。下体在锁里更加疯狂地悸动,每一次撞击都像是在为她的论断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
她笑出了声,然后,缓缓抬起了她那只穿着新袜子的脚。她用那依旧干净的、包裹在纯白棉袜里的足尖,轻轻地、带着一种近乎怜悯的、玩味的姿态,向上挑起了我的睾丸。
那个地方,好像瞬间被烈火灼烧着。一股尖锐的、酸楚的、难以忍耐的激流从接触点爆发,直冲我的小腹。
“哥哥的蛋蛋,似乎比五天前涨了不少呢,”她的足尖在上面轻轻地滚动、掂量,语气像是在评价一件有趣的收藏品,“软软的,涨鼓鼓的,踩上去的触感……嗯,很不错呢。”
这句临床观察般的评价,让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摆在实验台上的标本。羞耻感被放大到了极限,而快感也随之攀上了新的高峰。
“你看,”她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带着一种分享秘密般的亲昵感,“它在发抖呢,是在害怕,还是在兴奋呀?”
我感觉自己快要疯了。
那粗糙、板结的布料,紧紧地包裹着我最脆弱的部位。隔着这层布,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脚趾的轮廓,感觉到她不轻不重地、用脚趾的关节,在上面揉捏、挤压。
蛋里积蓄了多日的液体仿佛要被她彻底挤爆,极致的酸胀和灭顶般的快感交织在一起,将我的理智彻底焚毁。我再也无法抑制,喉咙里不受控制地发出了一声高亢的、破碎的、变了调的呻吟,那声音听起来如此陌生,如此下贱,连我自己都感到一阵战栗。
“噗~好厉害,只是这样,哥哥就已经流了这么多黏黏的液体了,”她看着从锁具缝隙中不断渗出的透明液体,啧啧称奇,“这只袜子,现在也吸饱了哥哥的味道呢,变得更脏了。你说,悠悠明天再穿上这只袜子去上学,会不会一整天都能感觉到哥哥黏糊糊的东西在脚心呀?”
这是一种我此生从未体验过的强烈难耐。精液仿佛在睾丸中积蓄、沸腾,顺着输精管一路向上,叫嚣着要寻找一个出口。而小小的锁体,则像一个冷酷的狱卒,将这股汹涌的洪流死死地禁锢在堤坝之后,任由它反复冲击我早已脆弱不堪的神经。
我感觉我的身体,特别是在蛋蛋的最深处,有一种滚烫的液体在不断地生成、上升,寻找着突破口。
就在这时,仿佛再一次看穿了我的想法,悠悠停止了她足尖的动作。她从脖颈的挂绳上,解下了那两把小小的、黄铜色的钥匙,用一根纤细的手指勾着,在我眼前轻轻地、来回地晃动。
那两片小小的金属,在昏黄的灯光下反射出冰冷而诱人的光泽,像两只飞舞的萤火虫,也像催眠师手中的怀表,每一次摆动,都牵引着我全部的视线和心神。
“哥哥,”她的声音轻柔得像一阵风,却带着不容抗拒的魔力,“是不是很想要,得到这个钥匙呢?”
我无法回答,只能伴随着强烈的心跳,急促地喘息着,喉咙里发出意义不明的、类似呜咽的声音。
她似乎对我的反应极为满意,脸上的笑容更甜了。她缓缓地抬起那只刚刚蹂躏过我的脚,将那穿着穿了一周的、早已污秽不堪的白袜的足尖,慢慢地、慢慢地,凑到我的嘴边。
“那就来,”她的声音如同恶魔的私语,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含住悠悠的足尖吧~”
我的目光落在她的袜尖上。那上面,不仅有她一周以来行走沾染的灰尘与汗渍,更有着刚刚从我锁中渗出的、属于我自己的、黏糊糊的透明液体。
“虽然是这么的脏污,”她仿佛能读懂我眼神中的犹豫与挣扎,用一种天真烂漫的语气,轻笑着说,“虽然上面沾满了哥哥顶锁流出的液体,但哥哥一定不会介意的,对吧~”
我的身体,背叛了我的意志。我张开嘴,在那股浓郁的酸臭气味中,将她那脏污的、温热的袜尖,含进了嘴里。
“噗呲~”她发出一声清脆的笑声。“这么脏的东西,居然真的含住了呢~哥哥,真的……无可救药了哦~”
我闭上眼,任由那粗糙的、板结的棉布纹理摩擦着我的舌苔,任由那咸涩的、混杂着各种味道的液体浸润我的味蕾。羞耻,在这一刻,抵达了顶点,也化作了最极致的、足以将我焚毁的快感。
“那好吧~”她似乎终于满意了,将钥匙从手指上解下,然后,轻轻地、仿佛一片羽毛般,将那两把冰凉的钥匙,放在了我那被束缚带捆在身侧、动弹不得的手心里。
我愣住了。
在我被牢牢捆绑、一动不动的情况下,我当然不可能用手去开锁。
我这时才意识到她刚刚的话里,那个恶劣的陷阱。我用尽全力,试图动一下手指,将钥匙握紧,但那只是徒劳。钥匙从我无力的手心滑落,“叮当”两声,掉在了身下的皮革上。
她立刻弯下腰,用两根手指,优雅地将钥匙重新捡了起来,放回自己的口袋。
“明明刚刚交给哥哥了,”她歪着头,一脸无辜,语气里却满是藏不住的笑意,“哥哥怎么又自愿送给人家了呀~这下,可不会那么轻易地交出来了哦~”
她顿了顿,难以压抑嘴角得意的微笑,补充道:“再说了,悠悠只是说了,会把钥匙‘变’出来,可从来没有说过,今晚会给哥哥开锁❤哦~”
我的心脏,彻底沉入了冰冷的深渊。但我的下体却好像被这句话点燃,继续疯狂的顶锁。
“哥哥顶锁的样子很有意思呢~”她看着我锁的丑态,愉快地评价道。
然后,她好像想起了什么,眼睛一亮:“诶,哥哥要给悠悠钱吗?是想买悠悠开心,让悠悠开锁吗?”
她自问自答,然后伸出一根手指,用一种商量的、却不容拒绝的口吻说:“那,一万块好不好?一万块,悠悠就大发慈悲,帮哥哥开锁❤”
一万块……这个数字让我脑子嗡的一声。但这漫长的、地狱般的折磨,我一刻也不想再体验了。几乎没有丝毫犹豫,便重重地点了点头。
“诶诶诶,真的答应了吗?这可是一万块哦~”她故作惊讶地捂住了嘴,眼睛却笑成了弯弯的月牙,“答应得这么爽快,悠悠可是会觉得自己有点吃亏了哦~”
她一边说着,一边慢条斯理地拿出钥匙。在我充满渴望的注视下,“咔”的一声,那个禁锢着我的小小的塑料贞操锁,被打开了。
下一刻,我那被压抑了太久的、早已变成深红色的下体,便猛地从锁里弹了出来,高高地、带着遍布的透明粘腻的液体,耸立在她的眼前。
“哥哥一定感觉很放松吧,”她微笑着,用一种纯洁无瑕的眼神,欣赏着我这副丑态,“毕竟,不用再噗呲噗呲地顶锁了。”
是的,第一瞬间的感觉,确实是很放松。但一种新的、更加难以忍耐的空虚感,迅速攫住了我。我本能的尝试想要撸动下体,但是如今,我已经是被蛛网束缚住的猎物。
“那为什么,”她的声音充满了好奇,“脸还这么红,这么烫呢?为什么,还一直含着悠悠的袜袜呢?”她用手指了指我的嘴,我这才意识到,我竟然还下意识地含着她那只无比脏污的袜子的袜尖。
“不许吐出来哦~”我刚红着脸想要吐出来,悠悠就补了一句,我只好重复着这个无比羞耻的动作。
“哥哥挣扎得好厉害啊,”她看着我徒劳地、本能地挺动着腰,试图为下体寻找任何一点快感的样子,笑得更开心了,“不会是……想要自己碰一碰那里吧~”
“你看,明明刚刚被锁起来的时候,哥哥还可以靠顶锁来获取一丝丝快感,可是现在呢?自由了,却一点快感也得不到了❤,真可惜呢。”
她的话,刺穿了我最后的伪装。是的,我自由了,也……彻底无能了。我在要把我焚毁的欲火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陷入了比之前更加绝望的境地。
“哥哥现在拼命顶腰的样子,看起来真可怜呀,”她的声音充满了怜悯,但眼神里却全是戏谑,“要不要悠悠帮帮你,把你再锁回去呢❤”
我剧烈地摇着头。顶锁的感觉太痛苦了,我真的不想在体验。
“诶,那……让悠悠用别的方式帮你吗?”她双手握拳,轻轻地放在下巴上,歪着头看着我,摆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这样的话,收费可是很贵的哦~”
我还能做什么?我只能像一个溺水者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般,拼命地点头。
“真的点头了呀~”她满意地确认道,“那就……一分钟一百块吧~”
她站起身,再次抬起了她那只白皙、小巧、却沾染着我屈辱痕迹的脚。
“不过,哥哥的那里,现在脏兮兮、黏糊糊的,悠悠才不会用手碰呢。”
“当然是……用哥哥最喜欢的足底,来帮助哥哥了~”
粗糙的、板结的袜底,在我那早已敏感不堪的龟头边缘反复碾磨。即使有着我自身分泌出的、羞耻的粘液作为润滑,每一次刮擦,依然带来一阵让我不得不死死咬住牙关的、尖锐的刺激感。那感觉,好像有无数细小的砂砾在研磨我最脆弱的神经。
此时,那些我曾重金购买的、承载着我无数幻想的“原味”,已经被悠悠一只只地、毫不留情地尽数塞进了我的嘴里。它们堵塞了我的口腔,也堵塞了我所有即将脱口而出的、不成体统的呻吟与哀求。悠悠说,这是为了避免我太大声引来邻居。于是,我只能用那被束缚在床沿、尚能小幅度活动的手,一下又一下地、无力地拍打着床垫,以此来宣泄那股几乎要将我撕裂的难耐感。
如果不是手脚被这冰冷的钢架和皮革牢牢固定,我恐怕早就无法忍受这种折磨,跳起来躲避了。但现在,我不能。我只能忍耐。
下体的胀痛、蛋蛋里那股积蓄了七日的、几乎要破体而出的鼓胀感,以及膀胱传来的、越来越无法忽视的酸楚尿意,这几种感觉交织、叠加,形成了一种我此生从未体验过的、地狱般的酷刑。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折磨中,我也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缓慢而坚定地,推上喷射的边缘。
鼓胀的膀胱传来了无比难耐的尿意,我感觉整个下体变得奇怪了起来。
这个时候,悠悠突然停下了动作。她缓缓地脱下了脚上那只穿了一周的、污秽不堪的袜子,露出了她那白皙、粉嫩的、与袜子形成鲜明对比的裸足。
接着,她将那只无比脏污的袜子,轻轻地、甚至可以说是温柔地,放到了我的鼻尖。这个动作,让我彻底地、毫无缝隙地被那种强烈的、属于她的味道所包裹。从口腔到鼻腔,再到我身体的末梢,无一幸免。
“这可是,”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商人的精明和孩童的炫耀,“价值一千块的,悠悠的裸足服务哦~”
“这样,就是每分钟两千块了~”
这句话,非但没有让我感到被勒索的愤怒,反而一种毁灭般的快感袭来了,像最烈的春药,让我更加无可救药地兴奋了起来。
裸足的触感与脏袜的粗糙截然不同,它光滑、温热、柔软。每一次划过,带来越来越难以抑制的、纯粹的快感。
终于,我感觉到那股熟悉的、决堤前的洪流,正在我的体内疯狂攀升,好像下一刻,就要冲破一切束缚,喷薄而出。
积累了七天,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的顶锁。
不知多少次在夜晚里难耐的摇晃。
鼓胀的蛋蛋和濒临极限的膀胱,都在这一刻发出了最强烈的、要求释放的咆哮。
要出来了……要出来了!
“不行哦~”
一声轻柔的、如同情人间的低语,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
我被死死地钉在了喷发的悬崖前一刻。强烈的射精欲望无处可去,只能疯狂地倒灌回我的头脑,与口腔和鼻腔里那股浓郁的足底气息混合在一起,让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身体变得无比奇怪。
“悠悠可没说过,开了锁,哥哥就可以射出来哦~”
悠悠的双脚,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完全离开了我的下体。
那股已经攀升到顶点的精子,在失去了所有引导和刺激后,开始无力地、痛苦地、缓慢地下沉。而小腹处那股强烈的尿意,同样找不到任何出口。一种混杂着两种不同的、绝望的憋胀感,如同一股电流,从我下体的最尖端轰然升起,瞬间贯穿我的全身,直到我的手心和脚趾都开始不受控制地抽搐。
我疯狂地、徒劳地向上顶着腰,试图从冰冷的空气中,从身下的皮革上,获得哪怕一丝丝微不足道的摩擦和快感。但这都是徒劳。
“哥哥的任何快感,”悠悠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她的声音里没有了戏谑,只剩下一种纯粹的、冰冷的陈述,“不取决于哥哥有多么想要,而是,取决于悠悠❤”
我抬起头,看向她。她就那样静静地坐在床边,带着一种纯粹的眼神,一种仿佛我只是一个的器具的眼神,平静地盯着我。
这种眼神让我毛骨悚然。但相比于害怕,我心中升起的,更多的却是兴奋。一种被彻底看穿、被完全支配的、可怕的兴奋。
等我的精子在我拼命的喘息中,缓慢而难耐的回流,第二次的挑逗开始了。这一次,悠悠似乎完全抓到了窍门。
她用她那光滑的裸足,稍稍温柔地刺激几下,等到我的射精欲望稍稍被重新点燃,就会立刻换上那只粗糙、肮脏的袜底。那强烈的、带着惩罚意味的刺激感,会瞬间将我的欲望和精子停止,并死死地保持在这种不上不下的、最难耐的状态。
如果她感觉到我的欲望因为过于痛苦而稍稍有下降的趋势,她又会立刻换回裸足,用温柔的脚心轻轻地碰上几下,给我一丝虚假的希望。
我就这样,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永恒地徘徊在地狱里离天堂最近的那个地方。明明,只要再多几下,再多十几秒,我就可以到达那个舒服的、喷发的彼岸,却又感觉那彼岸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但的确,即使是这样难耐的处境,我那积累了七天欲望的下体,也在这反复的拉扯中,变得越来越兴奋,越来越适应。我还是不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地,距离那条最后的界线越来越近。
精子,在我的体内再次攀升,这一次,它像要把我整个人都点燃一样,缓慢而坚定地向上攀升。我再次接近了那道边缘。因为这一次被折磨的过程格外漫长,那股强烈的尿意也变得再也无法抑制。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马上就要控制不住,要一股脑地从我身体里喷出来了。
“还是,不行哦~”
那个仿佛会读心术的小恶魔,还是在即将抵达高点的那一刻,再一次轻描淡写地停了下来。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这一次,我好像离那条线更近了一些,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我已经极度接近了。
这一次的边缘状态,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格外的漫长和痛苦。精子和尿意好像共同淤积在我的龟头尖端,像一团即将爆炸的星云,久久没办法回落。强烈的欲望彻底燃烧了我的大脑,让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燃烧起来,视线开始模糊,耳边只剩下自己的心跳和喘息声。
我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无助地张着嘴,却因为塞满了袜子的口腔而发不出任何声音。
就在这时,悠悠又开始了她新的折磨。
她不再进行大面积的刺激,只是时不时地,当我刚刚从那种极度的难耐和强烈的射精欲中稍稍回落的时候,她就会用那只脏污的、粗糙的袜尖,轻轻地、如同蜻蜓点水般,碰一下我那早已红肿不堪的龟头。
每一次触碰,都像一次精准的电击,让我再次瞬间陷入那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望的边缘境地。
悠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是一种蛊惑的口吻,带着甜美和一丝丝的冰冷。
“哥哥,想不想射精呀~”
我剧烈地战栗着,尽管我没办法出声,但身体的每一处都在尖叫着同一个字:想。
“想不想体验,此生最难忘的,最舒服的射精?”
我用力地点着头,泪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顺着脸颊滑落。
“价码呢,”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却却让我感觉不到丝毫温度。
“就是哥哥的一切哦~从身体到心灵,从金钱到尊严,从现在再到未来。哥哥会彻底成为悠悠的奴隶,那可是……比现在要凄惨得多的处境哦~”
她顿了顿,似乎在给我思考的时间,但她那只穿着脏污袜子的足底,却又一次轻轻地、若有若无地,刮蹭着我那早已红肿不堪的龟头。让我维持在最痛苦的,射精的边缘。
“答应的话,只要轻轻的点点头~就可以舒服的喷射了哦~”
她一字一顿的说,足底轻轻的摆动着,像一把小锤,敲碎我最后的理智。
“顺便一提,”她仿佛想起了什么,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补充道,“或许答应之后,除了这一次,哥哥就再也没办法……射出来了哦❤”
“即使这样,也要答应吗?”
我艰难地犹豫着。我的大脑里,一半是无法射精的、永恒的、地狱般的未来;另一半,则是眼下这同样像是永恒的、被悬吊在快感边缘的地狱。
我难以想象那种没有射精的生活会是怎样的绝望,但是那种徘徊在天堂门口的折磨,已经将我所有的理性都燃烧殆尽。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自己会在这场酷刑中昏厥过去。
我终于,用尽全身的力气,缓缓地、郑重地,点了头。
“噗呲。”
她笑了,那笑声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甜美和俏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粹的、冰冷的、仿佛在看一件物品般的轻蔑。
“居然真的答应了呢?连这样坏心眼的条件都答应了~看来我闺蜜说得没错呢~”她的眼神变得毫无温柔,幽深的古井,里面倒映着我此刻最卑微、最不堪的模样。
“男人,就是会为了射精,献上一切的公猪❤”
“那么,就开始吧~”
她的话音刚落,那只光滑、柔软的裸足和那只粗糙、肮脏的脏污足底,便用一种近乎暴力的、不容抗拒的力度,开始了用力的、疯狂的上下摩擦。
一股股前所未有的、山崩海啸般的强烈快感,伴随着史无前例的射精欲望,从我的下体最深处迸发出来。
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我无法形容。我感觉我的身体不再属于我,它只是一个被快感填满、即将爆炸的容器。
“射出来吧,哥哥,”悠悠的声音像一道神谕,在我的脑海中回响,“在悠悠的足底小穴里,舒服的射出来吧❤”
她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娇柔甜美的声音,伴随着她这句充满了色气的命令,我那积蓄了整整七天的、滚烫而浓稠的精液,终于冲破了最后的闸门,以一种无比强烈的、仿佛要一口气喷到天花板上的力度,喷发而出。
强烈的、好像要把我整个人都点燃的快感,让我眼前一片空白。我的灵魂,仿佛伴随着这个喷发的过程,被硬生生地从肉体中抽离了出来,飘向了无尽的、眩晕的远方。
喷射的过程,史无前例的漫长。强烈的快感让我感觉大脑都变得奇怪了起来,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她的双脚,没有在我喷射出来的时候停下。射精后的下体变得格外的、难以想象的敏感,曾经那灭顶的快感,在持续不断的、粗暴的摩擦下,迅速转变成了无比强烈的、尖锐的刺激和难以忍受的痛苦。这痛苦,又叠加着那股从未消退的、濒临极限的尿意和被尿意逼出的丝丝缕缕的快感,让我感觉自己下一秒就要彻底崩溃了。
“哥哥看起来很舒服呢,不过悠悠可没有允许你停下哦❤”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如果我还能够喊出来,一定就是这样语无伦次地哭泣求饶了吧。如果不是被绑着,或许我已经像一只被投入滚油的大虾一样,痛苦地弓起了身体。我拼命地试图挣脱,但是那些皮带却像长在我身上一样,根本动不了。我只能被动地接受着这种无比绝望而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刺激。
“继续❤继续❤继续❤”
她的命令是绝对的。
就在这时,又一次的,我喷射了。没有任何间隙,没有任何休息。一股无比灼热的感觉从我的根部疯狂蔓延至最尖端,好像我的尿道里被硬生生塞进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这一次喷出的,不再是浓稠的白色,而是稀薄的、带着点腥味的透明液体。
“喷出来了呢,可是,还不可以停下哦❤”
相比于快感,此刻更多的,是一种被榨干的、奇怪的喷发感,和无法忍受的强烈刺激。
“接下来是……龟头攻击❤”
但是,她依旧没有停下。那只粗糙、肮脏、板结的袜子,在此时,完全包裹住了我的龟头尖端。我那刚刚经历过两次喷发、早已红肿不堪、敏感到了极点的最脆弱之处,就这样被那粗糙的、如同砂纸般的布料,无情地、反复地、用力地摩擦着。
那是一种我此生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好像我的整个身体,都被一寸寸地碾碎,再重组成纯粹的痛苦和刺激。
震撼、失控、崩坏。
此时我恐怕早已涕泪横流,疯狂地喘息了吧。但我没有在眼前这个娇小少女的眼中,看到一丝一毫的同情或怜悯。只有纯粹的、好奇的、欣赏的目光。
几乎要让我肌肉痉挛的强烈收缩,伴随着龟头处那股无比的灼热和膀胱即将爆开的酸胀感,终于,我感觉身体里最后一道防线也崩塌了。
一股股透明的、带着点温热的液体,不受控制地、猛烈地喷射而出。
无比强烈的感觉,好像世界在我眼前炸开。
喷射,强烈的喷射。我能看到,那清亮的液体弄脏了她粉色的睡裙,甚至打湿了她那张带着得意微笑的、精致的脸。
“这就是,潮吹哦❤”她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带着一丝宣告胜利的、最终的判词,“男性可以拥有的,最棒的,最强烈的高潮了哦~”
“体验了这么强烈的高潮~哥哥,已经变成了没有悠悠,就没办法高潮的体质了呢~”
在我的意识逐渐模糊,整个人仿佛飘入一片无限深邃的海的时候,只有这两句话,像两根巨大的船锚,将我死死地钉在了原地。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从漫长的、几乎可以说是昏死的状态中醒来。第一时间感觉到的,并不是意料中强烈的顶锁和难耐,也不是这一周里无时无刻不在折磨我的强烈射精欲。
我依旧躺在那张拘束床上,但身上所有的束缚带,都已经被解开了。这昭示着我之前经历的一切并不是梦境。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被子。我摇了摇头,感觉自己清醒了一些,小心地避开地上那大片的、混合着水渍和白浊液体的、狼藉的痕迹,走进了客厅。
悠悠不在这里。
我本能地走向了大门。在门槛的边上,静静地放着几样东西。
一个比我之前戴过的那个更小的、全新的透明塑料小锁。
一封信。
以及,一堆散开的、整整齐齐的百元大钞。
我拿起那封信,信上只有一行她那可爱的字迹。
“这是你最后的选择机会。戴上锁,来找我。或者,带着你的钱,回归你原来的生活。”
信纸的末尾,还有一行小字,她的一个嘲笑,或者对我此刻处境的一个注解。
The heaviest chains are the ones you choose to wear.
我用一双还在微微颤抖的手,捧起了那个小小的、全新的塑料锁。
它的重量轻得像一个谎言,光滑的、带着工业制品特有的冰冷触感,安静地躺在我的掌心。然而,在我眼中,它却比我所继承的全部资产、比我过去二十一年的人生,都要更加沉重。
我闭上眼,过去七天的生活,便如同潮水般,裹挟着那股熟悉的、混合着汗酸与体香的气味,瞬间将我淹没。我想起了在每一个被欲望点燃的深夜里,下体被禁锢的、无望的胀痛;想起了每一次看见手机屏幕上那张足底照片时,身体不受控制的、羞耻的悸动;想起了在那间属于她的、昏暗的房间里,每一次高潮被悬置在悬崖边缘的、撕心裂肺的焦躁。那是一种没有出口的、永恒的、只能徒劳地顶着锁的生活。
这个新的锁,看起来更小,结构也更加严苛。我能想象,一旦戴上它,那灼热、痛苦、却又伴随着一丝奇异快感的难耐,将不再是间歇性的折磨,而会成为我呼吸的一部分。每一次心跳,每一次行走,都会化为一刻不停的顶锁。而我,也一定会,在某个无法忍受的瞬间,再次抛下所有名为“尊严”的、早已腐朽不堪的废铜烂铁,毫无悬念地,跪在那个高中少女的脚下。
跪下来,亲吻她那沾染着尘土的鞋尖,把一切都献给她。
我应该感到恐惧。我应该抓起旁边那沓厚厚的钞票,冲出这个房间,逃离这座城市,用酒精和时间将这一切埋葬。
但我无法阻止自己,用指尖,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这把小小的、通往地狱的钥匙。
我又想到了她的眼神。
那不是恋人的眼神,不是朋友的眼神,甚至不是一个人类看待另一个人类的眼神。那是一种冰冷的、纯粹的、非人的眼神。像一位精准的外科医生,在解剖台上审视着一具即将被拆解的标本;像一位严苛的造物主,在端详着一件刚刚被祂创造出来、尚有瑕疵的器具。
在那样的眼神注视下,我不再是一个有姓名、有过去、有思想的“人”。
我所有的社会属性——我的财富、我的学识、我的悲伤——都被彻底剥离。我被还原成了一个最原始的、只剩下欲望和反应的物。
而正是这种被彻底物化的感觉,这种被完全看穿、定义、剥夺了自我意志的感觉。
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几乎要让我痛哭流涕的兴奋。
还有……那次高潮。
不是一场温柔的释放,而是一场华丽的风暴,带着将我我彻底摧毁的暴力袭来。
我的灵魂在那一刻被粗暴地、连根拔起地拽出身体,又被她用痛苦和快感反复碾磨,最后再漫不经心地塞回这具已经变得陌生的、破败的躯壳。这一刻,是我的新生。
我低下头,再次看向那封信。那几行可爱的字迹背后,我看到的,依旧是那双眼睛。
她那双好像看穿一切的眼睛。
这一刻我才幡然醒悟,这根本不是一个选择。她不是在给我机会,而是在宣布一个早已注定的结果。
她将那沓钱和这个锁并置于此,并非出于仁慈,而是源于一种绝对的、洞悉了我灵魂本质的自信。
她知道,我一定会亲手戴上这个枷锁。
我又怎么可能逃得开呢?
我怎么可能忍住,不去亲吻她那比我的尊严更真实、比我的生命更有分量的足底?
我怎么可能,不心怀感激地,向她献上我这空洞的、毫无意义的一切呢?
或许,那个曾经心疼钱、会因为输掉游戏而懊恼、爱喝冰可乐的大学生,早已死在了父母下葬的那个秋日。
现在的我,只是一个空洞。一个只有用她的羞辱、她的控制、她的气味,才能勉强填满的、可悲的空洞。
我怀揣着无比的恐惧,颤抖着,但又毫不犹豫的,慢慢戴上了锁。
跳转至第四章
它的重量轻得像一个谎言,光滑的、带着工业制品特有的冰冷触感,安静地躺在我的掌心。然而,在我眼中,它却比我所继承的全部资产、比我过去二十一年的人生,都要更加沉重。
我闭上眼,过去七天的生活,便如同潮水般,裹挟着那股熟悉的、混合着汗酸与体香的气味,瞬间将我淹没。我想起了在每一个被欲望点燃的深夜里,下体被禁锢的、无望的胀痛;想起了每一次看见手机屏幕上那张足底照片时,身体不受控制的、羞耻的悸动;想起了在那间属于她的、昏暗的房间里,每一次高潮被悬置在悬崖边缘的、撕心裂肺的焦躁。那是一种没有出口的、永恒的、只能徒劳地顶着锁的生活。
这个新的锁,看起来更小,结构也更加严苛。我能想象,一旦戴上它,那灼热、痛苦、却又伴随着一丝奇异快感的难耐,将不再是间歇性的折磨,而会成为我呼吸的一部分。每一次心跳,每一次行走,都会化为一刻不停的顶锁。而我,也一定会,在某个无法忍受的瞬间,再次抛下所有名为“尊严”的、早已腐朽不堪的废铜烂铁,毫无悬念地,跪在那个高中少女的脚下。
跪下来,亲吻她那沾染着尘土的鞋尖,把一切都献给她。
我应该感到恐惧。我应该抓起旁边那沓厚厚的钞票,冲出这个房间,逃离这座城市,用酒精和时间将这一切埋葬。
但我无法阻止自己,用指尖,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这把小小的、通往地狱的钥匙。
我又想到了她的眼神。
那不是恋人的眼神,不是朋友的眼神,甚至不是一个人类看待另一个人类的眼神。那是一种冰冷的、纯粹的、非人的眼神。像一位精准的外科医生,在解剖台上审视着一具即将被拆解的标本;像一位严苛的造物主,在端详着一件刚刚被祂创造出来、尚有瑕疵的器具。
在那样的眼神注视下,我不再是一个有姓名、有过去、有思想的“人”。
我所有的社会属性——我的财富、我的学识、我的悲伤——都被彻底剥离。我被还原成了一个最原始的、只剩下欲望和反应的物。
而正是这种被彻底物化的感觉,这种被完全看穿、定义、剥夺了自我意志的感觉。
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几乎要让我痛哭流涕的兴奋。
还有……那次高潮。
不是一场温柔的释放,而是一场华丽的风暴,带着将我我彻底摧毁的暴力袭来。
我的灵魂在那一刻被粗暴地、连根拔起地拽出身体,又被她用痛苦和快感反复碾磨,最后再漫不经心地塞回这具已经变得陌生的、破败的躯壳。这一刻,是我的新生。
我低下头,再次看向那封信。那几行可爱的字迹背后,我看到的,依旧是那双眼睛。
她那双好像看穿一切的眼睛。
这一刻我才幡然醒悟,这根本不是一个选择。她不是在给我机会,而是在宣布一个早已注定的结果。
她将那沓钱和这个锁并置于此,并非出于仁慈,而是源于一种绝对的、洞悉了我灵魂本质的自信。
她知道,我一定会亲手戴上这个枷锁。
我又怎么可能逃得开呢?
我怎么可能忍住,不去亲吻她那比我的尊严更真实、比我的生命更有分量的足底?
我怎么可能,不心怀感激地,向她献上我这空洞的、毫无意义的一切呢?
或许,那个曾经心疼钱、会因为输掉游戏而懊恼、爱喝冰可乐的大学生,早已死在了父母下葬的那个秋日。
现在的我,只是一个空洞。一个只有用她的羞辱、她的控制、她的气味,才能勉强填满的、可悲的空洞。
我怀揣着无比的恐惧,颤抖着,但又毫不犹豫的,慢慢戴上了锁。
跳转至第四章
终章Ⅰ 岸
You chose the shore, and spent a lifetime dreaming of the deep.
我的手悬停了几秒,终究没有拿起那个塑料的小锁。
恐惧于那几乎将我焚尽的强烈快感,恐惧于镜中那个陌生的自己。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她是在谋取我的资产。像小叔他们一样,随时准备将我生吞活剥。
律师的警告如芒在背。我依旧记得,那个从小最喜欢给我带各种礼物的小叔,说服我让出董事会席位时候的眼神,直到不久前还会把我从梦中惊醒。
若非我已成年,又有律师从旁协助,恐怕我父母遗留给我的一切早已被他们蚕食殆尽。
我逃离了这座城市。目的地是三亚,我需要一片海来淹没自己。
我知道如果自己看到她那张脸,甚至只是听到一条语音,可能现在的想法就会变化。
我拿上现金和一张银行卡,没有带手机,而是走出屋子去营业厅买了个手机和新的电话卡。坐上飞机去了三亚。
把自己埋在酒店的沙滩里几天,我终于感觉自己好像冷静了下来一些。
我依旧没办法把视线从那些泳装丽人的身上离开,但有一个区别,别人看的是那些被布料遮挡的,凹凸有致的部位。
而我看的,是她们被沙子和海水沾污的足底。并无可救药的兴奋着。
转眼间,十年匆匆而过。那几年的酒精、喧嚣和一张张模糊而相似的脸孔,终究让我冷静了下来。我终究没有再去找她,当然,也可能是恐惧她对我不告而别的惩罚。
当然,她也没有主动找我。后面我也找了一些付费的女S,或者尝试开启一些圈子里的上贡关系,却从没有找到当初的感觉。
在两次失败的投资和一个背叛的朋友之后,我终于明白,自己不具备守护这么多财富的认知。
我找了一份普通的工作,把手里的现金换成了一个房子,其他的钱全部存入了当年父母给我准备的那个香港信托。
我找了一个妻子,我们谈不上格外相爱,但也算相处融洽,她不介意我过去的花天酒地,我也不介意她的过去。
我从不会想如果我没有这笔丰厚的每月信托收益,我们的关系会发生什么。
我们之间的性生活也从不涉及这些爱好。
只是在梦里,我总是会回到那个晚上,回到那一次强烈无比的喷发,再度怀念那种灵魂像要被抽走的感觉,怀念她的足底和笑容。
以及,最重要的,她的眼神,那种纯粹的眼神,好像我只是一个器具的,让我无比兴奋的眼神。
【解锁结局 她的眼神】
人终会为年少不可得之物困扰一生。
但你至少,没有堕落,选择了不屈,维持了正常人的生活。
只是不知午夜梦回,你是否为此而感到有些后悔。
明明可以轻易的把你握在掌心,她却慷慨的给了你选择。
或许,这是她最后的温柔。
或许,还藏着什么深意。
你逐渐长大了,伴随着阅历的丰富,你回忆起她那种过分成熟的表现,回忆起她那些超越年龄的话语,回忆起她那些完美的举止动作的背后藏着的东西。
这一切,过分的恰到好处,过分的符合你的喜好了。以至于,直到最后一刻,你没能窥探到哪怕她真实样子的一角。
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经历过怎样的痛苦?她究竟想要得到什么?
你得不到答案,你对她一无所知。
要不,我们把时钟倒回一些,回到那个意义深远的——选择?
(全文完)
看看其他结局
作者的话(建议查看所有结局后食用)
这是一个大章节,涉及到选择和分支,所以晚了一些。本来这是个单结局的作品,后面想了想还是设计多结局比较好,所以改了一些。后面会逐渐展开调教的过程。另外希望大家点点赞或者留言呀,你们的反馈是我更新的动力~
期待后续的调教!多来点闺蜜的戏份吧!悠悠电话三院的伏笔是不是还没写?
lili大佬的笔锋依旧犀利,像是锋利的刀锋一样轻易的划开了我形如虚设的心墙,墨水如同毒液一般淹没了我的灵魂😇。
虽然鄙人觉得主角被吃干抹净抽骨吸髓之后像是盛宴后的残羹剩饭一样被倒在垃圾桶里才像现实中只有利益关系里的贡奴的末路。但还是更想看主角作为奴隶被永远的关在名为悠悠的囚笼里痛苦着(并非痛苦),挣扎着(天堂呐😇),沉沦着的HE。
虽然鄙人觉得主角被吃干抹净抽骨吸髓之后像是盛宴后的残羹剩饭一样被倒在垃圾桶里才像现实中只有利益关系里的贡奴的末路。但还是更想看主角作为奴隶被永远的关在名为悠悠的囚笼里痛苦着(并非痛苦),挣扎着(天堂呐😇),沉沦着的HE。
期待更新
Akane7 于 在此处发布的回帖已于 被其自行删除
真的好 支持 徽章!
写的真好,喜欢岸这个结局,男主逃离了深渊,站在了岸边,却终生无法忘记深渊的感觉。女主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哇,多种选择,头一遭
第四章 烙印
The body is a page on which we are written.灼热,难耐,胀痛。
再一次戴上锁的感觉,比我想象中、甚至比记忆里的感受都要痛苦。冰冷的塑料边缘紧紧地、毫不留情地咬合在我那刚刚经历过酷刑、依旧红肿不堪的龟头上。或许是因为我的下体在回忆起昨夜那场风暴时,已经不争气地开始兴奋;又或许,是这个新的锁,比上一次的还要再小上一圈,那种胀痛伴随着灼热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尽管刚刚,已经下定了决心,做好了献上一切的准备,但是当我亲手将那“咔哒”一声的贞操锁亲手锁在自己身上时,我的内心依旧被巨大的、未知的忐忑所吞没。
就好像,昨夜那场强烈的、几乎要把我的灵魂一并发射出来的喷射,非但没有清空我的欲望,反而掘开了一口更深的、永远无法被填满的欲望之井。
一戴上这个新的枷锁,我的身体就又一次开始变得充满了灼热和渴求,渴望着舒畅的射精和喷发,渴望着解除这难耐的束缚。
我颤抖着拿起手机,解锁屏幕。屏幕的光亮起,映出那张我再熟悉不过的、少女的、脏污的足底。不出意外的,又是一次猛烈的顶锁。
“呃啊……”我痛得下意识蜷缩起了身子,额头抵着冰凉的床单。昨天的龟头摩擦,让我最脆弱的那个地方变得红肿不堪,此刻与坚硬的塑料锁体内壁的每一次碰撞,都带来一阵阵无比难耐的、尖锐的刺痛。
我挣扎着,拍下了现在这副狼狈不堪的照片,用依旧在颤抖的手指,给悠悠发了过去。
几乎是同时,一个视频电话的请求弹了出来。我接通,悠悠那张带着招牌式微笑的、精致的脸庞占满了整个屏幕。她穿着一件领口有些松垮、印着草莓图案的旧睡衣,几缕发丝慵懒地贴在脸颊上。她的目光没有看我的脸,而是越过镜头,带着一种审视和满意的神情,径直盯着我弓着身子也无法掩盖的、那可悲的凸起。
“还真的,戴上了呢~”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故作惊讶的笑意。
“噗呲~虽然也猜到了,不过没想到,哥哥都不让那里休息一会,这么迫不及待地就戴上了呀。”
“看来,”她拖长了尾音,用一种下定论的、宣判般的语气说,“哥哥已经是一个真正的锁奴了呢~”
“不过,离真正合格还有距离哦~”
“说起来,悠悠好像有个事情忘记告诉哥哥了。”
“那就是,一旦戴上悠悠的贞操锁,这辈子……就完了哦❤。永远只能做女孩子的足下用品了呢。哥哥会慢慢地忘记像一个真正的男性一样高潮的滋味,会像一只小狗摇尾巴一样,无助地、可怜地,摇动着那个小小的锁,只是为了渴求哪怕一点点的、难受的快感哦~”
“就像现在,”她看着屏幕里的我,笑得更开心了,“噗呲,就算哥哥难耐得弓着腰,就算下面很痛,你看,也还是一直在顶锁呢~”
“好了,哥哥把手机用支架放在桌子上,镜头对准自己。悠悠要教你,作为锁奴的第一条规矩了哦~”
“聊天的规矩就不多说了,跟之前一样,要有戴锁照片和门槛费~”
“另外呢,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们的聊天里,出现了‘袜袜’和‘足底’这一类的词语,哥哥都必须对着悠悠的脏袜子磕头哦~”
“比如现在,”她甜美的声音变得不容置喙,“跪下。”
手机屏幕里的悠悠,将她那只穿着袜子的脚,缓缓地、完全地,对准了镜头。那泛黄带着汗渍的足底,瞬间占满了我的屏幕和全部的视野。
相比于之前的每一次下跪时内心的天人交战,这一次,我的身体甚至比我的大脑更快地做出了反应。我毫不犹豫地,双膝一软,跪在了冰冷的地板上。
男儿膝下有黄金。这句古训如一声遥远的、无力的哀鸣,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随即被更强烈的、屈辱的快感和下体顶锁的痛感所吞噬。我对着那块小小的、发光的屏幕,对着那双脏污的足底,重重地磕下了头。
“噗呲,真难看呢~哥哥像公猪❤。”屏幕里传来她清脆的笑声。
“记得哦,这是命令。每次提到,哥哥都必须放下所有手头的事情,在十秒钟之内,向着悠悠的脏袜子磕头~”
“现在,去把家里悠悠的脏袜袜,都找出来,摆到书房最高处的架子上吧~像供奉神明一样。每次磕头,都要录下完整的视频发给悠悠哦~”
“如果有一次延迟,或者磕得不够响,就延后哥哥开锁的时间一天吧~”
伴随着少女这轻描淡写的宣判,我那充满痛苦与羞耻的新生活,开始了。
我几乎足不出户。我的整个世界,被压缩进了这间屋子和那个小小的手机屏幕里。
我好似被关在斯金纳箱里的老鼠,等待着那个不期而至的电击,无往的期待着那颗作为奖励的、虚无缥缈的糖丸。不知道什么时候,少女就会突然给我拍一张她的袜袜,或者在一条看似无关的闲聊中,轻飘飘地提到“足底”这个词。
每到那时,我便会像被雷击了一般,丢下手中的一切——无论是正在加热的饭菜,还是刚刚捧起的书本——分秒必争地冲进书房,对着那被我供奉在高处的、散发着少女强烈足底味道的“圣物”,屈辱地磕头,录下视频,发送给她。在这个过程中,那种被彻底支配的屈辱感和无法抗拒的兴奋感交织在一起,往往会带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剧烈、更加难耐的顶锁。
逐渐的,我发现自己甚至开始期待那个“信号”的出现。我开始因为这个磕头的行为本身,而切实的、无可救药地兴奋了起来。那种强烈的、被贬低到尘埃里的卑微感,让我每次不经意地目睹手机锁屏、或是瞥见书房里那些脏袜子时,下体都会忍不住地微微震颤。
不知不觉,三天过去了。戴锁的痛苦并没有因为习惯而有任何削减,反而因为那一次酷刑留下的敏感的龟头而愈演愈烈了。更难受的是,我感觉自己的欲望好像已经被那晚无比强烈的射精彻底唤醒了,每一次顶锁,我都感觉蛋蛋里有滚烫的东西在生长,在积蓄。现在,我已经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种深入骨髓的、蛋蛋的鼓胀和难耐,以及对下一次射精和少女足底的、近乎疯狂的强烈渴望。
得到微信的电子账单提示的时候我才发现,短短的三天里,我已经因为控制不住想要和她说话的欲望,给她打了三千块的“门槛费”。
虽然那一天的高潮,她并没有收我的钱,甚至把之前的门槛费也用现金的形式退了回来。但是我当然意识到了,这笔钱,包括我所有的钱,其实早已经属于她了。
我正在犹豫,是否要主动把这笔钱再次转给她,是否这样能够逗她开心一点,或许能换来片刻的、缓解下体灼热和难耐的慈悲。
没等我发出消息,那个专属于她的特别提示音响起了。一行简短的文字出现在屏幕上。
“开门。”
我打开门,悠悠依旧穿着那身标志性的校服,白色的运动鞋和一双薄薄的、几乎看不见的船袜。阳光从她身后照进来,配合着她看起来甜美的笑容,让她看起来像一个邻家小妹妹。
说起来确实,这么多次见面,我几乎没有看到她穿过休闲装或者其他的衣服。或许校服正是这个小恶魔的伪装。
穿着校服的青春少女,如此频繁地出入一个独居男人的家门。想到这一幕被邻居看到后,会对我的风评产生何种毁灭性的影响,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悠悠慢慢的走进来。少女的香甜扑面而来。
她就那样站在我面前。我比她高出整整一头,不自觉地俯视打量着她,她校服下那娇小的、却已初具规模的曲线一览无余。就在这时,我突然感到她的表情带着些许奇怪,厌恶?恐惧?,她突然毫无征兆地、用一种轻轻的、却又带着绝对命令的口吻,说了一句:
“跪下。”
我的身体,在我那可悲的、属于男性的自尊做出任何反应之前,就已经率先屈服了。我跪在了这个娇小的、甚至可能尚未成年的少女面前,膝盖撞击地板的声音,沉闷而又响亮。
“这条规矩,哥哥要用身体牢牢记住哦~”她的声音里,不知为何,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冰冷的愤怒。
“规矩就是,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哥哥的头,不许高过悠悠的胯部。”
“否则,”她抬起脚,用那穿着白色运动鞋的鞋尖,重重地踢了一下我的肩膀,“悠悠就用足底欺负你的蛋蛋,踢到你再也站不起来为止。”
那股真实的、毫不掩饰的怒意让我一下子慌了神,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
“知道了,知道了!”我连忙低下头,视线惊恐地转移到她的足底,然后,因为这个词汇的出现,我情不自禁地、条件反射般地,对着她的鞋底,重重地磕了一个头。
看到我这个动作,悠悠的脸色这才由阴转晴,仿佛刚才那瞬间的愤怒和暴戾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她满意地笑了,悠然地坐在了我家里的沙发上,然后抬起一只脚,露出了那沾满了灰尘的、白色的运动鞋鞋底。
虽然之前心里想着,我往后漫长人生的所有命运,都将取决于这个青春期少女阴晴不定的心情。
但当这一刻,当我终于对这句话有了切肤之实的这一刻,一种混杂着冰冷恐惧和背德兴奋的战栗,还是不受控制地从我的尾椎骨窜上了天灵盖。
我完了,理性的声音在脑中尖叫,但身体的另一部分却在为这彻底的沉沦而欢欣鼓舞。不管怎么样,实际上我还是有着侥幸的心理,但后面的事情也逐一印证了我的想法,或者说,我最深的恐惧。
我后知后觉的意识到,悠悠这次来,并没有给我开锁的打算。似乎她是过来写作业的?
刚刚她从书包里拿出课本和文具,安静地坐在我的书桌前,椅子发出的轻微挪动声,像巨锤一样敲打着我的神经。只有在这种时候,在她专注地与那些功课的时候,我才能产生她只是一个普通高中生的实感。
一中也是一所不错的省重点,只是校风相对宽容,学生的自由度高,才让她有如此多的时间。
当然,实际上此刻,我看不到她在写什么,也看不到她那张时而蹙眉时而轻笑的可爱脸庞。因为我正遵从着她之前的命令,像一只温顺的狗狗一样,跪趴在我自己那张宽阔的书桌下面。
这个曾经属于我的空间,现在成了囚禁我的牢笼。眼前所及的,只有悠悠那双白色的运动鞋,鞋面因为日常的穿着而带着些许灰尘和褶皱,以及从鞋口若隐若现的,同样是白色的船袜边缘。再往上,是她白皙的脚踝,以及被校服长裙下摆遮住一部分的、线条紧致的小腿。
从鞋底渗出的、混杂着干燥泥土的气息,伴随着少女身上独有的、淡淡的甜美香味,还有那被运动鞋包裹了一整天后,从船袜中蒸腾而出的,带着微汗的足底味道,这三种层次分明又完美交融的气味,便是我现在能够感知到的全世界。
我只能呆在这里,像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一样,保持绝对的安静。我忍受着,忍受着这些气味所引发的、让身下那小小的贞操锁被顶得生疼的生理反应,在书桌下的黑暗与寂静中,进行着一场漫长而焦灼的忍耐。
时间在这样的过程中失去了任何意义。不知是过了一小时,还是两小时,头顶上传来了椅子被向后推开的声音。悠悠脱下了一只鞋,那只脚随意地踩在地板上,然后,她冰冷又带着一丝戏谑的声音从上方传来:“喂,把鼻子凑过来。”
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我顺从地抬起头,那双已经有些泛黄的白色船袜就这样不容置疑地踩在了我的鼻子上,柔软的棉质触感,伴随着清晰的纹理,彻底覆盖了我眼前的一切。那股之前还若有若无的、强烈的少女足底味道,此刻如同决堤的洪水般灌满了我的鼻腔,让我无可救药地疯狂顶锁。锁环死死地勒着我的根部,每一次心跳都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但我却无法抑制这强烈的屈辱和兴奋。
作为她的脚垫,我不能出声,甚至不能有过于急促的呼吸。否则,我就要被罚。虽然她没有明说是什么惩罚,但那种未知的恐惧显然比任何已知的惩罚都更具威慑力。我不敢尝试。
直到悠悠做完作业离开这个屋子,我也没能得到任何形式的释放。欲望的火焰依旧在体内燃烧,我只是拖着因为长期的跪趴和持续顶锁而有些发软、颤抖的身体,从冰箱里随便找了点东西填进肚子,然后重重地躺倒在床上。
悠悠并没有用什么残忍激烈的方式挑逗我,她甚至没有多看我几眼。她只是用这样缓慢的、焦灼的、漫长的、近乎无视的忍耐,举重若轻地,将她足底的形状和味道,如同烙印一般,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生活、刻、我的灵魂深处。
除了偶尔的,白天或者傍晚来我这里写作业,把我当作脚凳。在没有课业压力的晚上,她偶尔也会过来,霸占我的沙发,惬意地看电视或者刷手机。而那时,我只能躺在沙发旁冰冷的地板上,一动不许动,被塞上耳塞,戴上眼罩。世界陷入一片死寂的黑暗,唯一能够感知到的,就是她偶尔会把那温热的足底,随意地搭在我身旁的地板上,甚至有时会轻轻地放在我的脸颊边。那属于少女的强烈味道,便成了我黑暗世界中唯一的信标,每一次呼吸都让我的下体忍不住地兴奋和跳动。
或者偶尔,她会心血来潮,用那双柔软的双足踩在我的鼻子上,用脚心和脚趾精准地控制着我的呼吸节奏,时而放松,时而收紧,让我体会濒临窒息的恐惧,直到她足底的味道完全充满我的肺叶和大脑。
这便是我能够感受到的一切。当然,还有伴随着时间流逝,一天比一天更加强烈的,近乎绝望的射精欲和难以忍受的尿意。
在这些时候,我不允许出声,不允许和她说话,自然也就没有请求上厕所的权力。实际上,即使身体上,悠悠与我同处一室,但是我却被剥夺了与她交流的资格,我们之间不存在沟通,只有她的足底对我单方面的、不容置喙的惩罚......亦或是奖励。
我只有在线上,像一个虔诚的信徒一样,更频繁地向她上贡和发送讨好的消息。她的回复变得越来越少了,寥寥数语,甚至只是一个表情,但我打过去的钱,却不受控制地越来越多了。
现在,已经是我戴上这把新的,小小的锁的第八天。也是我被禁止射精的第八天,我的蛋蛋已经因为持续的充血而鼓胀不堪,而频繁顶锁导致的、红肿发亮的龟头也已经让我在每次清洁的时候都感到无比的难耐。
这一天,悠悠一如既往地在我书桌前写着作业,而我则跪趴在她的脚下。她却突然伸手,一把摘下了我的耳塞。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我有些不适应。
“悠悠在意很久了呢~感觉跟哥哥相处的时候,哥哥好像一直在顶锁呢~嘻嘻~”她的声音甜美又残忍。
“哥哥知道吗,人家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种说法哦~每次不受控制的顶锁,都会让海绵体逐渐适应现在被束缚的大小呢~也就是说,每次顶锁之后,哥哥的肉棒都会小上一点,离真正的废物肉棒,更近了一步哦~”
我不被允许说话,只能将这羞辱的话语尽数吞下。但是强烈的羞耻和病态的兴奋感,如同一股电流,瞬间涌上了我的脑海。
“欸欸欸,明明人家都那样说了,怎么感觉哥哥的顶锁顶的更厉害了呀~难不成,被悠悠说中了,你真的很想变成废物肉棒呀~”
悠悠那穿着袜子的足尖,带着一丝凉意,轻轻划过我赤裸的身体,这是八天内,第一次她主动地触碰我。最终,她的脚趾轻轻地、试探性地触碰着我因为八天的禁止射精而鼓胀不堪的蛋蛋。我浑身一颤,几乎要控制不住地呻吟出声。
“嗯…这样的肉棒,暂时看来是没有放风的必要了呢~” “不过呢,悠悠可是很仁慈的呢,也不是不能让哥哥体会到一点点舒服哦,比如……像那天那样~” “但是呢,只有让悠悠满意了才可以哦~”
我的蛋蛋因为她的触碰和话语而感觉无比的酸胀难耐。
“比如说,能够戴上这个。这可是悠悠给哥哥新买的礼物哦~”
一个闪着冰冷金属光泽的,小小的贞操锁出现在了我的面前。锁体很小,目测也就跟我勃起后龟头的一半差不多大。仅仅是看到它,我就能想象到戴上之后会有怎样强烈到令人窒息的束缚感,或者说,以我现在的尺寸,可能根本就没办法戴上。
即使是现在这把锁,已经让我的根部留下了一圈无法消减的红肿,而这把更小的锁,必然会给那本就娇嫩的皮肤带来更强烈的、持续的折磨。
更何况,下体尺寸的被迫减小,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都可以说是绝对的、无法洗刷的羞辱。
但我依旧无可救药地兴奋着。为我自己正无可挽回地、向着一个彻底的锁奴方向堕落而兴奋。
“哥哥当然是……会给人家报销的,对吧~?连同上次的费用一起哦~”
悠悠的语气像是在撒娇,内容却是不容置疑的命令。
“每分钟的足交服务,收费是两千块哦~哥哥一共享受了……噗呲,上次十分钟就喷出来了呢~”她没忍住,轻笑出声,让我在屈辱中颤抖着,明明上次那种可怕的射精停止和最后疯狂的喷射,在我体感中长得像一个世纪,“所以是两万块。外加上次开锁的一万块,还有之前说要还给哥哥的上贡费,再加上这个新锁锁,一共是……三万三千零五百块哦~”
悠悠把我的手机递到了我的面前,甚至没有打开转账界面。这一刻我没有被绑着,当然也没有陷入上次在床上那样绝望无助的境地中。面对这样一个近乎天文数字的账单,我残存的理智本能地抗拒了一秒。
随后,那只穿着脏污船袜的足底,又一次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轻轻地晃动着。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那是一种无声的、却比任何语言都有力的警告。之前的话语里,提到了“足”。我瞬间放弃了所有抵抗,对着她那只脚,重重地磕了一个头。
磕头的那一刻,面对她脏污的足底,我切实的感觉到了一股触电般的感觉,鬼使神差的拿起了手机,颤抖着手指,把这一大笔钱转了过去。在点击确认的那一刻,一种奇异的、酥麻的快感攥住了我的心脏,好像整个人都被掏空了,然后又被一种更奇怪的东西填满。
“哥哥,磕头不够快呢~作为惩罚,加锁一天哦~”伴随着少女心满意足的微笑,她轻描淡写地宣判了我的刑期加一。
蛋蛋的鼓胀感伴随着下体那无处发泄的射精欲,让我感觉连思考都变得迟钝了。
那一天开始,按照悠悠的新要求,我几乎抛下了所有的娱乐活动。我空余的时间里,要么被迫看着手机里她特意拍下的、那些脏污足底的特写照片,要么躺在床上,鼻子上必须放着她换下来的袜子。那种无时无刻不在的、强烈的气味,让我一刻不停地疯狂顶锁,浑身肌肉都因为持续的紧张而酸软无力,感觉整个下体都要被欲望的压力撑得炸开。
但悠悠说,这是唯一能够让我尽快适应那个更小的锁,让我能够获得下一次射精资格的方法。
我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其他方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曾绝望地抓住锁,试图通过摇动和摩擦来获得一丝解脱。但是蛋蛋被锁环勒出的剧烈疼痛,和龟头与锁体摩擦产生的尖锐痛感,让我根本无法挣脱这个小小的金属囚笼,更别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射出精液。而且,内心深处那对悠悠的恐惧,让我根本不敢尝试用工具解开这把锁。我只能忍受着那一天比一天更猛烈,几乎要把我理智燃烧殆尽的射精欲。
每一次无法自控的顶锁,我都会想起悠悠的话,清晰地意识到我的下体正在她的控制下,逐渐地、不可逆地变得更小。一种极致的屈辱、羞耻,混杂着病态的兴奋和对未来的期待,让我的脑袋都变得混乱了。我也逐渐习惯了,甚至开始享受起待在悠悠足底下的生活,习惯了在无尽的黑暗和寂静中,唯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她足底那独一无二的气息。
终于,在足足被禁止射精了十五天的时候,在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次顶锁与挣扎之后,悠悠歪着头,仔细端详了我一番,用一种审视宠物的目光,宣布我暂时合格了。
我再一次被牢牢地绑在了那张熟悉的床上,悠悠又是像上次一样,让我等待了一会,才拿着我的钥匙回来,轻轻地把那折磨了我半个月的锁解开。
此时的下体已经因为长时间的束缚和充血而红肿不堪,紫红色的皮肤紧紧地绷着。在重获自由后,它只是高高地隆起了不长时间,就伴随着一阵酸痛,疲软了一些。是悠悠的手,在轻轻触碰着我蛋蛋根部那圈最严重的红肿。
“确实,看起来比之前要小一些了呢~看来哥哥这半个月以来,持续不断的,噗呲噗呲的顶锁,真的起到了作用呢~”她用一种天真又残忍的语气评价道。
悠悠今天又一次穿着那身洗得有些发白的校服。我突然发现,除了这身校服和上次折磨我时穿的那套休闲装,我似乎就没见过她穿别的衣服。
这十五天里,我的下体也并非完全没有离开过那个小小的贞操锁。实际上,中间还是有两次被允许的清洁和检查。
只是每一次,过程都如出一辙。我都会被她用绳索牢牢地捆在床上,动弹不得。
“作为锁奴,哥哥的下面和全身的其他地方,只能自由一个哦~”她曾这样对我宣布。
而且,她来这里的时候从来不会带着我的钥匙。每一次都是把我绑好了之后,才出门去她那个神秘的“闺蜜”那里取。我每次都特意注意了她的口袋,里面确实空空如也,没有钥匙的轮廓。
就这样,我,一个正处于欲望最强烈的年纪的大学男生,被这个看似无害的小恶魔,用一把小小的贞操锁,生生地禁锢了整整十五天,没有射出哪怕一滴精液。她似乎连我最微小的、最不起眼的反抗的可能,都已经算计了进去。
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地出过门了。为数不多的几次出门采购生活必需品,只要在街上目睹到路边行走的女性,特别是她们的鞋袜,我的身体就会不受控制地开始疯狂顶锁。那种强烈的冲动让我难耐得几乎要当街把腰弓起来,以缓解那令人发疯的酸胀感。而那种被悠悠戏称为“忍耐汁”的粘稠液体,更是一整天都流个不停。每一天早上,我都是在一片已经干涸的、粘腻的透明液体痕迹中醒来,带着对新一天忍耐的绝望,和对她不知何时会到来的、惩罚与奖赏并存的期待,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中。
“咔”一声,当那个小小的塑料贞操锁终于从我身上被解开时,我几乎是痛苦地、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下体终于自由的一刻,皮肤接触到空气时传来一阵几乎是刺痛的、久违的快感。被压抑了十几天、早已积蓄到极限的欲望,瞬间充盈了我的全身。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烧灼一切的射精欲。我能感觉到,我那刚刚获得解放的、早已红肿不堪的下体,正不受控制地、高高地挺立着。
当然,这个小恶魔怎么会让我如此痛快地得到满足呢?
她跪坐在床上,好整以暇地看着我这副丑态,然后,缓缓地歪了歪头,露出了那个我所熟悉的、标志性的甜美微笑。然而此刻,我已经对这个动作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恐惧。这个动作,像是每一次华丽却残忍的游戏序曲,证明着她已经构思好了下一个、令我既期待又恐惧的、折磨我的新方法。
“今天的放风时间,该和哥哥玩什么游戏好呢?”她的声音拖着长长的、撒娇般的尾音,每一个字都像羽毛,轻轻搔刮着我早已紧绷的神经,“哥哥你说是玩……”
“叮铃铃——”
一阵急促而刺耳的手机铃声,突兀的打断了她的话语。
她从校服裙的口袋里拿出手机。当她望向屏幕的那一刻,我清晰地看到,她脸上的表情,凝固了。
是我的错觉吗?
仅仅是一瞬间,那玩味的、甜美的、掌控一切”的笑容,便从她的脸上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冰冷、疲惫与烦躁。她的眉头不自觉地锁紧,嘴唇也抿成了一条僵硬的直线。
是我的错觉吗?
尽管她立刻就转过脸,快步向门外走去,但我那一直胆战心惊地、几乎是病态地盯着她每一寸表情的眼睛,还是捕捉到了这样的,让我不解的一瞬。
过了很久,久到我胯下那股灼热的欲望,都在这冰冷的、令人不安的沉默中,稍稍冷却了一些。她终于从门外走了回来。
她脸上依旧挂着那副甜美的笑容,眼睛也依旧弯成了月牙。但我总是觉得有些许的不对劲。那笑容,像一张画在脸上的、精致的贴纸,带着一种空洞的感觉。
“今天,”她开口了,声音依旧甜美好听,脸上的笑容也逐渐变得自然,“悠悠心情好。一万块,就可以让哥哥释放了哦~”
不玩游戏了吗?我把这句疑问,连同我心中那股强烈的不安,一并咽回了肚子里。不知为何,我格外恐惧这一刻的悠悠。她那双努力微笑着的眼睛背后,这个心情多变,又掌握着我的射精权的少女让我完全不敢反抗。我不敢多问,不敢有任何违逆,只是乖乖地拿起手机,将钱转给了她。
没有什么前戏,也没有那些足以将我理智烧毁的、羞辱性的话语。她只是沉默地、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心不在焉地,将那只泛黄的袜尖,压在了我的鼻子上。
然后,用她那白皙、小巧的裸足,开始了上下翻动。她的动作,不再像之前那样充满挑逗和绝望的缓慢,而是变得十分快速。
经过了十几天射精禁止的下体,早已变得格外的敏感。我从未想过,自己的身体会如此轻易地被点燃。悠悠的足底仅仅拨弄了不到几十秒的时间,我便感觉那股积蓄已久的洪流,正在我的体内疯狂攀升,好像下一刻,就要控制不住地泄露出来。
“诶诶诶,哥哥这就要坚持不住了吗?”她似乎也对我的反应感到有些惊讶,语气里带着嘲弄和玩味。
尽管这样,悠悠却不像之前那样故意拉长节奏,而是用尽全力,用她的足底,粗暴地推动着我的下体,向着射精的边缘疯狂冲锋。
“即使作为锁奴,这也真的太快了哦~这样下去,就真的变成没用的废物鸡鸡了呢~”这句触及到男性尊严的羞辱让我让我涨红了脸,也让我本能地绷紧了肌肉,努力地忍耐着那股越来越强烈的、灭顶般的快感。同时,也因为自己在一个高中生的足底下面,如此快速的到达,这样卑微的事情而感到无比的兴奋。
忍住……忍住……忍住……
但是,经历了十几天残酷的挑逗和完全禁止射精的下体,敏感度,早已超乎了我的想象。或许,真的连一分钟都不到,我就被悠悠快速地、毫不留情地,推向了射精的悬崖边缘。
正当我咬紧牙关,浑身颤抖,准备迎接那早已熟悉的、可怕的寸止拷问时——
悠悠,并没有在射精的前一刻停下来。
精子开始上升,下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收缩。就在那喷发已经进入无可挽回的、临界点的前一秒。
悠悠的足底,猛地、完全地,离开了我的阴茎。
“啊啊啊啊啊啊——”
一股强烈的、即将喷薄而出的精液,本来应该高高的喷射而出,却在最后一刻,失去了所有外界的引导和刺激。
没有了之前那强烈的、足以将灵魂都抽离的快感,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巨大的、令人发疯的空虚和难耐。我拼命地、徒劳地向上疯狂挺动着腰,试图从空气中,获得哪怕一丝丝微不足道的摩擦。
“求你,求你,求你”我的求饶并没有打动带着玩味的笑容看着我的美丽少女,她的足底始终放在了一个距离不远,但我的下体没办法触及的地方。
那积攒了十五天的、本应如火山般爆发的浓稠精子,只是微微地、可悲地,喷出了一小股,随后便无力地、毫无快感地,顺着我那依旧挺立的阴茎,缓缓地流淌下来。那场景,像是在流下一行屈辱的、浑浊的眼泪。
本应有的,喷射时的快感,被强烈的、无处宣泄的焦躁和空虚彻底取代了。
“悠悠说的,是‘释放’,”她甜美的声音,像一把淬了火的刀,插进我那因为强烈的射精欲和空虚感被点燃的下体里,“可没有让哥哥‘射精’的意思哦~”
“舒畅的、强烈的喷发,可是属于‘真正的男人’的东西呢~而哥哥,”她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个怜悯的、却又无比残忍的微笑,“是锁奴❤哦~”
伴随着这最终的、可怕的的宣判,悠悠拿出了那个冰冷的、闪着金属光泽的小锁。在她熟练的动作下,它被慢慢的戴在了我那依旧硬挺、却沾染着自己可悲体液的下体上。
比之前更强烈的束缚感,伴随着灼热的、没有丝毫削减的射精欲望,和那股几乎要将我吞噬的强烈空虚感,一同向我袭来。
悠悠解开了束缚床上我主要关节的拘束带,随后,没有继续挑逗或者嘲讽,也没有再多看我一眼,而是立刻转身,头也不回地,匆匆离去。
门,被重重地关上。只留下我,被半固定在这张床上,独自品尝着这无边无际的、混杂着欲望与绝望的强烈感觉,这是我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被毁灭的高潮,这时候,我想起了那天晚上,在那一次把我的灵魂都要抽出的射精之前,悠悠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答应之后,除了这一次,哥哥就再也没办法……射出来了哦❤”
直到这一刻,我才对这句话有了实感,强烈的射精欲伴随着绝望的快感从我的蛋蛋穿过脊髓流向大脑,在这个没有悠悠的房间里,我难以自控的颤抖着,战栗着。
跳转至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