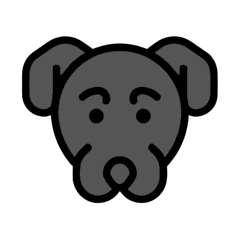上浮
连载中原创
coukou111别字小鬼发布于 2025-11-02 00:10
上浮
①
我已经连续一个月没有在Nico聊天了。
切断联系之后,一切都没什么变化,生活按照既定的轨道滑行——七点整准时起床,洗漱,吃早餐。坐一个小时的地铁到市区,晚上再坐一个小时的地铁回家。 9点半洗澡,10点在床上看一会儿书,11点以前睡觉。
我的口袋里常备一盒烟,但里面只装一支。如果是满盒的烟,那么想抽烟时便只管取出吸食。哪怕存有两支,也会想着“还有一支” 。但如果仅剩一支,就只能眷恋地摸一摸,再把它放回烟盒里。面对别人递上的烟,因为没有余烟作为交换的资本,也只能礼貌地拒绝。习惯,便在这自我设置的微小刑具之中,悄然养成。
“不能白受别人的好。”母亲皱着眉头,责备着年幼的我。我沉默应下,手里攥着邻居塞来的两颗橘子。
记忆缺失。
从意识的深海里逐渐上浮,逐渐唤醒来自身体的反馈。我逐寸确认皮肤传来的触感,确认自己的意识仍然被这具肉体囚禁。思绪可以飘向任何维度,但它永远属于这座由物质构成,被感知决定的躯壳牢笼。
我的行动取决于我的意志,但我的意志也不过是感知的傀儡。被烛液灼烧后背的时候,哪怕下了“不许动”的命令,也难以止住身体剧烈的颤抖。哪怕尽力想锁住精关,在无穷尽的快感不断冲刷理想的堤岸时,不论如何忍耐,白浊的精液也会从指缝中一点点流出来。意志永远也无法对抗身体,或许只是我不可以。
Nic并非全然无趣之物——尽管其的确充斥着虚伪和压抑。推荐墙上的dom无一例外地展示着自己的腿脚,如同商店里橱窗上摆放的精致人偶,精确划一地完成程式化的表演。放眼看去,无疑琳琅满目,但若逐条翻阅,不消片刻就已分不清图片的主人。这些账号属于所有人的凝视,唯独不属于她们自己。
但她不同。
情感缺失……
加载中,加载成功。
她已经三十一天没有上过线。她的动态中鲜有身体部位的展示,仅有的一张是一只做着京剧“醉红”手印的手。纤细,修长。如仙子落在人间的玉兰花枝。
她有一双无与伦比的手,她自己显然也知道这一点。像这样美丽轮廓的手有很多,但如此生动,像抽出新芽的嫩枝一样的富有生命力的手,我平生还是第一次见到。
她一定满意极了自己这双手,才会日日端详,夜夜端详,最终找到这样一种手势,这样一个角度,凝固成这样一张照片。
我曾经被这样的一双手控制过。指尖轻轻落下来,像一片雪花搭在乳尖。几乎是在触碰到手指的一瞬间,奔腾的血液就冲上大脑,向皮肤传递颤栗的信号。
她满意地轻点下颌,像收到骑士致意的女王。微微用力,指腹缓缓地在乳晕上打着转。
“别动。”
她轻声命令。拇指与食指骤然合拢,钳住早已硬实的乳头。一股尖锐的信号挤入胸腔,像火苗一样乱窜,把心跳搅做一团。一声短促地呜咽自我口中逸出,不似呻吟,更像是小动物被踩住尾巴时发出的哀鸣。
她笑了,唇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那两根修长的手指收缩,拉长,转动,像开启保险柜的机械锁。
呼吸已然碎成一片,胸膛不断起伏,试图对抗潮水般的快感所带来的窒息。却只能将更多的肌肤落入她的掌控。
乳头的压力骤然减轻,还未等久经凌虐的神经末梢发出解脱的叹息,在下一个呼吸间,她的整张手掌就已经覆了上来,温热地包裹住一侧乳肉。稍一用力,柔软的脂肉就从她白皙的指缝中溢出,形成一片色情的乳浪。放松,收紧,如此反复。她像揉搓一块湿润地陶土,冷静地重塑着我的形状。
酥麻的信号一路向下迁徙,滑过颤抖的小腹。她像精巧的人偶师,食指与中指只是在腰间极快地,轻巧地跳跃了几下,我便不受控制地弹起腰,随即被她稳稳地擒住冠沟。
她温润而微凉的掌心,严密的贴合住铃口,就着前端渗出的清液,开始缓慢地,持续地研磨,把淫水像润滑液一样,完整而细密地涂布在龟头上。她垂着眼,动作认真而专注。我望着她,忽然想到窗台上捕捉光斑的小猫。
“不行。”她微微皱眉,按住我抽动的柱身。
“不行”,她按住我拿烟的手腕。语气与两个月后的她同出一辙。她从我掌中抽走烟盒,倒出所有香烟,只留一支放回。
于是我忍住没有抽。
于是我忍住没有射,她用指甲划过冠状沟中最敏感的那条棱,一下下拨着。每一下,都引起我肌肉失控般的颤栗。我觉得我像一把大提琴,被她一次次撩拨着紧绷的琴弦。她开始有节奏套弄,指法繁复,时而轻抚,时而紧握。
“闭眼。”
温热的吐息呵上耳廓。
“闭眼。”
耳机里,她的声音由于录音设备的缘故,带着细微的电流声。她要我早睡,于是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这句话成为我唯一的锚点。
当视觉被关闭之后,触觉便会以千百倍的敏感度反扑,到了令人难堪的程度。快感在腹地疯狂囤积,我咬紧牙关,调动全身的意志筑起堤坝。
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学会了对抗痛苦,但从来没有学会抵抗舒适。在危机四伏的荒野中,裸露出生殖器的交配行为显然是最为脆弱的时刻。而在此刻,神经的高度紧张只会导向一个结局。
射精。
不被允许的液体玷污了这只完美的手。她并没有立刻擦拭,而是带着这片狼藉,张开五指,将它完整地贴近我的脸。腥膻的气味笼罩着我的嗅觉。
“看着我。”
我只能睁开眼,在尚未平息的急促喘息中,直视她掌心的污浊与自己的不堪。她俯下身去。那双手在我的视线里不断放大,最终支配了我的视线,留下一座象征着我屈从于欢愉的图腾。
于是我顺从地伸出舌头,沉默地,细致地清理起我留下的罪证。
她迟早会离开的,从很早的一次交谈中我就知道。当时我同她一起躺在床上,我赤裸着上身,把胸口贴向她的手臂。
“这一个月来我都有按时睡觉喔,三餐也准时吃,前两天称体重,我增重了5斤呢!”我雀跃地邀功。
“小狗真棒,”她揉乱我的头发,皱起鼻子笑着。“今后主人要是不在了,小狗也能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呢。”
“为什么突然说这样的话?”好像心头被刺了一下,我赶忙追问。
“因为主人也没法一直陪着小狗呀。我们因为相同的目的在一起:我喜欢把你培养得更好,你渴望被我管理。”她的语气严肃起来,“但我们终究会分开的。我只希望我能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也是我的快乐所在。”
我们终究会分开的。
这句话的重量实在太足,大脑一瞬间被压得凝滞,我猛地坐起身,试图从这句话之中挣脱出来。厚重的羽绒被从身上滑落,我靠在冰冷的床头板上,手指无意识地反复抠着木质边缘的一道划痕。
“离别”。
这个词在脑海里空转,我开始在脑中反复咀嚼这两个字。像在咀嚼一粒坚硬的橄榄核,没有滋味,只有坚硬的质感。它不像预演,也不像警告,更像是一个被提前剧透的、索然无味的结局。寒气从喉头倒灌出来,我的声音变得干涩而破碎,仅发出几声抵触的呓语。
她的声音传到耳中,像从一台信号不良的旧收音机里传来,每一个字都裹着沙沙的杂音,抵达耳边时已模糊不清。
“你有看过《爱乐之城》吗?艾玛和高斯林演的歌舞片。讲钢琴家和演员的爱情故事的那部。”她思索了一下,问我。
我说看过。
“他们最终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也有着自己的人生。很多时候相爱也并不会最终走到一起。”
我说是的。
“我很喜欢小狗喔,我只是说我对关系的理解,没有说现在就要离开啦。”她轻松地笑起来,安抚着我。
我说我也喜欢主人,想一直一直和主人在一起。
“你的人生不属于我,我不能让你做到你本来做不到的事情。我也不能改变我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我们都只是普通人,所以与其担忧未来,还是享受现在就好。”
我摇摇头说,没有主人,我根本没法像现在这样好好生活。
“小狗不要把我当成神啦,小狗在我的监督下戒了烟,调整了作息,也好好喝水,变成了非常好的人,但这都归功于小狗非常努力。我只是把你往好的方向上引导,并不是让你按照我的轨迹行动。”
我点点头。
“你不冷吗?”
时值九月,北京的叶子已经变黄,冷酷的空气从窗子里吹进来。我这才意识到冷,缩回温暖的被子里,用鼻子点了一下主人的脸。温温热热的,像刚出炉的小笼包。“喜欢主人。”我向着她撒起娇。
嘟……嘟…… 无人接听。
她的离开,发生在11月的第一天。没有预兆,没有告别。前一天晚上,她还在nico上和我吐槽万圣节有些吵闹,窗外的声音扰了她的清梦。我发了一个“抱抱”的表情包,说明天睡前给她讲故事听,亲昵得像还躺在一起。
然而第二天之后,闸门落下。
人和人的联系,原来可以如此干脆地被单方面剪断。只剩下一个名字,和一大堆繁杂的聊天记录。
她已上岸,而我仍在海底,窒息。
我耳不能听,目不能视,夜不能寐,茶饭不思。生活像一堆陌生的积木,而我失去了拼接它们的图纸。唯一的日常,是点开那个灰色的头像,看着离线天数一天天累加。然后,一头扎进聊天记录之中,像反刍动物一样,贪婪地、痛苦地回忆着过去的每一句对话。只有在这种回味中,我才能重新找回食欲与困意。
这很讽刺:我人生中第一次完全依靠自己意志坚持了超过二十八天的事,竟然是系统地、持续地,品尝一场再简单不过的失去。
胃里的食物像一团湿冷的沙子,沉甸甸地不肯安分。我用水压了压,勉强阻止自己把食物吐出来。动作太急,几滴水洒在了手机屏幕上。我用袖子擦去,屏幕划了几下,停留在Nico随机刷新的动态上。
无意间瞄了一眼,画面中是一位findom分享的调教日常。她的动态我刷到过很多次,无非是揽客的把戏,靠精心制作的照片来吸引精虫上脑的sub,随后赚他们的钱。
金钱统治。
我本能地抗拒这个词。它让我以为世界上所有柔软的东西,最终都会被塞进名为价格的冷库中,失去原有的温度。亲密,信赖,甚至疼痛,都会化为冰冷的标签。
虽然我已经失去了这份柔软,只抱着日渐麻木的痛。
这世道非同小可,没有什么不能花钱来买,哪怕同别人睡觉也行——服务业公司开出干干净净的发票,哪怕再龌龊不堪的勾当,也化为响当当的三个字——接待费。金钱就是有这样可怕的魔力,可以将一切肮脏的东西变正直,将正直的东西变扭曲。
将性与金钱共舞的findom,就像是行走在深渊之上的钢丝中,需要时时刻刻理清金钱在关系中的地位:是人与人的情感,而非物与物的交换。金钱就像无形体的梅菲斯特:当你的灵魂被标上价码的一刻,你便已坠向由空虚构成的无底深渊。
虽然是这样说,但照片本身并没什么错,反而因其带有引诱的目的,能让我满足自己压抑的性欲。欲望与恐惧像两条交媾的蛇,在胸腔内缠绕着。我一边警惕着这片沼泽,一边欣赏起这张照片。
照片另辟蹊径地没有展示自己的身体部位,反而是以自己的“狗”为主角拍摄的:镜头的前景用虚焦的手段处理,一只模糊的,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率先占据了观众的视线。虽然对别人品头论足并不太礼貌,但我想说——和她比起来,这双手的确不能说是完美,但也足够吸引人,具备着让男人浮想联翩的美丽。这只手的手心斜斜地摊着一支散鞭,鞭子从虎口处引出去,被拇指和食指夹住。剩余的手指托着男主角的下巴。男主的脸颊带着鞭痕,眼神迷离,痴情地望着镜头,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仔仔细细地端详着男主,忽然大脑嗡地一声炸开:是秋。
秋是我在大学时候的学长,大我三届,是动漫社的社长。也和大部分二次元一样,秋是他自己起的化名,因此他的名字并不念“qiu”,念作“aki”才算地道。名字并不很重要,我念出来,他应下,这便足够。名字是否真实,并不代表名字所对应的实体是否真实。而秋这个名字所对应的人,便是我理想中自己会变成的样子:多才多艺,成熟冷静,进退有度,像太阳一样在学校内闪耀着光辉。
我无法肯定照片中的人是否真的是秋。因为一来我对他的印象已仅仅停留在大一结束前的最后一次院宣晚会。二来他在我的印象中永远是矜持而冷淡的,鲜有如此狂热的瞬间。但我几乎在瞬间就从心底认定,这就是秋。
但我又难以接受屏幕中的人是秋,如果这并非艺术作品,我心目中理想的前辈又怎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的思绪迷乱得像经受过一场风暴的摧残,秋那痴迷的眼神印在了我的心底。无论是真是假,我想我需要亲自确定一下。
我点开这名dom的个人信息,“幽”,这是她的名字。我在心里想了许多接近她的借口,最终决定还是实话实说。正当我编辑好请求之后,我注意到她的个性签名——门槛52。
我闭上眼,深呼吸。
我必须上浮,是时候前往岸边了。我制作了52元的口令红包,并在好友请求里附上了那串随机数字。
我已经连续一个月没有在Nico聊天了。
切断联系之后,一切都没什么变化,生活按照既定的轨道滑行——七点整准时起床,洗漱,吃早餐。坐一个小时的地铁到市区,晚上再坐一个小时的地铁回家。 9点半洗澡,10点在床上看一会儿书,11点以前睡觉。
我的口袋里常备一盒烟,但里面只装一支。如果是满盒的烟,那么想抽烟时便只管取出吸食。哪怕存有两支,也会想着“还有一支” 。但如果仅剩一支,就只能眷恋地摸一摸,再把它放回烟盒里。面对别人递上的烟,因为没有余烟作为交换的资本,也只能礼貌地拒绝。习惯,便在这自我设置的微小刑具之中,悄然养成。
“不能白受别人的好。”母亲皱着眉头,责备着年幼的我。我沉默应下,手里攥着邻居塞来的两颗橘子。
记忆缺失。
从意识的深海里逐渐上浮,逐渐唤醒来自身体的反馈。我逐寸确认皮肤传来的触感,确认自己的意识仍然被这具肉体囚禁。思绪可以飘向任何维度,但它永远属于这座由物质构成,被感知决定的躯壳牢笼。
我的行动取决于我的意志,但我的意志也不过是感知的傀儡。被烛液灼烧后背的时候,哪怕下了“不许动”的命令,也难以止住身体剧烈的颤抖。哪怕尽力想锁住精关,在无穷尽的快感不断冲刷理想的堤岸时,不论如何忍耐,白浊的精液也会从指缝中一点点流出来。意志永远也无法对抗身体,或许只是我不可以。
Nic并非全然无趣之物——尽管其的确充斥着虚伪和压抑。推荐墙上的dom无一例外地展示着自己的腿脚,如同商店里橱窗上摆放的精致人偶,精确划一地完成程式化的表演。放眼看去,无疑琳琅满目,但若逐条翻阅,不消片刻就已分不清图片的主人。这些账号属于所有人的凝视,唯独不属于她们自己。
但她不同。
情感缺失……
加载中,加载成功。
她已经三十一天没有上过线。她的动态中鲜有身体部位的展示,仅有的一张是一只做着京剧“醉红”手印的手。纤细,修长。如仙子落在人间的玉兰花枝。
她有一双无与伦比的手,她自己显然也知道这一点。像这样美丽轮廓的手有很多,但如此生动,像抽出新芽的嫩枝一样的富有生命力的手,我平生还是第一次见到。
她一定满意极了自己这双手,才会日日端详,夜夜端详,最终找到这样一种手势,这样一个角度,凝固成这样一张照片。
我曾经被这样的一双手控制过。指尖轻轻落下来,像一片雪花搭在乳尖。几乎是在触碰到手指的一瞬间,奔腾的血液就冲上大脑,向皮肤传递颤栗的信号。
她满意地轻点下颌,像收到骑士致意的女王。微微用力,指腹缓缓地在乳晕上打着转。
“别动。”
她轻声命令。拇指与食指骤然合拢,钳住早已硬实的乳头。一股尖锐的信号挤入胸腔,像火苗一样乱窜,把心跳搅做一团。一声短促地呜咽自我口中逸出,不似呻吟,更像是小动物被踩住尾巴时发出的哀鸣。
她笑了,唇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那两根修长的手指收缩,拉长,转动,像开启保险柜的机械锁。
呼吸已然碎成一片,胸膛不断起伏,试图对抗潮水般的快感所带来的窒息。却只能将更多的肌肤落入她的掌控。
乳头的压力骤然减轻,还未等久经凌虐的神经末梢发出解脱的叹息,在下一个呼吸间,她的整张手掌就已经覆了上来,温热地包裹住一侧乳肉。稍一用力,柔软的脂肉就从她白皙的指缝中溢出,形成一片色情的乳浪。放松,收紧,如此反复。她像揉搓一块湿润地陶土,冷静地重塑着我的形状。
酥麻的信号一路向下迁徙,滑过颤抖的小腹。她像精巧的人偶师,食指与中指只是在腰间极快地,轻巧地跳跃了几下,我便不受控制地弹起腰,随即被她稳稳地擒住冠沟。
她温润而微凉的掌心,严密的贴合住铃口,就着前端渗出的清液,开始缓慢地,持续地研磨,把淫水像润滑液一样,完整而细密地涂布在龟头上。她垂着眼,动作认真而专注。我望着她,忽然想到窗台上捕捉光斑的小猫。
“不行。”她微微皱眉,按住我抽动的柱身。
“不行”,她按住我拿烟的手腕。语气与两个月后的她同出一辙。她从我掌中抽走烟盒,倒出所有香烟,只留一支放回。
于是我忍住没有抽。
于是我忍住没有射,她用指甲划过冠状沟中最敏感的那条棱,一下下拨着。每一下,都引起我肌肉失控般的颤栗。我觉得我像一把大提琴,被她一次次撩拨着紧绷的琴弦。她开始有节奏套弄,指法繁复,时而轻抚,时而紧握。
“闭眼。”
温热的吐息呵上耳廓。
“闭眼。”
耳机里,她的声音由于录音设备的缘故,带着细微的电流声。她要我早睡,于是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这句话成为我唯一的锚点。
当视觉被关闭之后,触觉便会以千百倍的敏感度反扑,到了令人难堪的程度。快感在腹地疯狂囤积,我咬紧牙关,调动全身的意志筑起堤坝。
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学会了对抗痛苦,但从来没有学会抵抗舒适。在危机四伏的荒野中,裸露出生殖器的交配行为显然是最为脆弱的时刻。而在此刻,神经的高度紧张只会导向一个结局。
射精。
不被允许的液体玷污了这只完美的手。她并没有立刻擦拭,而是带着这片狼藉,张开五指,将它完整地贴近我的脸。腥膻的气味笼罩着我的嗅觉。
“看着我。”
我只能睁开眼,在尚未平息的急促喘息中,直视她掌心的污浊与自己的不堪。她俯下身去。那双手在我的视线里不断放大,最终支配了我的视线,留下一座象征着我屈从于欢愉的图腾。
于是我顺从地伸出舌头,沉默地,细致地清理起我留下的罪证。
她迟早会离开的,从很早的一次交谈中我就知道。当时我同她一起躺在床上,我赤裸着上身,把胸口贴向她的手臂。
“这一个月来我都有按时睡觉喔,三餐也准时吃,前两天称体重,我增重了5斤呢!”我雀跃地邀功。
“小狗真棒,”她揉乱我的头发,皱起鼻子笑着。“今后主人要是不在了,小狗也能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呢。”
“为什么突然说这样的话?”好像心头被刺了一下,我赶忙追问。
“因为主人也没法一直陪着小狗呀。我们因为相同的目的在一起:我喜欢把你培养得更好,你渴望被我管理。”她的语气严肃起来,“但我们终究会分开的。我只希望我能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也是我的快乐所在。”
我们终究会分开的。
这句话的重量实在太足,大脑一瞬间被压得凝滞,我猛地坐起身,试图从这句话之中挣脱出来。厚重的羽绒被从身上滑落,我靠在冰冷的床头板上,手指无意识地反复抠着木质边缘的一道划痕。
“离别”。
这个词在脑海里空转,我开始在脑中反复咀嚼这两个字。像在咀嚼一粒坚硬的橄榄核,没有滋味,只有坚硬的质感。它不像预演,也不像警告,更像是一个被提前剧透的、索然无味的结局。寒气从喉头倒灌出来,我的声音变得干涩而破碎,仅发出几声抵触的呓语。
她的声音传到耳中,像从一台信号不良的旧收音机里传来,每一个字都裹着沙沙的杂音,抵达耳边时已模糊不清。
“你有看过《爱乐之城》吗?艾玛和高斯林演的歌舞片。讲钢琴家和演员的爱情故事的那部。”她思索了一下,问我。
我说看过。
“他们最终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也有着自己的人生。很多时候相爱也并不会最终走到一起。”
我说是的。
“我很喜欢小狗喔,我只是说我对关系的理解,没有说现在就要离开啦。”她轻松地笑起来,安抚着我。
我说我也喜欢主人,想一直一直和主人在一起。
“你的人生不属于我,我不能让你做到你本来做不到的事情。我也不能改变我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我们都只是普通人,所以与其担忧未来,还是享受现在就好。”
我摇摇头说,没有主人,我根本没法像现在这样好好生活。
“小狗不要把我当成神啦,小狗在我的监督下戒了烟,调整了作息,也好好喝水,变成了非常好的人,但这都归功于小狗非常努力。我只是把你往好的方向上引导,并不是让你按照我的轨迹行动。”
我点点头。
“你不冷吗?”
时值九月,北京的叶子已经变黄,冷酷的空气从窗子里吹进来。我这才意识到冷,缩回温暖的被子里,用鼻子点了一下主人的脸。温温热热的,像刚出炉的小笼包。“喜欢主人。”我向着她撒起娇。
嘟……嘟…… 无人接听。
她的离开,发生在11月的第一天。没有预兆,没有告别。前一天晚上,她还在nico上和我吐槽万圣节有些吵闹,窗外的声音扰了她的清梦。我发了一个“抱抱”的表情包,说明天睡前给她讲故事听,亲昵得像还躺在一起。
然而第二天之后,闸门落下。
人和人的联系,原来可以如此干脆地被单方面剪断。只剩下一个名字,和一大堆繁杂的聊天记录。
她已上岸,而我仍在海底,窒息。
我耳不能听,目不能视,夜不能寐,茶饭不思。生活像一堆陌生的积木,而我失去了拼接它们的图纸。唯一的日常,是点开那个灰色的头像,看着离线天数一天天累加。然后,一头扎进聊天记录之中,像反刍动物一样,贪婪地、痛苦地回忆着过去的每一句对话。只有在这种回味中,我才能重新找回食欲与困意。
这很讽刺:我人生中第一次完全依靠自己意志坚持了超过二十八天的事,竟然是系统地、持续地,品尝一场再简单不过的失去。
胃里的食物像一团湿冷的沙子,沉甸甸地不肯安分。我用水压了压,勉强阻止自己把食物吐出来。动作太急,几滴水洒在了手机屏幕上。我用袖子擦去,屏幕划了几下,停留在Nico随机刷新的动态上。
无意间瞄了一眼,画面中是一位findom分享的调教日常。她的动态我刷到过很多次,无非是揽客的把戏,靠精心制作的照片来吸引精虫上脑的sub,随后赚他们的钱。
金钱统治。
我本能地抗拒这个词。它让我以为世界上所有柔软的东西,最终都会被塞进名为价格的冷库中,失去原有的温度。亲密,信赖,甚至疼痛,都会化为冰冷的标签。
虽然我已经失去了这份柔软,只抱着日渐麻木的痛。
这世道非同小可,没有什么不能花钱来买,哪怕同别人睡觉也行——服务业公司开出干干净净的发票,哪怕再龌龊不堪的勾当,也化为响当当的三个字——接待费。金钱就是有这样可怕的魔力,可以将一切肮脏的东西变正直,将正直的东西变扭曲。
将性与金钱共舞的findom,就像是行走在深渊之上的钢丝中,需要时时刻刻理清金钱在关系中的地位:是人与人的情感,而非物与物的交换。金钱就像无形体的梅菲斯特:当你的灵魂被标上价码的一刻,你便已坠向由空虚构成的无底深渊。
虽然是这样说,但照片本身并没什么错,反而因其带有引诱的目的,能让我满足自己压抑的性欲。欲望与恐惧像两条交媾的蛇,在胸腔内缠绕着。我一边警惕着这片沼泽,一边欣赏起这张照片。
照片另辟蹊径地没有展示自己的身体部位,反而是以自己的“狗”为主角拍摄的:镜头的前景用虚焦的手段处理,一只模糊的,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率先占据了观众的视线。虽然对别人品头论足并不太礼貌,但我想说——和她比起来,这双手的确不能说是完美,但也足够吸引人,具备着让男人浮想联翩的美丽。这只手的手心斜斜地摊着一支散鞭,鞭子从虎口处引出去,被拇指和食指夹住。剩余的手指托着男主角的下巴。男主的脸颊带着鞭痕,眼神迷离,痴情地望着镜头,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仔仔细细地端详着男主,忽然大脑嗡地一声炸开:是秋。
秋是我在大学时候的学长,大我三届,是动漫社的社长。也和大部分二次元一样,秋是他自己起的化名,因此他的名字并不念“qiu”,念作“aki”才算地道。名字并不很重要,我念出来,他应下,这便足够。名字是否真实,并不代表名字所对应的实体是否真实。而秋这个名字所对应的人,便是我理想中自己会变成的样子:多才多艺,成熟冷静,进退有度,像太阳一样在学校内闪耀着光辉。
我无法肯定照片中的人是否真的是秋。因为一来我对他的印象已仅仅停留在大一结束前的最后一次院宣晚会。二来他在我的印象中永远是矜持而冷淡的,鲜有如此狂热的瞬间。但我几乎在瞬间就从心底认定,这就是秋。
但我又难以接受屏幕中的人是秋,如果这并非艺术作品,我心目中理想的前辈又怎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的思绪迷乱得像经受过一场风暴的摧残,秋那痴迷的眼神印在了我的心底。无论是真是假,我想我需要亲自确定一下。
我点开这名dom的个人信息,“幽”,这是她的名字。我在心里想了许多接近她的借口,最终决定还是实话实说。正当我编辑好请求之后,我注意到她的个性签名——门槛52。
我闭上眼,深呼吸。
我必须上浮,是时候前往岸边了。我制作了52元的口令红包,并在好友请求里附上了那串随机数字。
oso发布于 2025-11-02 00:40
Re: 上浮
CoCo老师悄无声息的发新作了!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2025-11-02 12:27
Re: 上浮
前排支持
coukou111别字小鬼发布于 2025-11-02 12:54
Re: Re: 上浮
humulation:↑前排支持人仿老师的献身什么时候出w
humulation破站文豪发布于 2025-11-02 23:38
Re: Re: Re: 上浮
coukou111:↑还没想好写啥……好难想……humulation:↑前排支持人仿老师的献身什么时候出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