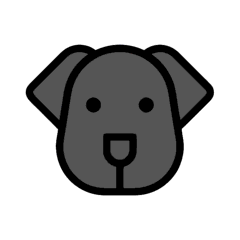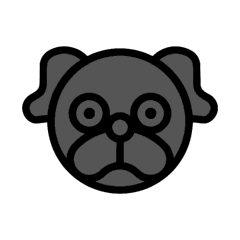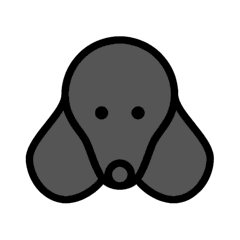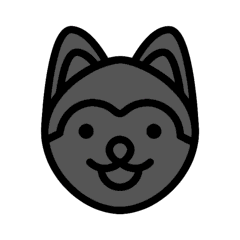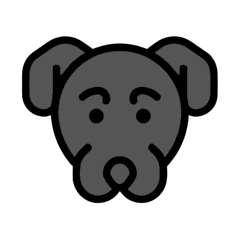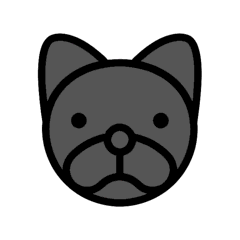🐾摸鱼茶水间✧🍵
終於回來了嗎
回来了,yue老师在哪里😭😭😭😭
因为身体的拖累,已经很久没发帖了。
当看到穿刺报告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毕竟恶性程度很低,生命无虞。短暂的阴霾过后,我便重新振作了起来。工作照旧,遛狗如常,耳边回荡着“不过是个小手术”的安慰,让我天真地忽略了病情的复杂,以及“四级手术”这四个字背后的重量。
直到术前谈话,医生冷静地宣读那些可能的代价:“手臂活动可能受限”“声音或将变得嘶哑”“面部神经或受影响”……而我的思绪却早已飘向远方,盘算着术后要溜去哪里散心,躺在麻醉台上时,满心憧憬的都是康复后要和K桑去探访哪些小店。
然后,我从麻醉中醒来。
然后,那些被轻描淡写提及的“万一”,竟如命运的玩笑般,一一应验在我身上。最先凋零的是曾经的容颜,然后是灵活自如的躯体,还有我的声音。
每一个黎明都成了一场无声的战役。昨夜辛苦筑起的心理防线总在醒来的瞬间如沙堡般溃散。那些自我劝慰与肯定,像被戳破的泡沫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仿佛被困在一场没有尽头的梦魇里。曾经熟悉的自己正一点点消逝,如同忒修斯之船,在身体的更迭中,属于“我”的部分被剥离,只留下一具残破的空壳。
每次恸哭之后都会伴随着心理防御机制的退行。我好像变回一个三岁的小孩,只能抓着K桑一遍遍说:“我害怕。”
如果人格是跨越生活情境的一致性,那么眼前这个支离破碎,悲观失据的我难道才是真实的底色?难道我素日引以为傲的坚强与尊严,竟都建立在容貌、声音、躯体这些浮华的沙土之上?
《病隙碎笔》中写道:“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可当苦难如潮水般涌来,信心该向何处寻觅?我竭尽全力,依然无法为眼前的处境涂上一抹亮色。
或许正因还在抵抗,所以痛得格外清晰。可能我的内核从来就不是坚不可摧的。
我忽然懂了春琴。当她说道“不知是谁因恨我而做出这样的事……但说心里话,只要不是你,我不在意被任何人看到我如今的容貌”时,该是怎样一种绝望与释然交织的心境。
今天,我低头轻抚K桑的脸庞问他:“我还能继续做你的主人吗?”
他气鼓鼓地用头顶了顶我:“什么叫还能!你永远都是啊!”
唯有在他身边,我才能从这场漫长的风暴中,偷得片刻的安宁。
祈愿有一天,光能照进这片灰暗,让我重新认出自己的模样。
当看到穿刺报告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毕竟恶性程度很低,生命无虞。短暂的阴霾过后,我便重新振作了起来。工作照旧,遛狗如常,耳边回荡着“不过是个小手术”的安慰,让我天真地忽略了病情的复杂,以及“四级手术”这四个字背后的重量。
直到术前谈话,医生冷静地宣读那些可能的代价:“手臂活动可能受限”“声音或将变得嘶哑”“面部神经或受影响”……而我的思绪却早已飘向远方,盘算着术后要溜去哪里散心,躺在麻醉台上时,满心憧憬的都是康复后要和K桑去探访哪些小店。
然后,我从麻醉中醒来。
然后,那些被轻描淡写提及的“万一”,竟如命运的玩笑般,一一应验在我身上。最先凋零的是曾经的容颜,然后是灵活自如的躯体,还有我的声音。
每一个黎明都成了一场无声的战役。昨夜辛苦筑起的心理防线总在醒来的瞬间如沙堡般溃散。那些自我劝慰与肯定,像被戳破的泡沫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仿佛被困在一场没有尽头的梦魇里。曾经熟悉的自己正一点点消逝,如同忒修斯之船,在身体的更迭中,属于“我”的部分被剥离,只留下一具残破的空壳。
每次恸哭之后都会伴随着心理防御机制的退行。我好像变回一个三岁的小孩,只能抓着K桑一遍遍说:“我害怕。”
如果人格是跨越生活情境的一致性,那么眼前这个支离破碎,悲观失据的我难道才是真实的底色?难道我素日引以为傲的坚强与尊严,竟都建立在容貌、声音、躯体这些浮华的沙土之上?
《病隙碎笔》中写道:“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可当苦难如潮水般涌来,信心该向何处寻觅?我竭尽全力,依然无法为眼前的处境涂上一抹亮色。
或许正因还在抵抗,所以痛得格外清晰。可能我的内核从来就不是坚不可摧的。
我忽然懂了春琴。当她说道“不知是谁因恨我而做出这样的事……但说心里话,只要不是你,我不在意被任何人看到我如今的容貌”时,该是怎样一种绝望与释然交织的心境。
今天,我低头轻抚K桑的脸庞问他:“我还能继续做你的主人吗?”
他气鼓鼓地用头顶了顶我:“什么叫还能!你永远都是啊!”
唯有在他身边,我才能从这场漫长的风暴中,偷得片刻的安宁。
祈愿有一天,光能照进这片灰暗,让我重新认出自己的模样。
yu-e:↑因为身体的拖累,已经很久没发帖了。希望一切安好
当看到穿刺报告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毕竟恶性程度很低,生命无虞。短暂的阴霾过后,我便重新挺振作了起来。工作照旧,遛狗如常,耳边回荡着“不过是个小手术”的安慰,让我天真地忽略了病情的复杂,以及“四级手术”这四个字背后的重量。
直到术前谈话,医生冷静地宣读那些可能的代价:“手臂活动可能受限”“声音或将变得嘶哑”“面部神经或受影响”……而我的思绪却早已飘向远方,盘算着术后要溜去哪里散心,躺在麻醉台上时,满心憧憬的都是康复后要和K桑去探访哪些小店。
然后,我从麻醉中醒来。
然后,那些被轻描淡写提及的“万一”,竟如命运的玩笑般,一一应验在我身上。最先凋零的是曾经的容颜,然后是灵活自如的躯体,还有我的声音。
每一个黎明都成了一场无声的战役。昨夜辛苦筑起的心理防线总在醒来的瞬间如沙堡般溃散。那些自我劝慰与肯定,像被戳破的泡沫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仿佛被困在一场没有尽头的梦魇里。曾经熟悉的自己正一点点消逝,如同忒修斯之船,在身体的更迭中,属于“我”的部分被剥离,只留下一具残破的空壳。
每次恸哭之后都会伴随着心理防御机制的退行。我好像变回一个三岁的小孩,只能抓着K桑一遍遍说:“我害怕。”
如果人格是跨越生活情境的一致性,那么眼前这个支离破碎,悲观失据的我难道才是真实的底色?难道我素日引以为傲的坚强与尊严,竟都建立在容貌、声音、躯体这些浮华的沙土之上?
《病隙碎笔》中写道:“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可当苦难如潮水般涌来,信心该向何处寻觅?我竭尽全力,依然无法为眼前的处境涂上一抹亮色。
或许正因还在抵抗,所以痛得格外清晰。可能我的内核从来就不是坚不可摧的。
我忽然懂了春琴。当她说道“不知是谁因恨我而做出这样的事……但说心里话,只要不是你,我不在意被任何人看到我如今的容貌”时,该是怎样一种绝望与释然交织的心境。
今天,我低头轻抚K桑的脸庞问他:“我还能继续做你的主人吗?”
他气鼓鼓地用头顶了顶我:“什么叫还能!你永远都是啊!”
唯有在他身边,我才能从这场漫长的风暴中,偷得片刻的安宁。
祈愿有一天,光能照进这片灰暗,让我重新认出自己的模样。
yu-e:↑因为身体的拖累,已经很久没发帖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跟yue姐姐分享我的自嘲熊。
当看到穿刺报告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毕竟恶性程度很低,生命无虞。短暂的阴霾过后,我便重新振作了起来。工作照旧,遛狗如常,耳边回荡着“不过是个小手术”的安慰,让我天真地忽略了病情的复杂,以及“四级手术”这四个字背后的重量。
直到术前谈话,医生冷静地宣读那些可能的代价:“手臂活动可能受限”“声音或将变得嘶哑”“面部神经或受影响”……而我的思绪却早已飘向远方,盘算着术后要溜去哪里散心,躺在麻醉台上时,满心憧憬的都是康复后要和K桑去探访哪些小店。
然后,我从麻醉中醒来。
然后,那些被轻描淡写提及的“万一”,竟如命运的玩笑般,一一应验在我身上。最先凋零的是曾经的容颜,然后是灵活自如的躯体,还有我的声音。
每一个黎明都成了一场无声的战役。昨夜辛苦筑起的心理防线总在醒来的瞬间如沙堡般溃散。那些自我劝慰与肯定,像被戳破的泡沫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仿佛被困在一场没有尽头的梦魇里。曾经熟悉的自己正一点点消逝,如同忒修斯之船,在身体的更迭中,属于“我”的部分被剥离,只留下一具残破的空壳。
每次恸哭之后都会伴随着心理防御机制的退行。我好像变回一个三岁的小孩,只能抓着K桑一遍遍说:“我害怕。”
如果人格是跨越生活情境的一致性,那么眼前这个支离破碎,悲观失据的我难道才是真实的底色?难道我素日引以为傲的坚强与尊严,竟都建立在容貌、声音、躯体这些浮华的沙土之上?
《病隙碎笔》中写道:“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可当苦难如潮水般涌来,信心该向何处寻觅?我竭尽全力,依然无法为眼前的处境涂上一抹亮色。
或许正因还在抵抗,所以痛得格外清晰。可能我的内核从来就不是坚不可摧的。
我忽然懂了春琴。当她说道“不知是谁因恨我而做出这样的事……但说心里话,只要不是你,我不在意被任何人看到我如今的容貌”时,该是怎样一种绝望与释然交织的心境。
今天,我低头轻抚K桑的脸庞问他:“我还能继续做你的主人吗?”
他气鼓鼓地用头顶了顶我:“什么叫还能!你永远都是啊!”
唯有在他身边,我才能从这场漫长的风暴中,偷得片刻的安宁。
祈愿有一天,光能照进这片灰暗,让我重新认出自己的模样。

yu-e:↑因为身体的拖累,已经很久没发帖了。加油,安好,
当看到穿刺报告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毕竟恶性程度很低,生命无虞。短暂的阴霾过后,我便重新振作了起来。工作照旧,遛狗如常,耳边回荡着“不过是个小手术”的安慰,让我天真地忽略了病情的复杂,以及“四级手术”这四个字背后的重量。
直到术前谈话,医生冷静地宣读那些可能的代价:“手臂活动可能受限”“声音或将变得嘶哑”“面部神经或受影响”……而我的思绪却早已飘向远方,盘算着术后要溜去哪里散心,躺在麻醉台上时,满心憧憬的都是康复后要和K桑去探访哪些小店。
然后,我从麻醉中醒来。
然后,那些被轻描淡写提及的“万一”,竟如命运的玩笑般,一一应验在我身上。最先凋零的是曾经的容颜,然后是灵活自如的躯体,还有我的声音。
每一个黎明都成了一场无声的战役。昨夜辛苦筑起的心理防线总在醒来的瞬间如沙堡般溃散。那些自我劝慰与肯定,像被戳破的泡沫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仿佛被困在一场没有尽头的梦魇里。曾经熟悉的自己正一点点消逝,如同忒修斯之船,在身体的更迭中,属于“我”的部分被剥离,只留下一具残破的空壳。
每次恸哭之后都会伴随着心理防御机制的退行。我好像变回一个三岁的小孩,只能抓着K桑一遍遍说:“我害怕。”
如果人格是跨越生活情境的一致性,那么眼前这个支离破碎,悲观失据的我难道才是真实的底色?难道我素日引以为傲的坚强与尊严,竟都建立在容貌、声音、躯体这些浮华的沙土之上?
《病隙碎笔》中写道:“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可当苦难如潮水般涌来,信心该向何处寻觅?我竭尽全力,依然无法为眼前的处境涂上一抹亮色。
或许正因还在抵抗,所以痛得格外清晰。可能我的内核从来就不是坚不可摧的。
我忽然懂了春琴。当她说道“不知是谁因恨我而做出这样的事……但说心里话,只要不是你,我不在意被任何人看到我如今的容貌”时,该是怎样一种绝望与释然交织的心境。
今天,我低头轻抚K桑的脸庞问他:“我还能继续做你的主人吗?”
他气鼓鼓地用头顶了顶我:“什么叫还能!你永远都是啊!”
唯有在他身边,我才能从这场漫长的风暴中,偷得片刻的安宁。
祈愿有一天,光能照进这片灰暗,让我重新认出自己的模样。
yu-e:↑因为身体的拖累,已经很久没发帖了。说实话,我从没有想过会出现这样的事。这种风暴一样的事实可以撕碎任何幻想与侥幸。发生在身体上的变化与痛苦也是强迫去面对的事实,无法逃避。
当看到穿刺报告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毕竟恶性程度很低,生命无虞。短暂的阴霾过后,我便重新挺振作了起来。工作照旧,遛狗如常,耳边回荡着“不过是个小手术”的安慰,让我天真地忽略了病情的复杂,以及“四级手术”这四个字背后的重量。
直到术前谈话,医生冷静地宣读那些可能的代价:“手臂活动可能受限”“声音或将变得嘶哑”“面部神经或受影响”……而我的思绪却早已飘向远方,盘算着术后要溜去哪里散心,躺在麻醉台上时,满心憧憬的都是康复后要和K桑去探访哪些小店。
然后,我从麻醉中醒来。
然后,那些被轻描淡写提及的“万一”,竟如命运的玩笑般,一一应验在我身上。最先凋零的是曾经的容颜,然后是灵活自如的躯体,还有我的声音。
每一个黎明都成了一场无声的战役。昨夜辛苦筑起的心理防线总在醒来的瞬间如沙堡般溃散。那些自我劝慰与肯定,像被戳破的泡沫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仿佛被困在一场没有尽头的梦魇里。曾经熟悉的自己正一点点消逝,如同忒修斯之船,在身体的更迭中,属于“我”的部分被剥离,只留下一具残破的空壳。
每次恸哭之后都会伴随着心理防御机制的退行。我好像变回一个三岁的小孩,只能抓着K桑一遍遍说:“我害怕。”
如果人格是跨越生活情境的一致性,那么眼前这个支离破碎,悲观失据的我难道才是真实的底色?难道我素日引以为傲的坚强与尊严,竟都建立在容貌、声音、躯体这些浮华的沙土之上?
《病隙碎笔》中写道:“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可当苦难如潮水般涌来,信心该向何处寻觅?我竭尽全力,依然无法为眼前的处境涂上一抹亮色。
或许正因还在抵抗,所以痛得格外清晰。可能我的内核从来就不是坚不可摧的。
我忽然懂了春琴。当她说道“不知是谁因恨我而做出这样的事……但说心里话,只要不是你,我不在意被任何人看到我如今的容貌”时,该是怎样一种绝望与释然交织的心境。
今天,我低头轻抚K桑的脸庞问他:“我还能继续做你的主人吗?”
他气鼓鼓地用头顶了顶我:“什么叫还能!你永远都是啊!”
唯有在他身边,我才能从这场漫长的风暴中,偷得片刻的安宁。
祈愿有一天,光能照进这片灰暗,让我重新认出自己的模样。
我不知道能说什么,也不知道该不该说,意料之外的事让我把先前的一切预想和准备全扔到一旁。我想试着笨拙地安慰一下您。
曾经所自信与喜欢的部分都在一点点瓦解,是莫大的痛苦。不能灵活掌控躯体也会导致烦躁和无力。您会产生激动的心情是再正常不过了。我不知道我如果遇到这一切是否会彻底崩溃。我不认为您的害怕是“心理退行”。成年人也具有依赖别人的权利,尤其是所爱的人,这是动物与生俱来的本能,在这种巨大的痛苦面前,任何举动都算不上可怜。您对k桑的爱与保持生活的勇气,在我看来是非常伟大的素质。
当熟悉的物质渐渐远去,灵魂的轮廓却越发清晰。忒休斯之船永远不会替换掉您的本质。您并非机械构成的混合物。至少在阅读这篇文字的时候,哪怕怀着再沉重不过的心情,我也能看到先前那个优雅,智慧,冷静,美丽的yue老师。
说再多其他的东西也没什么用,惟愿您能在烈火一般的煎熬中,抽出翠绿的新芽。
虽然现在说这些还为时过早,并且不应该是由我来说才对。但我仍然保留着,您在将来能说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信心。
yu-e:↑因为身体的拖累,已经很久没发帖了。不知道怎么安慰,但也绝对不是刻意说教的一段话:
当看到穿刺报告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毕竟恶性程度很低,生命无虞。短暂的阴霾过后,我便重新振作了起来。工作照旧,遛狗如常,耳边回荡着“不过是个小手术”的安慰,让我天真地忽略了病情的复杂,以及“四级手术”这四个字背后的重量。
直到术前谈话,医生冷静地宣读那些可能的代价:“手臂活动可能受限”“声音或将变得嘶哑”“面部神经或受影响”……而我的思绪却早已飘向远方,盘算着术后要溜去哪里散心,躺在麻醉台上时,满心憧憬的都是康复后要和K桑去探访哪些小店。
然后,我从麻醉中醒来。
然后,那些被轻描淡写提及的“万一”,竟如命运的玩笑般,一一应验在我身上。最先凋零的是曾经的容颜,然后是灵活自如的躯体,还有我的声音。
每一个黎明都成了一场无声的战役。昨夜辛苦筑起的心理防线总在醒来的瞬间如沙堡般溃散。那些自我劝慰与肯定,像被戳破的泡沫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仿佛被困在一场没有尽头的梦魇里。曾经熟悉的自己正一点点消逝,如同忒修斯之船,在身体的更迭中,属于“我”的部分被剥离,只留下一具残破的空壳。
每次恸哭之后都会伴随着心理防御机制的退行。我好像变回一个三岁的小孩,只能抓着K桑一遍遍说:“我害怕。”
如果人格是跨越生活情境的一致性,那么眼前这个支离破碎,悲观失据的我难道才是真实的底色?难道我素日引以为傲的坚强与尊严,竟都建立在容貌、声音、躯体这些浮华的沙土之上?
《病隙碎笔》中写道:“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可当苦难如潮水般涌来,信心该向何处寻觅?我竭尽全力,依然无法为眼前的处境涂上一抹亮色。
或许正因还在抵抗,所以痛得格外清晰。可能我的内核从来就不是坚不可摧的。
我忽然懂了春琴。当她说道“不知是谁因恨我而做出这样的事……但说心里话,只要不是你,我不在意被任何人看到我如今的容貌”时,该是怎样一种绝望与释然交织的心境。
今天,我低头轻抚K桑的脸庞问他:“我还能继续做你的主人吗?”
他气鼓鼓地用头顶了顶我:“什么叫还能!你永远都是啊!”
唯有在他身边,我才能从这场漫长的风暴中,偷得片刻的安宁。
祈愿有一天,光能照进这片灰暗,让我重新认出自己的模样。
人体自我修复能力很强,吃蛋白质和维生素,做好物理和药物干预,心理压力别太大,才能更好的恢复。即使恢复不到100%那些失去东西也已经完成它们的使命了,没什么好遗憾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身体欠佳的时候,“万一”发生在你身上有点倒霉,但不妨换个角度想:你不一定是最倒霉的“受害人”,但可以努力做最幸运的幸存者。
但我感觉你目前有些担忧太过于善良了,太有责任心了。
自己变化的时候他人的目光并不一定是异样的,也不一定带来悲观的审判。
唐僧总是疑心他人是否“安全”或者担心走不到目的地,内耗只会走得更慢,状态没那么好时候不如做猪八戒该吃吃该睡睡脸皮厚一点使唤别人获得愉悦心情。
总之要好好吃饭睡觉先保全自己以后当别人需要你才不会无能无力。
祝愿一切安好,人间自有真情yue and k桑
你有k桑护佑,不必害怕,一切安好
啊啊啊⋯Yue老師人美心善一定會好起來的!
非常感谢Yue老师让我找到了这个帖子,我不会说话,但是祝愿yue老师能赶快好起来。
祝yu-e老师一切顺利捏
我记得挺久之前我因为朋友们的死陷入痛苦中。
我记得那时我看过一个作家的自传,里面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深受触动。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
[困于黑暗中的我只想做一件事,走出去,然后在将来的某一天,蓦然回首,能心生勇气面对现在的自己。]
我记得那时我看过一个作家的自传,里面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深受触动。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
[困于黑暗中的我只想做一件事,走出去,然后在将来的某一天,蓦然回首,能心生勇气面对现在的自己。]
想说些什么,想了很久,但是自身未曾经历,何德何能说出像轻松应对挫折这样的话。记得第一次发现帖子的时候 ,在yue老师、coco桑和其他帖友的交谈中浮现出一个严谨纠正,富有文气 ,思想活跃,有时还有点小小腹黑的yue老师 ,在无法面对面交流的论坛里,这样的有趣的人格把我留住了,让我有动力继续关注着,灵魂纯粹不变,从前的事已经铭刻在了过去,但未来依旧充满奇迹, 在此,送上我真心的祝福 ,望yue老师在k桑的陪伴下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yu-e:↑因为身体的拖累,已经很久没发帖了。衰老、病痛、灾祸,以及一切人所不可抵抗的变故,都会让人感觉生活失去了根据,失去了地基,一切都变得不安定,变得像坠落时的失重感一样,令人恐惧和抵触。人会觉得自己像是一颗被大火烧毁了的树木,从前的茂盛都像是一场梦一样,化作灰烬飘散而去,并且自己以后再无能将枝叶伸展得和以前一样茂盛的可能性。
当看到穿刺报告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毕竟恶性程度很低,生命无虞。短暂的阴霾过后,我便重新振作了起来。工作照旧,遛狗如常,耳边回荡着“不过是个小手术”的安慰,让我天真地忽略了病情的复杂,以及“四级手术”这四个字背后的重量。
直到术前谈话,医生冷静地宣读那些可能的代价:“手臂活动可能受限”“声音或将变得嘶哑”“面部神经或受影响”……而我的思绪却早已飘向远方,盘算着术后要溜去哪里散心,躺在麻醉台上时,满心憧憬的都是康复后要和K桑去探访哪些小店。
然后,我从麻醉中醒来。
然后,那些被轻描淡写提及的“万一”,竟如命运的玩笑般,一一应验在我身上。最先凋零的是曾经的容颜,然后是灵活自如的躯体,还有我的声音。
每一个黎明都成了一场无声的战役。昨夜辛苦筑起的心理防线总在醒来的瞬间如沙堡般溃散。那些自我劝慰与肯定,像被戳破的泡沫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仿佛被困在一场没有尽头的梦魇里。曾经熟悉的自己正一点点消逝,如同忒修斯之船,在身体的更迭中,属于“我”的部分被剥离,只留下一具残破的空壳。
每次恸哭之后都会伴随着心理防御机制的退行。我好像变回一个三岁的小孩,只能抓着K桑一遍遍说:“我害怕。”
如果人格是跨越生活情境的一致性,那么眼前这个支离破碎,悲观失据的我难道才是真实的底色?难道我素日引以为傲的坚强与尊严,竟都建立在容貌、声音、躯体这些浮华的沙土之上?
《病隙碎笔》中写道:“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可当苦难如潮水般涌来,信心该向何处寻觅?我竭尽全力,依然无法为眼前的处境涂上一抹亮色。
或许正因还在抵抗,所以痛得格外清晰。可能我的内核从来就不是坚不可摧的。
我忽然懂了春琴。当她说道“不知是谁因恨我而做出这样的事……但说心里话,只要不是你,我不在意被任何人看到我如今的容貌”时,该是怎样一种绝望与释然交织的心境。
今天,我低头轻抚K桑的脸庞问他:“我还能继续做你的主人吗?”
他气鼓鼓地用头顶了顶我:“什么叫还能!你永远都是啊!”
唯有在他身边,我才能从这场漫长的风暴中,偷得片刻的安宁。
祈愿有一天,光能照进这片灰暗,让我重新认出自己的模样。
人会觉得自己枯萎了。
但人是不会枯萎的,yue 老师也绝没有枯萎。yue 老师核心的人格魅力,依然在由内而外地散发着光辉。不妨看看周围那些被您灯塔般的灵魂所吸引、所抚慰的人,看看我们眼中的您的样子,您所担心失去的魅力,正倒映在我们眼中。衷心祝愿 yue 老师在对镜自视时,也能看到这熠熠生辉的,无法通过视觉看到的,无比珍贵的枝叶。
人的语言不会骗人,yue 老师的文字还是如此令人触动,直达人心,映射出的 yue 老师的灵魂依旧如从前一样闪耀。从 yue 老师的文字里,我感受到您感到迷茫,感到一切都已改变,感到自己被强硬地剥去了伪装,而暴露出脆弱的自己,并误相信这脆弱的自己才是真实的自己。但这些都是一时的情绪作祟,既非真实,也非永恒。
相信 yue 老师很快就能发现自己从未离开过自己,且自己仍然是那个自己。
yu-e:↑因为身体的拖累,已经很久没发帖了。yue老师,好久不见!
当看到穿刺报告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毕竟恶性程度很低,生命无虞。短暂的阴霾过后,我便重新振作了起来。工作照旧,遛狗如常,耳边回荡着“不过是个小手术”的安慰,让我天真地忽略了病情的复杂,以及“四级手术”这四个字背后的重量。
直到术前谈话,医生冷静地宣读那些可能的代价:“手臂活动可能受限”“声音或将变得嘶哑”“面部神经或受影响”……而我的思绪却早已飘向远方,盘算着术后要溜去哪里散心,躺在麻醉台上时,满心憧憬的都是康复后要和K桑去探访哪些小店。
然后,我从麻醉中醒来。
然后,那些被轻描淡写提及的“万一”,竟如命运的玩笑般,一一应验在我身上。最先凋零的是曾经的容颜,然后是灵活自如的躯体,还有我的声音。
每一个黎明都成了一场无声的战役。昨夜辛苦筑起的心理防线总在醒来的瞬间如沙堡般溃散。那些自我劝慰与肯定,像被戳破的泡沫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仿佛被困在一场没有尽头的梦魇里。曾经熟悉的自己正一点点消逝,如同忒修斯之船,在身体的更迭中,属于“我”的部分被剥离,只留下一具残破的空壳。
每次恸哭之后都会伴随着心理防御机制的退行。我好像变回一个三岁的小孩,只能抓着K桑一遍遍说:“我害怕。”
如果人格是跨越生活情境的一致性,那么眼前这个支离破碎,悲观失据的我难道才是真实的底色?难道我素日引以为傲的坚强与尊严,竟都建立在容貌、声音、躯体这些浮华的沙土之上?
《病隙碎笔》中写道:“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可当苦难如潮水般涌来,信心该向何处寻觅?我竭尽全力,依然无法为眼前的处境涂上一抹亮色。
或许正因还在抵抗,所以痛得格外清晰。可能我的内核从来就不是坚不可摧的。
我忽然懂了春琴。当她说道“不知是谁因恨我而做出这样的事……但说心里话,只要不是你,我不在意被任何人看到我如今的容貌”时,该是怎样一种绝望与释然交织的心境。
今天,我低头轻抚K桑的脸庞问他:“我还能继续做你的主人吗?”
他气鼓鼓地用头顶了顶我:“什么叫还能!你永远都是啊!”
唯有在他身边,我才能从这场漫长的风暴中,偷得片刻的安宁。
祈愿有一天,光能照进这片灰暗,让我重新认出自己的模样。
在生活的每一天中的我们永远不知晓意外什么时候会到来,计划往往很多时候都是赶不上变化的,但我们人生的小船永远还在缓缓前行,也许在今天我们遭受的很多痛苦,到了明天,乃至很多年之后,重新回首往昔会发现也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熬过来了,就像疫情的三年,不也不知不觉过来了嘛,一眨眼间都已经快过去两年之久了。
“在身体的更迭中,属于“我”的部分被剥离,只留下一具残破的空壳。” “难道我素日引以为傲的坚强与尊严,竟都建立在容貌、声音、躯体这些浮华的沙土之上?” yue老师何必妄自菲薄呢,尽管从种种文字中,能够感受到yue老师如今些微低沉的情绪,但看到这一篇留言,我要说,还是一如既往,同我印象里的yue老师一样,还是那位我熟悉的yue老师,充满了鲜活的个人特点,构建出我们如今的“自我”的并不是身躯、容貌,声音,而是思想、认知、记忆、灵魂,如今我们依旧能够观察、阅读,思考,那就绝不是残破的空壳,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我依旧是我。
长夜也许漫漫,但伴随着我们的不断踱步前行,黎明的光亮终究会照亮如今的灰暗,亦终将会看到彼方升起的烈阳,那时亦将会是别样风采!祝yue老师一切安康顺利,早日走出如今的灰暗。
人就是即使某个时刻痛苦得想要跳楼或是割腕死掉,在情绪过去之后仍然能继续活得很精彩的生物。
每顶一次帖,关心一次yue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