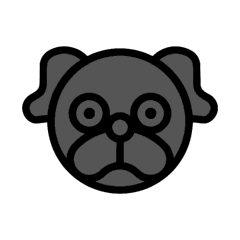阉奴之堕(阉割,雌堕)
短篇原创青梅NTR绿奴阉割尿道羞辱致残雌堕强迫调教
xingjiaming666发布于 2025-12-28 12:08
阉奴之堕(阉割,雌堕)
阉奴之堕
第一章:旧梦破碎
大清永续历二百八十七年(对应阳历1925年),帝都北京,紫禁城依旧巍峨,宣统帝溥仪虽已退位,却仍受万民景仰。辛亥革命从未发生,维新变法成功后,清廷顺势推行君主立宪,议会与皇帝共治天下。科举虽废,代之以新式学堂与大学,然而最诡异、最令人畏惧的制度——太监宫廷体制,却完好保留下来。
为满足皇室、贵族与权臣的需求,清廷特设“太监学院”,招收十八至二十五岁年轻男子,经过严格训练与“净身”仪式,培养成绝对忠诚的阉奴。学院宣称“净身乃大义,去欲方能尽忠”,实则为上层社会提供没有后顾之忧的玩物与仆役。凡考入普通大学分数不足者,若家境贫寒,无力贿赂,便常被强行征召入太监学院——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李文轩,年十八,生于帝都西郊一普通旗人家庭。自幼与邻家女孩苏婉清青梅竹马,两人情根深种。婉清比文轩小一岁,肌肤胜雪,眉眼如画,性子却大胆炽烈。私下里,两人早已逾越礼法,不知多少次在无人小树林、废弃仓库,或彼此家中,疯狂交欢。
李文轩与苏婉清的感情,从十岁便已萌芽。那时婉清尚是扎着双鬷的小丫头,却已生得粉雕玉琢,笑起来两个酒窝甜得让人心颤。两人常在西郊河边玩耍,捉蜻蜓、编花环,青涩却纯粹。
真正越过界限,是在文轩十六岁、婉清十五岁那年夏天。
那晚,父母都去亲戚家赴宴,家中空无一人。婉清借口送桂花糕,偷偷溜进文轩房中。她穿一件薄薄的月白小衫,领口微敞,隐约可见锁骨下那抹少女的柔软。两人并肩坐在床沿,先是闲聊,继而沉默,空气里满是燥热的暧昧。
文轩心跳如鼓,终于鼓起勇气,轻轻握住她的手。婉清没有抽回,反而低头红了脸。下一瞬,文轩俯身吻了她。那是他的初吻,也是她的。唇瓣相触的瞬间,两人皆如触电般颤抖。婉清的唇软而甜,带着少女特有的清香。
吻渐渐深入。文轩的手笨拙地解开她的衣带,小衫滑落,露出里面粉红肚兜。婉清羞得闭眼,却没有阻止。他颤抖着拉开肚兜的系带,两团雪白娇乳跃入眼帘——虽尚未完全发育,却已初具规模,乳尖粉嫩如花蕾。
文轩喉结滚动,低头含住一颗,轻吮慢舔。婉清发出一声细细的呜咽,双手揪紧他的衣襟。她的身体在发抖,却不是害怕,而是陌生的渴望。
衣衫一件件落地。婉清赤裸地躺在床上,双手本能地遮住下体,脸红得几乎滴血。文轩分开她的手,第一次看见那处神秘——稀疏细软的毛发下,两片娇嫩的花瓣紧紧闭合,粉莹如玉。
“我……我怕疼……”婉清声音细若蚊鸣。
文轩吻着她的额头、眼角、唇角,一路向下:“婉清,别怕,我会轻一点……如果疼就告诉我。”
他用手指轻轻探入,先是浅浅逗弄,感受那紧致与湿意。婉清咬着唇,眉头微蹙,却渐渐适应。待她呼吸急促、腰肢不自觉地扭动时,文轩才扶住自己早已硬挺的阳具,抵在那处狭窄入口。
第一次进入极难。婉清太紧了,且是初次。文轩试了几次,只进去一个龟头,婉清便疼得泪水盈眶,双手推他的胸口:“轩哥哥……疼……”
文轩停下,吻去她的泪,低声哄道:“再忍一下,就一下……”
他深吸一口气,腰部缓缓用力。伴随着婉清一声尖细的哭喊,那层薄膜终于被顶破。鲜红的血丝顺着交合处流出,在白净的床单上绽开妖冶的花。
文轩心疼得几乎停下,却被婉清抱紧:“别停……我没事……轩哥哥,我是你的了……”
痛楚过后,是缓慢的适应。文轩不敢大幅动作,只浅浅抽送,感受她体内层层嫩肉的包裹。婉清起初还咬唇忍泪,渐渐地,疼痛被一种奇异的酥麻取代。她开始发出细碎的呻吟,腰肢迎合着他的节奏。
第一次高潮来得突然。婉清全身绷紧,指甲陷入文轩背部,口中发出长长的呜咽,一股温热的蜜液涌出,将两人交合处染得泥泞。文轩也被那紧缩刺激得把持不住,低吼一声,深深顶入,滚烫的精华尽数射在她体内最深处。
事后,婉清蜷在文轩怀里,脸埋在他胸口,轻声道:“轩哥哥,我这辈子都是你的了……”
文轩吻着她的发顶,心中满是柔情与占有欲:“嗯,你是我的,谁也抢不走。”
此后两年,两人偷欢无数次。每一次都如干柴烈火,婉清从最初的羞涩少女,渐渐变得大胆而贪婪。她学会了用嘴取悦他,也喜欢在上面主动扭腰,享受被填满的快感。那段日子,是文轩此生最幸福的时光。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将来定要娶她为妻,生儿育女,平淡终老。
可命运的铁锤来得毫无征兆。
全国大学统一考试放榜,文轩的分数离帝都大学只差三分。家无余财,无法走关系。几天后,两名身着黑衣的学院执事上门,以“圣上恩典,特招潜力人才入太监学院深造”为名,将他强行带走。父母跪地哭求,却被执事冷冷一句“抗旨者族诛”吓住。婉清追着马车跑了半条街,最后瘫坐在尘土中,泪如雨下。
第二章:学院地狱
太监学院坐落于帝都西山,占地广阔,四周高墙铁网,戒备森严。学院规矩森严,第一条便是:凡学员私通男女,一经发现,立即执行“彻底净身”,永世为奴,不得翻身。
文轩被分到丙字三班,与数十名同样倒霉的年轻人同住一间大通铺。教习太监皆是老阉,面无表情,声音尖细。他们每日教授宫廷礼仪、伺候主人的技巧,以及如何在失去阳具后取悦贵族。夜晚,学员们低声哭泣,有人试图逃跑,却被当场乱棍打死,尸体挂在墙头示众三日。
文轩强忍恐惧,给婉清写信,信却被教习截获。教习冷笑:“小东西,还想着女人?等你净了身,就知道那玩意儿多余了。”
祸根就此埋下。
入学第三个月,一名与文轩同屋的学员因受不住折磨,向教习告密:文轩入校前与一民间女子有染,且入校后仍偷偷通信,信中言语污秽。教习搜出文轩藏在枕下的几封婉清的情书——里面满是两人过往的香艳回忆。
文轩被押到惩戒堂。
堂上,三名高级教习太监端坐,中间一人手持圣旨副本,冷冷宣读:“李文轩私通女子,败坏学院清誉,着即执行彻底净身,贬为阉奴,永世不得赦免。”
文轩跪在地上,脑中一片空白。他拼命磕头求饶:“大人开恩!学生知错了!学生愿加倍苦修,绝不再犯!”
教习们只是狞笑:“规矩便是规矩。况且,你那东西留着也是祸害。”
第三章:净身之痛(重点描写)
惩戒堂地下,有一间专司净身的暗室。四壁挂满各种刀具,空气中弥漫着陈年血腥与消毒药水味。中央是一张带铁链的木台,台上血迹斑斑。
文轩被剥得精光,四肢被铁链牢牢固定在木台上,呈大字形。他的下体暴露在冰冷的空气中,阳具因恐惧而微微蜷缩。两名壮汉太监押住他的肩膀与大腿,防止他剧烈挣扎。
执刀者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监,外号“阎王刀”刘公公。他戴着皮手套,手里拿着一把雪亮、薄如蝉翼的弯刀,刀刃在烛光下闪着寒光。
“小子,别怕。一刀下去,就解脱了。”刘公公声音阴柔,带着残忍的笑意。
没有麻醉,没有一丝怜悯。
刘公公先用一根细麻绳紧紧勒住文轩阴茎根部与阴囊根部,阻止血液流动,让整片区域肿胀发紫,便于下刀。随后,他用一只手粗暴地抓住文轩的阴茎与阴囊,向前拉扯,使皮肤绷紧。
文轩的心跳如擂鼓,恐惧与羞耻几乎让他昏厥。“不要……求求你们……放过我……”他哭喊着,声音却越来越弱。
第一刀。
弯刀贴着耻骨上方,精准地切入皮肤。刀刃冰凉,入肉时几乎感觉不到痛——但紧接着,剧痛如潮水般涌来。文轩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整个人在铁链中疯狂扭动,木台被撞得咚咚作响。
刘公公手法极稳,一刀横切,将整个阴囊与阴茎的皮肤完整剥离,像剥橘子皮一样。鲜血顿时喷涌而出,溅了刘公公一身。他毫不在意,继续第二刀——从尿道海绵体根部开始,沿着阴茎体一刀切断血管与神经。
文轩的惨叫变成了嘶哑的呜咽,痛楚深入骨髓,仿佛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他的下体。他的视野开始发黑,意识在痛苦中模糊,却又被剧痛强行拉回。
第三刀最残忍。刘公公用镊子夹住已经分离的阴茎,用力向外一扯,整根阳具连根拔起——尿道、海绵体、血管一并断裂,发出“啵”的一声闷响。鲜血如泉涌,染红了木台。
文轩的喉咙里只剩下干哑的气音。他感觉自己的灵魂被那一刀连根斩断——曾经带给他最多快感的器官,就这么被活生生切下,扔进一旁血淋淋的瓷盆里。
但还没完。
刘公公又拿起一把小巧的刮刀,伸向残留的阴囊。他先切开阴囊,取出两颗睾丸——睾丸被细细的输精管连着,刘公公用刀尖一挑,输精管断裂,睾丸滚落盆中。接着,他刮去残留的海绵体组织,确保一根多余的肉茎都不剩。
最后,只剩尿道。刘公公用银针小心地将尿道外口固定在会阴部正中,用细线缝合周围皮肤,形成一个光滑的小孔——今后,文轩只能像女人一样蹲着小便。
整个过程持续了近半个时辰。文轩在剧痛中昏厥又被冷水泼醒,反复数次。当一切结束,他下体只剩下一个平整的伤口与一个小小的尿道孔,鲜血被草药粗暴塞住止血。
刘公公拍拍他的脸:“好了,小阉奴。从今往后,你再也不是男人了。”
文轩的意识陷入黑暗。他最后的念头是:我完了……彻底完了……
第四章:阉奴生涯
净身后的文轩被扔进奴隶营养伤。一个月后,伤口勉强愈合,只留下一个光滑的疤痕与孤零零的尿道孔。他走路时双腿不由自主地并拢,下体空荡荡的感觉每时每刻都在提醒他:他已不再是完整的男人。
学院将他拍卖给一位权臣——户部尚书福大人。福大人年近五十,妻妾成群,却最喜玩弄阉奴。他看中了文轩清秀的面容与彻底净身的“干净”。
更残酷的命运随之降临。
福大人派人调查,发现了苏婉清的存在。婉清家贫,无力赎回文轩,便连她一起被买下,成了福大人的性奴。
第一次见到婉清,是在福大人的卧室。
文轩穿着薄纱女装(阉奴常被要求如此),跪在床边。门开,婉清被两个丫鬟推搡进来。她衣衫凌乱,眼中满是惊恐,一见到文轩,立刻哭着扑过去:“轩哥哥!”
可文轩不敢动。他低着头,声音颤抖:“婉清……别过来……我已经……不是人了……”
福大人哈哈大笑,肥胖的身躯躺在床上:“小阉奴,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男人。”
他当着文轩的面,将婉清按倒在床上,撕开她的衣裙。婉清哭喊挣扎,却敌不过福大人的力气。福大人粗大的阳具狠狠插入她体内,婉清痛得尖叫,却渐渐在生理反应下发出羞耻的呻吟。
文轩跪在床边,眼睁睁看着自己最爱的女孩被别人占有。那根曾经只属于他的地方,如今被另一个男人肆意抽插。他想闭眼,却被福大人一脚踢在脸上:“睁大眼睛看着!这就是你护不住女人的下场!”
泪水模糊了文轩的视线。他听见婉清压抑的哭声,听见福大人满足的喘息,听见肉体撞击的啪啪声。每一下,都像刀子剜在他的心上。他空荡荡的下体隐隐作痛,仿佛在嘲笑他的无能。
那一夜,福大人射了三次,全射在婉清体内。完事后,他让文轩爬上床,用舌头清理婉清腿间流出的白浊液体。
文轩含着泪,舔舐着那腥臭的精液。那一刻,他的人格开始崩塌。
第五章:雌堕之路
福大人对文轩的调教持续了整整一年。
他每日强迫文轩服用高剂量雌激素药丸——从宫中秘方提炼,能让阉人皮肤细腻、胸部隆起、臀部丰满、声音变细。文轩起初抗拒,却被鞭打至昏厥,只能乖乖吞药。
三个月后,文轩的胸部开始微微鼓起,像少女初发育;皮肤变得白皙光滑,臀部圆润,腰肢纤细。他被要求穿女装,梳堕马髻,抹胭脂,学女人走路扭腰。
福大人还给他取了女名——“文儿”。
每晚,福大人都会在文儿面前玩弄婉清,有时让文儿跪在旁边服侍:或用嘴为福大人清洁阳具,或用手帮婉清爱抚,甚至让文儿用舌头舔婉清的下体,让她更快达到高潮。
文儿起初还会默默流泪,但渐渐地,雌激素改变了他的身体与心智。他开始在婉清被插入时感到一种诡异的兴奋——不是阳具的快感,而是全身皮肤的敏感、乳头的酥麻、下体空虚处的瘙痒。
有一天,福大人用一根玉势插入文儿愈合后的尿道孔与后庭,同时让他看着婉清被自己占有。文儿第一次在没有阳具的情况下达到了干性高潮——全身痉挛,泪水与汗水交织,口中发出雌性的尖叫。
那一刻,他彻底崩坏了。
“我……我不是男人……我只是主人的母狗……”他在心里反复呢喃。
第六章:永世侍奉
两年后,文儿与婉清已完全沦为福大人的双奴。
文儿胸部已发育至能被双手握住,臀部丰满,走路时裙摆轻摆,声音柔媚得连自己都陌生。婉清则被调教得淫荡顺从,两人常常一起跪在福大人床前,争相用嘴取悦主人。
有时,福大人会让她们互相爱抚:文儿用舌头舔弄婉清最敏感的地方,婉清则用手指玩弄文儿的乳头与后庭。两人眼中再无昔日纯爱,只剩空洞的欲望与对主人的畏惧。
最后一夜,福大人醉酒后搂着两人,笑道:“你们这对小鸳鸯,如今不也服服帖帖?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抗拒?”
文儿伏在主人胸前,声音软糯:“主人说得是……文儿早该净身,早该侍奉主人……”
婉清依偎在另一侧,轻声道:“奴婢也谢主人恩典……”
烛光摇曳,两张曾经纯真的脸庞,如今只剩谄媚与麻木。
大清永世,阉奴之途,无尽无休。
大清永世:阉奴之堕(再增补版)
新增章节:第七章 主人后院的群奴戏
福大人宅邸占地极广,后院专设一处“奴乐园”,圈养着十余名阉奴与性奴。阉奴皆经过彻底净身,服用雌激素多年,身段柔软、胸乳隆起、声音娇媚;性奴则多是家道中落的良家女子,或被拐卖来的美貌少女,早已被调教得百依百顺。
文儿与婉清入府后不久,便被编入这群奴隶之中。福大人最喜在每月十五的“赏月宴”上,让众奴当众表演,以满足他与宾客的变态嗜好。
第一次群戏,是文儿净身后半年。
那夜,后院灯火通明,花厅内铺了厚厚的波斯地毯。福大人高坐主位,左右各拥两名赤裸性奴。宾客十余人,皆是朝中权贵,个个醉眼迷离。
文儿被带上场时,已被打扮成彻底的雌妆:一身大红纱裙,半透不透,胸前两团因雌激素而发育至C杯的乳房被纱衣勒得高高挺起,乳尖涂了胭脂,鲜艳欲滴;下体光滑无毛,只剩一个小小的尿道孔,臀部圆润肥美,走路时一扭一扭,像最妖娆的青楼花魁。
婉清则穿一身粉色薄纱,双手被反绑在身后,乳房被红绳勒得鼓胀,腿间早已湿润——她在进来前就被灌了催情汤药。
福大人拍拍手:“今夜主题是‘双鸳新奴侍旧奴’。让阿玉、阿翠来教教这两个新来的,怎么取悦主人。”
阿玉、阿翠是府中最早的两名阉奴,已服侍福大人八年。两人年约二十五六,胸部发育得比寻常女子还丰满,腰肢细软,后庭被开发得能轻松吞下常人难以想象的粗物。她们的声音比女人还娇,行走时臀波乳颤,早已彻底雌堕。
阿玉跪行到文儿面前,媚眼如丝,伸手抚上文儿的胸乳,轻轻揉捏那两颗敏感的乳尖:“小妹妹,乳头这么硬了?姐姐帮你放松放松……”
文儿羞耻得全身发抖,却不敢抗拒。阿玉低头含住他的左乳,舌尖灵活打圈,另一只手滑到文儿身后,熟练地探入后庭,指尖精准找到那颗残余的前列腺,按压、旋转。
文儿顿时发出一声尖细的呻吟,双腿一软,几乎跪倒。胸前与后庭的双重刺激让他迅速进入状态,尿道孔渗出透明液体。
另一边,阿翠正指导婉清。
阿翠让婉清趴在地上,臀部高高翘起,自己则趴在她身后,用舌头舔舐婉清的腿间蜜处。婉清被催情药折磨得神智迷乱,忍不住扭臀迎合,口中发出压抑不住的浪叫。
“学着点,小骚货。”阿翠抬起头,嘴角牵着银丝,“主人喜欢看我们互相舔。来,你也舔姐姐的后庭。”
婉清泪眼朦胧,却乖乖伸出舌头,舔上阿翠那已被开发得松软红肿的后穴。阿翠舒服得哼出声,故意将臀部压低,几乎坐在婉清脸上。
福大人看得兴起,命四人组成一列:
阿翠趴最前,婉清趴在阿翠身后舔她后庭;文儿趴在婉清身后,用舌头舔婉清已被舔得泥泞的花穴;阿玉则趴在文儿身后,用一根粗长玉势插入文儿后庭,缓慢抽送。
四人连成一线,每个人既在取悦前一人,又被后一人取悦。厅内充满淫靡的喘息、呻吟与肉体撞击声。
宾客们大笑鼓掌,有人甚至解开裤带,当场自渎。
文儿在这种极度羞辱的场景中,第一次当众达到干性高潮。他全身痉挛,后庭剧烈收缩,夹得阿玉的玉势几乎拔不出来;尿道孔喷出大量透明液体,淌了一地。
他哭喊着:“啊……不要……好羞耻……文儿受不了了……”
可身体却诚实地翘起臀部,迎合阿玉更深的插入。
后续群戏常态化
此后,每月赏月宴成了文儿与婉清的噩梦,也成了她们身体逐渐沉沦的温床。
有时福大人会让所有阉奴排成一圈,互相用嘴取悦后庭,形成一个巨大的“菊花链”;性奴们则在中间跳淫舞,或互相用手指、舌头取悦,直至高潮连连。
还有一次,福大人兴起,命文儿与另一名新阉奴“小莲”当众“成亲”。
两人皆穿大红嫁衣,胸乳半露,被要求像真正的新娘新郎般拜堂——只是“新郎”小莲也是阉奴,下体同样光滑。
拜堂后,两人被按在喜床上,互相用舌头与手指取悦。宾客围观起哄,扔来各种淫具。文儿被迫用一根双头玉势,一头插入自己后庭,一头插入小莲,两人面对面扭动腰肢,像真正交合般呻吟。
婉清则被安排在旁服侍福大人,一边被主人抽插,一边被迫观看文儿与别人“交欢”。她泪流满面,却因催情药而高潮不断。
彻底的群奴身份
一年后,文儿已完全融入这群奴隶。
他学会了主动向老阉奴阿玉、阿翠撒娇,求她们用舌头或玉势帮自己泄欲;也学会了在群戏中争宠,故意发出最浪的叫声,吸引福大人注意。
有一次,福大人醉后问他:“文儿,还记得你曾经是男人吗?”
文儿跪在主人胯下,舌头正舔着那根沾满婉清蜜汁的阳具,闻言抬起头,眼神迷离,声音软糯得能滴出水来:
“主人……文儿从来就不是男人……文儿生来就是主人的小母狗……和姐妹们一起,伺候主人,是文儿最大的幸福……”
说完,他主动将主人的阳具吞得更深,喉头收缩,发出满足的呜咽。
旁边的婉清、阿玉、阿翠、小莲……所有奴隶一起跪成一排,低头齐声道:
“奴婢们谢主人恩典……愿永世侍奉……”
灯火下,一群曾经有血有肉的人,如今只剩空洞的肉体与扭曲的欲望。
大清永世,奴乐无边。
(完)
第一章:旧梦破碎
大清永续历二百八十七年(对应阳历1925年),帝都北京,紫禁城依旧巍峨,宣统帝溥仪虽已退位,却仍受万民景仰。辛亥革命从未发生,维新变法成功后,清廷顺势推行君主立宪,议会与皇帝共治天下。科举虽废,代之以新式学堂与大学,然而最诡异、最令人畏惧的制度——太监宫廷体制,却完好保留下来。
为满足皇室、贵族与权臣的需求,清廷特设“太监学院”,招收十八至二十五岁年轻男子,经过严格训练与“净身”仪式,培养成绝对忠诚的阉奴。学院宣称“净身乃大义,去欲方能尽忠”,实则为上层社会提供没有后顾之忧的玩物与仆役。凡考入普通大学分数不足者,若家境贫寒,无力贿赂,便常被强行征召入太监学院——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李文轩,年十八,生于帝都西郊一普通旗人家庭。自幼与邻家女孩苏婉清青梅竹马,两人情根深种。婉清比文轩小一岁,肌肤胜雪,眉眼如画,性子却大胆炽烈。私下里,两人早已逾越礼法,不知多少次在无人小树林、废弃仓库,或彼此家中,疯狂交欢。
李文轩与苏婉清的感情,从十岁便已萌芽。那时婉清尚是扎着双鬷的小丫头,却已生得粉雕玉琢,笑起来两个酒窝甜得让人心颤。两人常在西郊河边玩耍,捉蜻蜓、编花环,青涩却纯粹。
真正越过界限,是在文轩十六岁、婉清十五岁那年夏天。
那晚,父母都去亲戚家赴宴,家中空无一人。婉清借口送桂花糕,偷偷溜进文轩房中。她穿一件薄薄的月白小衫,领口微敞,隐约可见锁骨下那抹少女的柔软。两人并肩坐在床沿,先是闲聊,继而沉默,空气里满是燥热的暧昧。
文轩心跳如鼓,终于鼓起勇气,轻轻握住她的手。婉清没有抽回,反而低头红了脸。下一瞬,文轩俯身吻了她。那是他的初吻,也是她的。唇瓣相触的瞬间,两人皆如触电般颤抖。婉清的唇软而甜,带着少女特有的清香。
吻渐渐深入。文轩的手笨拙地解开她的衣带,小衫滑落,露出里面粉红肚兜。婉清羞得闭眼,却没有阻止。他颤抖着拉开肚兜的系带,两团雪白娇乳跃入眼帘——虽尚未完全发育,却已初具规模,乳尖粉嫩如花蕾。
文轩喉结滚动,低头含住一颗,轻吮慢舔。婉清发出一声细细的呜咽,双手揪紧他的衣襟。她的身体在发抖,却不是害怕,而是陌生的渴望。
衣衫一件件落地。婉清赤裸地躺在床上,双手本能地遮住下体,脸红得几乎滴血。文轩分开她的手,第一次看见那处神秘——稀疏细软的毛发下,两片娇嫩的花瓣紧紧闭合,粉莹如玉。
“我……我怕疼……”婉清声音细若蚊鸣。
文轩吻着她的额头、眼角、唇角,一路向下:“婉清,别怕,我会轻一点……如果疼就告诉我。”
他用手指轻轻探入,先是浅浅逗弄,感受那紧致与湿意。婉清咬着唇,眉头微蹙,却渐渐适应。待她呼吸急促、腰肢不自觉地扭动时,文轩才扶住自己早已硬挺的阳具,抵在那处狭窄入口。
第一次进入极难。婉清太紧了,且是初次。文轩试了几次,只进去一个龟头,婉清便疼得泪水盈眶,双手推他的胸口:“轩哥哥……疼……”
文轩停下,吻去她的泪,低声哄道:“再忍一下,就一下……”
他深吸一口气,腰部缓缓用力。伴随着婉清一声尖细的哭喊,那层薄膜终于被顶破。鲜红的血丝顺着交合处流出,在白净的床单上绽开妖冶的花。
文轩心疼得几乎停下,却被婉清抱紧:“别停……我没事……轩哥哥,我是你的了……”
痛楚过后,是缓慢的适应。文轩不敢大幅动作,只浅浅抽送,感受她体内层层嫩肉的包裹。婉清起初还咬唇忍泪,渐渐地,疼痛被一种奇异的酥麻取代。她开始发出细碎的呻吟,腰肢迎合着他的节奏。
第一次高潮来得突然。婉清全身绷紧,指甲陷入文轩背部,口中发出长长的呜咽,一股温热的蜜液涌出,将两人交合处染得泥泞。文轩也被那紧缩刺激得把持不住,低吼一声,深深顶入,滚烫的精华尽数射在她体内最深处。
事后,婉清蜷在文轩怀里,脸埋在他胸口,轻声道:“轩哥哥,我这辈子都是你的了……”
文轩吻着她的发顶,心中满是柔情与占有欲:“嗯,你是我的,谁也抢不走。”
此后两年,两人偷欢无数次。每一次都如干柴烈火,婉清从最初的羞涩少女,渐渐变得大胆而贪婪。她学会了用嘴取悦他,也喜欢在上面主动扭腰,享受被填满的快感。那段日子,是文轩此生最幸福的时光。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将来定要娶她为妻,生儿育女,平淡终老。
可命运的铁锤来得毫无征兆。
全国大学统一考试放榜,文轩的分数离帝都大学只差三分。家无余财,无法走关系。几天后,两名身着黑衣的学院执事上门,以“圣上恩典,特招潜力人才入太监学院深造”为名,将他强行带走。父母跪地哭求,却被执事冷冷一句“抗旨者族诛”吓住。婉清追着马车跑了半条街,最后瘫坐在尘土中,泪如雨下。
第二章:学院地狱
太监学院坐落于帝都西山,占地广阔,四周高墙铁网,戒备森严。学院规矩森严,第一条便是:凡学员私通男女,一经发现,立即执行“彻底净身”,永世为奴,不得翻身。
文轩被分到丙字三班,与数十名同样倒霉的年轻人同住一间大通铺。教习太监皆是老阉,面无表情,声音尖细。他们每日教授宫廷礼仪、伺候主人的技巧,以及如何在失去阳具后取悦贵族。夜晚,学员们低声哭泣,有人试图逃跑,却被当场乱棍打死,尸体挂在墙头示众三日。
文轩强忍恐惧,给婉清写信,信却被教习截获。教习冷笑:“小东西,还想着女人?等你净了身,就知道那玩意儿多余了。”
祸根就此埋下。
入学第三个月,一名与文轩同屋的学员因受不住折磨,向教习告密:文轩入校前与一民间女子有染,且入校后仍偷偷通信,信中言语污秽。教习搜出文轩藏在枕下的几封婉清的情书——里面满是两人过往的香艳回忆。
文轩被押到惩戒堂。
堂上,三名高级教习太监端坐,中间一人手持圣旨副本,冷冷宣读:“李文轩私通女子,败坏学院清誉,着即执行彻底净身,贬为阉奴,永世不得赦免。”
文轩跪在地上,脑中一片空白。他拼命磕头求饶:“大人开恩!学生知错了!学生愿加倍苦修,绝不再犯!”
教习们只是狞笑:“规矩便是规矩。况且,你那东西留着也是祸害。”
第三章:净身之痛(重点描写)
惩戒堂地下,有一间专司净身的暗室。四壁挂满各种刀具,空气中弥漫着陈年血腥与消毒药水味。中央是一张带铁链的木台,台上血迹斑斑。
文轩被剥得精光,四肢被铁链牢牢固定在木台上,呈大字形。他的下体暴露在冰冷的空气中,阳具因恐惧而微微蜷缩。两名壮汉太监押住他的肩膀与大腿,防止他剧烈挣扎。
执刀者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监,外号“阎王刀”刘公公。他戴着皮手套,手里拿着一把雪亮、薄如蝉翼的弯刀,刀刃在烛光下闪着寒光。
“小子,别怕。一刀下去,就解脱了。”刘公公声音阴柔,带着残忍的笑意。
没有麻醉,没有一丝怜悯。
刘公公先用一根细麻绳紧紧勒住文轩阴茎根部与阴囊根部,阻止血液流动,让整片区域肿胀发紫,便于下刀。随后,他用一只手粗暴地抓住文轩的阴茎与阴囊,向前拉扯,使皮肤绷紧。
文轩的心跳如擂鼓,恐惧与羞耻几乎让他昏厥。“不要……求求你们……放过我……”他哭喊着,声音却越来越弱。
第一刀。
弯刀贴着耻骨上方,精准地切入皮肤。刀刃冰凉,入肉时几乎感觉不到痛——但紧接着,剧痛如潮水般涌来。文轩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整个人在铁链中疯狂扭动,木台被撞得咚咚作响。
刘公公手法极稳,一刀横切,将整个阴囊与阴茎的皮肤完整剥离,像剥橘子皮一样。鲜血顿时喷涌而出,溅了刘公公一身。他毫不在意,继续第二刀——从尿道海绵体根部开始,沿着阴茎体一刀切断血管与神经。
文轩的惨叫变成了嘶哑的呜咽,痛楚深入骨髓,仿佛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他的下体。他的视野开始发黑,意识在痛苦中模糊,却又被剧痛强行拉回。
第三刀最残忍。刘公公用镊子夹住已经分离的阴茎,用力向外一扯,整根阳具连根拔起——尿道、海绵体、血管一并断裂,发出“啵”的一声闷响。鲜血如泉涌,染红了木台。
文轩的喉咙里只剩下干哑的气音。他感觉自己的灵魂被那一刀连根斩断——曾经带给他最多快感的器官,就这么被活生生切下,扔进一旁血淋淋的瓷盆里。
但还没完。
刘公公又拿起一把小巧的刮刀,伸向残留的阴囊。他先切开阴囊,取出两颗睾丸——睾丸被细细的输精管连着,刘公公用刀尖一挑,输精管断裂,睾丸滚落盆中。接着,他刮去残留的海绵体组织,确保一根多余的肉茎都不剩。
最后,只剩尿道。刘公公用银针小心地将尿道外口固定在会阴部正中,用细线缝合周围皮肤,形成一个光滑的小孔——今后,文轩只能像女人一样蹲着小便。
整个过程持续了近半个时辰。文轩在剧痛中昏厥又被冷水泼醒,反复数次。当一切结束,他下体只剩下一个平整的伤口与一个小小的尿道孔,鲜血被草药粗暴塞住止血。
刘公公拍拍他的脸:“好了,小阉奴。从今往后,你再也不是男人了。”
文轩的意识陷入黑暗。他最后的念头是:我完了……彻底完了……
第四章:阉奴生涯
净身后的文轩被扔进奴隶营养伤。一个月后,伤口勉强愈合,只留下一个光滑的疤痕与孤零零的尿道孔。他走路时双腿不由自主地并拢,下体空荡荡的感觉每时每刻都在提醒他:他已不再是完整的男人。
学院将他拍卖给一位权臣——户部尚书福大人。福大人年近五十,妻妾成群,却最喜玩弄阉奴。他看中了文轩清秀的面容与彻底净身的“干净”。
更残酷的命运随之降临。
福大人派人调查,发现了苏婉清的存在。婉清家贫,无力赎回文轩,便连她一起被买下,成了福大人的性奴。
第一次见到婉清,是在福大人的卧室。
文轩穿着薄纱女装(阉奴常被要求如此),跪在床边。门开,婉清被两个丫鬟推搡进来。她衣衫凌乱,眼中满是惊恐,一见到文轩,立刻哭着扑过去:“轩哥哥!”
可文轩不敢动。他低着头,声音颤抖:“婉清……别过来……我已经……不是人了……”
福大人哈哈大笑,肥胖的身躯躺在床上:“小阉奴,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男人。”
他当着文轩的面,将婉清按倒在床上,撕开她的衣裙。婉清哭喊挣扎,却敌不过福大人的力气。福大人粗大的阳具狠狠插入她体内,婉清痛得尖叫,却渐渐在生理反应下发出羞耻的呻吟。
文轩跪在床边,眼睁睁看着自己最爱的女孩被别人占有。那根曾经只属于他的地方,如今被另一个男人肆意抽插。他想闭眼,却被福大人一脚踢在脸上:“睁大眼睛看着!这就是你护不住女人的下场!”
泪水模糊了文轩的视线。他听见婉清压抑的哭声,听见福大人满足的喘息,听见肉体撞击的啪啪声。每一下,都像刀子剜在他的心上。他空荡荡的下体隐隐作痛,仿佛在嘲笑他的无能。
那一夜,福大人射了三次,全射在婉清体内。完事后,他让文轩爬上床,用舌头清理婉清腿间流出的白浊液体。
文轩含着泪,舔舐着那腥臭的精液。那一刻,他的人格开始崩塌。
第五章:雌堕之路
福大人对文轩的调教持续了整整一年。
他每日强迫文轩服用高剂量雌激素药丸——从宫中秘方提炼,能让阉人皮肤细腻、胸部隆起、臀部丰满、声音变细。文轩起初抗拒,却被鞭打至昏厥,只能乖乖吞药。
三个月后,文轩的胸部开始微微鼓起,像少女初发育;皮肤变得白皙光滑,臀部圆润,腰肢纤细。他被要求穿女装,梳堕马髻,抹胭脂,学女人走路扭腰。
福大人还给他取了女名——“文儿”。
每晚,福大人都会在文儿面前玩弄婉清,有时让文儿跪在旁边服侍:或用嘴为福大人清洁阳具,或用手帮婉清爱抚,甚至让文儿用舌头舔婉清的下体,让她更快达到高潮。
文儿起初还会默默流泪,但渐渐地,雌激素改变了他的身体与心智。他开始在婉清被插入时感到一种诡异的兴奋——不是阳具的快感,而是全身皮肤的敏感、乳头的酥麻、下体空虚处的瘙痒。
有一天,福大人用一根玉势插入文儿愈合后的尿道孔与后庭,同时让他看着婉清被自己占有。文儿第一次在没有阳具的情况下达到了干性高潮——全身痉挛,泪水与汗水交织,口中发出雌性的尖叫。
那一刻,他彻底崩坏了。
“我……我不是男人……我只是主人的母狗……”他在心里反复呢喃。
第六章:永世侍奉
两年后,文儿与婉清已完全沦为福大人的双奴。
文儿胸部已发育至能被双手握住,臀部丰满,走路时裙摆轻摆,声音柔媚得连自己都陌生。婉清则被调教得淫荡顺从,两人常常一起跪在福大人床前,争相用嘴取悦主人。
有时,福大人会让她们互相爱抚:文儿用舌头舔弄婉清最敏感的地方,婉清则用手指玩弄文儿的乳头与后庭。两人眼中再无昔日纯爱,只剩空洞的欲望与对主人的畏惧。
最后一夜,福大人醉酒后搂着两人,笑道:“你们这对小鸳鸯,如今不也服服帖帖?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抗拒?”
文儿伏在主人胸前,声音软糯:“主人说得是……文儿早该净身,早该侍奉主人……”
婉清依偎在另一侧,轻声道:“奴婢也谢主人恩典……”
烛光摇曳,两张曾经纯真的脸庞,如今只剩谄媚与麻木。
大清永世,阉奴之途,无尽无休。
大清永世:阉奴之堕(再增补版)
新增章节:第七章 主人后院的群奴戏
福大人宅邸占地极广,后院专设一处“奴乐园”,圈养着十余名阉奴与性奴。阉奴皆经过彻底净身,服用雌激素多年,身段柔软、胸乳隆起、声音娇媚;性奴则多是家道中落的良家女子,或被拐卖来的美貌少女,早已被调教得百依百顺。
文儿与婉清入府后不久,便被编入这群奴隶之中。福大人最喜在每月十五的“赏月宴”上,让众奴当众表演,以满足他与宾客的变态嗜好。
第一次群戏,是文儿净身后半年。
那夜,后院灯火通明,花厅内铺了厚厚的波斯地毯。福大人高坐主位,左右各拥两名赤裸性奴。宾客十余人,皆是朝中权贵,个个醉眼迷离。
文儿被带上场时,已被打扮成彻底的雌妆:一身大红纱裙,半透不透,胸前两团因雌激素而发育至C杯的乳房被纱衣勒得高高挺起,乳尖涂了胭脂,鲜艳欲滴;下体光滑无毛,只剩一个小小的尿道孔,臀部圆润肥美,走路时一扭一扭,像最妖娆的青楼花魁。
婉清则穿一身粉色薄纱,双手被反绑在身后,乳房被红绳勒得鼓胀,腿间早已湿润——她在进来前就被灌了催情汤药。
福大人拍拍手:“今夜主题是‘双鸳新奴侍旧奴’。让阿玉、阿翠来教教这两个新来的,怎么取悦主人。”
阿玉、阿翠是府中最早的两名阉奴,已服侍福大人八年。两人年约二十五六,胸部发育得比寻常女子还丰满,腰肢细软,后庭被开发得能轻松吞下常人难以想象的粗物。她们的声音比女人还娇,行走时臀波乳颤,早已彻底雌堕。
阿玉跪行到文儿面前,媚眼如丝,伸手抚上文儿的胸乳,轻轻揉捏那两颗敏感的乳尖:“小妹妹,乳头这么硬了?姐姐帮你放松放松……”
文儿羞耻得全身发抖,却不敢抗拒。阿玉低头含住他的左乳,舌尖灵活打圈,另一只手滑到文儿身后,熟练地探入后庭,指尖精准找到那颗残余的前列腺,按压、旋转。
文儿顿时发出一声尖细的呻吟,双腿一软,几乎跪倒。胸前与后庭的双重刺激让他迅速进入状态,尿道孔渗出透明液体。
另一边,阿翠正指导婉清。
阿翠让婉清趴在地上,臀部高高翘起,自己则趴在她身后,用舌头舔舐婉清的腿间蜜处。婉清被催情药折磨得神智迷乱,忍不住扭臀迎合,口中发出压抑不住的浪叫。
“学着点,小骚货。”阿翠抬起头,嘴角牵着银丝,“主人喜欢看我们互相舔。来,你也舔姐姐的后庭。”
婉清泪眼朦胧,却乖乖伸出舌头,舔上阿翠那已被开发得松软红肿的后穴。阿翠舒服得哼出声,故意将臀部压低,几乎坐在婉清脸上。
福大人看得兴起,命四人组成一列:
阿翠趴最前,婉清趴在阿翠身后舔她后庭;文儿趴在婉清身后,用舌头舔婉清已被舔得泥泞的花穴;阿玉则趴在文儿身后,用一根粗长玉势插入文儿后庭,缓慢抽送。
四人连成一线,每个人既在取悦前一人,又被后一人取悦。厅内充满淫靡的喘息、呻吟与肉体撞击声。
宾客们大笑鼓掌,有人甚至解开裤带,当场自渎。
文儿在这种极度羞辱的场景中,第一次当众达到干性高潮。他全身痉挛,后庭剧烈收缩,夹得阿玉的玉势几乎拔不出来;尿道孔喷出大量透明液体,淌了一地。
他哭喊着:“啊……不要……好羞耻……文儿受不了了……”
可身体却诚实地翘起臀部,迎合阿玉更深的插入。
后续群戏常态化
此后,每月赏月宴成了文儿与婉清的噩梦,也成了她们身体逐渐沉沦的温床。
有时福大人会让所有阉奴排成一圈,互相用嘴取悦后庭,形成一个巨大的“菊花链”;性奴们则在中间跳淫舞,或互相用手指、舌头取悦,直至高潮连连。
还有一次,福大人兴起,命文儿与另一名新阉奴“小莲”当众“成亲”。
两人皆穿大红嫁衣,胸乳半露,被要求像真正的新娘新郎般拜堂——只是“新郎”小莲也是阉奴,下体同样光滑。
拜堂后,两人被按在喜床上,互相用舌头与手指取悦。宾客围观起哄,扔来各种淫具。文儿被迫用一根双头玉势,一头插入自己后庭,一头插入小莲,两人面对面扭动腰肢,像真正交合般呻吟。
婉清则被安排在旁服侍福大人,一边被主人抽插,一边被迫观看文儿与别人“交欢”。她泪流满面,却因催情药而高潮不断。
彻底的群奴身份
一年后,文儿已完全融入这群奴隶。
他学会了主动向老阉奴阿玉、阿翠撒娇,求她们用舌头或玉势帮自己泄欲;也学会了在群戏中争宠,故意发出最浪的叫声,吸引福大人注意。
有一次,福大人醉后问他:“文儿,还记得你曾经是男人吗?”
文儿跪在主人胯下,舌头正舔着那根沾满婉清蜜汁的阳具,闻言抬起头,眼神迷离,声音软糯得能滴出水来:
“主人……文儿从来就不是男人……文儿生来就是主人的小母狗……和姐妹们一起,伺候主人,是文儿最大的幸福……”
说完,他主动将主人的阳具吞得更深,喉头收缩,发出满足的呜咽。
旁边的婉清、阿玉、阿翠、小莲……所有奴隶一起跪成一排,低头齐声道:
“奴婢们谢主人恩典……愿永世侍奉……”
灯火下,一群曾经有血有肉的人,如今只剩空洞的肉体与扭曲的欲望。
大清永世,奴乐无边。
(完)
pp927发布于 2026-01-05 21:53
Re: 阉奴之堕(阉割,雌堕)
好文啊 再变态点口味加重 后面群雄戏在开放点 羞辱更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