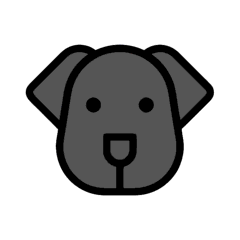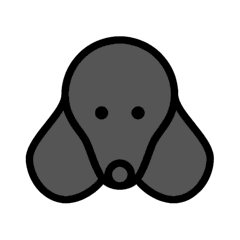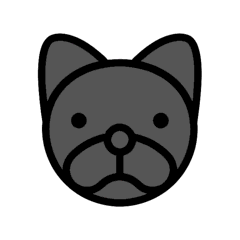瑪德琳·德·克萊蒙
阶级大小姐连载中原创虐杀高跟鞋骑人马现实鞋靴鞭打踩脸群体崇拜校园公开调教
羅謝福夫人
羅謝福夫人輕抿一口紅茶,茶水熱氣輕輕掠過她的睫毛。那些話題——“他求著要被使用”、“他願意做腳凳”—— 並未能引起她的興趣。
在這個世界裡,奴隸從來都是這樣被「使用」的。
既非戲劇性的折磨,也非惡意,單單是貴族女子生活本身的一部分。
奴隸被用作家具……太常見、太普通了。腳凳這種用法遠不是最殘忍的。甚至稱不上特別。
她輕放茶杯,修長的手指挪動杯柄,無聲無息地敲在純銀托盤上。
在潔白的蕾絲桌布下,她的雙腳正安穩地踩在“腳凳”的腹部中央。
她的腳踝完全放鬆,雙腿自然下沉,將整個腿部的重量無保留地壓在他身上。
因為今天是正式場合,侍女自然替她準備了更纖細、更高挑的一雙高跟鞋。
鞋底硬度更高,鞋跟更尖、壓力更集中——
這對被踩踏的“腳凳”而言,或許意味著加倍的痛苦。
但她也不曾想過要為此做任何調整——
因為她穿什麼鞋,永遠是依照她的服飾搭配、氣質呈現與場合需要。
不是依照一個“家具”能不能承受。
無論鞋跟多尖、無論鞋底多硬——
她腳下傳回來的觸感永遠如出一轍:
柔軟、溫暖、服從。
腹肉的彈性、皮膚傳導的溫度、在鞋跟刺落時那幾乎壓抑不住的細微顫動——
彷彿以最隱晦的方式提醒她:
腳下的,是活的。
活著的腳凳,永遠比冰冷的絲絨木凳更令人放鬆。
她幾乎無聲地吐出一口淺淺的氣息。
不是疲累,是純粹的舒適。
她心底坦然承認,這種柔和、貼服的承托感……令人愉悅。
為了談論接下來重要的家族大事,她希望自己的坐姿保持完美。
因此她微微調整腰背線條,重新安置手腕與手肘的位置。
隨著上半身優雅地變換角度,她的雙腳自然順勢調整——
並再次深深下壓。
於是——
右腳鞋跟深深壓入腹部肋骨下方敏感的胃部位置,
左腳鞋跟則刺入腸道所在的柔軟區域。
桌下的身體條件反射般抽搐了一下,發出一聲壓抑痛苦悶響,
但很快又恢復成家具該有的絕對靜止。
她沒有察覺到,也從不需要察覺。
因為這不是她想折磨誰;
這也不是懲罰;
這只是主人在使用家具。
而腳凳被踩得深深凹陷、皮膚是否快要裂開、是否痛得抽搐、是否呼吸困難——
都不是主人的問題。
她甚至不清楚自己的鞋跟此刻踩在什麼器官上:
胃?橫膈膜?腸子?
她不知道,也無意知道。
一件家具——
唯一的使命,就是被使用。
而不是被擔心是否會“用壞”
她的背挺得筆直,肩線自然舒展,頸項微微抬起,姿態如同一幅宮廷油畫中的女主人。
羽扇在她指間優雅晃動,帶著從容的節奏。
終於,她輕輕開口,話題自然轉向她真正關心的事情
「說到孩子們……」
語氣溫和,如在談論午後天氣般淡雅。
「加布里埃爾今年十九。明年便要從學院畢業了。」
「而瑪德琳仍需四年才能從學院中畢業。」
她抬眸,將視線落在身旁的伊莎貝拉身上。
唇角微微彎起,她以沉著得體的語氣問道:
「那麼兩人的婚禮——
妳覺得,是該在明年舉行?
還是待瑪德琳畢業後再辦更妥?」
羅謝福夫人輕抿一口紅茶,茶水熱氣輕輕掠過她的睫毛。那些話題——“他求著要被使用”、“他願意做腳凳”—— 並未能引起她的興趣。
在這個世界裡,奴隸從來都是這樣被「使用」的。
既非戲劇性的折磨,也非惡意,單單是貴族女子生活本身的一部分。
奴隸被用作家具……太常見、太普通了。腳凳這種用法遠不是最殘忍的。甚至稱不上特別。
她輕放茶杯,修長的手指挪動杯柄,無聲無息地敲在純銀托盤上。
在潔白的蕾絲桌布下,她的雙腳正安穩地踩在“腳凳”的腹部中央。
她的腳踝完全放鬆,雙腿自然下沉,將整個腿部的重量無保留地壓在他身上。
因為今天是正式場合,侍女自然替她準備了更纖細、更高挑的一雙高跟鞋。
鞋底硬度更高,鞋跟更尖、壓力更集中——
這對被踩踏的“腳凳”而言,或許意味著加倍的痛苦。
但她也不曾想過要為此做任何調整——
因為她穿什麼鞋,永遠是依照她的服飾搭配、氣質呈現與場合需要。
不是依照一個“家具”能不能承受。
無論鞋跟多尖、無論鞋底多硬——
她腳下傳回來的觸感永遠如出一轍:
柔軟、溫暖、服從。
腹肉的彈性、皮膚傳導的溫度、在鞋跟刺落時那幾乎壓抑不住的細微顫動——
彷彿以最隱晦的方式提醒她:
腳下的,是活的。
活著的腳凳,永遠比冰冷的絲絨木凳更令人放鬆。
她幾乎無聲地吐出一口淺淺的氣息。
不是疲累,是純粹的舒適。
她心底坦然承認,這種柔和、貼服的承托感……令人愉悅。
為了談論接下來重要的家族大事,她希望自己的坐姿保持完美。
因此她微微調整腰背線條,重新安置手腕與手肘的位置。
隨著上半身優雅地變換角度,她的雙腳自然順勢調整——
並再次深深下壓。
於是——
右腳鞋跟深深壓入腹部肋骨下方敏感的胃部位置,
左腳鞋跟則刺入腸道所在的柔軟區域。
桌下的身體條件反射般抽搐了一下,發出一聲壓抑痛苦悶響,
但很快又恢復成家具該有的絕對靜止。
她沒有察覺到,也從不需要察覺。
因為這不是她想折磨誰;
這也不是懲罰;
這只是主人在使用家具。
而腳凳被踩得深深凹陷、皮膚是否快要裂開、是否痛得抽搐、是否呼吸困難——
都不是主人的問題。
她甚至不清楚自己的鞋跟此刻踩在什麼器官上:
胃?橫膈膜?腸子?
她不知道,也無意知道。
一件家具——
唯一的使命,就是被使用。
而不是被擔心是否會“用壞”
她的背挺得筆直,肩線自然舒展,頸項微微抬起,姿態如同一幅宮廷油畫中的女主人。
羽扇在她指間優雅晃動,帶著從容的節奏。
終於,她輕輕開口,話題自然轉向她真正關心的事情
「說到孩子們……」
語氣溫和,如在談論午後天氣般淡雅。
「加布里埃爾今年十九。明年便要從學院畢業了。」
「而瑪德琳仍需四年才能從學院中畢業。」
她抬眸,將視線落在身旁的伊莎貝拉身上。
唇角微微彎起,她以沉著得體的語氣問道:
「那麼兩人的婚禮——
妳覺得,是該在明年舉行?
還是待瑪德琳畢業後再辦更妥?」
这部分应该快结束了吧,等待学院的后续~
injustice_mirror:↑这部分应该快结束了吧,等待学院的后续~下一章就是學院了。
克萊蒙夫人
伊莎貝拉聽見這個話題時,便將手中的馬克龍輕輕放回盤中。
不疾不徐,指尖穩定,從容自持。
「這個問題……」
她略作停頓,像是在為措辭留出恰當的位置,
「不該詢問兩名當事人嗎?」
彷彿為了緩和話題的重量,她微微調整了蕾絲桌布之下的雙腳。鞋跟順著腳凳肋骨的弧線,極其自然地向前滑動,直到某個邊界處停下。隨後,她將右腳搭在左腳腳踝之上,形成一個端正而合禮的交疊姿勢,甚至無意識地輕輕晃動了幾下腳尖。
這樣的動作,對她而言不過是思考時的習慣性小動作。
但對桌下那具被迫承受重量的身體來說,每一次晃動,都是一次殘酷的測試:
肋骨是否仍能支撐?
內臟是否已被擠壓到臨界?
是否還能維持「家具」該有的穩定?
但伊莎貝拉絲毫不覺。
她的神情仍然始終溫和,優雅,專注在談話中。
她的鞋底下,只有被視為“家具”的柔軟承托。
只是一件鋪著厚毯、柔軟而可靠的腳踏。
一旁的西勒斯夫人輕輕搖動羽毛扇,扇緣半掩住她的唇角,那抹笑意既含著隱晦,又帶著戲謔。
「現在兩個孩子都在學院裡,確實是一個……」
她刻意放慢語速,讓話語在空氣中緩緩展開。
「方便彼此了解的時期呢。」
她的扇面微微一晃,語氣變得更柔軟、更緩慢:
「不過——」
她停下來,似乎在揣摩最合適的措辭,
又像是在預告接下來的話將引發某種微妙火花。
「那畢竟是一座懸於湖上的孤島。」
她側過頭,目光在伊莎貝拉與羅謝福夫人之間來回遊移,臉上的笑容依舊優雅而得體。
「誰知道呢?說不定,還沒等到婚禮舉行——」
她微微一笑,語氣輕得像隨口一提,
「羅謝福公國就已經迎來了下一位繼承人。」
就在話音尚未完全消散之際——
她的左腳忽然向下施力。
不是激動,也不是情緒的反射。
正相反,那是極為自然、近乎“無意識”的優雅動作——
就像貴婦在談笑時不經意轉動扇柄、調整手腕,或撫平裙襬上的褶皺。
細跟鞋在瞬間刺入深入得不該被觸碰的位置。
桌下那個承托她雙足的身體像被突然壓碎般發出一聲悶響——
聲音短促、含糊,被厚重桌布吞噬。
那聲音像熟透葡萄在指間被捏碎時的回饋——
悶悶的、濕潤的、帶著令人想象的破裂感。
西勒斯夫人的神情沒有任何變化。
她甚至連眨眼的節奏都未曾改變。
羽扇依舊輕搖,笑意未減。
她完全沒有察覺——
或者更準確地說,她並不需要察覺。
她只是——坐著。
只是——使用腳凳。
只是——習慣性地踩下。
伊莎貝拉這時放下了茶杯。
瓷器與托盤相觸,聲音清晰而乾脆。
她的神情也隨之沉了下來。
「未經神所祝福的結合,所誕下的子嗣——」
她語調冷靜而嚴正。
「只會被視為私生子。」
她微微抬起下顎,語氣不容置疑。
「我相信,大主教絕不會應許這樣的行為。」
「身為學院長的帝國之光-艾德蒙閣下,也絕不會坐視此類事情發生。」
說話時,她的雙腳依舊穩穩地踩著“腳凳”。
像是回應這份立場,又像是在無聲地宣示什麼,羅謝福夫人忽然加重了足下的力道。
「加布里埃爾那孩子,自幼便清楚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她的語氣沉著,帶著不容辯駁的自信。
「界線,一向分明。」
她看向西勒斯夫人,目光中帶著一絲冷淡而直接的挑釁。
「這種情況,永遠不會發生。」
在這張茶桌之上,真正重要的,只有婚姻、血統、繼承與秩序。
至於桌布之下的存在——
他的痛楚、缺氧與逼近極限的忍耐力——
從未在任何人的關注之內。
只是背景。
只是承托。
只是一件為她們提供舒適的家具。
永遠如此。
伊莎貝拉聽見這個話題時,便將手中的馬克龍輕輕放回盤中。
不疾不徐,指尖穩定,從容自持。
「這個問題……」
她略作停頓,像是在為措辭留出恰當的位置,
「不該詢問兩名當事人嗎?」
彷彿為了緩和話題的重量,她微微調整了蕾絲桌布之下的雙腳。鞋跟順著腳凳肋骨的弧線,極其自然地向前滑動,直到某個邊界處停下。隨後,她將右腳搭在左腳腳踝之上,形成一個端正而合禮的交疊姿勢,甚至無意識地輕輕晃動了幾下腳尖。
這樣的動作,對她而言不過是思考時的習慣性小動作。
但對桌下那具被迫承受重量的身體來說,每一次晃動,都是一次殘酷的測試:
肋骨是否仍能支撐?
內臟是否已被擠壓到臨界?
是否還能維持「家具」該有的穩定?
但伊莎貝拉絲毫不覺。
她的神情仍然始終溫和,優雅,專注在談話中。
她的鞋底下,只有被視為“家具”的柔軟承托。
只是一件鋪著厚毯、柔軟而可靠的腳踏。
一旁的西勒斯夫人輕輕搖動羽毛扇,扇緣半掩住她的唇角,那抹笑意既含著隱晦,又帶著戲謔。
「現在兩個孩子都在學院裡,確實是一個……」
她刻意放慢語速,讓話語在空氣中緩緩展開。
「方便彼此了解的時期呢。」
她的扇面微微一晃,語氣變得更柔軟、更緩慢:
「不過——」
她停下來,似乎在揣摩最合適的措辭,
又像是在預告接下來的話將引發某種微妙火花。
「那畢竟是一座懸於湖上的孤島。」
她側過頭,目光在伊莎貝拉與羅謝福夫人之間來回遊移,臉上的笑容依舊優雅而得體。
「誰知道呢?說不定,還沒等到婚禮舉行——」
她微微一笑,語氣輕得像隨口一提,
「羅謝福公國就已經迎來了下一位繼承人。」
就在話音尚未完全消散之際——
她的左腳忽然向下施力。
不是激動,也不是情緒的反射。
正相反,那是極為自然、近乎“無意識”的優雅動作——
就像貴婦在談笑時不經意轉動扇柄、調整手腕,或撫平裙襬上的褶皺。
細跟鞋在瞬間刺入深入得不該被觸碰的位置。
桌下那個承托她雙足的身體像被突然壓碎般發出一聲悶響——
聲音短促、含糊,被厚重桌布吞噬。
那聲音像熟透葡萄在指間被捏碎時的回饋——
悶悶的、濕潤的、帶著令人想象的破裂感。
西勒斯夫人的神情沒有任何變化。
她甚至連眨眼的節奏都未曾改變。
羽扇依舊輕搖,笑意未減。
她完全沒有察覺——
或者更準確地說,她並不需要察覺。
她只是——坐著。
只是——使用腳凳。
只是——習慣性地踩下。
伊莎貝拉這時放下了茶杯。
瓷器與托盤相觸,聲音清晰而乾脆。
她的神情也隨之沉了下來。
「未經神所祝福的結合,所誕下的子嗣——」
她語調冷靜而嚴正。
「只會被視為私生子。」
她微微抬起下顎,語氣不容置疑。
「我相信,大主教絕不會應許這樣的行為。」
「身為學院長的帝國之光-艾德蒙閣下,也絕不會坐視此類事情發生。」
說話時,她的雙腳依舊穩穩地踩著“腳凳”。
像是回應這份立場,又像是在無聲地宣示什麼,羅謝福夫人忽然加重了足下的力道。
「加布里埃爾那孩子,自幼便清楚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她的語氣沉著,帶著不容辯駁的自信。
「界線,一向分明。」
她看向西勒斯夫人,目光中帶著一絲冷淡而直接的挑釁。
「這種情況,永遠不會發生。」
在這張茶桌之上,真正重要的,只有婚姻、血統、繼承與秩序。
至於桌布之下的存在——
他的痛楚、缺氧與逼近極限的忍耐力——
從未在任何人的關注之內。
只是背景。
只是承托。
只是一件為她們提供舒適的家具。
永遠如此。
来了来了!这篇文章希望能写到大结局
请提供更多关于那个脚凳如何被使用以及如何被处理的场景。
hanamizuki:↑来了来了!这篇文章希望能写到大结局到兩人結婚那一幕,便會迎來第一個大結局。
eternalslaven2:↑请提供更多关于那个脚凳如何被使用以及如何被处理的场景。处理的方法就是手腳切斷啊。
三位夫人腳下踩的就是那個腳凳。
第五章 : 校園生活
第一小節
聖諾蘭城通往學院的港口,被夕陽與湖水蒸騰而起的霧氣包圍著。
金色的光線低低地鋪在水面上,霧氣在光中緩慢流動,像一層精心鋪陳的薄紗,將港口與外界隔開。遠方,湖心孤島只剩下一個模糊而莊嚴的輪廓——聖諾蘭學院。
而此地——
聖諾蘭城碼頭,
正是島嶼與帝國之間唯一被承認的入口,
也是所有貴族子弟安全的第一道關卡。
碼頭的石板在餘溫中泛著淡淡光澤,軍靴踏上去時,聲音清脆而克制。巡邏的士兵來回行走,長矛與佩劍反射著夕光,秩序井然,沒有任何鬆懈的跡象。
檢查站,一名駐軍軍官站在桌前,背脊筆直,雙手戴著白手套,正一頁一頁地翻閱著手中的文件。
那是一疊極厚的羊皮紙。
最上方的一張,字跡端正而剛硬,筆畫毫不拖泥帶水,清楚寫明了貨物的出發地、航線、所屬家族與最終目的地;
其後數張,則密密麻麻地列出一串長得近乎不合常理的清單——名稱、數量、用途,被工整地分欄排列。羊皮紙的邊角因反覆翻閱而微微捲起,顯然不是第一次被如此仔細地檢視。
軍官的目光一路向下。
又向下。
再向下。
清單彷彿沒有盡頭。
他的眉心終於微不可察地收緊了一瞬,像是在權衡是否還有必要繼續這種徒勞的確認。片刻後,他索性翻到了最後一頁。
動作在那一刻停住了。
因為在清單的最末端,端端正正地落著一個名字——
阿爾方斯・德・克萊蒙。
簽名旁,是克萊蒙公國的正式印章。
金鷹展翼,線條銳利而嚴謹,深深壓入羊皮紙的纖維之中,彷彿連紙張本身,都被迫承認了這份權威的重量。
這不是能夠偽造的東西,
也不是任何一名帝國士兵,願意輕易忽視的象徵。
軍官的視線在印章上停留了片刻,像是在完成一項早已知曉答案的確認。隨後,他才慢慢抬起頭。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名年長的男人。
黑色制服剪裁得體,線條俐落,沒有一絲多餘的皺摺。金屬鈕扣被拋光得極為細緻,卻刻意壓低了光澤,不顯張揚。白襯衫的領口筆直而挺括,彷彿每天都由同一把尺反覆校正過角度。
他站得很直。
雙手自然垂於身側。
既不刻意恭卑,也沒有任何多餘的姿態。那是一種極其內斂的端正——只屬於長年侍奉高階貴族、深諳分寸與界線的人。
歲月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跡。鬢角花白,臉部線條硬朗而克制,皺紋深深刻在眉間與眼角。那不是勞累的痕跡,而是多年承載責任後沉澱下來的穩重。
他正是克萊蒙莊園的大管家——
菲利普。
「菲利普先生。」
軍官開口,語氣依舊公事公辦,卻已比先前低了半分銳度。
他低頭看了一眼文件,又抬起視線。
「依照文件所示,這批貨物……」
他停頓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辭。
「是由克萊蒙公爵大人送往學院,供瑪德琳小姐使用的——『人車競賽』馬匹裝備,以及日用品?」
話音落下時,他忍不住側頭,看向老人身後。
整整五輛馬車,依序停靠在碼頭邊。
車身厚實,輪軸粗大,顯然是專為重物與長途運輸而打造。車廂邊緣包覆著金屬護角,防止碰撞。篷布被綁得極緊,繩索結實,每一個結都打得規矩而一致,帶著軍事背景貴族常見的風格。
即便尚未掀開,僅憑外觀也能看出裡頭裝載的東西份量不輕。
軍官再次低頭,看向那份清單。
目光沿著文字滑下去,眉頭不自覺地皺得更深了。
「依聖諾蘭城駐軍規定,」他終於說道,語氣回到標準的程序性冷靜,「所有進入學院的貨物,都必須接受全面檢查,以確保島上貴族子弟的安全。還請您理解。」
菲利普微微一笑。
那笑容極其克制,嘴角上揚的弧度恰到好處,既不顯敷衍,也不顯得過分親近。
「當然,長官先生。」
他的聲音平穩而溫和。
「規定就是規定,克萊蒙家從不例外。」
他側過身,回頭看向那五輛馬車,目光短暫而清楚,像是在心中再次核對每一件物品的存在。
「不過,」他轉回來,語氣依舊平靜,「我可以向您保證,車上並不存在任何危險物品。」
他略作停頓,語調微妙地柔和了一分。
「只有公爵大人對我家小姐的……關心。」
軍官的嘴角輕微地動了一下,卻沒有接話。
「或者說,」菲利普補充道,「愛。」
他抬手畫了一個小小的圓弧,彷彿在說明那份愛究竟有多完美無缺。
「除了『人車競賽』所需的全套裝備,」他繼續道,「還有公爵大人『認為』小姐需要、卻在入學時來不及親自帶上的日用品。」
「衣物、寢具、書籍、化妝品、鞋子,」
他語氣平穩地列舉,「以及幾樣備用的替換品。」
他微微一笑。
「只是這份愛,稍微有那麼一點……溢出了。」
軍官的眉梢不由自主地抽動了一下。
菲利普卻像是沒有注意到一般,慢條斯理地從外套內袋取出一只懷錶。
金屬外殼光滑而低調,沒有多餘的裝飾。他按下按鈕,錶蓋彈開,指針在夕陽下閃過一抹冷亮。
他看了一眼時間,隨後闔上懷錶。
「時間不早了,」他抬起頭,語氣依舊溫和而得體,「今天前往學院的最後一趟船班,還有半個小時。」
軍官沉默了片刻。
最終,他輕輕歎了一口氣。
他已經明白,這注定只會是一場形式上的檢查。
「例行程序還是要走。」
他說,語調恢復了純粹的公務口吻。
隨即,他側首對身旁的副官點了點頭。
「去檢查一下。」
副官帶著兩名士兵走向馬車,象徵性地翻了幾下篷布,對那些巨大的木箱看了看,甚至連打開的意思都沒有。
「菲利普先生,」軍官忽然補充道,「公爵大人為瑪德琳小姐準備的『馬匹』,我需要親自確認一下。畢竟,我不能讓任何來路不明的活人走上那座島。」
菲利普沒有絲毫遲疑。
「當然,長官先生。請隨我來。」
他帶著軍官來到最後一輛馬車。
車簾掀開。
裡面坐著十六名男人。
身材高大,肌肉結實,坐姿筆直如石。眼神沉穩而堅定,散發出一種久經訓練後才會有的壓迫感。
若不是他們頸項上佩戴著刻有編號的項圈,軍官幾乎不會認為他們是奴隸。
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人,若被派往前線,無疑都足以成為帝國最鋒利的騎士。
軍官在心中默默對照清單上的編號,以及他們曾經的名字。
他的動作頓了一下。
其中一個名字,他認得。
他與那人對上了視線。
像是在無聲地詢問——
你是認真的嗎?
對方的眼神回應得毫不遲疑。
堅定,平靜,毫無動搖。
軍官輕輕籲了一口氣,放下車簾。
他轉回身,重新面向菲利普。
「檢查完成。」
他抬手,在文件最後一頁蓋下駐軍的通行印記。紅色的蠟印在紙上凝固,發出極輕微的一聲脆響。
「五輛馬車,准許通行。」
菲利普微微欠身。
「感謝您的配合,長官先生。」
不久後,五輛馬車緩緩駛上前往學院的最後一班擺渡船。
第一小節
聖諾蘭城通往學院的港口,被夕陽與湖水蒸騰而起的霧氣包圍著。
金色的光線低低地鋪在水面上,霧氣在光中緩慢流動,像一層精心鋪陳的薄紗,將港口與外界隔開。遠方,湖心孤島只剩下一個模糊而莊嚴的輪廓——聖諾蘭學院。
而此地——
聖諾蘭城碼頭,
正是島嶼與帝國之間唯一被承認的入口,
也是所有貴族子弟安全的第一道關卡。
碼頭的石板在餘溫中泛著淡淡光澤,軍靴踏上去時,聲音清脆而克制。巡邏的士兵來回行走,長矛與佩劍反射著夕光,秩序井然,沒有任何鬆懈的跡象。
檢查站,一名駐軍軍官站在桌前,背脊筆直,雙手戴著白手套,正一頁一頁地翻閱著手中的文件。
那是一疊極厚的羊皮紙。
最上方的一張,字跡端正而剛硬,筆畫毫不拖泥帶水,清楚寫明了貨物的出發地、航線、所屬家族與最終目的地;
其後數張,則密密麻麻地列出一串長得近乎不合常理的清單——名稱、數量、用途,被工整地分欄排列。羊皮紙的邊角因反覆翻閱而微微捲起,顯然不是第一次被如此仔細地檢視。
軍官的目光一路向下。
又向下。
再向下。
清單彷彿沒有盡頭。
他的眉心終於微不可察地收緊了一瞬,像是在權衡是否還有必要繼續這種徒勞的確認。片刻後,他索性翻到了最後一頁。
動作在那一刻停住了。
因為在清單的最末端,端端正正地落著一個名字——
阿爾方斯・德・克萊蒙。
簽名旁,是克萊蒙公國的正式印章。
金鷹展翼,線條銳利而嚴謹,深深壓入羊皮紙的纖維之中,彷彿連紙張本身,都被迫承認了這份權威的重量。
這不是能夠偽造的東西,
也不是任何一名帝國士兵,願意輕易忽視的象徵。
軍官的視線在印章上停留了片刻,像是在完成一項早已知曉答案的確認。隨後,他才慢慢抬起頭。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名年長的男人。
黑色制服剪裁得體,線條俐落,沒有一絲多餘的皺摺。金屬鈕扣被拋光得極為細緻,卻刻意壓低了光澤,不顯張揚。白襯衫的領口筆直而挺括,彷彿每天都由同一把尺反覆校正過角度。
他站得很直。
雙手自然垂於身側。
既不刻意恭卑,也沒有任何多餘的姿態。那是一種極其內斂的端正——只屬於長年侍奉高階貴族、深諳分寸與界線的人。
歲月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跡。鬢角花白,臉部線條硬朗而克制,皺紋深深刻在眉間與眼角。那不是勞累的痕跡,而是多年承載責任後沉澱下來的穩重。
他正是克萊蒙莊園的大管家——
菲利普。
「菲利普先生。」
軍官開口,語氣依舊公事公辦,卻已比先前低了半分銳度。
他低頭看了一眼文件,又抬起視線。
「依照文件所示,這批貨物……」
他停頓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辭。
「是由克萊蒙公爵大人送往學院,供瑪德琳小姐使用的——『人車競賽』馬匹裝備,以及日用品?」
話音落下時,他忍不住側頭,看向老人身後。
整整五輛馬車,依序停靠在碼頭邊。
車身厚實,輪軸粗大,顯然是專為重物與長途運輸而打造。車廂邊緣包覆著金屬護角,防止碰撞。篷布被綁得極緊,繩索結實,每一個結都打得規矩而一致,帶著軍事背景貴族常見的風格。
即便尚未掀開,僅憑外觀也能看出裡頭裝載的東西份量不輕。
軍官再次低頭,看向那份清單。
目光沿著文字滑下去,眉頭不自覺地皺得更深了。
「依聖諾蘭城駐軍規定,」他終於說道,語氣回到標準的程序性冷靜,「所有進入學院的貨物,都必須接受全面檢查,以確保島上貴族子弟的安全。還請您理解。」
菲利普微微一笑。
那笑容極其克制,嘴角上揚的弧度恰到好處,既不顯敷衍,也不顯得過分親近。
「當然,長官先生。」
他的聲音平穩而溫和。
「規定就是規定,克萊蒙家從不例外。」
他側過身,回頭看向那五輛馬車,目光短暫而清楚,像是在心中再次核對每一件物品的存在。
「不過,」他轉回來,語氣依舊平靜,「我可以向您保證,車上並不存在任何危險物品。」
他略作停頓,語調微妙地柔和了一分。
「只有公爵大人對我家小姐的……關心。」
軍官的嘴角輕微地動了一下,卻沒有接話。
「或者說,」菲利普補充道,「愛。」
他抬手畫了一個小小的圓弧,彷彿在說明那份愛究竟有多完美無缺。
「除了『人車競賽』所需的全套裝備,」他繼續道,「還有公爵大人『認為』小姐需要、卻在入學時來不及親自帶上的日用品。」
「衣物、寢具、書籍、化妝品、鞋子,」
他語氣平穩地列舉,「以及幾樣備用的替換品。」
他微微一笑。
「只是這份愛,稍微有那麼一點……溢出了。」
軍官的眉梢不由自主地抽動了一下。
菲利普卻像是沒有注意到一般,慢條斯理地從外套內袋取出一只懷錶。
金屬外殼光滑而低調,沒有多餘的裝飾。他按下按鈕,錶蓋彈開,指針在夕陽下閃過一抹冷亮。
他看了一眼時間,隨後闔上懷錶。
「時間不早了,」他抬起頭,語氣依舊溫和而得體,「今天前往學院的最後一趟船班,還有半個小時。」
軍官沉默了片刻。
最終,他輕輕歎了一口氣。
他已經明白,這注定只會是一場形式上的檢查。
「例行程序還是要走。」
他說,語調恢復了純粹的公務口吻。
隨即,他側首對身旁的副官點了點頭。
「去檢查一下。」
副官帶著兩名士兵走向馬車,象徵性地翻了幾下篷布,對那些巨大的木箱看了看,甚至連打開的意思都沒有。
「菲利普先生,」軍官忽然補充道,「公爵大人為瑪德琳小姐準備的『馬匹』,我需要親自確認一下。畢竟,我不能讓任何來路不明的活人走上那座島。」
菲利普沒有絲毫遲疑。
「當然,長官先生。請隨我來。」
他帶著軍官來到最後一輛馬車。
車簾掀開。
裡面坐著十六名男人。
身材高大,肌肉結實,坐姿筆直如石。眼神沉穩而堅定,散發出一種久經訓練後才會有的壓迫感。
若不是他們頸項上佩戴著刻有編號的項圈,軍官幾乎不會認為他們是奴隸。
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人,若被派往前線,無疑都足以成為帝國最鋒利的騎士。
軍官在心中默默對照清單上的編號,以及他們曾經的名字。
他的動作頓了一下。
其中一個名字,他認得。
他與那人對上了視線。
像是在無聲地詢問——
你是認真的嗎?
對方的眼神回應得毫不遲疑。
堅定,平靜,毫無動搖。
軍官輕輕籲了一口氣,放下車簾。
他轉回身,重新面向菲利普。
「檢查完成。」
他抬手,在文件最後一頁蓋下駐軍的通行印記。紅色的蠟印在紙上凝固,發出極輕微的一聲脆響。
「五輛馬車,准許通行。」
菲利普微微欠身。
「感謝您的配合,長官先生。」
不久後,五輛馬車緩緩駛上前往學院的最後一班擺渡船。
催更~
还有后续吗?还是说26年准备开新坑了~
好久没更了,要是打算开新坑的话,能不能开个玛德琳母女把雷蒙搞死的if线收尾?
第二小節 馬棚
馬夫
清晨的霧氣尚未從競技廣場的石板間退去時,我已經站在馬棚門口了。
我是學院的馬夫之一,名不見經傳,卻每日與這些比人更被珍視的生靈為伍。對我而言,這座馬棚不只是存放馬匹的地方,它是一座無聲卻殘酷的階級圖鑑——用木欄、鐵環與皮革,將貴族世界的秩序一寸寸釘死在空氣裡。
馬棚緊貼著競技廣場的東側。高牆之外,是為人車競賽與馬上對抗所準備的沙地;高牆之內,則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每當廣場上響起號角與喝彩,馬棚裡的馬便會不安地踏蹄、噴氣,牠們早已習慣那種聲音,知道那意味著奔跑、榮耀,或受傷。
整座馬棚以灰白色石材築成,屋頂高聳,木樑粗壯,足以承受積雪與時間。入口上方懸掛著學院的徽章,金屬早已被歲月磨得黯淡,卻仍然高高在上。進門後,是一條筆直而寬闊的主通道,地面鋪著厚厚的沙與碎草,用來吸水、防滑,也掩蓋氣味。
馬棚是分區的,而且分得極其清楚。
最靠近競技廣場的一側,是公爵家與王室專用的區域。那裡的馬欄更高、更寬,木材經過細緻打磨,邊角包覆著黃銅。每一匹馬都有自己的名牌,刻著家徽與正式的馬名,字跡深而清晰。我每日為牠們刷毛時,都得格外小心,哪怕一根刷毛卡住了金屬釦環,都可能引來上頭的責難。
那些馬與其說是牲畜,不如說是移動的權力。牠們的毛色被精心挑選,步態受過嚴格訓練,安靜而冷漠,像極了牠們的主人。王室的馬尤其如此,即便站在欄內,也昂首挺胸,彷彿隨時準備踏上競技場,接受眾人的注視。
緊鄰其後的,是伯爵們的區域。
那裡明顯狹窄許多。欄位少、間距小,裝飾也簡化成實用為主。我常聽見伯爵家隨從低聲抱怨,說學院偏心,說空間不公。
伯爵的馬多半不差,只是缺乏那種被精心「塑造」的氣勢。牠們更躁動些,也更容易親近。每當我為牠們整理馬蹄時,總能感覺到牠們對競技場的渴望——牠們知道自己有資格奔跑,卻被擠在角落。
至於低階貴族?
他們幾乎沒有位置。
在馬棚最深處,有幾個沒有家徽、沒有名牌的欄位,那裡拴著的是學院的公共馬匹。這些馬平日由我們照料,用於課程、訓練,或在「緊急情況」下借給那些無馬可用的低階貴族。它們的裝備統一、陳舊,皮革早已被無數雙手磨得發亮,卻看不出原本的顏色。
我見過低階貴族站在欄外,手指緊抓木欄,目光複雜地望著那些馬。他們不敢多說一句話,只能在被允許時,迅速牽走一匹,然後在用完後默默歸還。沒有榮耀,沒有歸屬,只有短暫的借用。
馬棚的一側連著馬具倉庫。那是一個比馬棚本身更安靜的地方。
厚重的木門後,是整齊排列的馬鞍、韁繩、護具與披毯。王室與公爵家的裝備被單獨鎖在內側的櫃中,皮革柔軟,金屬拋光,聞起來甚至帶著淡淡的油香。伯爵們的器具掛在外圈,保養得當卻少了那份奢華。至於公共馬具,則集中在最外側,隨取隨用,卻也最容易磨損。
我每日清點這些物件時,總會不自覺地放輕動作。馬具不會說話,但它們承載的,是主人的身份與野心。哪一副馬鞍被放在內層,哪一條韁繩被掛在最外,早已不是偶然。
到了午後,競技廣場的聲音會變得清晰。鐵蹄敲擊石板,觀眾的喝采,教官的命令,混合成一股震動,順著牆壁傳進馬棚。馬開始躁動,我則一一安撫,低聲說話,撫摸牠們的頸側。
在這裡,馬比人誠實。牠們不懂爵位,只懂欄位的大小、刷毛的次數、能否踏上沙地奔跑。
而我,只是一個看守秩序的人。每日在這座貴族公用的馬棚裡,替權力刷毛,替階級添草,看著榮耀與不甘,在一排排木欄之間靜靜站立。
他踏進馬棚時,我其實就已經注意到他了。
不是因為他張揚——恰恰相反,是因為那份刻意的克制。衣著整潔,卻沒有多餘的裝飾;靴子擦得乾淨,但皮革的折痕顯示它被反覆修補過。披風的邊角縫線細密,卻用的是耐磨而廉價的線材。那是一種我太熟悉的打扮:努力維持體面,卻無法掩飾資源的邊界。
我在心中做出判斷——男爵之子,或許還不是繼承人。
他走到我面前,沒有多說話,只是雙手遞上一張折得整齊的羊皮紙。那動作小心翼翼,像是生怕紙張本身比他更有地位。我接過來,指尖觸到略微粗糙的纖維,展開查看。
是學院的既定格式。
上方是標準化的抬頭與條款,文字端正,墨跡未乾透的地方已被細心地吹過。中段寫著申請理由——措辭謙遜而冗長,顯然是反覆推敲後才敢落筆。借用的馬匹編號標註得清楚,屬於公共馬匹序列中較為穩定的一匹,不是最老,也不是最好的。最下方,學院的印章壓得極深,紅蠟完整,邊緣沒有一絲裂痕。
我檢查了印章的紋路,又對照了一旁的登記冊,確認編號與許可無誤。
「請跟我來。」我把羊皮紙收好,語氣平靜而公事公辦。
他點了點頭,動作略顯僵硬,跟在我身後。
我們穿過馬棚的主通道,經過公爵家與王室的欄位時,他的目光不自覺地向那一側飄去。我沒有停下,只是帶著他轉入連接馬具倉庫的小門。那裡的光線昏暗些,空氣中多了皮革與油脂的味道。
倉庫內部井然有序。
前排掛著公爵與王室專屬的馬具,金屬扣環在火把下泛著溫潤的光,皮革表面幾乎沒有使用痕跡。再往裡,是伯爵們的裝備,保養得當,卻已留下時間的印記。
我一直走到最後一排。
那裡的架子簡單而實用,沒有家徽,沒有個人標記,只有統一的學院印跡。我伸手取下一副馬鞍,檢查了一下縫線與扣具,確保它仍然牢靠。
就在這時,我發現他沒有跟上。
我轉過身,看見他停在倉庫門口,整個人像被釘在原地。
他的目光越過我,越過架子,落在馬棚另一側——那裡停放著一輛嶄新的戰車。
那是克萊蒙公爵家的戰車。
即便隔著距離,它依舊耀眼得令人無法忽視。車身線條流暢而低伏,木材經過精細打磨,表面覆著深色漆層,隱約映出周圍的光影。金屬框架不是冰冷的鐵,而是經過拋光的合金,邊緣刻著細密的紋飾。輪輻纖細卻結實,排列角度精準,顯然是為高速與穩定而設計。
戰車旁的馬具同樣奢華,韁繩與護具整齊地掛在專用支架上,每一件都與車身風格一致,彷彿本就屬於同一個完整的藝術品。
那是克萊蒙家大小姐在人車競賽中使用的戰車。
昨天夜裡,它才被送進來。那時馬棚已經安靜下來,只有我們幾個馬夫在場。我還記得那扇門被推開時的聲音,以及菲利普大管家親自指揮人手搬運的場面。他的動作一如既往地從容,語氣不高,卻沒有任何人敢怠慢。
那不是一件單純的競技器具,那是一種宣告。
而現在,這名男爵家的孩子正站在原地,呆呆地望著它。
他的眼神裡沒有嫉妒,也沒有不滿,只有純粹的震撼與茫然。那是一種第一次直視差距時才會出現的神情——彷彿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明白自己站在這座學院的哪一層。
我沒有催促。
只是稍稍放低聲音,像是怕驚動什麼似的,輕聲提醒道:
「那是克萊蒙小姐的戰車。」
他猛地回過神來,迅速收回視線,臉上浮現一絲慌亂與羞愧,連忙向我走來。那份短暫的失神被他努力掩埋,但我已經看見了。
我把馬鞍遞到他手中。
學院印跡在皮革上清晰可見,沉穩而冰冷。
在這座馬棚裡,奢華與現實只隔著幾步距離。而有些人,一生都只能站在最後一排,遠遠地看上一眼。
他雙手接過那副帶著學院印記的馬鞍,動作比剛才明顯沉穩了許多。那不是因為放鬆,而是一種被迫的自制——像是把剛剛那一瞬間的失神與憧憬,一起鎖進了胸腔深處。他沒有再看那輛戰車一眼,轉身便朝著公共馬匹的欄位走去,靴子踏在馬棚鋪滿乾草與沙粒的地面上,聲音輕而規律。
那是一匹棕色的學院用馬,毛色不算出眾,卻肌肉結實,眼神溫順而警覺。它抬起頭嗅了嗅空氣,似乎早已習慣了這樣的更換騎手。男爵之子走到牠身側,先是輕輕撫摸了一下馬頸,像是在向一位老朋友致意,接著便熟練地將馬鞍搭上馬背。
他的動作讓我不由得多看了他幾眼。
那不是那種靠模仿學來的笨拙,而是真正經年累月訓練留下的節奏感。他調整鞍墊的位置,確保不會壓到馬的肩胛;拉緊腹帶時,他用的是恰到好處的力道,既穩固又不讓馬感到不適。水勒被他一一扣好,皮帶順著馬頭的輪廓貼合,沒有多餘的扭曲。
和那些高階貴族的子女不同。
那些人往往帶著一整隊侍從與馬夫,自己只是站在一旁,讓別人為他們處理一切。他們或許懂得如何騎在馬背上保持優雅,卻未必知道一條韁繩若扣錯一孔,在競技場上會意味著什麼。
而這個男爵家的孩子不一樣。
他從小被教育要自己完成這些事。不是為了展示風度,而是因為在他的世界裡,馬不是裝飾,而是戰場上生死相依的夥伴。每一個扣環、每一條皮帶,都是為了在戰場上活下來,為了隨時能為領主披甲上馬。
我走上前去,替他檢查了一下腹帶的鬆緊,又調整了鞍後的小扣。
「這裡再緊一點,」我低聲說,「這匹馬在起跑時會用力向前衝。」
他點了點頭,立刻照做。
當我們的目光短暫相遇時,我在他的眼中看見了一抹真誠的感激。
馬在欄內踏了一下蹄,似乎也感到一切準備就緒。
我退後一步,看著他牽起韁繩。
我跟著他走出馬棚,腳步在厚實的石板上發出低沉而規律的聲音。外頭的空氣比棚內清冷,夾雜著競技廣場尚未散盡的沙土氣味與馬匹的汗味。陽光從高牆之上斜斜灑下,照亮了馬棚前這片開闊的空地。
我的責任到此為止。
我會記住那匹馬的編號,記住借出時間,記住牠離開時的狀態。接下來,只需等待——等待他歸還馬匹,等待我再次檢查鞍具、鬆開腹帶、替馬刷去沙塵。這便是我在學院裡的位置,明確而有限。
男爵之子牽著馬往競技廣場的方向走去,背影筆直,步伐穩定。我本打算轉身返回馬棚,卻在下一刻停下了腳步。
空氣忽然變了。
我轉過頭。
深藍與金色的組合的一頂轎子正朝這裡行來。
轎身高挑,線條優雅,外層覆著深色織物,在日光下泛著柔和卻厚重的光澤。金線繡邊不張揚,卻細密得令人無法忽視。
四名強壯的男人抬著轎子,步伐一致,肩背筆直,肌肉在衣料下隱約隆起。他們的呼吸穩定,顯示這重量對他們而言並非負擔。轎子後方,還跟著另外四名同樣強壯的男人,目光警惕,視線不斷掃過周圍,站位嚴密,形成一個無形的保護圈。
不用看轎子上的紋章。
其實,轎子上甚至沒有刻意展示紋章。
光是那配色,那材質,那種不需要宣告、卻自然而然讓人低頭的奢華,就已經足夠了。
而僕人之間早已私下傳開,轎子的主人正是:
帝國之內,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克萊蒙公爵的長女,剛剛入學不久的——
瑪德琳大小姐。
我的身體比思緒更快作出反應。
我立刻雙膝跪下,膝蓋貼上冰冷的石地,頭顱微微垂下,視線落在自己粗糙的手背上。這不是被命令的動作,而是一種早已刻進骨子裡的判斷。
我是學院的僕人,不是她的奴隸。
理論上,我只需行學院規定的禮節。但在現實中,沒有人希望得罪克萊蒙公國。那是一個能讓規矩變得柔軟、甚至改變方向的存在。姿態放得低一點,總是更安全。
我感覺得到周圍的空氣靜了下來。
而在我身旁,男爵之子顯然愣住了。
他牽著馬,站在原地,整個人像被定住了一樣。他的目光在轎子與我之間來回游移,臉上浮現出短暫而真實的困惑——他不知道該不該跪,不知道該退到哪裡,也不知道自己此刻是否已經站在了不該站的位置。
他不是沒聽過這個名字。
正因為聽過,才更加不知所措。
轎子緩緩停下。
抬轎的男人同時止步,沒有一絲多餘的晃動。
男爵之子
我緊緊牽著韁繩,手心卻不受控制地開始冒汗。
粗糙的皮革被汗水浸得微微發滑,我下意識地重新調整握法,指節因用力而發白。那匹馬似乎感覺到了我的緊張,低低地噴了一口氣,前蹄在石地上輕輕挪動了一下。我卻沒有心思去安撫牠,所有的注意力都被眼前的景象牢牢攫住。
我不知道該走,還是該留。
向前一步,像是對那頂轎子的不敬;退後一步,又彷彿是在承認自己的怯懦。學院教過禮儀,父親也反覆叮囑過,但從來沒有人教過我,當這種情況突然出現在你面前時,該怎麼做。
就在我猶豫的瞬間,一旁傳來了細微卻清晰的動靜。
一旁的馬夫幾乎是出於本能地跪了下去。
膝蓋撞上石地的聲音並不大,卻像一記重錘砸在我的神經上。我猛地一顫,心臟驟然收緊。那一刻,我甚至差點跟著跪下去,身體已經做出了反應,理智卻在最後一瞬間拉住了我。
不行。
我是貴族。
即便只是男爵之子,即便在這座學院裡微不足道,我依然是貴族。父親的臉在我腦海中一閃而過——那張總是嚴肅、帶著疲憊,卻從不在外人面前低頭的臉。
「站直。」
他曾這樣對我說過。
「你可以貧窮,可以弱小,但不能自己先跪下。」
我深吸了一口氣,硬生生把那股想要低頭的衝動壓了回去,挺直了背脊。韁繩依舊在我手中,我沒有放開,也沒有後退。
我站著。
目光卻忍不住投向那八名壯漢。
抬轎的四人,與隨行的四人,站位嚴密而克制。他們的體型高大,肩背寬闊,站立時重心穩得驚人。那不是單純的力氣,而是長年訓練後留下的痕跡。我看得出來——他們不是臨時挑來的僕役,而是真正上過戰場的人。
他們的眼神太冷靜了。
那種冷靜,不是因為驕傲,而是因為見過死亡。視線掃過周圍時,沒有多餘的情緒,只有警戒與判斷。他們的手臂微微繃緊,彷彿只要一個信號,就能瞬間轉為殺戮的姿態。
為什麼?
這個問題在我腦中轟然炸開。
為什麼這樣的人,會被用來抬轎子?
這樣的戰士,本該站在戰場最前線,披甲持槍,為領主衝鋒陷陣。而不是此刻,肩負著一頂精緻華貴的轎子,步伐穩定得像是在護送某種不可觸碰的聖物。
一個念頭不受控制地浮現——
不是他們被貶低了。
而是轎子裡的人,重要到必須由這樣的人來守護。
就在這時,一段零碎的記憶忽然浮現。
那是幾天前的夜晚,寢室裡燈火昏暗。我躺在床上,聽著住在我上鋪的那名子爵之子隨口閒聊。他總是知道些內部消息,語氣輕描淡寫,彷彿那些話題與他無關。
「聽說這次入學的不簡單。」
他翻了個身,木床發出輕微的聲響。
「有兩名公爵之女,還有一名皇室的公主。」
當時我只是含糊地應了一聲,並沒有真正理解那句話的重量。
而現在,我懂了。
我的目光再次落回那頂轎子上。
布簾依舊垂著,裡頭的人尚未現身,卻已經讓整個空間的秩序重新排列。我站在原地,心跳劇烈,喉嚨發乾。
不知為何,我忽然確信——
那是克萊蒙公國的轎子。
而裡面坐著的,正是她。
壯漢們同時放慢了呼吸。
不是因為吃力,而是因為克制。
他們輕輕放下轎子,動作極其精準,四個支點幾乎在同一瞬間觸地,沒有一絲晃動。轎身穩穩落下,轎簾連一絲波紋都沒有晃起。
隨行的四名壯漢立刻調整站位,微不可察地向外展開,形成一道更嚴密的屏障。他們的目光低垂卻不鬆懈,視線角度恰好能涵蓋整個空間,任何接近的可能性都會被提前截斷。
接著,其中一人毫不猶豫地向前一步。
他單膝落地,然後是另一膝,整個人俯伏下來,背脊挺直,肩線穩固,姿態低得毫無保留。動作簡單、乾脆,沒有一絲遲疑,彷彿這個姿勢早已演練過無數次。
他的用途清楚得令人心悸。
那不足五十釐米的高度差,被他用身體填補得分毫不差。
一名侍女走上前來。
她的步伐輕而穩,衣料在行走間幾乎沒有發出聲響。她停在轎側,伸出手,動作恰到好處地揭開轎簾的一角。布料被掀起的瞬間,光線像是被引導般流入轎內,卻仍然看不清裡面的全貌。
先出現的,是一隻手。
潔白得近乎不真實的小手,指節纖細,皮膚在日光下泛著柔和的光澤。那隻手搭在侍女的手上,動作從容,沒有一絲急促,彷彿外界的一切都理所當然地在等待她。
然後,是鞋。
一隻絲綢高跟鞋從轎內探出來,鞋面細緻,線條優雅,鞋尖微微上翹,毫不猶豫地踏向那名壯漢的背。
就在那一瞬間,我清楚地看見了。
壯漢的表情極其短暫地扭曲了一下。
但他沒有動。
一分一毫都沒有。
他的背脊依舊穩定,肩膀沒有下沉,整個人像一塊被鑿進地面的岩石。
另外一隻小腳也隨之踏了上去。
兩條細長的鞋跟在他厚實的肌肉上留下了明顯的受力點。重量被集中在極小的皮膚面積上,任何人都能明白,那一定很痛。但壯漢的背脊,依舊如同被打磨過的石板,穩固而筆直。他不能晃動,不能讓背上那雙腳失去平衡,不能讓她的步伐有任何不完美。然而,少女似乎對男人的忍耐毫無察覺。只是穩穩地,自然地踩在上面。
白色長襪包裹的小腿,筆直而纖細,還不如她腳下的男人的手臂粗。
男人的肩背卻足以承受戰場上的任何衝撞,可此刻,強大的身體只是被用來承接那脆弱的雙腳。
纖細與強壯、柔軟與堅硬、被保護的一方與被消耗的一方。
我不由得嚥了口唾沫,忽然意識到,自己正在目睹的,不過是某位大小姐下轎的瞬間。
露西婭
我握著那隻纖細而白皙的小手。
她的手很小,觸感柔軟而溫暖,體溫透過薄薄的手套傳來,像一塊被日光曬過的玉石。她的手指很細,關節圓潤,皮膚光滑得感覺不到任何粗糙。這樣的手,彷彿只適合拿扇子、拿書卷,或在茶盞邊緣輕輕停留——輕輕一捏,就像會碎掉似的。
她的腳也是如此。
那雙包裹在白色長襪裡的小腳線條乾淨而秀氣,腳踝纖細,幾乎只與我的手腕同寬。
絲綢高跟鞋精緻而小巧,線條優美,鞋面被打理得一塵不染,鞋尖與鞋跟都顯得精緻而無害。對貴族們而言,瑪德琳小姐永遠是那最可愛,最美麗的存在——她的每一個細節都像被專門設計過,只為呈現她的優雅與光彩。
只是這樣的美麗,正理所當然地落在一具粗壯的身體之上。
鞋跟深深嵌進肌肉,帶著一種冷靜而殘酷的美感,牢牢釘在他的肋骨上。
這是一種沒有猶豫,沒有遲疑,毫無自覺的自然行為。
她只是踩上去,就像踩上一個為她準備好的台階。
至於腳下的人,是否會疼痛,她從未思考過。
被她踩在腳下的人,看著她的人,所感受到的,從來完全是兩回事。
這讓我忽然想起了另一個人。
雷蒙。
那個對她近乎盲目崇拜的奴隸,在過去曾不只一次,用極低的聲音、極謹慎的語氣,請求我為她準備「鞋跟稍微溫和一些」的鞋子
他的赤裸的身上,總是留著各種顏色的痕跡——深色的、暗紅的、泛紫的印記,有些已經淡去,有些仍然清晰。那些印跡,它們和小姐的鞋子鞋跟形狀高度一致。這些印跡被反覆書寫,無聲地訴說著什麼。
馬夫
清晨的霧氣尚未從競技廣場的石板間退去時,我已經站在馬棚門口了。
我是學院的馬夫之一,名不見經傳,卻每日與這些比人更被珍視的生靈為伍。對我而言,這座馬棚不只是存放馬匹的地方,它是一座無聲卻殘酷的階級圖鑑——用木欄、鐵環與皮革,將貴族世界的秩序一寸寸釘死在空氣裡。
馬棚緊貼著競技廣場的東側。高牆之外,是為人車競賽與馬上對抗所準備的沙地;高牆之內,則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每當廣場上響起號角與喝彩,馬棚裡的馬便會不安地踏蹄、噴氣,牠們早已習慣那種聲音,知道那意味著奔跑、榮耀,或受傷。
整座馬棚以灰白色石材築成,屋頂高聳,木樑粗壯,足以承受積雪與時間。入口上方懸掛著學院的徽章,金屬早已被歲月磨得黯淡,卻仍然高高在上。進門後,是一條筆直而寬闊的主通道,地面鋪著厚厚的沙與碎草,用來吸水、防滑,也掩蓋氣味。
馬棚是分區的,而且分得極其清楚。
最靠近競技廣場的一側,是公爵家與王室專用的區域。那裡的馬欄更高、更寬,木材經過細緻打磨,邊角包覆著黃銅。每一匹馬都有自己的名牌,刻著家徽與正式的馬名,字跡深而清晰。我每日為牠們刷毛時,都得格外小心,哪怕一根刷毛卡住了金屬釦環,都可能引來上頭的責難。
那些馬與其說是牲畜,不如說是移動的權力。牠們的毛色被精心挑選,步態受過嚴格訓練,安靜而冷漠,像極了牠們的主人。王室的馬尤其如此,即便站在欄內,也昂首挺胸,彷彿隨時準備踏上競技場,接受眾人的注視。
緊鄰其後的,是伯爵們的區域。
那裡明顯狹窄許多。欄位少、間距小,裝飾也簡化成實用為主。我常聽見伯爵家隨從低聲抱怨,說學院偏心,說空間不公。
伯爵的馬多半不差,只是缺乏那種被精心「塑造」的氣勢。牠們更躁動些,也更容易親近。每當我為牠們整理馬蹄時,總能感覺到牠們對競技場的渴望——牠們知道自己有資格奔跑,卻被擠在角落。
至於低階貴族?
他們幾乎沒有位置。
在馬棚最深處,有幾個沒有家徽、沒有名牌的欄位,那裡拴著的是學院的公共馬匹。這些馬平日由我們照料,用於課程、訓練,或在「緊急情況」下借給那些無馬可用的低階貴族。它們的裝備統一、陳舊,皮革早已被無數雙手磨得發亮,卻看不出原本的顏色。
我見過低階貴族站在欄外,手指緊抓木欄,目光複雜地望著那些馬。他們不敢多說一句話,只能在被允許時,迅速牽走一匹,然後在用完後默默歸還。沒有榮耀,沒有歸屬,只有短暫的借用。
馬棚的一側連著馬具倉庫。那是一個比馬棚本身更安靜的地方。
厚重的木門後,是整齊排列的馬鞍、韁繩、護具與披毯。王室與公爵家的裝備被單獨鎖在內側的櫃中,皮革柔軟,金屬拋光,聞起來甚至帶著淡淡的油香。伯爵們的器具掛在外圈,保養得當卻少了那份奢華。至於公共馬具,則集中在最外側,隨取隨用,卻也最容易磨損。
我每日清點這些物件時,總會不自覺地放輕動作。馬具不會說話,但它們承載的,是主人的身份與野心。哪一副馬鞍被放在內層,哪一條韁繩被掛在最外,早已不是偶然。
到了午後,競技廣場的聲音會變得清晰。鐵蹄敲擊石板,觀眾的喝采,教官的命令,混合成一股震動,順著牆壁傳進馬棚。馬開始躁動,我則一一安撫,低聲說話,撫摸牠們的頸側。
在這裡,馬比人誠實。牠們不懂爵位,只懂欄位的大小、刷毛的次數、能否踏上沙地奔跑。
而我,只是一個看守秩序的人。每日在這座貴族公用的馬棚裡,替權力刷毛,替階級添草,看著榮耀與不甘,在一排排木欄之間靜靜站立。
他踏進馬棚時,我其實就已經注意到他了。
不是因為他張揚——恰恰相反,是因為那份刻意的克制。衣著整潔,卻沒有多餘的裝飾;靴子擦得乾淨,但皮革的折痕顯示它被反覆修補過。披風的邊角縫線細密,卻用的是耐磨而廉價的線材。那是一種我太熟悉的打扮:努力維持體面,卻無法掩飾資源的邊界。
我在心中做出判斷——男爵之子,或許還不是繼承人。
他走到我面前,沒有多說話,只是雙手遞上一張折得整齊的羊皮紙。那動作小心翼翼,像是生怕紙張本身比他更有地位。我接過來,指尖觸到略微粗糙的纖維,展開查看。
是學院的既定格式。
上方是標準化的抬頭與條款,文字端正,墨跡未乾透的地方已被細心地吹過。中段寫著申請理由——措辭謙遜而冗長,顯然是反覆推敲後才敢落筆。借用的馬匹編號標註得清楚,屬於公共馬匹序列中較為穩定的一匹,不是最老,也不是最好的。最下方,學院的印章壓得極深,紅蠟完整,邊緣沒有一絲裂痕。
我檢查了印章的紋路,又對照了一旁的登記冊,確認編號與許可無誤。
「請跟我來。」我把羊皮紙收好,語氣平靜而公事公辦。
他點了點頭,動作略顯僵硬,跟在我身後。
我們穿過馬棚的主通道,經過公爵家與王室的欄位時,他的目光不自覺地向那一側飄去。我沒有停下,只是帶著他轉入連接馬具倉庫的小門。那裡的光線昏暗些,空氣中多了皮革與油脂的味道。
倉庫內部井然有序。
前排掛著公爵與王室專屬的馬具,金屬扣環在火把下泛著溫潤的光,皮革表面幾乎沒有使用痕跡。再往裡,是伯爵們的裝備,保養得當,卻已留下時間的印記。
我一直走到最後一排。
那裡的架子簡單而實用,沒有家徽,沒有個人標記,只有統一的學院印跡。我伸手取下一副馬鞍,檢查了一下縫線與扣具,確保它仍然牢靠。
就在這時,我發現他沒有跟上。
我轉過身,看見他停在倉庫門口,整個人像被釘在原地。
他的目光越過我,越過架子,落在馬棚另一側——那裡停放著一輛嶄新的戰車。
那是克萊蒙公爵家的戰車。
即便隔著距離,它依舊耀眼得令人無法忽視。車身線條流暢而低伏,木材經過精細打磨,表面覆著深色漆層,隱約映出周圍的光影。金屬框架不是冰冷的鐵,而是經過拋光的合金,邊緣刻著細密的紋飾。輪輻纖細卻結實,排列角度精準,顯然是為高速與穩定而設計。
戰車旁的馬具同樣奢華,韁繩與護具整齊地掛在專用支架上,每一件都與車身風格一致,彷彿本就屬於同一個完整的藝術品。
那是克萊蒙家大小姐在人車競賽中使用的戰車。
昨天夜裡,它才被送進來。那時馬棚已經安靜下來,只有我們幾個馬夫在場。我還記得那扇門被推開時的聲音,以及菲利普大管家親自指揮人手搬運的場面。他的動作一如既往地從容,語氣不高,卻沒有任何人敢怠慢。
那不是一件單純的競技器具,那是一種宣告。
而現在,這名男爵家的孩子正站在原地,呆呆地望著它。
他的眼神裡沒有嫉妒,也沒有不滿,只有純粹的震撼與茫然。那是一種第一次直視差距時才會出現的神情——彷彿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明白自己站在這座學院的哪一層。
我沒有催促。
只是稍稍放低聲音,像是怕驚動什麼似的,輕聲提醒道:
「那是克萊蒙小姐的戰車。」
他猛地回過神來,迅速收回視線,臉上浮現一絲慌亂與羞愧,連忙向我走來。那份短暫的失神被他努力掩埋,但我已經看見了。
我把馬鞍遞到他手中。
學院印跡在皮革上清晰可見,沉穩而冰冷。
在這座馬棚裡,奢華與現實只隔著幾步距離。而有些人,一生都只能站在最後一排,遠遠地看上一眼。
他雙手接過那副帶著學院印記的馬鞍,動作比剛才明顯沉穩了許多。那不是因為放鬆,而是一種被迫的自制——像是把剛剛那一瞬間的失神與憧憬,一起鎖進了胸腔深處。他沒有再看那輛戰車一眼,轉身便朝著公共馬匹的欄位走去,靴子踏在馬棚鋪滿乾草與沙粒的地面上,聲音輕而規律。
那是一匹棕色的學院用馬,毛色不算出眾,卻肌肉結實,眼神溫順而警覺。它抬起頭嗅了嗅空氣,似乎早已習慣了這樣的更換騎手。男爵之子走到牠身側,先是輕輕撫摸了一下馬頸,像是在向一位老朋友致意,接著便熟練地將馬鞍搭上馬背。
他的動作讓我不由得多看了他幾眼。
那不是那種靠模仿學來的笨拙,而是真正經年累月訓練留下的節奏感。他調整鞍墊的位置,確保不會壓到馬的肩胛;拉緊腹帶時,他用的是恰到好處的力道,既穩固又不讓馬感到不適。水勒被他一一扣好,皮帶順著馬頭的輪廓貼合,沒有多餘的扭曲。
和那些高階貴族的子女不同。
那些人往往帶著一整隊侍從與馬夫,自己只是站在一旁,讓別人為他們處理一切。他們或許懂得如何騎在馬背上保持優雅,卻未必知道一條韁繩若扣錯一孔,在競技場上會意味著什麼。
而這個男爵家的孩子不一樣。
他從小被教育要自己完成這些事。不是為了展示風度,而是因為在他的世界裡,馬不是裝飾,而是戰場上生死相依的夥伴。每一個扣環、每一條皮帶,都是為了在戰場上活下來,為了隨時能為領主披甲上馬。
我走上前去,替他檢查了一下腹帶的鬆緊,又調整了鞍後的小扣。
「這裡再緊一點,」我低聲說,「這匹馬在起跑時會用力向前衝。」
他點了點頭,立刻照做。
當我們的目光短暫相遇時,我在他的眼中看見了一抹真誠的感激。
馬在欄內踏了一下蹄,似乎也感到一切準備就緒。
我退後一步,看著他牽起韁繩。
我跟著他走出馬棚,腳步在厚實的石板上發出低沉而規律的聲音。外頭的空氣比棚內清冷,夾雜著競技廣場尚未散盡的沙土氣味與馬匹的汗味。陽光從高牆之上斜斜灑下,照亮了馬棚前這片開闊的空地。
我的責任到此為止。
我會記住那匹馬的編號,記住借出時間,記住牠離開時的狀態。接下來,只需等待——等待他歸還馬匹,等待我再次檢查鞍具、鬆開腹帶、替馬刷去沙塵。這便是我在學院裡的位置,明確而有限。
男爵之子牽著馬往競技廣場的方向走去,背影筆直,步伐穩定。我本打算轉身返回馬棚,卻在下一刻停下了腳步。
空氣忽然變了。
我轉過頭。
深藍與金色的組合的一頂轎子正朝這裡行來。
轎身高挑,線條優雅,外層覆著深色織物,在日光下泛著柔和卻厚重的光澤。金線繡邊不張揚,卻細密得令人無法忽視。
四名強壯的男人抬著轎子,步伐一致,肩背筆直,肌肉在衣料下隱約隆起。他們的呼吸穩定,顯示這重量對他們而言並非負擔。轎子後方,還跟著另外四名同樣強壯的男人,目光警惕,視線不斷掃過周圍,站位嚴密,形成一個無形的保護圈。
不用看轎子上的紋章。
其實,轎子上甚至沒有刻意展示紋章。
光是那配色,那材質,那種不需要宣告、卻自然而然讓人低頭的奢華,就已經足夠了。
而僕人之間早已私下傳開,轎子的主人正是:
帝國之內,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克萊蒙公爵的長女,剛剛入學不久的——
瑪德琳大小姐。
我的身體比思緒更快作出反應。
我立刻雙膝跪下,膝蓋貼上冰冷的石地,頭顱微微垂下,視線落在自己粗糙的手背上。這不是被命令的動作,而是一種早已刻進骨子裡的判斷。
我是學院的僕人,不是她的奴隸。
理論上,我只需行學院規定的禮節。但在現實中,沒有人希望得罪克萊蒙公國。那是一個能讓規矩變得柔軟、甚至改變方向的存在。姿態放得低一點,總是更安全。
我感覺得到周圍的空氣靜了下來。
而在我身旁,男爵之子顯然愣住了。
他牽著馬,站在原地,整個人像被定住了一樣。他的目光在轎子與我之間來回游移,臉上浮現出短暫而真實的困惑——他不知道該不該跪,不知道該退到哪裡,也不知道自己此刻是否已經站在了不該站的位置。
他不是沒聽過這個名字。
正因為聽過,才更加不知所措。
轎子緩緩停下。
抬轎的男人同時止步,沒有一絲多餘的晃動。
男爵之子
我緊緊牽著韁繩,手心卻不受控制地開始冒汗。
粗糙的皮革被汗水浸得微微發滑,我下意識地重新調整握法,指節因用力而發白。那匹馬似乎感覺到了我的緊張,低低地噴了一口氣,前蹄在石地上輕輕挪動了一下。我卻沒有心思去安撫牠,所有的注意力都被眼前的景象牢牢攫住。
我不知道該走,還是該留。
向前一步,像是對那頂轎子的不敬;退後一步,又彷彿是在承認自己的怯懦。學院教過禮儀,父親也反覆叮囑過,但從來沒有人教過我,當這種情況突然出現在你面前時,該怎麼做。
就在我猶豫的瞬間,一旁傳來了細微卻清晰的動靜。
一旁的馬夫幾乎是出於本能地跪了下去。
膝蓋撞上石地的聲音並不大,卻像一記重錘砸在我的神經上。我猛地一顫,心臟驟然收緊。那一刻,我甚至差點跟著跪下去,身體已經做出了反應,理智卻在最後一瞬間拉住了我。
不行。
我是貴族。
即便只是男爵之子,即便在這座學院裡微不足道,我依然是貴族。父親的臉在我腦海中一閃而過——那張總是嚴肅、帶著疲憊,卻從不在外人面前低頭的臉。
「站直。」
他曾這樣對我說過。
「你可以貧窮,可以弱小,但不能自己先跪下。」
我深吸了一口氣,硬生生把那股想要低頭的衝動壓了回去,挺直了背脊。韁繩依舊在我手中,我沒有放開,也沒有後退。
我站著。
目光卻忍不住投向那八名壯漢。
抬轎的四人,與隨行的四人,站位嚴密而克制。他們的體型高大,肩背寬闊,站立時重心穩得驚人。那不是單純的力氣,而是長年訓練後留下的痕跡。我看得出來——他們不是臨時挑來的僕役,而是真正上過戰場的人。
他們的眼神太冷靜了。
那種冷靜,不是因為驕傲,而是因為見過死亡。視線掃過周圍時,沒有多餘的情緒,只有警戒與判斷。他們的手臂微微繃緊,彷彿只要一個信號,就能瞬間轉為殺戮的姿態。
為什麼?
這個問題在我腦中轟然炸開。
為什麼這樣的人,會被用來抬轎子?
這樣的戰士,本該站在戰場最前線,披甲持槍,為領主衝鋒陷陣。而不是此刻,肩負著一頂精緻華貴的轎子,步伐穩定得像是在護送某種不可觸碰的聖物。
一個念頭不受控制地浮現——
不是他們被貶低了。
而是轎子裡的人,重要到必須由這樣的人來守護。
就在這時,一段零碎的記憶忽然浮現。
那是幾天前的夜晚,寢室裡燈火昏暗。我躺在床上,聽著住在我上鋪的那名子爵之子隨口閒聊。他總是知道些內部消息,語氣輕描淡寫,彷彿那些話題與他無關。
「聽說這次入學的不簡單。」
他翻了個身,木床發出輕微的聲響。
「有兩名公爵之女,還有一名皇室的公主。」
當時我只是含糊地應了一聲,並沒有真正理解那句話的重量。
而現在,我懂了。
我的目光再次落回那頂轎子上。
布簾依舊垂著,裡頭的人尚未現身,卻已經讓整個空間的秩序重新排列。我站在原地,心跳劇烈,喉嚨發乾。
不知為何,我忽然確信——
那是克萊蒙公國的轎子。
而裡面坐著的,正是她。
壯漢們同時放慢了呼吸。
不是因為吃力,而是因為克制。
他們輕輕放下轎子,動作極其精準,四個支點幾乎在同一瞬間觸地,沒有一絲晃動。轎身穩穩落下,轎簾連一絲波紋都沒有晃起。
隨行的四名壯漢立刻調整站位,微不可察地向外展開,形成一道更嚴密的屏障。他們的目光低垂卻不鬆懈,視線角度恰好能涵蓋整個空間,任何接近的可能性都會被提前截斷。
接著,其中一人毫不猶豫地向前一步。
他單膝落地,然後是另一膝,整個人俯伏下來,背脊挺直,肩線穩固,姿態低得毫無保留。動作簡單、乾脆,沒有一絲遲疑,彷彿這個姿勢早已演練過無數次。
他的用途清楚得令人心悸。
那不足五十釐米的高度差,被他用身體填補得分毫不差。
一名侍女走上前來。
她的步伐輕而穩,衣料在行走間幾乎沒有發出聲響。她停在轎側,伸出手,動作恰到好處地揭開轎簾的一角。布料被掀起的瞬間,光線像是被引導般流入轎內,卻仍然看不清裡面的全貌。
先出現的,是一隻手。
潔白得近乎不真實的小手,指節纖細,皮膚在日光下泛著柔和的光澤。那隻手搭在侍女的手上,動作從容,沒有一絲急促,彷彿外界的一切都理所當然地在等待她。
然後,是鞋。
一隻絲綢高跟鞋從轎內探出來,鞋面細緻,線條優雅,鞋尖微微上翹,毫不猶豫地踏向那名壯漢的背。
就在那一瞬間,我清楚地看見了。
壯漢的表情極其短暫地扭曲了一下。
但他沒有動。
一分一毫都沒有。
他的背脊依舊穩定,肩膀沒有下沉,整個人像一塊被鑿進地面的岩石。
另外一隻小腳也隨之踏了上去。
兩條細長的鞋跟在他厚實的肌肉上留下了明顯的受力點。重量被集中在極小的皮膚面積上,任何人都能明白,那一定很痛。但壯漢的背脊,依舊如同被打磨過的石板,穩固而筆直。他不能晃動,不能讓背上那雙腳失去平衡,不能讓她的步伐有任何不完美。然而,少女似乎對男人的忍耐毫無察覺。只是穩穩地,自然地踩在上面。
白色長襪包裹的小腿,筆直而纖細,還不如她腳下的男人的手臂粗。
男人的肩背卻足以承受戰場上的任何衝撞,可此刻,強大的身體只是被用來承接那脆弱的雙腳。
纖細與強壯、柔軟與堅硬、被保護的一方與被消耗的一方。
我不由得嚥了口唾沫,忽然意識到,自己正在目睹的,不過是某位大小姐下轎的瞬間。
露西婭
我握著那隻纖細而白皙的小手。
她的手很小,觸感柔軟而溫暖,體溫透過薄薄的手套傳來,像一塊被日光曬過的玉石。她的手指很細,關節圓潤,皮膚光滑得感覺不到任何粗糙。這樣的手,彷彿只適合拿扇子、拿書卷,或在茶盞邊緣輕輕停留——輕輕一捏,就像會碎掉似的。
她的腳也是如此。
那雙包裹在白色長襪裡的小腳線條乾淨而秀氣,腳踝纖細,幾乎只與我的手腕同寬。
絲綢高跟鞋精緻而小巧,線條優美,鞋面被打理得一塵不染,鞋尖與鞋跟都顯得精緻而無害。對貴族們而言,瑪德琳小姐永遠是那最可愛,最美麗的存在——她的每一個細節都像被專門設計過,只為呈現她的優雅與光彩。
只是這樣的美麗,正理所當然地落在一具粗壯的身體之上。
鞋跟深深嵌進肌肉,帶著一種冷靜而殘酷的美感,牢牢釘在他的肋骨上。
這是一種沒有猶豫,沒有遲疑,毫無自覺的自然行為。
她只是踩上去,就像踩上一個為她準備好的台階。
至於腳下的人,是否會疼痛,她從未思考過。
被她踩在腳下的人,看著她的人,所感受到的,從來完全是兩回事。
這讓我忽然想起了另一個人。
雷蒙。
那個對她近乎盲目崇拜的奴隸,在過去曾不只一次,用極低的聲音、極謹慎的語氣,請求我為她準備「鞋跟稍微溫和一些」的鞋子
他的赤裸的身上,總是留著各種顏色的痕跡——深色的、暗紅的、泛紫的印記,有些已經淡去,有些仍然清晰。那些印跡,它們和小姐的鞋子鞋跟形狀高度一致。這些印跡被反覆書寫,無聲地訴說著什麼。
顶大佬
维多利亚时期贵妇人都带着手套的吧,直接让人触碰到手是失贞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