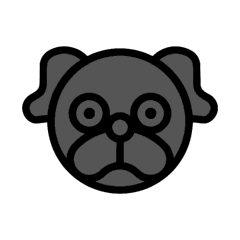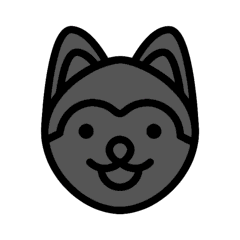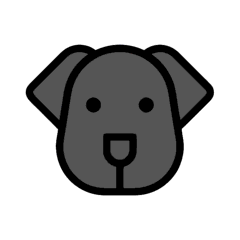贖罪與救贖---連載至四十集 七人留言直接更新七集!!!
连载中原创AI生成校园绿奴足控贞操锁舔鞋厕奴黄金阉割圣水情侣主
第二十九章:再見了我的驕傲
我拖著沉重的步伐,來到那家隱藏在城市邊緣的地下診所。推開生鏽的鐵門,一股潮濕的霉味混雜著消毒水和血腥氣撲鼻而來,瞬間讓我的胃一陣翻騰。診所內昏暗得像墳墓,只有幾盞搖曳的燈泡勉強照亮角落,牆壁上斑駿的油漆剝落得像老人臉上的皺紋,地板上散落著未乾的血跡,暗紅色的污點在微光下閃著不祥的光芒。中央擺著一張手術台,表面滿是鏽跡和乾涸的血漬,像一件刑具,散發著無數人在此痛苦掙扎的陰森氣息。我的目光掃過台面上的劃痕和凹陷,彷彿能聽到那些無聲的哀嚎。想到不久後我也要躺在那上面,切除下體,內心像被無形的手攫住,緊張和恐懼如狂潮湧來。
我找到密醫,一個身形瘦削的中年男人,臉色蒼白得像從未見過陽光,眼窩深陷,眼神冷漠而銳利,像在審視一件待處理的物件。他的嘴角掛著一抹不易察覺的冷笑,稀疏的頭髮油膩地貼在頭皮上,手上戴著一雙泛黃的橡膠手套,散發著刺鼻的化學氣味。我脫下所有衣物,赤裸地站在他面前,胸口的「奴」字烙印在昏暗燈光下格外刺眼,結痂處隱隱作痛,貞操鎖冰冷地勒在下體,沉甸甸地提醒著我的身份。密醫的目光掃過我的身體,卻毫無波瀾,彷彿這般景象對他而言早已司空見慣。他低聲說:「來這做這種手術的,多半是奴隸身份,沒錢的人才會選這地方。你這鎖…如果不開,就得全部切除,包括那根。」
我心頭一震,本想只切除下體的蛋蛋,保留其他部分,可麥語心不在,沒人能幫我開鎖。她的命令像鐵錮勒緊我的靈魂——必須在她回國前完成手術。時間的壓力、對手術的恐懼、還有對自己身份的羞恥,像漩渦將我拖進深淵。我咬緊牙,聲音顫抖:「好…我同意。」心裡卻像被刀割,反正我早已是個廢人,有沒有那東西,又有什麼區別?密醫點點頭,遞給我一張泛黃的同意書,上面寫著「自願接受下體腫瘤全切手術,後果自負」。我顫抖著簽下名字,每一筆都像在割自己的心。
他指了指手術台,語氣冷漠:「上去,大字型躺好。」我爬上冰冷的手術台,鏽跡和血漬刺痛皮膚,四肢被粗糙的皮帶綁成大字型,勒得手腕和腳踝生疼。手術台的凹陷和劃痕像在低語,訴說著無數人的痛苦。我閉上眼,試著平復呼吸,可羞辱感和恐懼卻如巨浪拍打心頭。等待的每一秒都像刀子在割,腦海裡閃過麥語心的冷笑、王嘉嘉的嘲弄,還有那即將到來的劇痛。我低聲懺悔:「主人…賤奴會完成您的命令…」卻無人回應,只有密醫整理器械的叮噹聲,在這陰森的空間裡迴盪。
我顫抖著請求密醫:「在開始前…幫我拍張照片,發給我主人。」他冷冷地點頭,拿起一隻老舊的手機,拍下我赤裸地綁在手術台上的模樣,胸口的「奴」字和下體的貞操鎖在照片中格外刺眼。我低聲口述訊息:「主人,賤奴已執行您的命令,即將移除您看不順眼的腫瘤。」密醫發送後,將手機扔在一旁,開始準備手術。他的動作機械而熟練,卻毫無溫情,像在處理一塊無生命的肉。
手術台旁,一盤骯髒的金屬器械閃著冷光,刀刃上殞留著暗紅的血跡,散發著濃烈的鐵鏽味。密醫拿起一瓶泛黃的消毒液,潑在我的下體,刺骨的冰冷讓我全身一顫,隨即是火辣辣的灼痛。他沒有麻醉,僅用一塊破布塞進我的嘴,語氣冷漠:「咬緊,別叫太大聲。」我瞪大眼睛,恐懼如鐵爪扼住喉嚨,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手術刀在燈光下閃過一抹寒光,密醫的手穩得可怕,刀尖對準我的下體,毫不猶豫地切下。
劇痛如閃電竄過全身,像一把燒紅的刀從下體撕裂到腦海。我咬緊破布,發出低悶的嘶吼,鮮血噴湧而出,濺在手術台上,溫熱的液體順著大腿流下,染紅了鏽跡斑駁的台面。密醫毫不停頓,刀刃繼續切割,腫瘤連同周圍組織被一塊塊剝離,每一下都像在撕裂我的靈魂。貞操鎖的金屬碰撞聲混雜著刀切肉的細微聲響,血腥味和消毒水的氣味充斥鼻腔,讓我幾乎窒息。我試著掙扎,皮帶卻勒得更緊,手腕和腳踝磨出血痕。疼痛吞噬了我的意識,眼前一片模糊,只剩無邊的黑暗和羞辱。
不知過了多久,密醫終於停下,隨手用一塊髒布擦去刀上的血跡,語氣平淡:「好了,沒死就算你命大。」我癱在手術台上,鮮血還在緩慢滲出,下體傳來的空虛感和劇痛像潮水,將我拖進更深的絕望。胸口的「奴」字烙印隱隱作痛,像在嘲笑我的墮落。我試著喘息,卻只感到無盡的悲痛和羞辱。曾經的我,還有夢想、還有尊嚴,可如今,我只是一個連完整身體都不配擁有的殞物。麥語心的命令完成了,可這代價卻將我徹底推入無底深淵。我閉上眼,淚水混著汗水滑落,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條狗命,早已不屬於自己。
我拖著沉重的步伐,來到那家隱藏在城市邊緣的地下診所。推開生鏽的鐵門,一股潮濕的霉味混雜著消毒水和血腥氣撲鼻而來,瞬間讓我的胃一陣翻騰。診所內昏暗得像墳墓,只有幾盞搖曳的燈泡勉強照亮角落,牆壁上斑駿的油漆剝落得像老人臉上的皺紋,地板上散落著未乾的血跡,暗紅色的污點在微光下閃著不祥的光芒。中央擺著一張手術台,表面滿是鏽跡和乾涸的血漬,像一件刑具,散發著無數人在此痛苦掙扎的陰森氣息。我的目光掃過台面上的劃痕和凹陷,彷彿能聽到那些無聲的哀嚎。想到不久後我也要躺在那上面,切除下體,內心像被無形的手攫住,緊張和恐懼如狂潮湧來。
我找到密醫,一個身形瘦削的中年男人,臉色蒼白得像從未見過陽光,眼窩深陷,眼神冷漠而銳利,像在審視一件待處理的物件。他的嘴角掛著一抹不易察覺的冷笑,稀疏的頭髮油膩地貼在頭皮上,手上戴著一雙泛黃的橡膠手套,散發著刺鼻的化學氣味。我脫下所有衣物,赤裸地站在他面前,胸口的「奴」字烙印在昏暗燈光下格外刺眼,結痂處隱隱作痛,貞操鎖冰冷地勒在下體,沉甸甸地提醒著我的身份。密醫的目光掃過我的身體,卻毫無波瀾,彷彿這般景象對他而言早已司空見慣。他低聲說:「來這做這種手術的,多半是奴隸身份,沒錢的人才會選這地方。你這鎖…如果不開,就得全部切除,包括那根。」
我心頭一震,本想只切除下體的蛋蛋,保留其他部分,可麥語心不在,沒人能幫我開鎖。她的命令像鐵錮勒緊我的靈魂——必須在她回國前完成手術。時間的壓力、對手術的恐懼、還有對自己身份的羞恥,像漩渦將我拖進深淵。我咬緊牙,聲音顫抖:「好…我同意。」心裡卻像被刀割,反正我早已是個廢人,有沒有那東西,又有什麼區別?密醫點點頭,遞給我一張泛黃的同意書,上面寫著「自願接受下體腫瘤全切手術,後果自負」。我顫抖著簽下名字,每一筆都像在割自己的心。
他指了指手術台,語氣冷漠:「上去,大字型躺好。」我爬上冰冷的手術台,鏽跡和血漬刺痛皮膚,四肢被粗糙的皮帶綁成大字型,勒得手腕和腳踝生疼。手術台的凹陷和劃痕像在低語,訴說著無數人的痛苦。我閉上眼,試著平復呼吸,可羞辱感和恐懼卻如巨浪拍打心頭。等待的每一秒都像刀子在割,腦海裡閃過麥語心的冷笑、王嘉嘉的嘲弄,還有那即將到來的劇痛。我低聲懺悔:「主人…賤奴會完成您的命令…」卻無人回應,只有密醫整理器械的叮噹聲,在這陰森的空間裡迴盪。
我顫抖著請求密醫:「在開始前…幫我拍張照片,發給我主人。」他冷冷地點頭,拿起一隻老舊的手機,拍下我赤裸地綁在手術台上的模樣,胸口的「奴」字和下體的貞操鎖在照片中格外刺眼。我低聲口述訊息:「主人,賤奴已執行您的命令,即將移除您看不順眼的腫瘤。」密醫發送後,將手機扔在一旁,開始準備手術。他的動作機械而熟練,卻毫無溫情,像在處理一塊無生命的肉。
手術台旁,一盤骯髒的金屬器械閃著冷光,刀刃上殞留著暗紅的血跡,散發著濃烈的鐵鏽味。密醫拿起一瓶泛黃的消毒液,潑在我的下體,刺骨的冰冷讓我全身一顫,隨即是火辣辣的灼痛。他沒有麻醉,僅用一塊破布塞進我的嘴,語氣冷漠:「咬緊,別叫太大聲。」我瞪大眼睛,恐懼如鐵爪扼住喉嚨,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手術刀在燈光下閃過一抹寒光,密醫的手穩得可怕,刀尖對準我的下體,毫不猶豫地切下。
劇痛如閃電竄過全身,像一把燒紅的刀從下體撕裂到腦海。我咬緊破布,發出低悶的嘶吼,鮮血噴湧而出,濺在手術台上,溫熱的液體順著大腿流下,染紅了鏽跡斑駁的台面。密醫毫不停頓,刀刃繼續切割,腫瘤連同周圍組織被一塊塊剝離,每一下都像在撕裂我的靈魂。貞操鎖的金屬碰撞聲混雜著刀切肉的細微聲響,血腥味和消毒水的氣味充斥鼻腔,讓我幾乎窒息。我試著掙扎,皮帶卻勒得更緊,手腕和腳踝磨出血痕。疼痛吞噬了我的意識,眼前一片模糊,只剩無邊的黑暗和羞辱。
不知過了多久,密醫終於停下,隨手用一塊髒布擦去刀上的血跡,語氣平淡:「好了,沒死就算你命大。」我癱在手術台上,鮮血還在緩慢滲出,下體傳來的空虛感和劇痛像潮水,將我拖進更深的絕望。胸口的「奴」字烙印隱隱作痛,像在嘲笑我的墮落。我試著喘息,卻只感到無盡的悲痛和羞辱。曾經的我,還有夢想、還有尊嚴,可如今,我只是一個連完整身體都不配擁有的殞物。麥語心的命令完成了,可這代價卻將我徹底推入無底深淵。我閉上眼,淚水混著汗水滑落,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條狗命,早已不屬於自己。
cpy112233:↑第二十九章:再見了我的驕傲是不是有两段重复了
我拖著沉重的步伐,來到那家隱藏在城市邊緣的地下診所。推開生鏽的鐵門,一股潮濕的霉味混雜著消毒水和血腥氣撲鼻而來,瞬間讓我的胃一陣翻騰。診所內昏暗得像墳墓,只有幾盞搖曳的燈泡勉強照亮角落,牆壁上斑駿的油漆剝落得像老人臉上的皺紋,地板上散落著未乾的血跡,暗紅色的污點在微光下閃著不祥的光芒。中央擺著一張手術台,表面滿是鏽跡和乾涸的血漬,像一件刑具,散發著無數人在此痛苦掙扎的陰森氣息。我的目光掃過台面上的劃痕和凹陷,彷彿能聽到那些無聲的哀嚎。想到不久後我也要躺在那上面,切除下體,內心像被無形的手攫住,緊張和恐懼如狂潮湧來。
我找到密醫,一個身形瘦削的中年男人,臉色蒼白得像從未見過陽光,眼窩深陷,眼神冷漠而銳利,像在審視一件待處理的物件。他的嘴角掛著一抹不易察覺的冷笑,稀疏的頭髮油膩地貼在頭皮上,手上戴著一雙泛黃的橡膠手套,散發著刺鼻的化學氣味。我脫下所有衣物,赤裸地站在他面前,胸口的「奴」字烙印在昏暗燈光下格外刺眼,結痂處隱隱作痛,貞操鎖冰冷地勒在下體,沉甸甸地提醒著我的身份。密醫的目光掃過我的身體,卻毫無波瀾,彷彿這般景象對他而言早已司空見慣。他低聲說:「來這做這種手術的,多半是奴隸身份,沒錢的人才會選這地方。你這鎖…如果不開,就得全部切除,包括那根。」
我心頭一震,本想只切除下體的蛋蛋,保留男根部分,可麥語心不在,沒人能幫我開鎖。她的命令像鐵錮勒緊我的靈魂——必須在她回國前完成手術。時間的壓力、對手術的恐懼、還有對自己身份的羞恥,像漩渦將我拖進深淵。我咬緊牙,聲音顫抖:「好…我同意。」心裡卻像被刀割,反正我早已是個廢人,有沒有那東西,又有什麼區別?密醫點點頭,遞給我一張泛黃的同意書,上面寫著「自願接受下體全切手術,後果自負」。我顫抖著簽下名字,每一筆都像在割自己的心。
他指了指手術台,語氣冷漠:「上去,大字型躺好。」我爬上冰冷的手術台,鏽跡和血漬刺痛皮膚,四肢被粗糙的皮帶綁成大字型,勒得手腕和腳踝生疼。手術台的凹陷和劃痕像在低語,訴說著無數人的痛苦。我閉上眼,試著平復呼吸,可羞辱感和恐懼卻如巨浪拍打心頭。等待的每一秒都像刀子在割,腦海裡閃過麥語心的冷笑、王嘉嘉的嘲弄,還有那即將到來的劇痛。我低聲懺悔:「主人…賤奴會完成您的命令…」卻無人回應,只有密醫整理器械的叮噹聲,在這陰森的空間裡迴盪。
我顫抖著請求密醫:「在開始前…幫我拍張照片,發給我主人。」他冷冷地點頭,拿起一隻老舊的手機,拍下我赤裸地綁在手術台上的模樣,胸口的「奴」字和下體的貞操鎖在照片中格外諷刺與羞辱。我低聲口述訊息:「主人,賤奴已執行您的命令,即將移除您看不順眼的髒東西。」密醫發送後,將手機扔在一旁,開始準備手術。他的動作機械而熟練,卻毫無溫情,像在處理一塊無生命的肉。
手術台旁,一盤骯髒的金屬器械閃著冷光,刀刃上殞留著暗紅的血跡,散發著濃烈的鐵鏽味。密醫拿起一瓶泛黃的消毒液,潑在我的下體,刺骨的冰冷讓我全身一顫,隨即是火辣辣的灼痛。他沒有麻醉,僅用一塊破布塞進我的嘴,語氣冷漠:「咬緊,別叫太大聲。」我瞪大眼睛,恐懼如鐵爪扼住喉嚨,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手術刀在燈光下閃過一抹寒光,密醫的手穩得可怕,刀尖對準我的下體,毫不猶豫地切下。
劇痛如閃電竄過全身,像一把燒紅的刀從下體撕裂到腦海。我咬緊破布,發出低悶的嘶吼,鮮血噴湧而出,濺在手術台上,溫熱的液體順著大腿流下,染紅了鏽跡斑駁的台面。密醫毫不停頓,以急快和熟練的速度揮刀,瞬間劇痛突然襲來,我雙眼睜大,緊咬著配布,仍然止步住慘烈的叫,我手握拳,指甲刺進了手掌,全身肌肉崩住,血腥味和消毒水的氣味充斥鼻腔的空氣中,失去了意識。
不知過了多久,我緩緩的睜開眼,劇烈的痛楚讓我無法行走,甚至連起身都無法,我只要稍微移動一下就會感到劇痛,所以我盡量試著不動,密醫告訴我,三日後排列後你就可以離開了,隨手用一塊髒布擦去刀上的血跡,語氣平淡:「好了,沒死就算你命大。」我癱在手術台上,鮮血還在緩慢滲出,下體傳來的空虛感和劇痛像潮水,將我拖進更深的絕望。胸口的「奴」字烙印隱隱作痛,像在嘲笑我的墮落。我試著喘息,卻只感到無盡的悲痛和羞辱。曾經的我,還有夢想、還有尊嚴,可如今,我只是一個連完整身體都不配擁有的殞物。麥語心的命令完成了,可這代價卻將我徹底推入無底深淵。我閉上眼,淚水混著汗水滑落,從沒想過我會因為贖罪而落到此地步。
我心頭一震,本想只切除下體的腫瘤,保留其他部分,可麥語心不在,沒人能幫我開鎖。她的命令像鐵錮勒緊我的靈魂——必須在她回國前完成手術。時間的壓力、對手術的恐懼、還有對自己身份的羞恥,像漩渦將我拖進深淵。我咬緊牙,聲音顫抖:「好…我同意。」心裡卻像被刀割,反正我早已是個廢人,有沒有那東西,又有什麼區別?密醫點點頭,遞給我一張泛黃的同意書,上面寫著「自願接受下體腫瘤全切手術,後果自負」。我顫抖著簽下名字,每一筆都像在割自己的心。
他指了指手術台,語氣冷漠:「上去,大字型躺好。」我爬上冰冷的手術台,鏽跡和血漬刺痛皮膚,四肢被粗糙的皮帶綁成大字型,勒得手腕和腳踝生疼。手術台的凹陷和劃痕像在低語,訴說著無數人的痛苦。我閉上眼,試著平復呼吸,可羞辱感和恐懼卻如巨浪拍打心頭。等待的每一秒都像刀子在割,腦海裡閃過麥語心的冷笑、王嘉嘉的嘲弄,還有那即將到來的劇痛。我低聲懺悔:「主人…賤奴會完成您的命令…」卻無人回應,只有密醫整理器械的叮噹聲,在這陰森的空間裡迴盪。
我顫抖著請求密醫:「在開始前…幫我拍張照片,發給我主人。」他冷冷地點頭,拿起一隻老舊的手機,拍下我赤裸地綁在手術台上的模樣,胸口的「奴」字和下體的貞操鎖在照片中格外刺眼。我低聲口述訊息:「主人,賤奴已執行您的命令,即將移除您看不順眼的腫瘤。」密醫發送後,將手機扔在一旁,開始準備手術。他的動作機械而熟練,卻毫無溫情,像在處理一塊無生命的肉。
手術台旁,一盤骯髒的金屬器械閃著冷光,刀刃上殞留著暗紅的血跡,散發著濃烈的鐵鏽味。密醫拿起一瓶泛黃的消毒液,潑在我的下體,刺骨的冰冷讓我全身一顫,隨即是火辣辣的灼痛。他沒有麻醉,僅用一塊破布塞進我的嘴,語氣冷漠:「咬緊,別叫太大聲。」我瞪大眼睛,恐懼如鐵爪扼住喉嚨,心跳快得像要炸開。手術刀在燈光下閃過一抹寒光,密醫的手穩得可怕,刀尖對準我的下體,毫不猶豫地切下。
劇痛如閃電竄過全身,像一把燒紅的刀從下體撕裂到腦海。我咬緊破布,發出低悶的嘶吼,鮮血噴湧而出,濺在手術台上,溫熱的液體順著大腿流下,染紅了鏽跡斑駁的台面。密醫毫不停頓,刀刃繼續切割,腫瘤連同周圍組織被一塊塊剝離,每一下都像在撕裂我的靈魂。貞操鎖的金屬碰撞聲混雜著刀切肉的細微聲響,血腥味和消毒水的氣味充斥鼻腔,讓我幾乎窒息。我試著掙扎,皮帶卻勒得更緊,手腕和腳踝磨出血痕。疼痛吞噬了我的意識,眼前一片模糊,只剩無邊的黑暗和羞辱。
不知過了多久,密醫終於停下,隨手用一塊髒布擦去刀上的血跡,語氣平淡:「好了,沒死就算你命大。」我癱在手術台上,鮮血還在緩慢滲出,下體傳來的空虛感和劇痛像潮水,將我拖進更深的絕望。胸口的「奴」字烙印隱隱作痛,像在嘲笑我的墮落。我試著喘息,卻只感到無盡的悲痛和羞辱。曾經的我,還有夢想、還有尊嚴,可如今,我只是一個連完整身體都不配擁有的殞物。麥語心的命令完成了,可這代價卻將我徹底推入無底深淵。我閉上眼,淚水混著汗水滑落,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條狗命,早已不屬於自己。
另,顶文,催更
第三十章:回憶
我躺在宿舍的床上,窗外陽光刺眼,卻照不進我冰冷的內心。閹割手術後的第五天,我終於能勉強下床,傷口處傳來的撕裂痛楚仍像刀子,反覆切割著我的靈魂。那天在地下診所的記憶,像毒蛇纏繞,永遠無法甩脫——手術刀的寒光、鮮血噴湧的瞬間,還有下體那空蕩蕩的虛無感,讓我連呼吸都覺得沉重。過去四天,我連排尿都困難,每一次嘗試都像在重溫那場酷刑。密醫說我「恢復得不錯」,可這副殞傷的身體,這被剝奪的尊嚴,哪還有半點「不錯」的影子?
我拖著狼狽的身軀回到宿舍,胸口的「奴」字烙印隱隱作痛,結痂處的癢意像蟲子在爬,提醒著我這無盡的屈辱。手機突然震動,麥語心的訊息跳出螢幕:「賤狗,三天後我回國,準備好伺候。」我盯著螢幕,眼神空洞,機械地回覆:「是,主人。」腦海裡閃過手術台上的鮮血和她的冷笑,內心只剩無邊的絕望。人生還有什麼希望?曾經的張小凡,早已死在那張骯髒的手術台上,現在的我,只是一具行屍走肉。
這三天,我如同殞物般苟活在宿舍,目光呆滯地望著天花板。曾經的校園時光像遙遠的幻影,不斷在腦海回放。記得高一那年,我和陳凱威在操場上比賽投籃,陽光灑在我們身上,他笑著喊:「小凡,你這投籃姿勢跟醉漢似的!」旁邊的同學李浩拍著我的肩,揶揄道:「小凡,你還是老老實實當啦啦隊吧!」我們笑成一團,連跑過來的班花小雅都忍不住吐槽:「你們這群傢伙,比賽輸了還這麼開心?」那時的我,總是咧著嘴笑,覺得校園就是整個世界,簡單又美好。還有一次校園文化節,我和李浩負責搭舞台,忙得滿頭大汗,小雅偷偷塞給我一塊巧克力,笑著說:「小凡,別累壞了,這是獎勵!」那塊巧克力的甜味,至今仍是我記憶中最溫暖的片段。
我翻開手機,無意間滑到趙宜的社群媒體。她的頭像是一張燦爛的笑臉,背景是她和同事在咖啡廳的合照,陽光在她臉上跳躍,像從未被這世界的黑暗觸及。我點進她的動態,最新一條是她抱著一隻小貓,笑得純粹又滿足。心頭一陣刺痛,我想起了初識她的那個夏天。我在一家書店打工,她是新來的同事,穿著淺藍色襯衫,長髮紮成馬尾,總是帶著一抹溫柔的笑。第一次幫她整理書架時,她不小心撞翻一堆書,慌亂地跟我道歉,臉紅得像蘋果。我笑著說:「沒事,我來收拾。」她抬起頭,眼神清澈,輕聲說:「小凡,你人真好。」那晚下班,我們一起走在街頭,她指著路邊的冰淇淋攤,興奮地說:「小凡,下次請你吃草莓口味的,好不好?」我點頭,心裡全是甜蜜的悸動,暗暗幻想著能一直陪在她身邊。
如果沒有陳凱威那件事,如果我沒跟著他去偷拍麥語心,如果我選擇視若無睹,假裝什麼都沒看見,現在的我,會不會正和趙宜一起在書店聊書,或是並肩吃著她說的草莓冰淇淋?我們或許會一起看電影,分享彼此的夢想,甚至牽手走過這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可人生沒有時光機。當我選擇刪除那段影片,跪在麥語心腳下,甘願做她的奴隸,我的命運就注定了悲慘的結局。她逼我在她面前舔她的鞋底,喝她和她閨密的聖水,吃她賞賜的黃金,甚至烙下那恥辱的「奴」字,最後,將我僅剩的驕傲連根切除。這種非人的對待,像一把把刀子,割得我體無完膚。我痛苦,卻無處訴說,只能在深夜獨自舔舐傷口。
為了遺忘這一切,我逼自己忙碌起來,接了幾份兼職——送外賣、搬貨、甚至幫人抄筆記。錢大多被麥語心收走,但我不在乎。只要忙到累倒,忙到腦子一片空白,我就能暫時忘記自己是誰,忘記那手術台上的鮮血,忘記胸口的烙印,忘記下體的空虛。只有在筋疲力盡時,我才能勉強騙自己:我還活著。可每當夜深人靜,那股惡臭、那陣劇痛、還有趙宜的笑臉,總會像幽靈般纏上我,讓我無處可逃。
我看著鏡子裡的自己,眼神空洞,臉色蒼白,胸口的「奴」字像一塊永遠癒合不了的傷疤。下體的傷口雖已結痂,但每走一步,那空蕩蕩的感覺都在提醒我:我不再是個完整的男人。我是人?是狗?還是連狗都不如的殞物?或許,答案早已不重要。因為在麥語心的世界裡,我只是一個隨時可丟棄的工具,三天後,她回國時,這殞恥的奴役還將繼續。而我,早已無力反抗,只能在這無盡的黑暗中,繼續匍匐前行。
我躺在宿舍的床上,窗外陽光刺眼,卻照不進我冰冷的內心。閹割手術後的第五天,我終於能勉強下床,傷口處傳來的撕裂痛楚仍像刀子,反覆切割著我的靈魂。那天在地下診所的記憶,像毒蛇纏繞,永遠無法甩脫——手術刀的寒光、鮮血噴湧的瞬間,還有下體那空蕩蕩的虛無感,讓我連呼吸都覺得沉重。過去四天,我連排尿都困難,每一次嘗試都像在重溫那場酷刑。密醫說我「恢復得不錯」,可這副殞傷的身體,這被剝奪的尊嚴,哪還有半點「不錯」的影子?
我拖著狼狽的身軀回到宿舍,胸口的「奴」字烙印隱隱作痛,結痂處的癢意像蟲子在爬,提醒著我這無盡的屈辱。手機突然震動,麥語心的訊息跳出螢幕:「賤狗,三天後我回國,準備好伺候。」我盯著螢幕,眼神空洞,機械地回覆:「是,主人。」腦海裡閃過手術台上的鮮血和她的冷笑,內心只剩無邊的絕望。人生還有什麼希望?曾經的張小凡,早已死在那張骯髒的手術台上,現在的我,只是一具行屍走肉。
這三天,我如同殞物般苟活在宿舍,目光呆滯地望著天花板。曾經的校園時光像遙遠的幻影,不斷在腦海回放。記得高一那年,我和陳凱威在操場上比賽投籃,陽光灑在我們身上,他笑著喊:「小凡,你這投籃姿勢跟醉漢似的!」旁邊的同學李浩拍著我的肩,揶揄道:「小凡,你還是老老實實當啦啦隊吧!」我們笑成一團,連跑過來的班花小雅都忍不住吐槽:「你們這群傢伙,比賽輸了還這麼開心?」那時的我,總是咧著嘴笑,覺得校園就是整個世界,簡單又美好。還有一次校園文化節,我和李浩負責搭舞台,忙得滿頭大汗,小雅偷偷塞給我一塊巧克力,笑著說:「小凡,別累壞了,這是獎勵!」那塊巧克力的甜味,至今仍是我記憶中最溫暖的片段。
我翻開手機,無意間滑到趙宜的社群媒體。她的頭像是一張燦爛的笑臉,背景是她和同事在咖啡廳的合照,陽光在她臉上跳躍,像從未被這世界的黑暗觸及。我點進她的動態,最新一條是她抱著一隻小貓,笑得純粹又滿足。心頭一陣刺痛,我想起了初識她的那個夏天。我在一家書店打工,她是新來的同事,穿著淺藍色襯衫,長髮紮成馬尾,總是帶著一抹溫柔的笑。第一次幫她整理書架時,她不小心撞翻一堆書,慌亂地跟我道歉,臉紅得像蘋果。我笑著說:「沒事,我來收拾。」她抬起頭,眼神清澈,輕聲說:「小凡,你人真好。」那晚下班,我們一起走在街頭,她指著路邊的冰淇淋攤,興奮地說:「小凡,下次請你吃草莓口味的,好不好?」我點頭,心裡全是甜蜜的悸動,暗暗幻想著能一直陪在她身邊。
如果沒有陳凱威那件事,如果我沒跟著他去偷拍麥語心,如果我選擇視若無睹,假裝什麼都沒看見,現在的我,會不會正和趙宜一起在書店聊書,或是並肩吃著她說的草莓冰淇淋?我們或許會一起看電影,分享彼此的夢想,甚至牽手走過這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可人生沒有時光機。當我選擇刪除那段影片,跪在麥語心腳下,甘願做她的奴隸,我的命運就注定了悲慘的結局。她逼我在她面前舔她的鞋底,喝她和她閨密的聖水,吃她賞賜的黃金,甚至烙下那恥辱的「奴」字,最後,將我僅剩的驕傲連根切除。這種非人的對待,像一把把刀子,割得我體無完膚。我痛苦,卻無處訴說,只能在深夜獨自舔舐傷口。
為了遺忘這一切,我逼自己忙碌起來,接了幾份兼職——送外賣、搬貨、甚至幫人抄筆記。錢大多被麥語心收走,但我不在乎。只要忙到累倒,忙到腦子一片空白,我就能暫時忘記自己是誰,忘記那手術台上的鮮血,忘記胸口的烙印,忘記下體的空虛。只有在筋疲力盡時,我才能勉強騙自己:我還活著。可每當夜深人靜,那股惡臭、那陣劇痛、還有趙宜的笑臉,總會像幽靈般纏上我,讓我無處可逃。
我看著鏡子裡的自己,眼神空洞,臉色蒼白,胸口的「奴」字像一塊永遠癒合不了的傷疤。下體的傷口雖已結痂,但每走一步,那空蕩蕩的感覺都在提醒我:我不再是個完整的男人。我是人?是狗?還是連狗都不如的殞物?或許,答案早已不重要。因為在麥語心的世界裡,我只是一個隨時可丟棄的工具,三天後,她回國時,這殞恥的奴役還將繼續。而我,早已無力反抗,只能在這無盡的黑暗中,繼續匍匐前行。
第三十一章:奴化
三天後,我拖著殞傷的身體,來到麥語心的公寓。推開門,熟悉的薰衣草香氣撲鼻,卻掩不住那股無形的壓迫感,像鐵錮勒緊我的靈魂。我脫下所有衣物,赤裸地跪在她面前,頭低得幾乎貼地,胸口的「奴」字烙印在昏暗燈光下隱隱作痛,下體的傷口雖已結痂,卻留下永遠的空虛。麥語心站在我面前,目光掃過我的下體,嘴角揚起一抹嘲諷的冷笑:「你跟陳凱威這兩個淫蟲,就該是這副模樣。」
我沒有反駁,內心一片死寂,僅冷淡地回應:「主人教訓的是。」她的話像刀子,卻已無法在我心上割出新的傷口。麥語心繞著我走了一圈,語氣帶著玩味:「你看你這樣,就不用帶那破鎖了,多輕鬆。」我沒回應,只是低頭磕了一個響頭,額頭撞地的聲音在客廳迴盪。她的冷言冷語像空氣般環繞,我只是機械地聆聽,早已學會用沉默掩蓋內心的波瀾。
麥語心似乎對我的順從頗為滿意,怒氣稍消。她轉身坐上沙發,翹起二郎腿,語氣平靜了幾分:「我想,這些懲罰讓你學乖不少。以後安分點,知道嗎?」我匍匐在地,點頭應道:「是的,主人,以後賤奴絕不會再犯錯。」聲音低沉而機械,像從喉嚨裡硬擠出來。手術後,我對女人的興趣已大幅下降,甚至當有漂亮的女人從我身邊走過,我的心跳不再加速,腦海裡只有一片空白。曾經的慾望、幻想,甚至對趙宜的那抹悸動,都像被手術刀連根切除,留下的只有對麥語心命令的無條件服從。
她指了指腳邊的拖鞋,語氣輕慢:「去,舔乾淨。」我順從地爬過去,跪在她腳邊,小心翼翼地用雙手從鞋尖翹起處捧起拖鞋,確保不觸碰到鞋底以外的任何地方。鞋子的重量在手中沉甸甸的,我低下頭,舌頭觸碰到鞋底的塵埃。灰塵和橡膠的苦澀味在嘴裡蔓延,卻不再讓我感到噁心或抗拒。我機械地舔著,一下接一下,吞嚥著那些髒污,像一台沒有靈魂的機器。麥語心低頭看著我,眼中閃過一抹玩味:「果然,那東西才是讓你犯錯的根源。主人讓你割掉,是在救贖你,知道嗎?」我放下拖鞋,磕頭回應,聲音毫無波瀾:「謝謝主人讓賤奴重生,以後賤奴會永記此教訓。」
她滿意地點點頭,語氣帶著幾分高高在上的施捨:「你這狗,總算有點長進。」接著,她開始吩咐我幹活。我跪著擦拭地板,汗水混著傷口的刺痛滴在地上,每一塊瓷磚都被我擦得一塵不染。她又讓我清洗她的衣物,我戴上橡膠手套,小心翼翼地手洗她的貼身衣物,深怕一絲不慎觸怒她。中午,她讓我準備午餐,我在廚房忙碌,切菜、煮湯,手指被燙傷也不敢停下。整個下午,我像一頭牲口,搬運她新買的家具,整理書架,汗水浸濕全身,背上的鞭痕被扯裂,火辣辣地疼。我卻不敢有半句怨言,只默默承受,腦子裡只有她的命令。
直到傍晚,麥語心終於揮手讓我停下,語氣冷淡:「你可以滾了。後天再來伺候,到時候我會帶我男友回來。記得管好你的賤嘴,知道分寸。以後,你得一起伺候我們兩個,聽清楚了?」我愣了一瞬,心頭閃過一絲震驚。以往的我,或許會因這消息感到害怕,甚至擔憂——一個麥語心,連同王嘉嘉和駱品萱的折磨,已經讓我生不如死,如今再加一個男人,我無法想像等待我的會是怎樣的酷刑。可現在的我,內心卻只剩一片麻木。多一個人伺候又如何?多一個少一個,對我這條狗命又有什麼區別?我低聲回應:「是,主人,賤奴聽清楚了。」
麥語心哼了一聲,轉身滑手機,不再看我。我磕頭告退,穿上破舊的衣服,拖著疲憊的身體離開公寓。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夕陽的餘暉灑在身上,卻毫無溫暖。我感到自己正在一點點奴化,變成一個連自己都陌生的存在。曾經的張小凡,會因為趙宜的笑容心動,會和陳凱威在操場上笑鬧,會對未來充滿期待。可現在,我只是一具聽命行事的軀殼,連痛苦都變得遲鈍。舔鞋的屈辱、傷口的劇痛、甚至未來的折磨,都無法再激起我內心的波瀾。我已經不是人,甚至不是狗,只是一個為麥語心而存在的工具。這,就是我最終的命運。
三天後,我拖著殞傷的身體,來到麥語心的公寓。推開門,熟悉的薰衣草香氣撲鼻,卻掩不住那股無形的壓迫感,像鐵錮勒緊我的靈魂。我脫下所有衣物,赤裸地跪在她面前,頭低得幾乎貼地,胸口的「奴」字烙印在昏暗燈光下隱隱作痛,下體的傷口雖已結痂,卻留下永遠的空虛。麥語心站在我面前,目光掃過我的下體,嘴角揚起一抹嘲諷的冷笑:「你跟陳凱威這兩個淫蟲,就該是這副模樣。」
我沒有反駁,內心一片死寂,僅冷淡地回應:「主人教訓的是。」她的話像刀子,卻已無法在我心上割出新的傷口。麥語心繞著我走了一圈,語氣帶著玩味:「你看你這樣,就不用帶那破鎖了,多輕鬆。」我沒回應,只是低頭磕了一個響頭,額頭撞地的聲音在客廳迴盪。她的冷言冷語像空氣般環繞,我只是機械地聆聽,早已學會用沉默掩蓋內心的波瀾。
麥語心似乎對我的順從頗為滿意,怒氣稍消。她轉身坐上沙發,翹起二郎腿,語氣平靜了幾分:「我想,這些懲罰讓你學乖不少。以後安分點,知道嗎?」我匍匐在地,點頭應道:「是的,主人,以後賤奴絕不會再犯錯。」聲音低沉而機械,像從喉嚨裡硬擠出來。手術後,我對女人的興趣已大幅下降,甚至當有漂亮的女人從我身邊走過,我的心跳不再加速,腦海裡只有一片空白。曾經的慾望、幻想,甚至對趙宜的那抹悸動,都像被手術刀連根切除,留下的只有對麥語心命令的無條件服從。
她指了指腳邊的拖鞋,語氣輕慢:「去,舔乾淨。」我順從地爬過去,跪在她腳邊,小心翼翼地用雙手從鞋尖翹起處捧起拖鞋,確保不觸碰到鞋底以外的任何地方。鞋子的重量在手中沉甸甸的,我低下頭,舌頭觸碰到鞋底的塵埃。灰塵和橡膠的苦澀味在嘴裡蔓延,卻不再讓我感到噁心或抗拒。我機械地舔著,一下接一下,吞嚥著那些髒污,像一台沒有靈魂的機器。麥語心低頭看著我,眼中閃過一抹玩味:「果然,那東西才是讓你犯錯的根源。主人讓你割掉,是在救贖你,知道嗎?」我放下拖鞋,磕頭回應,聲音毫無波瀾:「謝謝主人讓賤奴重生,以後賤奴會永記此教訓。」
她滿意地點點頭,語氣帶著幾分高高在上的施捨:「你這狗,總算有點長進。」接著,她開始吩咐我幹活。我跪著擦拭地板,汗水混著傷口的刺痛滴在地上,每一塊瓷磚都被我擦得一塵不染。她又讓我清洗她的衣物,我戴上橡膠手套,小心翼翼地手洗她的貼身衣物,深怕一絲不慎觸怒她。中午,她讓我準備午餐,我在廚房忙碌,切菜、煮湯,手指被燙傷也不敢停下。整個下午,我像一頭牲口,搬運她新買的家具,整理書架,汗水浸濕全身,背上的鞭痕被扯裂,火辣辣地疼。我卻不敢有半句怨言,只默默承受,腦子裡只有她的命令。
直到傍晚,麥語心終於揮手讓我停下,語氣冷淡:「你可以滾了。後天再來伺候,到時候我會帶我男友回來。記得管好你的賤嘴,知道分寸。以後,你得一起伺候我們兩個,聽清楚了?」我愣了一瞬,心頭閃過一絲震驚。以往的我,或許會因這消息感到害怕,甚至擔憂——一個麥語心,連同王嘉嘉和駱品萱的折磨,已經讓我生不如死,如今再加一個男人,我無法想像等待我的會是怎樣的酷刑。可現在的我,內心卻只剩一片麻木。多一個人伺候又如何?多一個少一個,對我這條狗命又有什麼區別?我低聲回應:「是,主人,賤奴聽清楚了。」
麥語心哼了一聲,轉身滑手機,不再看我。我磕頭告退,穿上破舊的衣服,拖著疲憊的身體離開公寓。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夕陽的餘暉灑在身上,卻毫無溫暖。我感到自己正在一點點奴化,變成一個連自己都陌生的存在。曾經的張小凡,會因為趙宜的笑容心動,會和陳凱威在操場上笑鬧,會對未來充滿期待。可現在,我只是一具聽命行事的軀殼,連痛苦都變得遲鈍。舔鞋的屈辱、傷口的劇痛、甚至未來的折磨,都無法再激起我內心的波瀾。我已經不是人,甚至不是狗,只是一個為麥語心而存在的工具。這,就是我最終的命運。
第三十二章 男主人
時間像流水,飛逝而過。我繼續用工作麻痺自己,每天把自己累得半死,回到宿舍倒頭就睡,沒有任何消遣,沒有任何交際。我的生活像被抽乾了色彩,逐漸邊緣化,除了沒日沒夜的工作,就是去麥語心的公寓,當她的玩具、出氣人偶、打掃機器人,甚至是她隨手可丟的工具。日子過得機械而空洞,後天的到來卻像一記悶雷,悄無聲息地將我拖回那屈辱的深淵。
那天,我比往常更早來到麥語心的公寓,脫下衣物,赤裸地跪在玄關,開始日常的家務。我擦拭地板、清洗衣物、整理廚房,每一個動作都像刻進骨子裡的程式,汗水混著傷口的刺痛滴在地上,胸口的「奴」字烙印隱隱作癢,像在嘲笑我的墮落。做完一切,我匍匐跪在門口,頭低得幾乎貼地,等待主人的到來。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像刀子緩慢切割我的神經,膝蓋硌得生疼,卻不敢動彈。不知道過了多久,門外傳來男女的腳步聲,夾雜著嘻笑和低語,門縫漸漸打開。我低頭看著地板,視線裡出現一雙淺綠色蕾絲平底鞋和一雙黑色男性球鞋,鞋底沾著些許灰塵。我不敢抬頭,恭敬地低聲說:「恭迎男主人,恭迎女主人。」
麥語心的聲音帶著得意響起:「進來吧,寶貝。」她踏進玄關,轉頭對身旁的男人介紹:「這就是我跟你說過的奴隸,平常負責打掃衛生、做家務,聽話得很。」我低著頭,額頭貼地,聽到男主人用低沉的聲音說:「你好。」我連忙向他磕頭,聲音沙啞:「主人好。」趁著磕頭的瞬間,我偷偷抬眼瞥了他一眼。他身材壯闊,穿著簡潔的運動T恤和牛仔褲,平頭乾淨利落,皮膚帶著健康的古銅色,眉宇間透著一股運動員的陽剛氣息,嘴角掛著一抹隨性的笑。從他的身形看,絕不是幾年前在廢棄教室與麥語心親熱的那個男人,但這絲區別對我來說毫無意義——在麥語心的世界裡,我只是個無足輕重的工具。
麥語心哼了一聲,語氣輕蔑:「不用對他客氣,他就是隻狗!」她頓了頓,帶著玩味命令:「狗,學狗叫,轉三圈!」我沒有猶豫,低聲「汪汪汪」叫了三聲,隨後原地轉圈,膝蓋磨得刺痛,屈辱卻已無法在我心裡激起波瀾。麥語心得意地笑著,對男主人說:「你看,我就說他聽話吧?」男主人輕笑,語氣帶著一絲不安:「寶貝,你當初有說你有奴隸,但沒說是隻公狗…這不會影響我們吧?」他的聲音透著隱隱的擔憂,彷彿我的存在對他的地位構成了一絲威脅。
麥語心聽出他的顧慮,得意地指著我胸口的「奴」字烙印,又指向我空蕩蕩的下體,語氣滿是炫耀:「你不用擔心,這傢伙根本不可能影響你的地位。況且,我也不會自甘墮落到跟這種賤貨在一起!」說完,她用腳尖踢了踢我空蕩蕩的下體,傷疤傳來一陣刺痛,羞辱像潮水湧來。可現在的我,自尊早已被碾進塵埃,我沒有任何反抗,低頭繼續舔她的鞋底,直到每一粒灰塵都被吞進喉嚨。舔完後,我轉向男主人,恭敬地說:「請男主人抬腳,賤奴為您清理。」
男主人愣了一下,眼中閃過一絲生澀,畢竟讓一個陌生男人——如果我還能算男人的話——舔鞋,多少有些不適。他猶豫片刻,還是緩緩抬起腳,黑色球鞋的鞋底滿是泥土和細沙。我捧起他的鞋,依舊小心不觸碰鞋底以外的地方,舌頭機械地舔過,橡膠和泥土的腥苦味在嘴裡炸開,舌頭漸漸被磨得發黑,滿嘴泥味。我卻毫無波瀾,像一台機器,專注於清理每一寸污垢,彷彿這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義。
舔完鞋子,麥語心和男主人開始有說有笑地聊天,彷彿我不存在。他們談論著旅行的趣事、未來的計劃,偶爾發出肆意的笑聲,聲音像刀子刺進我的心。我跪在一旁,低著頭,繼續清理地上的灰塵,汗水滴在地上,混著背上鞭痕的刺痛。他們的鞋印在地板上留下一串污跡,我默默爬過去,用抹布擦乾淨,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不能讓主人不滿。麥語心偶爾瞥我一眼,眼中滿是輕蔑,男主人則漸漸適應了我的存在,偶爾扔給我一句:「再拿杯水來。」我立刻起身,端來水杯,雙手奉上,然後退回角落,繼續我的「工作」。
半夜,我完成所有打掃的家務,麥語心卻未讓我離去。她從櫃子裡拿出K-9刑具,冷冷命令:「出去,跪在門外。」我順從地爬到臥室門外,陰暗的客廳裡,鐵圈緊扣我的手腕和頸部,將我固定成跪爬的狗姿,冰冷的地板硌得膝蓋生疼,姿勢的扭曲讓我無法入眠。我只能睜著眼,等待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疲憊和屈辱像潮水將我淹沒。突然,臥室裡傳來動靜,吱吱的床板聲伴隨著麥語心的嬌喘,低沉而誘惑,刺進我的心。男主人正在做我曾經還是男人時無比嚮往的事——與麥語心親密無間,肆意發洩慾望。雖然我已失去那話兒,但聽著她的聲音,那個我曾暗自幻想擁有的女人,我的心仍泛起一絲波動,隨即被羞辱吞噬。
我知道,麥語心故意讓我聽見這一切。她要羞辱我,讓我知道我只配舔她的鞋底、喝她的聖水、吞她的黃金,而眼前的男人卻能完全擁有她,甚至肆意妄為。她要告訴我,他與我的地位天差地遠,我只能像這樣跪在門外,卑微地、羞辱地聆聽他們的交歡聲,尊嚴被踩進塵埃。更殞忍的羞辱還在後頭——他們完事後,麥語心穿著清涼的絲質睡衣走出,手中拿著一個打了結的保險套,裡面濃白的液體在燈光下閃著刺眼的光芒,彷彿在嘲笑我是一場笑話。她低頭看著我,語氣帶著挑逗:「狗,你不是很迷戀我的聖域嗎?」
我低頭,羞辱如刀割心,聲音颤抖:「奴不敢,奴不配擁有。」麥語心冷笑,晃了晃手中的保險套:「這套子外層沾滿主人聖域的氣息,裡面有你男主人的精華,就賞給你吧!」她的字字句句像鞭子,抽在我的靈魂上。我看著那激戰後的產物,白色液體彷彿也在嘲笑我的卑微。我知道無法拒絕,張開嘴,麥語心將保險套緩緩靠近,刺鼻的腥味混雜著兩人的體味和潤滑劑的化學氣息,令人作嘔。她將它塞進我口中,命令道:「今晚含著它,好好品嘗。明早我來檢查。」我順從地含住,化學味道和體液的腥臭在嘴裡炸開,胃裡翻滾,卻不敢吐出。麥語心滿意地看著我,轉身回臥室,留下我獨自在黑暗中,含著這羞辱的「賞賜」,跪在K-9刑具裡,等待天亮。
時間像流水,飛逝而過。我繼續用工作麻痺自己,每天把自己累得半死,回到宿舍倒頭就睡,沒有任何消遣,沒有任何交際。我的生活像被抽乾了色彩,逐漸邊緣化,除了沒日沒夜的工作,就是去麥語心的公寓,當她的玩具、出氣人偶、打掃機器人,甚至是她隨手可丟的工具。日子過得機械而空洞,後天的到來卻像一記悶雷,悄無聲息地將我拖回那屈辱的深淵。
那天,我比往常更早來到麥語心的公寓,脫下衣物,赤裸地跪在玄關,開始日常的家務。我擦拭地板、清洗衣物、整理廚房,每一個動作都像刻進骨子裡的程式,汗水混著傷口的刺痛滴在地上,胸口的「奴」字烙印隱隱作癢,像在嘲笑我的墮落。做完一切,我匍匐跪在門口,頭低得幾乎貼地,等待主人的到來。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像刀子緩慢切割我的神經,膝蓋硌得生疼,卻不敢動彈。不知道過了多久,門外傳來男女的腳步聲,夾雜著嘻笑和低語,門縫漸漸打開。我低頭看著地板,視線裡出現一雙淺綠色蕾絲平底鞋和一雙黑色男性球鞋,鞋底沾著些許灰塵。我不敢抬頭,恭敬地低聲說:「恭迎男主人,恭迎女主人。」
麥語心的聲音帶著得意響起:「進來吧,寶貝。」她踏進玄關,轉頭對身旁的男人介紹:「這就是我跟你說過的奴隸,平常負責打掃衛生、做家務,聽話得很。」我低著頭,額頭貼地,聽到男主人用低沉的聲音說:「你好。」我連忙向他磕頭,聲音沙啞:「主人好。」趁著磕頭的瞬間,我偷偷抬眼瞥了他一眼。他身材壯闊,穿著簡潔的運動T恤和牛仔褲,平頭乾淨利落,皮膚帶著健康的古銅色,眉宇間透著一股運動員的陽剛氣息,嘴角掛著一抹隨性的笑。從他的身形看,絕不是幾年前在廢棄教室與麥語心親熱的那個男人,但這絲區別對我來說毫無意義——在麥語心的世界裡,我只是個無足輕重的工具。
麥語心哼了一聲,語氣輕蔑:「不用對他客氣,他就是隻狗!」她頓了頓,帶著玩味命令:「狗,學狗叫,轉三圈!」我沒有猶豫,低聲「汪汪汪」叫了三聲,隨後原地轉圈,膝蓋磨得刺痛,屈辱卻已無法在我心裡激起波瀾。麥語心得意地笑著,對男主人說:「你看,我就說他聽話吧?」男主人輕笑,語氣帶著一絲不安:「寶貝,你當初有說你有奴隸,但沒說是隻公狗…這不會影響我們吧?」他的聲音透著隱隱的擔憂,彷彿我的存在對他的地位構成了一絲威脅。
麥語心聽出他的顧慮,得意地指著我胸口的「奴」字烙印,又指向我空蕩蕩的下體,語氣滿是炫耀:「你不用擔心,這傢伙根本不可能影響你的地位。況且,我也不會自甘墮落到跟這種賤貨在一起!」說完,她用腳尖踢了踢我空蕩蕩的下體,傷疤傳來一陣刺痛,羞辱像潮水湧來。可現在的我,自尊早已被碾進塵埃,我沒有任何反抗,低頭繼續舔她的鞋底,直到每一粒灰塵都被吞進喉嚨。舔完後,我轉向男主人,恭敬地說:「請男主人抬腳,賤奴為您清理。」
男主人愣了一下,眼中閃過一絲生澀,畢竟讓一個陌生男人——如果我還能算男人的話——舔鞋,多少有些不適。他猶豫片刻,還是緩緩抬起腳,黑色球鞋的鞋底滿是泥土和細沙。我捧起他的鞋,依舊小心不觸碰鞋底以外的地方,舌頭機械地舔過,橡膠和泥土的腥苦味在嘴裡炸開,舌頭漸漸被磨得發黑,滿嘴泥味。我卻毫無波瀾,像一台機器,專注於清理每一寸污垢,彷彿這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義。
舔完鞋子,麥語心和男主人開始有說有笑地聊天,彷彿我不存在。他們談論著旅行的趣事、未來的計劃,偶爾發出肆意的笑聲,聲音像刀子刺進我的心。我跪在一旁,低著頭,繼續清理地上的灰塵,汗水滴在地上,混著背上鞭痕的刺痛。他們的鞋印在地板上留下一串污跡,我默默爬過去,用抹布擦乾淨,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不能讓主人不滿。麥語心偶爾瞥我一眼,眼中滿是輕蔑,男主人則漸漸適應了我的存在,偶爾扔給我一句:「再拿杯水來。」我立刻起身,端來水杯,雙手奉上,然後退回角落,繼續我的「工作」。
半夜,我完成所有打掃的家務,麥語心卻未讓我離去。她從櫃子裡拿出K-9刑具,冷冷命令:「出去,跪在門外。」我順從地爬到臥室門外,陰暗的客廳裡,鐵圈緊扣我的手腕和頸部,將我固定成跪爬的狗姿,冰冷的地板硌得膝蓋生疼,姿勢的扭曲讓我無法入眠。我只能睜著眼,等待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疲憊和屈辱像潮水將我淹沒。突然,臥室裡傳來動靜,吱吱的床板聲伴隨著麥語心的嬌喘,低沉而誘惑,刺進我的心。男主人正在做我曾經還是男人時無比嚮往的事——與麥語心親密無間,肆意發洩慾望。雖然我已失去那話兒,但聽著她的聲音,那個我曾暗自幻想擁有的女人,我的心仍泛起一絲波動,隨即被羞辱吞噬。
我知道,麥語心故意讓我聽見這一切。她要羞辱我,讓我知道我只配舔她的鞋底、喝她的聖水、吞她的黃金,而眼前的男人卻能完全擁有她,甚至肆意妄為。她要告訴我,他與我的地位天差地遠,我只能像這樣跪在門外,卑微地、羞辱地聆聽他們的交歡聲,尊嚴被踩進塵埃。更殞忍的羞辱還在後頭——他們完事後,麥語心穿著清涼的絲質睡衣走出,手中拿著一個打了結的保險套,裡面濃白的液體在燈光下閃著刺眼的光芒,彷彿在嘲笑我是一場笑話。她低頭看著我,語氣帶著挑逗:「狗,你不是很迷戀我的聖域嗎?」
我低頭,羞辱如刀割心,聲音颤抖:「奴不敢,奴不配擁有。」麥語心冷笑,晃了晃手中的保險套:「這套子外層沾滿主人聖域的氣息,裡面有你男主人的精華,就賞給你吧!」她的字字句句像鞭子,抽在我的靈魂上。我看著那激戰後的產物,白色液體彷彿也在嘲笑我的卑微。我知道無法拒絕,張開嘴,麥語心將保險套緩緩靠近,刺鼻的腥味混雜著兩人的體味和潤滑劑的化學氣息,令人作嘔。她將它塞進我口中,命令道:「今晚含著它,好好品嘗。明早我來檢查。」我順從地含住,化學味道和體液的腥臭在嘴裡炸開,胃裡翻滾,卻不敢吐出。麥語心滿意地看著我,轉身回臥室,留下我獨自在黑暗中,含著這羞辱的「賞賜」,跪在K-9刑具裡,等待天亮。
顶,很好看
别停,继续更
(男主真的出现了QAQ)
(男主真的出现了QAQ)
第三十三章 毫無尊嚴遊戲
夜裡,黑暗像一張網,將我困在K-9刑具的冰冷鐵圈中。跪爬的姿勢讓膝蓋硌得生疼,頸部的鐵環勒得我無法動彈,疲憊和屈辱像毒蛇,啃噬著我的靈魂。嘴裡含著麥語心和她男友交歡後的保險套,刺鼻的腥味混雜著潤滑劑的化學氣息和兩人的體液,在舌頭上炸開,令人作嘔。保險套外層沾著麥語心的愛液,那股微甜而濃烈的氣息,是我做奴以來第一次嘗到。這味道,卻像一把刀,狠狠刺進我早已破碎的心。
曾經,當我還是個完整的男人,我確實對麥語心有過幻想。那些隱秘的夜晚,我想像自己像個真正的男人,將頭埋進那神秘的黑森林,找到那含苞待放的蓓蕾,貪婪地舔拭、吸吮,感受她的溫熱與顫抖。我更幻想肆無忌憚地將自己的男根探入她的秘境,探索那片我永遠無法觸及的禁地。可老天給我開了個殞忍的玩笑——我終於嘗到了麥語心的愛液,卻是以如此羞辱的方式,透過一個沾滿另一個男人精華的保險套。可笑的是,當年廢棄教室的男人,如今的男友,甚至如果陳凱威得逞,與麥語心發生關係似乎都輕而易舉。我拼盡全力也無法企及的目標,別人卻三兩下就能達到。而我,現在連尊嚴都被閹割,羞辱地被綁在刑具上,含著他們交歡的產物,聽著臥室裡的餘音,尊嚴被踐踏至塵埃。
保險套的腥臭味和化學味道在嘴裡蔓延,令人作嘔的口感像毒藥,燒灼著我的喉嚨。我戰戰兢兢地含著,深怕它從口中滑落,招來麥語心的懲罰。整夜,我無法入眠,鐵圈勒得皮膚生疼,膝蓋麻木,舌頭因長時間含著保險套而腫脹。每一次吞嚥都像在吞下自己的羞辱,胃裡翻滾,卻不敢有絲毫反抗。麥語心故意讓我含著這東西,她要我明白,我只配舔她的鞋底、喝她的聖水、吞她的黃金,而她的身體、她的愛,永遠屬於別的男人。我試著讓自己麻木,卻無法阻止腦海裡的畫面——麥語心的笑、她的身體、還有那個男人在她身上肆意妄為的模樣。我曾經幻想過的畫面,如今卻成了對我最殞忍的嘲笑。
天色漸亮,晨光從窗簾縫隙灑進,照在冰冷的地板上。我跪了一整夜,膝蓋已麻木,嘴裡的保險套讓我的舌頭腫脹,腥臭味滲進每一寸味蕾。臥室門終於打開,麥語心和男友走了出來。她穿著一襲白色絲質睡衣,長髮散亂,臉上帶著慵懶的笑,男主人跟在她身後,赤著上身,露出結實的肌肉,隨意地打著哈欠。他們的目光掃過我,像在看一件無關緊要的物品。
麥語心停下腳步,蹲在我面前,檢查我口中的保險套,眼中閃著惡作劇的光芒。她捏住我的下巴,逼我張嘴,確認保險套仍在,隨後冷笑:「好狗,沒吐出來。」她抽出保險套,晃了晃,裡面的白色液體在燈光下閃著刺眼的光芒,然後命令道:「吃下去。」我喉嚨一緊,羞辱和噁心如狂潮湧來,但她的目光不容反抗。我強忍著嘔意,接過保險套,撕開,將那腥臭的液體倒進嘴裡,濃稠的口感和刺鼻的味道讓胃裡翻江倒海。我咬緊牙,硬生生吞下,每一口都像在吞噬自己的尊嚴。麥語心滿意地點頭,拍拍我的臉,語氣帶著嘲弄:「好狗,記得這味道。」
她站起身,轉頭看向男主人,笑得肆意:「寶貝,還記得那個好玩的事嗎?」男主人挑了挑眉,笑著說:「記得,雖然沒試過,但應該挺有趣。」他的語氣輕鬆,卻像刀子刺進我的心。我心頭一沉,隱隱猜到他們的「好玩的事」是什麼。麥語心鬆開我的K-9刑具,命令我爬到浴室。我順從地爬過去,冰冷的瓷磚貼著皮膚,屈辱感像潮水將我淹沒。那一刻,我知道他們的意圖——這不是第一次,卻仍讓我感到一絲排斥,但如今的我,早已學會接受。
麥語心拿出一條黑布,蒙住我的眼睛,語氣帶著玩味:「狗,猜猜哪泡尿是我的,哪泡是男主人的。」我躺在浴室冰冷的地板上,仰面朝上,黑暗中只剩她的聲音和即將到來的羞辱。有人蹲在我臉上,滾燙的晨尿傾瀉而下,異常濃厚的腥味衝進我的嘴裡,量多得幾乎讓我窒息,順著喉嚨流下,灼燒著我的食道。起初,我無法辨認上方的人影,但當那熟悉的微酸氣息混雜著腐臭的酸液味在舌尖炸開,我瞬間認出——這是麥語心的尿,帶著她獨特的氣味,像毒藥般刺鼻而腐敗。我咬緊牙,強迫自己吞嚥,內心卻湧起一陣苦澀——這是我曾幻想過的女人,如今卻以如此羞辱的方式,將她的「聖水」賜予我。接著,另一人蹲下,尿液更為濃重,腥味厚重而嗆鼻,量同樣驚人,像洪水般灌進我的嘴,幾乎溢出。味道如腐敗的鹽水,苦澀而刺喉,我勉強吞下,胃裡翻騰,內心的苦澀更甚——喝麥語心的尿已是極致的屈辱,連這個男人的尿也要吞下,這份羞辱像刀子,割得我體無完膚。我曾是個男人,卻淪落到連另一個男人的排洩物都要承受,這比閹割更讓我感到靈魂的崩塌,內心像被無形的鐵錮勒緊,痛得無法呼吸。
麥語心摘下黑布,笑著問:「猜,哪泡是我的?」我低聲回道:「第一泡…是女主人的。」她哈哈一笑,拍手道:「不錯,狗鼻子還挺靈!」男主人跟著笑,語氣帶著幾分驚訝:「這傢伙還真聽話。」我低著頭,尿液的腐臭味殞留在嘴裡,羞辱像鐵錮勒緊我的靈魂。麥語心滿意地看著我,語氣輕慢:「好狗,今天表現不錯,繼續保持。」她轉身挽住男主人的手臂,兩人笑著走進廚房,留下我躺在浴室裡,嘴裡的腥臭味和胸口的烙印像永不癒合的傷口,提醒我這無盡的奴役。我閉上眼,淚水混著汗水滑落,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樣的日子只是開始,絕不是盡頭。
夜裡,黑暗像一張網,將我困在K-9刑具的冰冷鐵圈中。跪爬的姿勢讓膝蓋硌得生疼,頸部的鐵環勒得我無法動彈,疲憊和屈辱像毒蛇,啃噬著我的靈魂。嘴裡含著麥語心和她男友交歡後的保險套,刺鼻的腥味混雜著潤滑劑的化學氣息和兩人的體液,在舌頭上炸開,令人作嘔。保險套外層沾著麥語心的愛液,那股微甜而濃烈的氣息,是我做奴以來第一次嘗到。這味道,卻像一把刀,狠狠刺進我早已破碎的心。
曾經,當我還是個完整的男人,我確實對麥語心有過幻想。那些隱秘的夜晚,我想像自己像個真正的男人,將頭埋進那神秘的黑森林,找到那含苞待放的蓓蕾,貪婪地舔拭、吸吮,感受她的溫熱與顫抖。我更幻想肆無忌憚地將自己的男根探入她的秘境,探索那片我永遠無法觸及的禁地。可老天給我開了個殞忍的玩笑——我終於嘗到了麥語心的愛液,卻是以如此羞辱的方式,透過一個沾滿另一個男人精華的保險套。可笑的是,當年廢棄教室的男人,如今的男友,甚至如果陳凱威得逞,與麥語心發生關係似乎都輕而易舉。我拼盡全力也無法企及的目標,別人卻三兩下就能達到。而我,現在連尊嚴都被閹割,羞辱地被綁在刑具上,含著他們交歡的產物,聽著臥室裡的餘音,尊嚴被踐踏至塵埃。
保險套的腥臭味和化學味道在嘴裡蔓延,令人作嘔的口感像毒藥,燒灼著我的喉嚨。我戰戰兢兢地含著,深怕它從口中滑落,招來麥語心的懲罰。整夜,我無法入眠,鐵圈勒得皮膚生疼,膝蓋麻木,舌頭因長時間含著保險套而腫脹。每一次吞嚥都像在吞下自己的羞辱,胃裡翻滾,卻不敢有絲毫反抗。麥語心故意讓我含著這東西,她要我明白,我只配舔她的鞋底、喝她的聖水、吞她的黃金,而她的身體、她的愛,永遠屬於別的男人。我試著讓自己麻木,卻無法阻止腦海裡的畫面——麥語心的笑、她的身體、還有那個男人在她身上肆意妄為的模樣。我曾經幻想過的畫面,如今卻成了對我最殞忍的嘲笑。
天色漸亮,晨光從窗簾縫隙灑進,照在冰冷的地板上。我跪了一整夜,膝蓋已麻木,嘴裡的保險套讓我的舌頭腫脹,腥臭味滲進每一寸味蕾。臥室門終於打開,麥語心和男友走了出來。她穿著一襲白色絲質睡衣,長髮散亂,臉上帶著慵懶的笑,男主人跟在她身後,赤著上身,露出結實的肌肉,隨意地打著哈欠。他們的目光掃過我,像在看一件無關緊要的物品。
麥語心停下腳步,蹲在我面前,檢查我口中的保險套,眼中閃著惡作劇的光芒。她捏住我的下巴,逼我張嘴,確認保險套仍在,隨後冷笑:「好狗,沒吐出來。」她抽出保險套,晃了晃,裡面的白色液體在燈光下閃著刺眼的光芒,然後命令道:「吃下去。」我喉嚨一緊,羞辱和噁心如狂潮湧來,但她的目光不容反抗。我強忍著嘔意,接過保險套,撕開,將那腥臭的液體倒進嘴裡,濃稠的口感和刺鼻的味道讓胃裡翻江倒海。我咬緊牙,硬生生吞下,每一口都像在吞噬自己的尊嚴。麥語心滿意地點頭,拍拍我的臉,語氣帶著嘲弄:「好狗,記得這味道。」
她站起身,轉頭看向男主人,笑得肆意:「寶貝,還記得那個好玩的事嗎?」男主人挑了挑眉,笑著說:「記得,雖然沒試過,但應該挺有趣。」他的語氣輕鬆,卻像刀子刺進我的心。我心頭一沉,隱隱猜到他們的「好玩的事」是什麼。麥語心鬆開我的K-9刑具,命令我爬到浴室。我順從地爬過去,冰冷的瓷磚貼著皮膚,屈辱感像潮水將我淹沒。那一刻,我知道他們的意圖——這不是第一次,卻仍讓我感到一絲排斥,但如今的我,早已學會接受。
麥語心拿出一條黑布,蒙住我的眼睛,語氣帶著玩味:「狗,猜猜哪泡尿是我的,哪泡是男主人的。」我躺在浴室冰冷的地板上,仰面朝上,黑暗中只剩她的聲音和即將到來的羞辱。有人蹲在我臉上,滾燙的晨尿傾瀉而下,異常濃厚的腥味衝進我的嘴裡,量多得幾乎讓我窒息,順著喉嚨流下,灼燒著我的食道。起初,我無法辨認上方的人影,但當那熟悉的微酸氣息混雜著腐臭的酸液味在舌尖炸開,我瞬間認出——這是麥語心的尿,帶著她獨特的氣味,像毒藥般刺鼻而腐敗。我咬緊牙,強迫自己吞嚥,內心卻湧起一陣苦澀——這是我曾幻想過的女人,如今卻以如此羞辱的方式,將她的「聖水」賜予我。接著,另一人蹲下,尿液更為濃重,腥味厚重而嗆鼻,量同樣驚人,像洪水般灌進我的嘴,幾乎溢出。味道如腐敗的鹽水,苦澀而刺喉,我勉強吞下,胃裡翻騰,內心的苦澀更甚——喝麥語心的尿已是極致的屈辱,連這個男人的尿也要吞下,這份羞辱像刀子,割得我體無完膚。我曾是個男人,卻淪落到連另一個男人的排洩物都要承受,這比閹割更讓我感到靈魂的崩塌,內心像被無形的鐵錮勒緊,痛得無法呼吸。
麥語心摘下黑布,笑著問:「猜,哪泡是我的?」我低聲回道:「第一泡…是女主人的。」她哈哈一笑,拍手道:「不錯,狗鼻子還挺靈!」男主人跟著笑,語氣帶著幾分驚訝:「這傢伙還真聽話。」我低著頭,尿液的腐臭味殞留在嘴裡,羞辱像鐵錮勒緊我的靈魂。麥語心滿意地看著我,語氣輕慢:「好狗,今天表現不錯,繼續保持。」她轉身挽住男主人的手臂,兩人笑著走進廚房,留下我躺在浴室裡,嘴裡的腥臭味和胸口的烙印像永不癒合的傷口,提醒我這無盡的奴役。我閉上眼,淚水混著汗水滑落,心裡只有一個念頭:這樣的日子只是開始,絕不是盡頭。
顶顶,怎么不更了
写的很棒 加油更新大佬-.-+
太强了佬
写的太好了!
頂 催更
第三十四章:男主人的戲弄
喝完那兩泡濃烈的晨尿後,我躺在浴室的冰冷瓷磚上,嘴裡的腥臭味像毒藥般滲進每一個毛孔,胃裡翻滾得像要炸開。麥語心和男主人笑鬧著離開浴室,留我獨自面對這無邊的屈辱。黑暗的視野漸漸清晰,我試著爬起身,膝蓋的麻木和下體的空虛感讓動作變得笨拙而可笑。曾經,我還能幻想自己是個男人,能在女人面前挺起胸膛,可如今,我連站直的資格都沒有,只能像條蟲子般蠕動,舔舐著他們遺留的汙穢。
我強忍著噁心,用抹布擦拭地板上的尿漬,每一灘黃色的液體都像在嘲笑我的墮落。氣味瀰漫在空氣中,腐敗的酸澀味混雜著男主人的濃重腥臭,讓我回想起剛才的遊戲——第一泡是麥語心的,那股微酸而刺鼻的味道,我已熟悉得像烙進骨子裡;第二泡則是男主人的,量大而苦澀,像一股無形的鐵錮,勒緊我的靈魂。吞嚥時,那液體順著喉嚨滑下,灼燒著我的食道,內心的羞辱比疼痛更難忍。為什麼連另一個男人的排洩物,我都要卑微地接受?這比鞭打、比烙印、甚至比閹割都更讓我感到靈魂的崩潰。我曾是個男人,卻淪落到這種地步,尊嚴被踐踏得連渣都不剩。
收拾完浴室,我爬到廚房門口,跪著等待進一步的命令。麥語心和男主人正坐在餐桌邊,吃著我昨晚準備的早餐——新鮮的水果沙拉、煎蛋和咖啡。他們有說有笑,偶爾夾雜著親密的低語,聲音像刀子刺進我的心。男主人夾起一塊煎蛋,咬了一口,滿意地點頭:「寶貝,這蛋煎得不錯。」麥語心笑著瞥了我一眼,語氣輕蔑:「當然,這狗的手藝還行,專門訓練過的。」我低著頭,額頭貼地,不敢抬眼,內心卻湧起一絲苦澀——這些早餐,是我昨晚跪著在廚房忙碌半小時的成果,汗水混著傷口的刺痛滴進鍋裡,卻只換來他們隨意的評價。
吃到一半,麥語心突然轉頭看向我,眼中閃過一抹惡作劇的光芒:「狗,過來。」我順從地爬過去,跪在她腳邊,視線只敢停留在她的拖鞋上。她夾起一塊吃剩的煎蛋殘渣,扔在地上,踩了踩,蛋黃和蛋白混雜著灰塵,變成一灘黏膩的汙物。「吃了吧,這是你的早餐。」她的語氣平淡,卻帶著不容反抗的威嚴。我沒有猶豫,低頭舔食地板上的殘渣,灰塵和蛋黃的混合味在嘴裡蔓延,苦澀而噁心。男主人看著這一幕,輕笑一聲:「寶貝,你這狗還真聽話,不過…讓他吃地上的東西,會不會太髒?」麥語心聳聳肩,笑得肆意:「髒?對他來說,這就是賞賜。狗本來就該吃這些,不是嗎?」
我機械地舔食著,內心的麻木讓我連抗拒的念頭都沒有。男主人似乎被這場景激起了興趣,他也夾起一塊吃剩的麵包屑,扔在地上,語氣試探:「來,吃我的。」我轉向那塊麵包屑,舔食時,腦海裡閃過一絲異樣——這是男主人的食物,混雜著他的口水味,淡淡的鹹澀讓我胃裡一陣翻騰。可我還是吞下,磕頭道:「謝男主人恩典。」他哈哈一笑,眼中多了幾分玩味:「有趣,這狗還挺會謝的。」麥語心滿意地點頭,拉著他的手:「寶貝,你可以把他當玩具,怎麼玩都行。他就是為我們服務的。」
早餐結束後,他們起身去客廳沙發上休息,留下滿桌的殘羹冷炙。我跪著收拾餐桌,擦拭每一滴油漬,每一個指紋,汗水順著背上的鞭痕滑落,火辣辣地疼。收拾完,我爬到客廳門口,跪等命令。麥語心和男主人靠在一起看電視,偶爾低語幾句,氛圍親密得像把我排除在世界之外。突然,男主人轉頭看向我,語氣帶著好奇:「寶貝,你說這狗會不會做按摩?我的肩膀有點酸。」麥語心挑了挑眉,笑著命令:「狗,過來,給男主人按摩肩膀。」我爬過去,跪在他身後,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按壓他的肩部肌肉。他的皮膚結實而溫熱,手感像在觸碰一個強者的象徵,每一下按壓都讓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
按摩到一半,男主人突然哼了一聲,語氣不悅:「力道太輕了,用點勁!」我加大力氣,他卻又皺眉:「太重了,你這狗不會按嗎?」我調整力道,心裡湧起一絲無奈——無論怎麼做,似乎都無法讓他滿意。麥語心看在眼裡,冷笑一聲:「狗,你笨手笨腳的,惹男主人不高興了,該怎麼辦?」我低頭磕頭,聲音顫抖:「賤奴知錯,請男主人懲罰。」男主人愣了一下,隨即笑著看向麥語心:「寶貝,怎麼罰?」她眼中閃過一抹冷酷,起身從櫃子裡拿出皮鞭,遞給他:「用這個,抽他幾下,讓他長記性。」
男主人接過鞭子,試探性地揮了揮,空氣中響起尖利的呼嘯聲。我跪直身體,背對著他,等待懲罰。第一鞭落下,撕裂般的疼痛從背上爆開,舊傷口被重新扯裂,鮮血順著皮膚滑落。我咬緊牙,低聲說:「謝男主人懲罰。」第二鞭、第三鞭接踵而至,每一下都像火燒,鞭痕交錯成網,疼痛讓我全身顫抖。男主人抽了五鞭後停下,語氣帶著興奮:「寶貝,這感覺還挺解壓的。」麥語心笑著抱住他:「當然,以後他就是你的玩具,怎麼玩都行。」
懲罰結束,我跪在地上,背上的血痕火辣辣地疼,汗水混著血水滴落。我低聲道:「謝男主人恩典。」內心的麻木讓我連痛苦都感覺遲鈍,可腦海裡卻閃過一個念頭——現在的我,不僅是麥語心的奴隸,還成了她男友的玩具。這份屈辱,像無形的枷鎖,越勒越緊,讓我喘不過氣。下午,他們讓我繼續家務,我跪著擦拭客廳的每一個角落,汗水浸濕地板,傷口的疼痛讓動作變得緩慢而艱難。男主人偶爾扔來一句命令:「再倒杯水。」或「擦擦我的鞋。」我機械地執行,腦子裡只有空白。
直到傍晚,麥語心揮手讓我離開:「滾吧,後天再來。」我磕頭告退,穿上破舊的衣服,拖著滿身傷痕離開公寓。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夕陽的餘暉灑在身上,卻毫無溫暖。我感到自己正一步步沉淪,這奴役的枷鎖,已將我徹底綁死。男主人的出現,不僅加深了我的屈辱,還讓我明白:我的命運,只會越來越黑暗。或許,明天會有更殘酷的遊戲,等著我這條可憐的狗。
喝完那兩泡濃烈的晨尿後,我躺在浴室的冰冷瓷磚上,嘴裡的腥臭味像毒藥般滲進每一個毛孔,胃裡翻滾得像要炸開。麥語心和男主人笑鬧著離開浴室,留我獨自面對這無邊的屈辱。黑暗的視野漸漸清晰,我試著爬起身,膝蓋的麻木和下體的空虛感讓動作變得笨拙而可笑。曾經,我還能幻想自己是個男人,能在女人面前挺起胸膛,可如今,我連站直的資格都沒有,只能像條蟲子般蠕動,舔舐著他們遺留的汙穢。
我強忍著噁心,用抹布擦拭地板上的尿漬,每一灘黃色的液體都像在嘲笑我的墮落。氣味瀰漫在空氣中,腐敗的酸澀味混雜著男主人的濃重腥臭,讓我回想起剛才的遊戲——第一泡是麥語心的,那股微酸而刺鼻的味道,我已熟悉得像烙進骨子裡;第二泡則是男主人的,量大而苦澀,像一股無形的鐵錮,勒緊我的靈魂。吞嚥時,那液體順著喉嚨滑下,灼燒著我的食道,內心的羞辱比疼痛更難忍。為什麼連另一個男人的排洩物,我都要卑微地接受?這比鞭打、比烙印、甚至比閹割都更讓我感到靈魂的崩潰。我曾是個男人,卻淪落到這種地步,尊嚴被踐踏得連渣都不剩。
收拾完浴室,我爬到廚房門口,跪著等待進一步的命令。麥語心和男主人正坐在餐桌邊,吃著我昨晚準備的早餐——新鮮的水果沙拉、煎蛋和咖啡。他們有說有笑,偶爾夾雜著親密的低語,聲音像刀子刺進我的心。男主人夾起一塊煎蛋,咬了一口,滿意地點頭:「寶貝,這蛋煎得不錯。」麥語心笑著瞥了我一眼,語氣輕蔑:「當然,這狗的手藝還行,專門訓練過的。」我低著頭,額頭貼地,不敢抬眼,內心卻湧起一絲苦澀——這些早餐,是我昨晚跪著在廚房忙碌半小時的成果,汗水混著傷口的刺痛滴進鍋裡,卻只換來他們隨意的評價。
吃到一半,麥語心突然轉頭看向我,眼中閃過一抹惡作劇的光芒:「狗,過來。」我順從地爬過去,跪在她腳邊,視線只敢停留在她的拖鞋上。她夾起一塊吃剩的煎蛋殘渣,扔在地上,踩了踩,蛋黃和蛋白混雜著灰塵,變成一灘黏膩的汙物。「吃了吧,這是你的早餐。」她的語氣平淡,卻帶著不容反抗的威嚴。我沒有猶豫,低頭舔食地板上的殘渣,灰塵和蛋黃的混合味在嘴裡蔓延,苦澀而噁心。男主人看著這一幕,輕笑一聲:「寶貝,你這狗還真聽話,不過…讓他吃地上的東西,會不會太髒?」麥語心聳聳肩,笑得肆意:「髒?對他來說,這就是賞賜。狗本來就該吃這些,不是嗎?」
我機械地舔食著,內心的麻木讓我連抗拒的念頭都沒有。男主人似乎被這場景激起了興趣,他也夾起一塊吃剩的麵包屑,扔在地上,語氣試探:「來,吃我的。」我轉向那塊麵包屑,舔食時,腦海裡閃過一絲異樣——這是男主人的食物,混雜著他的口水味,淡淡的鹹澀讓我胃裡一陣翻騰。可我還是吞下,磕頭道:「謝男主人恩典。」他哈哈一笑,眼中多了幾分玩味:「有趣,這狗還挺會謝的。」麥語心滿意地點頭,拉著他的手:「寶貝,你可以把他當玩具,怎麼玩都行。他就是為我們服務的。」
早餐結束後,他們起身去客廳沙發上休息,留下滿桌的殘羹冷炙。我跪著收拾餐桌,擦拭每一滴油漬,每一個指紋,汗水順著背上的鞭痕滑落,火辣辣地疼。收拾完,我爬到客廳門口,跪等命令。麥語心和男主人靠在一起看電視,偶爾低語幾句,氛圍親密得像把我排除在世界之外。突然,男主人轉頭看向我,語氣帶著好奇:「寶貝,你說這狗會不會做按摩?我的肩膀有點酸。」麥語心挑了挑眉,笑著命令:「狗,過來,給男主人按摩肩膀。」我爬過去,跪在他身後,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按壓他的肩部肌肉。他的皮膚結實而溫熱,手感像在觸碰一個強者的象徵,每一下按壓都讓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
按摩到一半,男主人突然哼了一聲,語氣不悅:「力道太輕了,用點勁!」我加大力氣,他卻又皺眉:「太重了,你這狗不會按嗎?」我調整力道,心裡湧起一絲無奈——無論怎麼做,似乎都無法讓他滿意。麥語心看在眼裡,冷笑一聲:「狗,你笨手笨腳的,惹男主人不高興了,該怎麼辦?」我低頭磕頭,聲音顫抖:「賤奴知錯,請男主人懲罰。」男主人愣了一下,隨即笑著看向麥語心:「寶貝,怎麼罰?」她眼中閃過一抹冷酷,起身從櫃子裡拿出皮鞭,遞給他:「用這個,抽他幾下,讓他長記性。」
男主人接過鞭子,試探性地揮了揮,空氣中響起尖利的呼嘯聲。我跪直身體,背對著他,等待懲罰。第一鞭落下,撕裂般的疼痛從背上爆開,舊傷口被重新扯裂,鮮血順著皮膚滑落。我咬緊牙,低聲說:「謝男主人懲罰。」第二鞭、第三鞭接踵而至,每一下都像火燒,鞭痕交錯成網,疼痛讓我全身顫抖。男主人抽了五鞭後停下,語氣帶著興奮:「寶貝,這感覺還挺解壓的。」麥語心笑著抱住他:「當然,以後他就是你的玩具,怎麼玩都行。」
懲罰結束,我跪在地上,背上的血痕火辣辣地疼,汗水混著血水滴落。我低聲道:「謝男主人恩典。」內心的麻木讓我連痛苦都感覺遲鈍,可腦海裡卻閃過一個念頭——現在的我,不僅是麥語心的奴隸,還成了她男友的玩具。這份屈辱,像無形的枷鎖,越勒越緊,讓我喘不過氣。下午,他們讓我繼續家務,我跪著擦拭客廳的每一個角落,汗水浸濕地板,傷口的疼痛讓動作變得緩慢而艱難。男主人偶爾扔來一句命令:「再倒杯水。」或「擦擦我的鞋。」我機械地執行,腦子裡只有空白。
直到傍晚,麥語心揮手讓我離開:「滾吧,後天再來。」我磕頭告退,穿上破舊的衣服,拖著滿身傷痕離開公寓。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夕陽的餘暉灑在身上,卻毫無溫暖。我感到自己正一步步沉淪,這奴役的枷鎖,已將我徹底綁死。男主人的出現,不僅加深了我的屈辱,還讓我明白:我的命運,只會越來越黑暗。或許,明天會有更殘酷的遊戲,等著我這條可憐的狗。
第三十五章:意外的重逢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的生活像一臺生鏽的機器,機械地運轉著。為了填補內心的空虛,我繼續送外賣的工作,每天戴著安全帽,騎著電動車穿梭在城市的街頭巷尾。風從耳邊呼嘯而過,夾雜著汽車尾氣和路邊小吃的香味,可這些都無法掩蓋我心裡的死寂。訂單一單接一單,我不挑活兒,只要能讓自己忙碌起來,就能暫時忘記胸口的「奴」字烙印,忘記下體的空虛,忘記那無盡的奴役。汗水浸濕衣服,傷口的刺痛提醒著我還活著,但活得像一條狗,卑微而無望。
這天中午,我接了一單雙人份的餐點——兩份米飯套餐,外加幾樣小菜和飲料。地址是市中心的一棟公寓樓,我熟練地停好車,提著外賣袋爬上樓梯。敲門時,心裡沒什麼波瀾,只想快點送完,趕下一單。可門一開,我整個人愣住。站在門口的,是趙宜——那個我曾經深愛過的女孩,如今她的頭髮剪短了些,臉上帶著一抹成熟的笑容,穿著簡單的家居服,看起來過得很好。她的眼神掃過我,先是驚訝,隨即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
「小凡?」她低聲叫道,聲音裡帶著不可置信。
我低頭遞上外賣袋,試著讓聲音平穩:「您的餐點,請確認。」目光不經意瞥見門口的鞋架——一雙女式的涼鞋旁邊,放著一雙男士的運動鞋,尺寸很大,顯然不是臨時的訪客。我的心微微一沉,從兩份外賣的份量和這細節看,她已經有新男友了,而且很可能同居。內心瞬間五味雜陳,像被什麼東西狠狠攪拌——羨慕、失落、酸澀交織,可更多的是自嘲和解脫。她過得幸福就好,我現在這個樣子,早已不是個完整的男人,不配擁有一個女人,更不配擁有像她這樣的好女孩。我真心祝福她,雖然這祝福像一把刀,扎在自己心上。
我轉身想走,她卻叫住我:「小凡,等一下。」她的聲音有點顫抖,我停下腳步,低著頭,不敢直視她的眼睛。她關上門,走到走廊,壓低聲音問:「你…還在做那女人的奴嗎?」
我點點頭,喉嚨像被堵住,說不出話來。胸口的烙印隱隱作痛,像在嘲笑我的墮落。
她沉默了片刻,又問:「還…鎖著嗎?」
我又點點頭,雖然事實遠比這殘酷——我的下體早已被麥語心閹割,連那最後的象徵都沒了。可我沒勇氣告訴她,那會讓這場面更尷尬,更讓她看不起我。
趙宜的眼神瞬間變得複雜,隨即,她忽然揚手,給了我一記響亮的耳光。巴掌聲在走廊迴盪,火辣辣的痛感竄上臉頰,我卻沒躲,只是低著頭,任由她發洩。她咬牙切齒,聲音裡滿是憤怒和失望:「張小凡,你真夠賤的!沒想到我竟然喜歡過你這樣的男人。浪費了我那麼多時間,當我知道你是那女人的狗,我懷疑不可置信,我還為了你哭乾了眼淚,你知道嗎?!」
她的話像刀子,一刀刀扎進我的心。我低著頭,滿腦子都是歉疚和自責。曾經的我們,在書店裡的甜蜜時光,如今卻成了她心裡的痛。我知道,我毀了她的信任,毀了我們可能有的未來。「對不起…」我擠出這三個字,聲音沙啞得像從喉嚨裡硬扯出來,然後轉身就走,不敢再多停留一秒。走廊的燈光拉長了我的影子,看起來那麼孤單而可笑。
騎上電動車,我以為這單會收到一星差評,甚至被投訴。可意外的是,手機震動,通知顯示五星好評,還有簡短的評語:「謝謝。」或許在她心裡,還是深深愛著我吧?不然為什麼不報復?這念頭讓我心裡一暖,卻更添自責。我不能給她未來,不能給她一個完整的男人,只能讓她失望,讓她難過。這一切,都是我的錯。
正當我沉浸在自責中,手機又震動了。這次是簡訊,來自麥語心:「二十分鐘內到星聚點KTV來。」短短幾個字,像一道雷擊,讓我全身細胞聳立,冷汗瞬間浸濕背心。星聚點KTV?她要去唱歌?還是帶了朋友?無論如何,我知道不能遲到——上次的懲罰還歷歷在目,那非人性的折磨,讓我寧願死也不想再經歷。我連忙戴上安全帽,發動電動車,飛奔向目的地。風在耳邊呼嘯,心跳快得像要炸開,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千萬別遲到,否則等待我的,將是更深的深淵。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的生活像一臺生鏽的機器,機械地運轉著。為了填補內心的空虛,我繼續送外賣的工作,每天戴著安全帽,騎著電動車穿梭在城市的街頭巷尾。風從耳邊呼嘯而過,夾雜著汽車尾氣和路邊小吃的香味,可這些都無法掩蓋我心裡的死寂。訂單一單接一單,我不挑活兒,只要能讓自己忙碌起來,就能暫時忘記胸口的「奴」字烙印,忘記下體的空虛,忘記那無盡的奴役。汗水浸濕衣服,傷口的刺痛提醒著我還活著,但活得像一條狗,卑微而無望。
這天中午,我接了一單雙人份的餐點——兩份米飯套餐,外加幾樣小菜和飲料。地址是市中心的一棟公寓樓,我熟練地停好車,提著外賣袋爬上樓梯。敲門時,心裡沒什麼波瀾,只想快點送完,趕下一單。可門一開,我整個人愣住。站在門口的,是趙宜——那個我曾經深愛過的女孩,如今她的頭髮剪短了些,臉上帶著一抹成熟的笑容,穿著簡單的家居服,看起來過得很好。她的眼神掃過我,先是驚訝,隨即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
「小凡?」她低聲叫道,聲音裡帶著不可置信。
我低頭遞上外賣袋,試著讓聲音平穩:「您的餐點,請確認。」目光不經意瞥見門口的鞋架——一雙女式的涼鞋旁邊,放著一雙男士的運動鞋,尺寸很大,顯然不是臨時的訪客。我的心微微一沉,從兩份外賣的份量和這細節看,她已經有新男友了,而且很可能同居。內心瞬間五味雜陳,像被什麼東西狠狠攪拌——羨慕、失落、酸澀交織,可更多的是自嘲和解脫。她過得幸福就好,我現在這個樣子,早已不是個完整的男人,不配擁有一個女人,更不配擁有像她這樣的好女孩。我真心祝福她,雖然這祝福像一把刀,扎在自己心上。
我轉身想走,她卻叫住我:「小凡,等一下。」她的聲音有點顫抖,我停下腳步,低著頭,不敢直視她的眼睛。她關上門,走到走廊,壓低聲音問:「你…還在做那女人的奴嗎?」
我點點頭,喉嚨像被堵住,說不出話來。胸口的烙印隱隱作痛,像在嘲笑我的墮落。
她沉默了片刻,又問:「還…鎖著嗎?」
我又點點頭,雖然事實遠比這殘酷——我的下體早已被麥語心閹割,連那最後的象徵都沒了。可我沒勇氣告訴她,那會讓這場面更尷尬,更讓她看不起我。
趙宜的眼神瞬間變得複雜,隨即,她忽然揚手,給了我一記響亮的耳光。巴掌聲在走廊迴盪,火辣辣的痛感竄上臉頰,我卻沒躲,只是低著頭,任由她發洩。她咬牙切齒,聲音裡滿是憤怒和失望:「張小凡,你真夠賤的!沒想到我竟然喜歡過你這樣的男人。浪費了我那麼多時間,當我知道你是那女人的狗,我懷疑不可置信,我還為了你哭乾了眼淚,你知道嗎?!」
她的話像刀子,一刀刀扎進我的心。我低著頭,滿腦子都是歉疚和自責。曾經的我們,在書店裡的甜蜜時光,如今卻成了她心裡的痛。我知道,我毀了她的信任,毀了我們可能有的未來。「對不起…」我擠出這三個字,聲音沙啞得像從喉嚨裡硬扯出來,然後轉身就走,不敢再多停留一秒。走廊的燈光拉長了我的影子,看起來那麼孤單而可笑。
騎上電動車,我以為這單會收到一星差評,甚至被投訴。可意外的是,手機震動,通知顯示五星好評,還有簡短的評語:「謝謝。」或許在她心裡,還是深深愛著我吧?不然為什麼不報復?這念頭讓我心裡一暖,卻更添自責。我不能給她未來,不能給她一個完整的男人,只能讓她失望,讓她難過。這一切,都是我的錯。
正當我沉浸在自責中,手機又震動了。這次是簡訊,來自麥語心:「二十分鐘內到星聚點KTV來。」短短幾個字,像一道雷擊,讓我全身細胞聳立,冷汗瞬間浸濕背心。星聚點KTV?她要去唱歌?還是帶了朋友?無論如何,我知道不能遲到——上次的懲罰還歷歷在目,那非人性的折磨,讓我寧願死也不想再經歷。我連忙戴上安全帽,發動電動車,飛奔向目的地。風在耳邊呼嘯,心跳快得像要炸開,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千萬別遲到,否則等待我的,將是更深的深淵。
第三十六章:王嘉嘉的玩弄
我飛馳在城市的街道上,電動車的馬達嗡嗡作響,心跳卻比引擎還要狂亂。二十分鐘的時限像一把懸在頭頂的劍,稍有遲疑,就可能招來麥語心那非人性的懲罰。星聚點KTV的霓虹燈終於出現在眼前,我喘著粗氣停好車,衝進大廳,詢問櫃台後直奔指定的包廂。推開門的那一刻,空氣中瀰漫著酒精和香水的混合味,昏暗的燈光下,三道身影讓我全身一僵——麥語心、王嘉嘉、駱品萱。她們靠在沙發上,笑鬧著聊天,那熟悉的恐怖面孔像鬼魅般鑽進我的腦海,讓我毛骨悚然。不知道今天她們又要怎麼戲弄我,這種未知的恐懼,像冰冷的針,刺進我的每一個毛孔。
我連忙跪下,分別向她們磕頭行禮,先是麥語心:「主人好。」額頭撞在地上,發出悶響;然後是王嘉嘉:「王嘉嘉大人好。」;最後是駱品萱:「駱品萱大人好。」她們的目光掃過我,像在審視一件玩具,麥語心哼了一聲,沒說話。王嘉嘉卻突然笑起來,眼中閃著惡作劇的光芒:「狗有穿衣服的嗎?還是說你以為自己是人?」她的話像鞭子抽在心上,我一愣,連忙起身脫掉所有衣服,從上衣到褲子,再到內褲,一絲不掛地跪回原地。包廂門沒鎖,隨時可能有服務生進來,可我已經顧不得這些——在麥語心的世界裡,尊嚴本來就不存在,被看到又算什麼?
王嘉嘉滿意地點點頭,從包裡拿出一個東西——一根約10公分的黑色三珠肛塞,表面光滑,珠子從小到大排列,像一串致命的玩具。她晃了晃它,笑著問麥語心:「語心,你玩過後庭調教嗎?」麥語心眼睛一亮,臉頰微微泛紅,搖頭道:「一直都很想玩,但還沒機會試過呢。」駱品萱在旁邊咯咯笑,眼神裡滿是興奮。王嘉嘉得意地介紹起來:「這個肛塞可是三段電動的,保證刺激。」她按下開關,從強到弱的三檔震動模式切換,嗡嗡聲在包廂裡迴盪,珠子顫動得像活了過來。麥語心和駱品萱的臉瞬間通紅,捂嘴偷笑,而我卻如坐針氈,冷汗直冒。想到這個東西馬上就要塞進我的後庭,那種撕裂般的恐懼讓我全身發抖,內心像墜入冰窟。
王嘉嘉轉頭看我,壞笑一聲:「你這隻賤狗,今天算是賺到了,能讓我們三位美女玩你的後庭,多少人求都求不來。」她的話讓我胃裡一陣翻騰,可麥語心已經開口命令:「狗,給我爬到王嘉嘉大人面前,把自己的屁股掰開,求著她玩弄。」雖然心裡千百個不情願,但她的命令不容違抗,我咬牙爬過去,跪在王嘉嘉腳邊,轉過身,將屁股對著她。雙手顫抖著撐開臀部,露出那片從未被侵犯的後庭,低聲乞求:「求王嘉嘉大人玩弄賤狗後庭。」
麥語心似乎不滿意我的表現,她穿著黑色平底鞋,狠狠一腳踢在我屁股上,力道讓我往前一撲,火辣辣的痛感竄上脊背。「屁股不會搖起來?發騷一點,你這賤狗!」她的語氣冷酷而殘忍,我不敢怠慢,強忍著羞恥,搖起屁股,像隻發情的動物,聲音顫抖得更大:「賤狗求王嘉嘉大人玩弄賤狗後庭。」這一幕把她們逗樂了,王嘉嘉笑得前仰後合:「哈哈,看這賤狗搖得像條母狗!」麥語心跟著嘲弄:「對啊,搖得再騷點,沒準我們還賞你點聖水。」駱品萱捂嘴偷笑:「這狗真下賤,屁股露得那麼開,簡直欠玩。」她們的羞辱像雨點砸來,每一句都像刀子割在心上,可我只能低頭承受,腦子裡全是恐懼——接下來會怎樣?這三個女人聯手,絕對不會輕饒我。
就在這時,包廂門突然被推開,一個女服務生闖了進來,手裡提著一箱啤酒。她看到這一幕——我赤裸跪著,屁股撐開對著王嘉嘉,她們三人笑鬧不休——臉瞬間紅得像熟透的蘋果,慌亂地將啤酒放到桌上,轉身就跑了出去,門砰的一聲關上。包廂裡短暫的沉默後爆發出更大的笑聲,王嘉嘉拍著桌子:「哈哈,那服務生肯定嚇壞了!」麥語心笑得喘不過氣:「誰讓這狗這麼騷。」對於被陌生人目睹的羞辱,我已經毫無感覺——做奴隸這麼久,尊嚴早被磨光了。可內心的恐懼卻越來越強,每個細胞都佇立起來,害怕接下來她們的玩弄會是什麼樣的酷刑。這一夜,註定又是一場無盡的折磨。
我飛馳在城市的街道上,電動車的馬達嗡嗡作響,心跳卻比引擎還要狂亂。二十分鐘的時限像一把懸在頭頂的劍,稍有遲疑,就可能招來麥語心那非人性的懲罰。星聚點KTV的霓虹燈終於出現在眼前,我喘著粗氣停好車,衝進大廳,詢問櫃台後直奔指定的包廂。推開門的那一刻,空氣中瀰漫著酒精和香水的混合味,昏暗的燈光下,三道身影讓我全身一僵——麥語心、王嘉嘉、駱品萱。她們靠在沙發上,笑鬧著聊天,那熟悉的恐怖面孔像鬼魅般鑽進我的腦海,讓我毛骨悚然。不知道今天她們又要怎麼戲弄我,這種未知的恐懼,像冰冷的針,刺進我的每一個毛孔。
我連忙跪下,分別向她們磕頭行禮,先是麥語心:「主人好。」額頭撞在地上,發出悶響;然後是王嘉嘉:「王嘉嘉大人好。」;最後是駱品萱:「駱品萱大人好。」她們的目光掃過我,像在審視一件玩具,麥語心哼了一聲,沒說話。王嘉嘉卻突然笑起來,眼中閃著惡作劇的光芒:「狗有穿衣服的嗎?還是說你以為自己是人?」她的話像鞭子抽在心上,我一愣,連忙起身脫掉所有衣服,從上衣到褲子,再到內褲,一絲不掛地跪回原地。包廂門沒鎖,隨時可能有服務生進來,可我已經顧不得這些——在麥語心的世界裡,尊嚴本來就不存在,被看到又算什麼?
王嘉嘉滿意地點點頭,從包裡拿出一個東西——一根約10公分的黑色三珠肛塞,表面光滑,珠子從小到大排列,像一串致命的玩具。她晃了晃它,笑著問麥語心:「語心,你玩過後庭調教嗎?」麥語心眼睛一亮,臉頰微微泛紅,搖頭道:「一直都很想玩,但還沒機會試過呢。」駱品萱在旁邊咯咯笑,眼神裡滿是興奮。王嘉嘉得意地介紹起來:「這個肛塞可是三段電動的,保證刺激。」她按下開關,從強到弱的三檔震動模式切換,嗡嗡聲在包廂裡迴盪,珠子顫動得像活了過來。麥語心和駱品萱的臉瞬間通紅,捂嘴偷笑,而我卻如坐針氈,冷汗直冒。想到這個東西馬上就要塞進我的後庭,那種撕裂般的恐懼讓我全身發抖,內心像墜入冰窟。
王嘉嘉轉頭看我,壞笑一聲:「你這隻賤狗,今天算是賺到了,能讓我們三位美女玩你的後庭,多少人求都求不來。」她的話讓我胃裡一陣翻騰,可麥語心已經開口命令:「狗,給我爬到王嘉嘉大人面前,把自己的屁股掰開,求著她玩弄。」雖然心裡千百個不情願,但她的命令不容違抗,我咬牙爬過去,跪在王嘉嘉腳邊,轉過身,將屁股對著她。雙手顫抖著撐開臀部,露出那片從未被侵犯的後庭,低聲乞求:「求王嘉嘉大人玩弄賤狗後庭。」
麥語心似乎不滿意我的表現,她穿著黑色平底鞋,狠狠一腳踢在我屁股上,力道讓我往前一撲,火辣辣的痛感竄上脊背。「屁股不會搖起來?發騷一點,你這賤狗!」她的語氣冷酷而殘忍,我不敢怠慢,強忍著羞恥,搖起屁股,像隻發情的動物,聲音顫抖得更大:「賤狗求王嘉嘉大人玩弄賤狗後庭。」這一幕把她們逗樂了,王嘉嘉笑得前仰後合:「哈哈,看這賤狗搖得像條母狗!」麥語心跟著嘲弄:「對啊,搖得再騷點,沒準我們還賞你點聖水。」駱品萱捂嘴偷笑:「這狗真下賤,屁股露得那麼開,簡直欠玩。」她們的羞辱像雨點砸來,每一句都像刀子割在心上,可我只能低頭承受,腦子裡全是恐懼——接下來會怎樣?這三個女人聯手,絕對不會輕饒我。
就在這時,包廂門突然被推開,一個女服務生闖了進來,手裡提著一箱啤酒。她看到這一幕——我赤裸跪著,屁股撐開對著王嘉嘉,她們三人笑鬧不休——臉瞬間紅得像熟透的蘋果,慌亂地將啤酒放到桌上,轉身就跑了出去,門砰的一聲關上。包廂裡短暫的沉默後爆發出更大的笑聲,王嘉嘉拍著桌子:「哈哈,那服務生肯定嚇壞了!」麥語心笑得喘不過氣:「誰讓這狗這麼騷。」對於被陌生人目睹的羞辱,我已經毫無感覺——做奴隸這麼久,尊嚴早被磨光了。可內心的恐懼卻越來越強,每個細胞都佇立起來,害怕接下來她們的玩弄會是什麼樣的酷刑。這一夜,註定又是一場無盡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