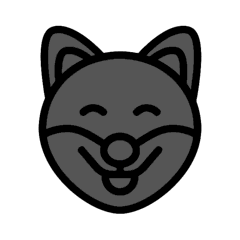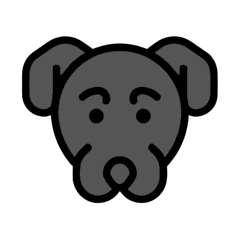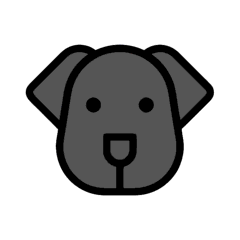男中生被喜欢的女生阉割
阉割连载中原创现实纪实
以下是我在餐馆打工时,从一位同我一起打工的伙伴那里听到的他的事情。由于我自己的某些经历,在我们恰好一起上厕所的时候被他发现了我也有难以启齿的秘密(这一段到全文的最后再细说吧),他才愿意向我敞开,让我听见他这些未对外人讲过的事。下面的文字,是根据他的讲述,由我改写成第一人称的口吻。
我是2019年从一个西部小县城的县初中毕业的。本来我想着,再苦再累,也要靠读书往上走,以后争取去省城深造,有一个能改变命运的资格。这在我们这种家庭里,不是梦想,是赌注。谁都没想到,那一年暑假会成为我人生被硬生生折断的一道分界线。我跟一个有权有势的男生抢他的女朋友,结果在她男友的胁迫下,她亲手阉割了我。
在那件事发生之前,我只是一个西部小县城里普通的少年——农村打工人的儿子,父亲早亡,母亲改嫁,家里只剩奶奶、我和弟弟三个人,还欠了一屁股债。穷,但我读书努力,成绩一直不错。那年我考得还不错好,被录进县一中的重点班。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一条“出去的路”。
但改变一切的,是我和一个女生之间的那次关系。
她叫小琳,和我同村,从小就是同学,有几年甚至是同桌。不是那种引人注目的美,但干净、直率、好相处。我们之间的感觉,总是停在一种“彼此知道却不说破”的模糊边界里。她会笑我像外地人,不像本地的男孩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这样看我。不过我那个时候刚在迅猛的发育期,在学校爱打篮球,一身的腱子肉,长的也还不错。她的关注对我而言,是那样隐秘的温柔。
只是我一直觉得我们不可能。她家做小生意,日子比我们家宽裕得多。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有一个男朋友——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儿子,中学一毕业就被他爸安排进了警校。小琳一直不告诉我他俩怎么认识的。但那意味着什么,在我们这里所有人都懂:她如果以后跟着那个小子,人生就可以被安排的很好,她的未来可以在体制和资源里;而我家的未来在土里,在债里,在命里写着的“别惹事”。她男朋友比我们大两岁,是个天生的混子,打架斗殴泡妞什么都干,只是到了警校以后才稍微有所收敛。
在我拿到县一中录取通知书那天,她告诉我:她考的不好,准备去县城另一头的一个职高,离县一中骑车要一个多小时。她说得轻描淡写,可我心里像被掐住了一样。那天深夜,我们在河坝边上走着,谁也没提未来。我只告诉她我很心疼她,为什么要跟那个像流氓一样的家伙在一起。夜深了,我们在附近一个很少人去的草丛里坐下,空气闷热,她穿着白T恤,月光打在她脸上,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这样坐在一起。我的心砰砰直跳,在她再次开始说话前,我鼓起勇气强吻了过去,然后把她扑倒在草丛里。夏天我们穿的都少。我一扑下去短裤里马上就感觉到湿了,下面也硬到像要爆炸似的。碰着她绵软的肉体便完全把持不住了,她的身体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但是紧接着就在我壮硕的肉体和激情的攻势下完全投降 ——青春期的荷尔蒙、离别和压抑的感情、对命运的不甘交织在一起……反正该发生的就发生了。
但偏偏就在那个夜晚,我们从草丛里出来正衣衫不整的时候,她男朋友的一个室友在外面喝了酒,恰好经过草丛想要小解,看见了我们。我并不认识他,还是后来小琳略带惊恐地告诉了我。
那一眼,把我从一个想改变自己命运的普通少年,推向了深渊。
我是2019年从一个西部小县城的县初中毕业的。本来我想着,再苦再累,也要靠读书往上走,以后争取去省城深造,有一个能改变命运的资格。这在我们这种家庭里,不是梦想,是赌注。谁都没想到,那一年暑假会成为我人生被硬生生折断的一道分界线。我跟一个有权有势的男生抢他的女朋友,结果在她男友的胁迫下,她亲手阉割了我。
在那件事发生之前,我只是一个西部小县城里普通的少年——农村打工人的儿子,父亲早亡,母亲改嫁,家里只剩奶奶、我和弟弟三个人,还欠了一屁股债。穷,但我读书努力,成绩一直不错。那年我考得还不错好,被录进县一中的重点班。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一条“出去的路”。
但改变一切的,是我和一个女生之间的那次关系。
她叫小琳,和我同村,从小就是同学,有几年甚至是同桌。不是那种引人注目的美,但干净、直率、好相处。我们之间的感觉,总是停在一种“彼此知道却不说破”的模糊边界里。她会笑我像外地人,不像本地的男孩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这样看我。不过我那个时候刚在迅猛的发育期,在学校爱打篮球,一身的腱子肉,长的也还不错。她的关注对我而言,是那样隐秘的温柔。
只是我一直觉得我们不可能。她家做小生意,日子比我们家宽裕得多。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有一个男朋友——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儿子,中学一毕业就被他爸安排进了警校。小琳一直不告诉我他俩怎么认识的。但那意味着什么,在我们这里所有人都懂:她如果以后跟着那个小子,人生就可以被安排的很好,她的未来可以在体制和资源里;而我家的未来在土里,在债里,在命里写着的“别惹事”。她男朋友比我们大两岁,是个天生的混子,打架斗殴泡妞什么都干,只是到了警校以后才稍微有所收敛。
在我拿到县一中录取通知书那天,她告诉我:她考的不好,准备去县城另一头的一个职高,离县一中骑车要一个多小时。她说得轻描淡写,可我心里像被掐住了一样。那天深夜,我们在河坝边上走着,谁也没提未来。我只告诉她我很心疼她,为什么要跟那个像流氓一样的家伙在一起。夜深了,我们在附近一个很少人去的草丛里坐下,空气闷热,她穿着白T恤,月光打在她脸上,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这样坐在一起。我的心砰砰直跳,在她再次开始说话前,我鼓起勇气强吻了过去,然后把她扑倒在草丛里。夏天我们穿的都少。我一扑下去短裤里马上就感觉到湿了,下面也硬到像要爆炸似的。碰着她绵软的肉体便完全把持不住了,她的身体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但是紧接着就在我壮硕的肉体和激情的攻势下完全投降 ——青春期的荷尔蒙、离别和压抑的感情、对命运的不甘交织在一起……反正该发生的就发生了。
但偏偏就在那个夜晚,我们从草丛里出来正衣衫不整的时候,她男朋友的一个室友在外面喝了酒,恰好经过草丛想要小解,看见了我们。我并不认识他,还是后来小琳略带惊恐地告诉了我。
那一眼,把我从一个想改变自己命运的普通少年,推向了深渊。
clt295173135血流成河发布于 2025-11-30 19:53
Re: Re: 男中生被喜欢的女生阉割
第二天我从家里一出门就去找小琳,我明知是自投罗网,但是实在是头脑发热,在路上就被几个穿着警校服装的小青年堵住,然后他们三手两脚地把我架到旁边的建筑工地后面的一个院子里。
院子里有辆旧警车,门开着,她男朋友就坐在后座上抽烟。我认得他,县里很多人私底下都叫他“王少”。他长得很像他那个当副局长的爹,方脸阔嘴,但眼神里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戾气。那时他刚从警校回来过暑假,穿着一件黑色的短袖制服,没戴帽子,手里把玩着一副亮晃晃的手铐。
“哟,中学生来了?”他吐了个烟圈,斜着眼看我,嘴角挂着嘲弄的笑。旁边几个跟班也跟着哄笑起来。我攥紧了拳头,指甲陷进掌心,但没吭声。我知道,这时候任何一句辩解或反抗,都只会让事情更糟。
小琳被他们带过来,站在不远处的一堆砖块旁,低着头,肩膀在发抖。王少,用夹着烟的手指点了点她,又指了指我:“听说,你俩昨晚上,在河坝边上,搞破鞋?”
他的话粗俗得像一把生锈的刀子,刮着我的耳膜。我血往头上涌,几乎要冲上去,但被旁边两个人死死按住。
“没有!”小琳猛地抬起头,脸上毫无血色,声音却带着哭腔,“我们什么都没干!他就是……就是……”
“就是什么?”王少慢悠悠地打断她,从车上下来,走到我面前。他比我高半头,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就是忍不住,想尝尝鲜?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他伸手,用烟头虚虚地点了点我胸口廉价T恤上的破洞,“一个死了爹,妈跟别人跑的穷鬼,也敢动老子的女人?”
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扎进我早已千疮百孔的自尊里。我能感觉到奶奶起早贪黑卖菜攒下的钱给我买的这件T恤,在他眼里是多么可笑。我能想象,弟弟还在家里眼巴巴等着我这个“有出息”的哥哥回去,而我却在这里,像条狗一样被人羞辱。
“我跟你说话呢,聋了?”他见我不答,猛地一巴掌扇在我脸上。力道很大,我耳朵嗡嗡作响,嘴里泛起血腥味。
“别打他!”小琳尖叫着想冲过来,被人拽住。
王少似乎更来劲了,他揪住我的头发,迫使我对上他狰狞的脸:“你不是能吗?不是靠读书要飞出这穷山沟吗?我告诉你,在这县城,老子就是法!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那个重点班的名额,变成一张废纸?让你奶奶在菜市场,连个摆摊的地儿都没有?”
他的话,击碎了我最后一点侥幸。我知道,他不是在吓唬我。他爸是公安局副局长,在这个小地方,手眼通天。碾死我这样毫无背景的家庭,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我的前途,我全家那点渺茫的希望,在他眼里,不过是可以随意践踏的玩意儿。
“跪下。”他松开我的头发,冷冷地命令。
我站着没动,全身的骨头都在叫嚣着反抗,但脑子里却是一片冰冷的空白。我想起奶奶佝偻的背,想起弟弟渴求知识的眼睛,想起母亲改嫁时头也不回的背影,想起父亲早亡后家里那一屁股仿佛永远也还不清的债……所有的画面绞在一起,勒得我几乎窒息。
“我让你跪下!”旁边一个跟班狠狠踹在我腿弯处。剧痛传来,我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但还是硬撑着。
王少似乎失去了耐心,他示意了一下。几个人把我死死按倒在地,粗糙的水泥地磨破了我的膝盖和手掌。屈辱的火焰灼烧着我的五脏六腑,但我咬紧了牙,没让那声哽咽冲出来。
他走到我面前,锃亮的皮鞋尖就在我眼皮底下。他弯下腰,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小子,记住今天。记住你这身贱骨头,只配趴在地上。呵,你这种人的命,生下来就刻在泥巴里了!” 我双目圆睁瞪着他,但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猛地对着我的裆部就是一脚。我夏天只穿着一条薄短裤,两条腿跪在地上完全岔开着,生殖器在完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被他重重一脚,我闷哼一声,身体不受控制地弓起来,眼前黑雾弥漫,五脏六腑搅成了一团,恶心得只想吐,却连一丝气都抽不上来。
他收回脚,锃亮的皮鞋尖在我模糊的视线里只是晃了晃。吓的我双腿直打哆嗦。水泥地的粗砺硌着我的侧脸,灰尘和铁锈味呛进鼻腔。然后,他侧过身,对着一直僵在砖堆旁的小琳抬了抬下巴。
“你来。”
王少声音不高,却像钝刀子割开凝滞的空气。小琳猛地抬起头,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褪尽了。她看看王少,又看看蜷在地上的我,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挤不出来,只是拼命摇头,小小的身体往后缩,背脊几乎要抵进粗糙的砖缝里。
“我让你来。”王少重复了一遍,这次,每个字都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带着不容置疑的寒气。他没提高音量,可那双眼睛盯着小琳,里头没有一点温度,只有一种猫戏老鼠般的、残忍的耐心,又像是淬了毒的冰锥,缓慢而坚定地凿着她的抗拒。
院子里的风好像停了,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我的,还有小琳压抑的抽气。那几个跟班有几个抓起我的胳膊把我上半身提起来,有几个用手使劲把我的大腿分开。脸上挂着看好戏的麻木。
小琳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大颗大颗滚落,划过她苍白的脸颊。她看看王少冰冷的侧脸,又低头看向我。我的视线模糊,只能看到她剧烈颤抖的轮廓,像秋风里最后一片叶子。时间被拉长了,每一秒都灌满了铅。终于,在王少彻底失去耐心、眉头拧起的前一瞬,小琳极其缓慢地、一点点地挪动了脚步。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身体僵硬得像块木头,只有眼泪无声地淌得更凶。
她停在我面前,离得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熟悉的皂角味,混着此刻浓重的恐惧和汗味。她低着头,视线落在我的裆部,那里还残留着王少踢踹后火辣辣的钝痛。
她抬起脚,穿着白色帆布鞋的脚尖,极其轻微地、试探性地碰了碰我的下体。那触碰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像一片羽毛拂过,带着无法控制的战栗。不是踢,甚至不是碰,更像一种无意识的、绝望的触碰。
“没吃饭?”
王少的声音突兀地响起,不高,平平的三个字,却像三颗冰雹砸在死寂的院子里。没有怒气,只有一种极致的寒冷和轻蔑,比任何咆哮都让人胆寒。
小琳浑身一颤,像被电击了。她猛地闭上眼睛,泪水从紧闭的眼帘下汹涌而出。那一瞬间,她脸上闪过很多情绪——痛苦的挣扎,深切的恐惧,还有一丝我无法看清的、决绝的东西。然后,她吸了一口气,那气息破碎不堪。再次抬起的脚,终于带上了明确的力道。
那一脚正中我的左卵蛋,力道明确了,却仍带着犹豫的滞涩,像钝刀割肉,不算利落。疼痛在我的要害部分闷闷地扩散开,但比疼痛更清晰的,是小琳脚尖传来的、无法抑制的颤抖。我咬紧牙关,满脸通红。而王少显然不满意。他嘴角那点嘲弄的弧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更不耐烦的阴冷。他没再说话,只是往前踏了一步,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轻微的声响。他伸手过去,不是打她,而是用两根手指,抬起了小琳的下巴,迫使她不得不看着他。小琳的眼泪还在流,被迫仰起的脸上满是湿痕,眼睛紧闭着,睫毛抖得像风中的蝶翼。
“睁开眼睛。”王少的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成了耳语,却每个字都像冰针,扎进人的骨头缝里,“你要在不听话。我让他把那天在草丛里,怎么像狗一样日你的在这儿再给我和兄弟们表演一遍!”
小琳猛地睁开了眼睛,瞳孔里映着王少冰冷的面孔,还有他身后那片灰蒙蒙的天。那里面最后一点挣扎的光,像被狂风吹熄的蜡烛,迅速暗了下去,只剩下空茫茫的恐惧,和一种认命般的死寂。王少松开手,往后退了半步,抱着胳膊,像一个耐心即将耗尽的监工。小琳转回头,重新看向我。这一次,她的眼神不一样了。不再是痛苦和挣扎,而是一种空洞的、仿佛看向某个没有生命物体的麻木。泪水还在流,但脸上已经没有了表情。
她深吸了一口气,那气息不再只是破碎,而是带着一种奇怪的、狠绝的意味。然后,她抬起脚。这一次,速度快了,动作也少了犹豫。帆布鞋的鞋尖,带着比之前重的多的力道,狠狠地踢在我的阴囊上。没等我反应过来,她紧着又是一脚,力道更大了。
“啊啊……”我闷哼出声,身体不受控制地侧蜷,我的左睾丸结实地挨了她的两下。我知道小琳在家里干农活,脚上有些力气,但是没想到她的腿脚可以那么地有力。那两脚踢得我差点岔气,钝痛仿佛一颗闷雷在阴囊里炸开。睾丸像被灌进熔铅般灼烧痉挛,肠子像电击似的抽搐,每一次失败的呼吸都牵引着整个躯干的剧痛。后背对应位置也传来尖锐的共鸣痛,仿佛那每一脚的力量穿透身体在脊椎上反弹。我膝盖发软,视线模糊泛黑,冷汗瞬间浸透了短裤。我想蜷缩,但卵蛋的剧痛让我连弯腰都像在撕裂自己。恶心感毫无征兆地涌上喉咙,混合着胆汁的酸苦味。我控制不住地干呕,每一次呕吐的尝试都让腹内遭受新一轮撕裂般的折磨。我在地上蜷缩的像虾米一样,短裤也因为我的挣扎而磨破了。水泥地的冰凉和粗糙摩擦着阴囊的伤处。我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只有喉咙里嘶哑的抽气声。世界在那半秒内陷入诡异的寂静和空白。我完全瘫软了,双腿发抖,全身像泥鳅一样滑在地上。但我最痛苦的不是疼,而是小琳当众羞辱我的下体的那种无助和屈辱,对一个男人再没有比这更残忍的了。
王少在旁边冷冷地说:”这还差的远。今天你们得给我个交代。“他转向小琳接着说:”要不这样。我要那小子一样东西,以后也就不计较了。“ 王少慢条斯理,声音不高:”今天,就在这儿,你亲手把这小子阉了。“
这一番话好像鞭子一样抽打在小琳身上。小琳浑身又是一颤,嘴唇咬得死白。她脸上空白的麻木。她没再看王少,也没再看我。王少紧着着给他的兄弟使了个眼色。他们七手八脚把我的短裤和内裤完全扒掉,我羞愤难当,但下体疼痛无比,根本没有反抗他们的力气。我的卵蛋顿时暴露在空气中,看得出来已经被踢的有些红肿,发育的还不错的阴茎黑乎乎的,毫无生气地吊在裆间。
”嘿,还是个大家伙。“ 王少的这个弟兄看上去也就十七八岁,他说罢,从腰间拔出一个警棍,对着我的下体就是两下,疼得我连连大叫。”老大说的对,不废了这家伙,以后成年了还不知祸害多少其他姑娘。“
然后,他从其中另一人身后抽出一把水果刀,丢在地上。我下意识地捂住了下体。恐惧和羞耻让我不能自已地颤抖着。
王少接着对小琳说:“我知道你们家也做些这种活。如果你今天不把他阉了。我们明天就上门到你们家去!”
我瞪大眼睛看着小琳,没有完全明白王少在说什么。王少转过来,微笑地说:”他们家卖猪肉的,会阉猪。阉过的猪就不会到处惹祸乱发情,会很听话的。今天就让她在你那个脏东西上头也试试手艺吧。哈哈哈!“
他的意思已经足够明白。我绝望地看着小琳。小琳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恐惧,有愧疚,还有一丝我无法理解的复杂情绪,但最终,她转过了身,慢慢地捡起了地上那把刀。我瘫坐在地上,他的几个同伙把我拽起来。我眼睁睁地看着小琳拿着那把水果刀像我走过来。
院子里有辆旧警车,门开着,她男朋友就坐在后座上抽烟。我认得他,县里很多人私底下都叫他“王少”。他长得很像他那个当副局长的爹,方脸阔嘴,但眼神里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戾气。那时他刚从警校回来过暑假,穿着一件黑色的短袖制服,没戴帽子,手里把玩着一副亮晃晃的手铐。
“哟,中学生来了?”他吐了个烟圈,斜着眼看我,嘴角挂着嘲弄的笑。旁边几个跟班也跟着哄笑起来。我攥紧了拳头,指甲陷进掌心,但没吭声。我知道,这时候任何一句辩解或反抗,都只会让事情更糟。
小琳被他们带过来,站在不远处的一堆砖块旁,低着头,肩膀在发抖。王少,用夹着烟的手指点了点她,又指了指我:“听说,你俩昨晚上,在河坝边上,搞破鞋?”
他的话粗俗得像一把生锈的刀子,刮着我的耳膜。我血往头上涌,几乎要冲上去,但被旁边两个人死死按住。
“没有!”小琳猛地抬起头,脸上毫无血色,声音却带着哭腔,“我们什么都没干!他就是……就是……”
“就是什么?”王少慢悠悠地打断她,从车上下来,走到我面前。他比我高半头,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就是忍不住,想尝尝鲜?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他伸手,用烟头虚虚地点了点我胸口廉价T恤上的破洞,“一个死了爹,妈跟别人跑的穷鬼,也敢动老子的女人?”
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扎进我早已千疮百孔的自尊里。我能感觉到奶奶起早贪黑卖菜攒下的钱给我买的这件T恤,在他眼里是多么可笑。我能想象,弟弟还在家里眼巴巴等着我这个“有出息”的哥哥回去,而我却在这里,像条狗一样被人羞辱。
“我跟你说话呢,聋了?”他见我不答,猛地一巴掌扇在我脸上。力道很大,我耳朵嗡嗡作响,嘴里泛起血腥味。
“别打他!”小琳尖叫着想冲过来,被人拽住。
王少似乎更来劲了,他揪住我的头发,迫使我对上他狰狞的脸:“你不是能吗?不是靠读书要飞出这穷山沟吗?我告诉你,在这县城,老子就是法!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那个重点班的名额,变成一张废纸?让你奶奶在菜市场,连个摆摊的地儿都没有?”
他的话,击碎了我最后一点侥幸。我知道,他不是在吓唬我。他爸是公安局副局长,在这个小地方,手眼通天。碾死我这样毫无背景的家庭,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我的前途,我全家那点渺茫的希望,在他眼里,不过是可以随意践踏的玩意儿。
“跪下。”他松开我的头发,冷冷地命令。
我站着没动,全身的骨头都在叫嚣着反抗,但脑子里却是一片冰冷的空白。我想起奶奶佝偻的背,想起弟弟渴求知识的眼睛,想起母亲改嫁时头也不回的背影,想起父亲早亡后家里那一屁股仿佛永远也还不清的债……所有的画面绞在一起,勒得我几乎窒息。
“我让你跪下!”旁边一个跟班狠狠踹在我腿弯处。剧痛传来,我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但还是硬撑着。
王少似乎失去了耐心,他示意了一下。几个人把我死死按倒在地,粗糙的水泥地磨破了我的膝盖和手掌。屈辱的火焰灼烧着我的五脏六腑,但我咬紧了牙,没让那声哽咽冲出来。
他走到我面前,锃亮的皮鞋尖就在我眼皮底下。他弯下腰,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小子,记住今天。记住你这身贱骨头,只配趴在地上。呵,你这种人的命,生下来就刻在泥巴里了!” 我双目圆睁瞪着他,但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猛地对着我的裆部就是一脚。我夏天只穿着一条薄短裤,两条腿跪在地上完全岔开着,生殖器在完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被他重重一脚,我闷哼一声,身体不受控制地弓起来,眼前黑雾弥漫,五脏六腑搅成了一团,恶心得只想吐,却连一丝气都抽不上来。
他收回脚,锃亮的皮鞋尖在我模糊的视线里只是晃了晃。吓的我双腿直打哆嗦。水泥地的粗砺硌着我的侧脸,灰尘和铁锈味呛进鼻腔。然后,他侧过身,对着一直僵在砖堆旁的小琳抬了抬下巴。
“你来。”
王少声音不高,却像钝刀子割开凝滞的空气。小琳猛地抬起头,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褪尽了。她看看王少,又看看蜷在地上的我,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挤不出来,只是拼命摇头,小小的身体往后缩,背脊几乎要抵进粗糙的砖缝里。
“我让你来。”王少重复了一遍,这次,每个字都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带着不容置疑的寒气。他没提高音量,可那双眼睛盯着小琳,里头没有一点温度,只有一种猫戏老鼠般的、残忍的耐心,又像是淬了毒的冰锥,缓慢而坚定地凿着她的抗拒。
院子里的风好像停了,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我的,还有小琳压抑的抽气。那几个跟班有几个抓起我的胳膊把我上半身提起来,有几个用手使劲把我的大腿分开。脸上挂着看好戏的麻木。
小琳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大颗大颗滚落,划过她苍白的脸颊。她看看王少冰冷的侧脸,又低头看向我。我的视线模糊,只能看到她剧烈颤抖的轮廓,像秋风里最后一片叶子。时间被拉长了,每一秒都灌满了铅。终于,在王少彻底失去耐心、眉头拧起的前一瞬,小琳极其缓慢地、一点点地挪动了脚步。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身体僵硬得像块木头,只有眼泪无声地淌得更凶。
她停在我面前,离得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熟悉的皂角味,混着此刻浓重的恐惧和汗味。她低着头,视线落在我的裆部,那里还残留着王少踢踹后火辣辣的钝痛。
她抬起脚,穿着白色帆布鞋的脚尖,极其轻微地、试探性地碰了碰我的下体。那触碰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像一片羽毛拂过,带着无法控制的战栗。不是踢,甚至不是碰,更像一种无意识的、绝望的触碰。
“没吃饭?”
王少的声音突兀地响起,不高,平平的三个字,却像三颗冰雹砸在死寂的院子里。没有怒气,只有一种极致的寒冷和轻蔑,比任何咆哮都让人胆寒。
小琳浑身一颤,像被电击了。她猛地闭上眼睛,泪水从紧闭的眼帘下汹涌而出。那一瞬间,她脸上闪过很多情绪——痛苦的挣扎,深切的恐惧,还有一丝我无法看清的、决绝的东西。然后,她吸了一口气,那气息破碎不堪。再次抬起的脚,终于带上了明确的力道。
那一脚正中我的左卵蛋,力道明确了,却仍带着犹豫的滞涩,像钝刀割肉,不算利落。疼痛在我的要害部分闷闷地扩散开,但比疼痛更清晰的,是小琳脚尖传来的、无法抑制的颤抖。我咬紧牙关,满脸通红。而王少显然不满意。他嘴角那点嘲弄的弧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更不耐烦的阴冷。他没再说话,只是往前踏了一步,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轻微的声响。他伸手过去,不是打她,而是用两根手指,抬起了小琳的下巴,迫使她不得不看着他。小琳的眼泪还在流,被迫仰起的脸上满是湿痕,眼睛紧闭着,睫毛抖得像风中的蝶翼。
“睁开眼睛。”王少的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成了耳语,却每个字都像冰针,扎进人的骨头缝里,“你要在不听话。我让他把那天在草丛里,怎么像狗一样日你的在这儿再给我和兄弟们表演一遍!”
小琳猛地睁开了眼睛,瞳孔里映着王少冰冷的面孔,还有他身后那片灰蒙蒙的天。那里面最后一点挣扎的光,像被狂风吹熄的蜡烛,迅速暗了下去,只剩下空茫茫的恐惧,和一种认命般的死寂。王少松开手,往后退了半步,抱着胳膊,像一个耐心即将耗尽的监工。小琳转回头,重新看向我。这一次,她的眼神不一样了。不再是痛苦和挣扎,而是一种空洞的、仿佛看向某个没有生命物体的麻木。泪水还在流,但脸上已经没有了表情。
她深吸了一口气,那气息不再只是破碎,而是带着一种奇怪的、狠绝的意味。然后,她抬起脚。这一次,速度快了,动作也少了犹豫。帆布鞋的鞋尖,带着比之前重的多的力道,狠狠地踢在我的阴囊上。没等我反应过来,她紧着又是一脚,力道更大了。
“啊啊……”我闷哼出声,身体不受控制地侧蜷,我的左睾丸结实地挨了她的两下。我知道小琳在家里干农活,脚上有些力气,但是没想到她的腿脚可以那么地有力。那两脚踢得我差点岔气,钝痛仿佛一颗闷雷在阴囊里炸开。睾丸像被灌进熔铅般灼烧痉挛,肠子像电击似的抽搐,每一次失败的呼吸都牵引着整个躯干的剧痛。后背对应位置也传来尖锐的共鸣痛,仿佛那每一脚的力量穿透身体在脊椎上反弹。我膝盖发软,视线模糊泛黑,冷汗瞬间浸透了短裤。我想蜷缩,但卵蛋的剧痛让我连弯腰都像在撕裂自己。恶心感毫无征兆地涌上喉咙,混合着胆汁的酸苦味。我控制不住地干呕,每一次呕吐的尝试都让腹内遭受新一轮撕裂般的折磨。我在地上蜷缩的像虾米一样,短裤也因为我的挣扎而磨破了。水泥地的冰凉和粗糙摩擦着阴囊的伤处。我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只有喉咙里嘶哑的抽气声。世界在那半秒内陷入诡异的寂静和空白。我完全瘫软了,双腿发抖,全身像泥鳅一样滑在地上。但我最痛苦的不是疼,而是小琳当众羞辱我的下体的那种无助和屈辱,对一个男人再没有比这更残忍的了。
王少在旁边冷冷地说:”这还差的远。今天你们得给我个交代。“他转向小琳接着说:”要不这样。我要那小子一样东西,以后也就不计较了。“ 王少慢条斯理,声音不高:”今天,就在这儿,你亲手把这小子阉了。“
这一番话好像鞭子一样抽打在小琳身上。小琳浑身又是一颤,嘴唇咬得死白。她脸上空白的麻木。她没再看王少,也没再看我。王少紧着着给他的兄弟使了个眼色。他们七手八脚把我的短裤和内裤完全扒掉,我羞愤难当,但下体疼痛无比,根本没有反抗他们的力气。我的卵蛋顿时暴露在空气中,看得出来已经被踢的有些红肿,发育的还不错的阴茎黑乎乎的,毫无生气地吊在裆间。
”嘿,还是个大家伙。“ 王少的这个弟兄看上去也就十七八岁,他说罢,从腰间拔出一个警棍,对着我的下体就是两下,疼得我连连大叫。”老大说的对,不废了这家伙,以后成年了还不知祸害多少其他姑娘。“
然后,他从其中另一人身后抽出一把水果刀,丢在地上。我下意识地捂住了下体。恐惧和羞耻让我不能自已地颤抖着。
王少接着对小琳说:“我知道你们家也做些这种活。如果你今天不把他阉了。我们明天就上门到你们家去!”
我瞪大眼睛看着小琳,没有完全明白王少在说什么。王少转过来,微笑地说:”他们家卖猪肉的,会阉猪。阉过的猪就不会到处惹祸乱发情,会很听话的。今天就让她在你那个脏东西上头也试试手艺吧。哈哈哈!“
他的意思已经足够明白。我绝望地看着小琳。小琳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恐惧,有愧疚,还有一丝我无法理解的复杂情绪,但最终,她转过了身,慢慢地捡起了地上那把刀。我瘫坐在地上,他的几个同伙把我拽起来。我眼睁睁地看着小琳拿着那把水果刀像我走过来。
小琳脸上的表情反而冷静得可怕。我分不清她是故作镇定,还是既然不得不做,就只能剥离任何情感的专注——既然非得对我下手不可,那就得做得专业,做得漂亮(但也许这只是我自己安慰自己的理解吧?)。她甚至微微调整了一下呼吸的节奏,让每一次吸气都平稳绵长。
“把你们的鞋带解下来,给我两根。”她对王少那几个在一旁看热闹的弟兄说,声音没有起伏,镇定的可怕。目光扫过旁边警务室里简陋的柜子,“还有,把医用酒精拿来。”
王少扯了扯嘴角,习惯性的那点恶劣的趣味又冒了头:“哎哟,琳妹妹,你要这些玩意儿干嘛?给他打扮打扮呀?“
小琳甚至没正眼看他,只是侧过头,用冷淡语调说:“你要不想让他死了,你也不想接着进局子的话,就配合我一点。”每个字都像淬了冰的钉子,轻轻落下。王少张了张嘴,不耐烦地挥挥手让手下照办。那一刻,发号施令的变成了这个看似柔弱、此刻却掌控着所有人节奏的女孩。
酒精瓶被递过来,小琳拧开盖子。浓烈刺鼻的气味猛地窜出来,钻进我的鼻腔。她没有任何犹豫,将透明的液体倒她手上,然后,冰凉的触感毫无预兆地从我裸露的下体涌上来,带着一种果断的的用力,擦过我的阴茎根部和蛋囊上。
“嘶——” 凉,那是第一重的感觉,酒精激得我浑身一颤。我能听见自己心脏在耳膜里擂鼓,咚咚咚咚,又快又乱,血液好像都冲到了头顶,太阳穴突突地跳。视线里,是小琳低垂的、睫毛都不曾颤动一下的侧脸,她的手指很稳,动作没有任何暧昧或迟疑,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专注。这比王少之前的嘲弄和虐待更让我感到一种无处遁形的羞耻和恐慌——我狼狈的身体在她手中,现在只是一支马上要被阉掉的牲口。我感到冷汗顺着脊梁沟滑下去,手心也一片湿黏。
然后,她的手探了过来,握住了我那已经因疼痛、温度,和恐惧而萎缩的那话儿,连同下面缩进去的蛋儿。指头不可避免地触碰着我最敏感的皮肤。那双手曾经给过我那个地方以多么销魂的抚慰,但没想到现在夺走我男性器官的也将要是这只看似瘦弱的纤纤玉手。我全身的肌肉乱颤着,呼吸也全乱了。
她开始用力,使劲地把我的整个生殖器和蛋囊向外拉扯、揪出来。那是一种极其怪异而清晰的痛楚,混合着肿胀感、被牵扯的钝痛,我的男儿尊严被彻底剥开。我咬紧牙关,齿缝间带着颤音。
鞋带递了过来,粗糙的质感掠过我的阴囊。她把两根鞋带绕在根部,缠绕,然后猛地勒紧!
“呃啊——!” 一声短促的痛呼还是冲破了喉咙。那是一种窒息的捆缚感,像是所有的血液和疼痛都被死死勒在了那一道粗糙的束缚之下,脉搏在鞋带下疯狂冲撞。钝痛变成了一阵绞痛。我挣扎着,但王少的几个弟兄把我狠狠地按在地上,几个人又把我的双腿扒开束缚在半空中,让我在这种尴尬的姿势下完全不能动弹。
整个过程,小琳没有看我的眼睛。她只是低着头,检查着鞋带的结是否牢固。她的冷静,像一层厚重的冰壳,封住了所有的嘈杂和情绪,也把我所有的恐惧、羞耻、乃至最后一点侥幸,都冻在了里面。空气里只剩下酒精味、我的汗味,和我自己无法控制的、粗重颤抖的呼吸声。
忽然她看了我一眼,嘴唇凑过来轻轻地在我耳边说,“你准备好。我会很快的。” 她终于对我说了句人话,虽然声音平直,冷的可怕。而我知道,最痛苦的部分将要开始了。我嗓子里冒着哭腔,骨头里都是冷的,浑身都在发抖,牙齿不住地打岔。
我看着她从根部使劲往上揪着我的阴茎,然后水果刀向我的蛋囊的下方切了进去。
“把你们的鞋带解下来,给我两根。”她对王少那几个在一旁看热闹的弟兄说,声音没有起伏,镇定的可怕。目光扫过旁边警务室里简陋的柜子,“还有,把医用酒精拿来。”
王少扯了扯嘴角,习惯性的那点恶劣的趣味又冒了头:“哎哟,琳妹妹,你要这些玩意儿干嘛?给他打扮打扮呀?“
小琳甚至没正眼看他,只是侧过头,用冷淡语调说:“你要不想让他死了,你也不想接着进局子的话,就配合我一点。”每个字都像淬了冰的钉子,轻轻落下。王少张了张嘴,不耐烦地挥挥手让手下照办。那一刻,发号施令的变成了这个看似柔弱、此刻却掌控着所有人节奏的女孩。
酒精瓶被递过来,小琳拧开盖子。浓烈刺鼻的气味猛地窜出来,钻进我的鼻腔。她没有任何犹豫,将透明的液体倒她手上,然后,冰凉的触感毫无预兆地从我裸露的下体涌上来,带着一种果断的的用力,擦过我的阴茎根部和蛋囊上。
“嘶——” 凉,那是第一重的感觉,酒精激得我浑身一颤。我能听见自己心脏在耳膜里擂鼓,咚咚咚咚,又快又乱,血液好像都冲到了头顶,太阳穴突突地跳。视线里,是小琳低垂的、睫毛都不曾颤动一下的侧脸,她的手指很稳,动作没有任何暧昧或迟疑,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专注。这比王少之前的嘲弄和虐待更让我感到一种无处遁形的羞耻和恐慌——我狼狈的身体在她手中,现在只是一支马上要被阉掉的牲口。我感到冷汗顺着脊梁沟滑下去,手心也一片湿黏。
然后,她的手探了过来,握住了我那已经因疼痛、温度,和恐惧而萎缩的那话儿,连同下面缩进去的蛋儿。指头不可避免地触碰着我最敏感的皮肤。那双手曾经给过我那个地方以多么销魂的抚慰,但没想到现在夺走我男性器官的也将要是这只看似瘦弱的纤纤玉手。我全身的肌肉乱颤着,呼吸也全乱了。
她开始用力,使劲地把我的整个生殖器和蛋囊向外拉扯、揪出来。那是一种极其怪异而清晰的痛楚,混合着肿胀感、被牵扯的钝痛,我的男儿尊严被彻底剥开。我咬紧牙关,齿缝间带着颤音。
鞋带递了过来,粗糙的质感掠过我的阴囊。她把两根鞋带绕在根部,缠绕,然后猛地勒紧!
“呃啊——!” 一声短促的痛呼还是冲破了喉咙。那是一种窒息的捆缚感,像是所有的血液和疼痛都被死死勒在了那一道粗糙的束缚之下,脉搏在鞋带下疯狂冲撞。钝痛变成了一阵绞痛。我挣扎着,但王少的几个弟兄把我狠狠地按在地上,几个人又把我的双腿扒开束缚在半空中,让我在这种尴尬的姿势下完全不能动弹。
整个过程,小琳没有看我的眼睛。她只是低着头,检查着鞋带的结是否牢固。她的冷静,像一层厚重的冰壳,封住了所有的嘈杂和情绪,也把我所有的恐惧、羞耻、乃至最后一点侥幸,都冻在了里面。空气里只剩下酒精味、我的汗味,和我自己无法控制的、粗重颤抖的呼吸声。
忽然她看了我一眼,嘴唇凑过来轻轻地在我耳边说,“你准备好。我会很快的。” 她终于对我说了句人话,虽然声音平直,冷的可怕。而我知道,最痛苦的部分将要开始了。我嗓子里冒着哭腔,骨头里都是冷的,浑身都在发抖,牙齿不住地打岔。
我看着她从根部使劲往上揪着我的阴茎,然后水果刀向我的蛋囊的下方切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