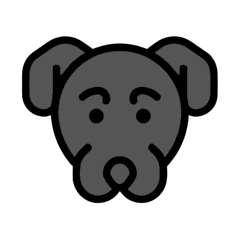ai生成短篇小说合集
短篇AI生成榨精榨死
redghost马可波罗发布于 2026-02-05 10:37
Re: ai生成短篇小说合集
17.圣枪的囚笼
失败的气味,是铁锈、焦土、还有魔力回路过载灼烧后挥之不去的辛辣焦臭,混着喉咙深处涌上的血腥甜腻。
藤丸立香背靠着冰冷粗糙的石壁,缓缓滑坐下去,身体与石头摩擦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在这死寂的囚室里格外刺耳。手臂上,那三道曾联结着无数奇迹、象征着希望与抗争的鲜红令咒,此刻只余下焦黑扭曲的灼痕,像三条丑陋的伤疤盘踞在皮肤上,每一次心跳都牵扯着神经末梢,传来一阵阵深入骨髓的、闷雷般的钝痛。耳边仿佛还残留着方才战场上的余响——玛修那声带着哭腔与决绝的“前辈——!”,伴随着她手中那面巨大十字盾“拟似宝具·已然遥远的理想之城(Lord Camelot)”在圣枪无匹光芒下碎裂的、令人心胆俱裂的清脆爆鸣;达芬奇亲在通讯频道里急促到变调的呼喊与最后被狂暴魔力乱流彻底淹没的刺耳杂音;还有高文卿那沉稳、冷漠、不带丝毫个人情感,如同宣读律法条文般的声音,穿透爆炸的轰鸣,清晰地在废墟上空回荡:
“此身即为圣都之壁,此剑即为法则之刃。凡王之治下,皆为正理。王命,不可违抗,不容置疑。”
圣都卡美洛。宏伟,圣洁,巍然屹立于这片被“狮子王”的意志所固化的特异点大地上,散发着净化一切、终结一切的神性光辉。就在片刻之前,这里还是迦勒底一行人眼中必须攻破的、囚禁人理希望的最终堡垒,是他们跨越无数艰难险阻、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抵达的决战之地。而现在,它成了囚笼,一座光芒万丈、却冰冷彻骨的囚笼。
宏伟的殿堂内,白银的骑士们肃立两旁,盔甲锃亮,面容隐藏在头盔的阴影下,只有冰冷的视线如同实质,钉在被无形力量压制、跪在冰冷玉石地面的藤丸立香身上。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魔力与神圣气息,混合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威压。王座高踞于层层阶梯之上,尽头之塔——圣枪伦戈米尼亚德——静静矗立在王座旁,枪尖流淌着凝固时空般的微光。
王座之上,端坐着那位“女神”。
阿尔托莉雅·潘德拉贡。曾经的不列颠红龙,骑士王,迦勒底记录中值得信赖的盟友与强大的从者。但此刻,端坐于此的,是“狮子王”,是以圣枪为凭依,将自身神性与“固定”概念强行融合,意图以圣都之威净化人理、塑造“永恒静止之国”的、高踞于人类之上的审判者与执行者。她身披白银与蓝色相间的神圣铠甲,金色的长发如熔化的阳光垂落肩侧,头顶是简约而威严的王冠。但最令人心悸的是那双眼睛——曾经碧绿如湖、时而清澈时而坚毅的眼眸,此刻化为了纯粹的金色,如同两颗凝固的太阳,里面再也映不出任何属于“阿尔托莉雅”的人性波澜,只有俯瞰尘世、漠视兴衰的神性冰冷,如同在观察脚下微不足道的蚁群。
“无垢之人,无暇之魂,携异世之理,行逆反之举。”她的声音在大殿中响起,并不洪亮,却带着奇异的共鸣,仿佛直接响彻在灵魂深处,庄严,宏大,遥远得像是从天际传来。“汝之执着,源于羁绊;汝之抗争,起于妄念。此等情感,此等联系,皆为人理冗余之残渣,文明前行之桎梏。于此光辉之下终结,亦为一种……净化。”
没有审判的程序,没有辩解的余地,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或审视。她的宣判简洁,直接,如同陈述一个早已注定的自然法则。话音落下的瞬间,她手中并未动作,仅仅是那金色的瞳孔光芒微微一闪。
嗡——
无形的力量,并非物理的冲击,而是更高维度的“固定”与“排斥”之力,瞬间笼罩了藤丸立香。他感到自己与周围世界的“联系”被强行扭曲、剥离,身体被一股无可抗拒的伟力包裹、束缚,如同被封入琥珀的昆虫。视野中,大殿的景象迅速倒退、模糊,耳边最后掠过的是贝德维尔卿那撕心裂肺却又被某种力量强行压抑的呐喊,以及兰斯洛特卿那压抑着无尽痛苦的沉重呼吸。
下一秒,天旋地转的感觉袭来,然后是沉重的撞击和彻底的黑暗。
等他再次恢复些许感知,已身处这高塔深处的囚室。
没有窗户,只有四面冰冷光滑、不知何种材质构成的灰白色石壁,严丝合缝,毫无瑕疵。唯一的光源来自天花板中央一块自发光的、刻满复杂卢恩符文的石板,投下冰冷而不带温度的白光。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石尘的干燥气味,以及一丝极其淡薄、却无法忽视的、类似古老教堂深处焚烧极品乳香与没药混合后的奇异冷香,这香气非但不能让人宁神,反而加剧了空间的孤寂与压抑。最令人绝望的是,他与迦勒底的通讯、与所有从者间的契约联系,都被压制到了近乎断绝的程度,只有手腕上那三道灼痕还残留着微弱的、仿佛随时会熄灭的刺痛感,提醒着他曾经拥有的力量与背负的责任,也反衬出此刻的无助。
魔力被彻底抑制,身体因为连番激战和最后的冲击而遍布暗伤,疲惫如同最沉重的铅水,灌满了每一寸骨骼、每一块肌肉。他挣扎着,用尽最后力气挪到墙角,背靠冰冷的石壁蜷缩起来,试图保存一丝体温,也试图从这微不足道的支撑中汲取一点虚幻的安全感。
人类最后的御主,迦勒底仅存的希望,曾连接泛人类史无数闪耀星辰的纽带,此刻如同被遗弃的残破玩偶,孤零零地躺在这被神性光芒彻底遗忘的角落。失败带来的不仅是身体的创伤,更有信念动摇的裂痕。玛修她……还活着吗?达芬奇亲她们是否安全撤离?医生……罗曼医生牺牲所换来的时间与机会,难道就要这样毫无价值地断送在这里?一个个问题如同毒蛇,啃噬着他残存的理智。
他强迫自己思考,在绝望的泥沼中寻找可能存在的藤蔓。思考这囚室的结构,思考抑制魔力的符文原理,思考残存的一丝令咒联系能否被再次激活,思考外面那些圆桌骑士中是否还存在一丝动摇的可能……但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向那双金色的、非人的眼眸,和那柄曾指向星辰、此刻却指向人理尽头的圣枪。那光芒并非救赎,而是终结的宣告。
时间在这里失去了刻度。没有日升月落,没有饥渴困倦的明确周期,只有永恒不变的冰冷白光和死寂。或许过去了几个小时,或许已经几天。疲倦如潮水般反复冲刷着意识的堤岸,但他不敢真正沉睡,生怕一旦放松,那紧绷的弦就会彻底断裂,或者错过某个渺茫的、可能根本不存在的转机。
就在他因极度疲惫而意识开始模糊,眼皮沉重得快要合拢时——
厚重的、刻满封印符文、本应坚不可摧的石门,无声无息地,向一侧滑开了。
没有铰链的摩擦,没有守卫沉重的脚步声,甚至没有空气流动的细微声响。只有一道身影,被自身散发出的、柔和却充满绝对存在感的白金色光芒拉长的、笔直而威严的影子,先一步投射在囚室粗糙冰冷的石地上,将那单调的灰白切割成明暗分明的两半。
藤丸立香的心脏猛地一缩,残存的睡意被瞬间驱散。他挣扎着想爬起来,摆出哪怕是最无力的防御姿态,身体却因久未活动和魔力压制而异常沉重僵硬,根本不听使唤。最终他只是勉强用肘部撑起上半身,背脊更紧地抵住石壁,抬起沉重的头颅,用布满血丝却依旧努力保持锐利的眼睛,望向门口。
狮子王,阿尔托莉雅,走了进来。
她褪去了那身标志性的、华丽而沉重的神圣铠甲,只穿着一袭式样极为古朴简洁的白色亚麻长袍。袍子质地柔软,却毫无褶皱,自然地垂落,勾勒出挺拔修长的身形轮廓。金色的长发并未束起,如同流淌的熔金般披散在肩头背后,在昏暗囚室自身光芒的映照下,每一根发丝都仿佛在散发着微光。她没有佩戴王冠,面容平静无波,但那份源自圣枪、源自其“女神”位格的神性威压并未因此减少分毫,反而因为去除了盔甲的物理阻隔,更直接、更纯粹、更沉重地压迫过来,充盈了整个狭小的空间,让藤丸立香感到呼吸都变得困难。她手中没有握着那柄象征性的圣枪,但赤足立于石地的姿态本身,就充满了“裁决”与“终焉”的意味,比任何武器都更具威慑力。
她走进囚室,石门在她身后无声地关闭,隔绝了内外。冰冷的白光下,只有她自身散发的、温暖与冰冷奇异交融的白金光晕,成为这空间唯一的光源与中心。
阿尔托莉雅在距离藤丸立香几步远的地方停下脚步,金色的眼眸平静地垂下,落在他身上。那目光并非审视,也非探究,更像是在“确认”某个物体的状态,或者在进行某项仪式前必要的“观察”。眼神中没有憎恨,没有怜悯,没有好奇,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属于更高存在俯视低维造物的漠然。
片刻的静默,只有藤丸立香自己粗重压抑的呼吸声在石壁间微微回荡。
然后,阿尔托莉雅缓缓抬起了右手。手臂的动作优雅而稳定,仿佛早已演练过千万遍。她的指尖在空中看似随意地划过一道简洁的、却蕴含着某种宇宙至理的弧线。
嗡——
空气发出轻微的震颤。一个由纯粹白金色光芒构成、结构复杂精密到令人目眩的卢恩符文,随着她指尖的轨迹凭空浮现,静静悬浮在她掌心前方。符文缓缓旋转,每一个笔画都流淌着神圣而庞大的能量,散发出温暖却不灼热的光芒,将阿尔托莉雅平静的面容和藤丸立香惊愕的脸都映照得一片明亮。
符文成型后,轻轻飘起,如同拥有生命的精灵,缓缓飞向蜷缩在墙角的藤丸立香,在他紧缩的瞳孔注视下,没入了他胸口正中。
“呃——!”
藤丸立香身体猛地一震,发出一声压抑的闷哼。预想中的剧痛或冲击并未到来。相反,就在符文没入身体的瞬间,一股温润、醇和、仿佛浸泡在生命之泉中的暖流,以胸口为中心,轰然炸开,瞬间涌向他四肢百骸的每一个角落!连日激战积累的、深入骨髓的疲惫感,如同烈日下的朝露,迅速蒸发消散;身上各处伤口隐隐的刺痛和不适,被轻柔地抚平、愈合;魔力被彻底压制带来的那种空虚、乏力、仿佛与整个世界隔着一层厚玻璃的滞涩感,也如同破碎的冰层般片片剥落!
力量感,一种前所未有的、充沛到几乎要满溢出来的活力感,重新回到了这具饱经摧残的身体。他甚至能清晰地听到自己血液在血管中欢快奔腾的声音,感受到肌肉纤维充满弹性的收缩力量,指尖传来的触感变得异常敏锐。他难以置信地抬起手,看着自己原本有些苍白、此刻却迅速恢复健康红润、连细微擦伤都消失不见的手掌,又猛地抬头,死死盯住几步外静立不动的“女神”。
“为……什么?”他听到自己嘶哑干涩的声音在囚室中响起,带着无法掩饰的惊愕与更深沉的警惕。这绝非善意。迦勒底的记录,以及他与“阿尔托莉雅”并肩作战的经历(尽管是不同侧面),都清晰地告诉他,眼前这位“狮子王”的行事逻辑早已偏离常理,其“善意”往往比纯粹的恶意更加致命。
“此非慈悲之举,亦非救赎之途。”阿尔托莉雅的声音适时响起,打断了他混乱的思绪。她的声音依旧平稳无波,听不出任何情绪起伏,却罕见地带上了一丝近乎“解释”的意味,尽管这解释本身冰冷如斯。“污浊之杯,难以盛接无暇清泉;残破之器,不配承纳神圣恩泽。汝之躯壳,将行承载最终‘净化’之仪,需暂且恢复其完满之态,以为容器。”
净化?仪式?容器?!
这几个词如同冰锥,狠狠刺入藤丸立香刚刚因身体恢复而稍缓的心神。迦勒底对“狮子王”理念的分析、对“圣拔”的观察、以及对“固定”概念的研究碎片,瞬间在脑海中拼凑出一个模糊却令人毛骨悚然的图景。这绝非简单的处刑或囚禁!
“你要做什么?!”他厉声喝问,身体本能地向后猛缩,背脊重重撞在冰冷的石壁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试图调动体内刚刚恢复的魔力,哪怕只是一丝,来激活令咒或进行最基本的强化,但魔力依旧沉寂,仿佛被更高级别的力量彻底“管理”着,只能用于维持这具身体的“完满”。
阿尔托莉雅没有回答。她只是向前迈出了一步。赤足踩在冰冷的石地上,依旧没有发出丝毫声响,只有那白色的袍角轻轻拂过地面。随着她的靠近,那股神圣的、温暖的、却令人窒息的神性气息如同实质的潮水,越来越浓烈地包裹上来。她走到藤丸立香身前,停下,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两人的距离近得藤丸立香能清晰地看到她金色眼眸中自己缩小、惊惶的倒影,能闻到她身上那股冰冷的、混合了钢铁、阳光与古老誓约的奇异气息。
然后,她做出了一个让藤丸立香大脑瞬间空白、连恐惧都暂时凝固的动作。
她微微俯身,伸出了左手——那只没有佩戴任何饰物、骨节分明、带着常年握剑留下的薄茧、却依旧修长有力的手,轻轻探向藤丸立香的脸颊。指尖带着微凉的温度,动作甚至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属于“阿尔托莉雅”这个存在本身的、久远记忆般的生涩与……近似“温柔”的触碰。她的指尖拂过他沾着灰尘、残留着疲惫痕迹的脸颊,动作轻缓,如同拂去一件珍贵瓷器上的尘埃。
但她的眼神,依旧冰冷如万载寒冰雕琢的神像,没有任何情感的温度,只有一片绝对的、非人的平静。这矛盾的触感与眼神,比任何直接的暴行更让人心底发寒。
“无谓挣扎,”她低语,声音近在咫尺,带着温热的气息拂过藤丸立香的耳廓,那声音低沉,近乎叹息,却字字清晰,如同最后的判决书,“此身所行之道,即为‘正确’,即为‘终结’。人理冗余之残渣,文明痼疾之具现,当于圣枪光辉之下彻底净除,归于永恒静滞之‘无’。汝之终结,亦为汝之……归途。”
话音未落,她原本垂在身侧的右手,倏然抬起,五指张开,掌心对着藤丸立香,虚虚一按。
“嗡——!!!”
远比之前更强烈、更宏大的无形力场瞬间爆发!这不是物理的冲击或压迫,而是直接作用于空间、规则乃至存在本身的“固定”之力!藤丸立香感到自己周围的空间瞬间“凝固”了,变成了比最坚硬的合金更牢固的囚笼。他整个人被这股力量死死地、彻底地“钉”在了背后的石壁上,从头发梢到脚趾尖,连最细微的颤抖都无法做到。呼吸变得极其困难,肺部每次收缩都仿佛在对抗千钧重压。只有眼球还能勉强转动,惊骇欲绝地瞪着近在咫尺的阿尔托莉雅。
阿尔托莉雅收回了拂过他脸颊的左手,双手自然垂落身侧。然后,在藤丸立香几乎要瞪裂的眼眶注视下,她开始进行下一个动作。
她微微低下头,目光落在自己白色亚麻长袍侧边的系带上。那系带是同样质地的亚麻编织,打着简洁的结。她抬起双手,动作依旧缓慢,带着一种近乎仪式性的、庄重而精准的韵律,开始解开那个结。
系带松开。她双手轻轻拉住袍襟,向两侧微微分开。
白色的亚麻长袍前襟随之敞开,露出了其下的景象。
那并非寻常人类的躯体。形态依然是完美无瑕的女性身躯,肌肤莹白如玉,在自身散发和白金符文映照的光晕下,流转着一种圣洁而冰冷的光泽,仿佛是由最上等的光之宝石雕琢而成,毫无瑕疵。但真正让藤丸立香灵魂都为之冻结的,是在那平坦紧实、线条优美的小腹正中,脐下三寸的位置——
一个复杂、精密、宏大到了极点的、由纯粹白金色光芒构成的图案,正在缓缓浮现、旋转、变得清晰。那图案的线条仿佛由无数微缩的、相互勾连的圣枪伦戈米尼亚德投影交织而成,又像是某种阐述宇宙“固定”、“终结”、“净化”终极真理的法则具现化,每一个转折,每一道弧线,都蕴含着令人头晕目眩的庞大信息与神性威能。图案的中心,并非实体,而是一个缓缓逆时针旋转的、深邃无比的微型漩涡,那漩涡仿佛连通着“无”的本身,散发着冰冷、神圣、却又充满绝对“吞噬”与“净化”意味的恐怖吸力!
神圣,完美,非人。充满了至高无上的美感,却也充满了令人绝望的、作为“异物”即将被“处理”的恐惧。
藤丸立香的呼吸彻底停滞了。所有的疑惑、侥幸、微弱的希望,在这一刻被眼前这超乎理解的景象碾得粉碎。他明白了,完全明白了那“净化仪式”意味着什么。这绝非死亡那么简单,这是更本质的、更残酷的“处理”方式!
“不——!!!!!!”
一声混合了极致愤怒、恐惧、不甘与最后抗争意志的嘶吼,终于冲破了被无形力场压迫的喉咙,在狭小的囚室中爆开,撞在石壁上,激起微弱而绝望的回响。藤丸立香用尽刚刚恢复的、以及灵魂深处榨出的每一分力气,疯狂地挣扎起来!肌肉绷紧到极限,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咯”声,被固定在石壁上的身体因为剧烈的对抗而微微震颤。但这一切在狮子王那源自圣枪的“固定”之力面前,显得如此可笑而徒劳。力场纹丝不动,如同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了他身上。
阿尔托莉雅对他的挣扎与嘶吼恍若未闻。她的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金色的眼眸低垂,看着自己小腹上那缓缓旋转的光芒图案,仿佛在确认其状态。然后,她向前一步,两人的身体几乎贴在一起。那散发着微光的神性躯体带来的不是温暖,而是一种刺骨的、神圣的、令人灵魂都要冻结的寒意。
她微微调整了一下站姿,分开了双腿。然后,在藤丸立香瞪大到极致、充满血丝的眼睛的绝望注视下,她缓缓地、平稳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仿佛在将圣枪钉入大地以固定人理般的沉重与决绝,沉下了腰肢。
接触,发生了。
但并非预想中肉体的碰撞。在接触的刹那,藤丸立香感到的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直达灵魂最深处的“对接”与“侵入”!他小腹上那个光芒图案的中心,那个缓缓旋转的微型漩涡,猛然扩张,产生一股无法抗拒的、冰冷到极致却又带着神圣灼热感的恐怖吸力!这股吸力并非作用于他的肉体,而是直接作用在他体内那刚刚被恢复、充盈澎湃的生命力本源之上——那是他作为御主与无数英灵缔结契约的根基,是跨越无数特异点凝聚的信念与羁绊的显化,是维系着他“存在”的最核心的“精气”!
这股精纯而庞大的生命能量,在这神圣漩涡的吸力下,开始被疯狂地、高效地、不可逆转地抽离、攫取、引流!仿佛他整个人变成了一口被强行凿穿的泉眼,生命之泉正哀鸣着被抽向那光芒的无底深渊。
“啊啊啊啊——!!!”
难以言喻的感受让藤丸立香发出了不似人声的惨嚎。那是比肉体凌迟更痛苦的、生命本质被掠夺的剧痛!是信念与存在被强行撕裂、吞噬的绝望!与此同时,阿尔托莉雅那沉下的腰肢并未静止。她开始了动作。
极其缓慢,却沉重如山岳,稳定如时光流逝般的起伏。
那不是情欲的律动,而是某种宏大的、充满“终结”与“固定”仪式感的、仿佛圣枪一次次钉入历史与命运节点的庄重律动。每一次深深地、彻底地下沉,那神圣漩涡的吸力就暴涨数倍,吞噬精气的速度就加快数分,仿佛要将藤丸立香灵魂都吸扯进去;每一次缓缓地、平稳地抬起,都带来短暂的凝滞,仿佛在进行“确认”、“转化”或“消化”,那光芒图案会随之微微明暗变化。她的动作精准,稳定,带着一种非人的、机械般的精确性,却又蕴含着神性的威严。
“呃……哈啊……住手……阿尔托……莉雅……!”藤丸立香的嘶吼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混合着剧痛、窒息与某种完全陌生感觉的呻吟。巨大的、被侵犯被掠夺的愤怒与恐惧,与身体在这超越理解的、神圣而暴戾的仪式中被强行激发出的、完全陌生的、混合了冰冷神性压迫与毁灭性生理快感的复杂反应,如同两股狂暴的乱流,在他体内疯狂对冲,将他残存的意志撕扯得支离破碎。他想到了玛修举盾挡在身前的背影,想到了达芬奇亲灵子转移时的叮嘱,想到了医生最后那释然又歉然的微笑,想到了风雪中的俄罗斯、燃烧的北美、波涛汹涌的七海、神明盘踞的巴比伦、迷雾笼罩的伦敦、还有那最终冠位时间神殿中,无数人为之奋战、牺牲的泛人类史……
不能在这里结束!不能以这种被“净化”、被“吞噬”的方式结束!迦勒底!人理!大家……!
但一切挣扎与呐喊都是徒劳。力量,生命力,意识,都在那持续不断的、缓慢而坚定的起伏与吞噬中飞速流失。视线开始模糊、摇晃,阿尔托莉雅那绝美而冰冷如雕塑的脸庞在眼前晃动、重叠,金色的眼眸中清晰地倒映着他因痛苦和快感而扭曲、逐渐失去神采的面容,但那眼眸深处,只有一片亘古的、神性的漠然,无悲无喜,无波无澜。
白色的、炽热的、粘稠的、内部仿佛闪烁着无数细微羁绊光点的液体——那是高度浓缩的生命精华与灵魂能量的混合物——开始不受控制地从藤丸立香体内涌出,如同溃堤的洪流,尽数没入那光芒的、缓缓旋转的神圣漩涡之中,被瞬间吞噬、分解、净化。那漩涡的光芒似乎因为吸收了这高质量的“祭品”而变得更加凝实、璀璨,仿佛一颗微型的、正在孕育着什么的白金星体。
阿尔托莉雅的起伏变得更深沉,更缓慢,仿佛在进行最后的、彻底的汲取与“固定”。她的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一种绝对的、沉浸在神圣职责中的专注。她甚至微微仰起了线条优美的脖颈,闭上了那双金色的眼眸,长长的睫毛在光晕下投下淡淡的阴影。喉咙深处,溢出一声极轻、极悠长的、仿佛叹息又仿佛满足的气音,周身那神圣的白金光晕在这一刻明亮、凝结到了极致,将她整个人衬托得如同降临凡间的、执行最终审判的光之神祇。
藤丸立香最后看到的,是囚室天花板上那些冰冷的、模糊的发光符文纹路。最后感觉到的,是身体被彻底掏空、轻飘飘仿佛下一刻就要化为光尘消散的绝对虚无,是手腕上那三道令咒灼痕最后一丝微弱的、不甘的灼热如同风中残烛般彻底熄灭,是灵魂深处与遥远某处(也许是迦勒底,也许是某个英灵座)最后一丝微弱联系的、如同琴弦崩断般的清脆碎裂感。
然后,是无边无际的、温柔而冰冷的黑暗,如同回归了生命最原始的、未被召唤的“无”。没有痛苦,没有恐惧,没有遗憾,甚至连“自己”这个概念,都随之消散了。
……
阿尔托莉雅缓缓地、极其平稳地抬起了身体。
那沉重如山的起伏终于停止。覆盖在小腹上的、那复杂到极致的光芒图案,迅速黯淡、收缩,最终彻底隐没在她莹白如玉的肌肤之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仿佛从未出现过。小腹恢复光滑平整,线条优美,依旧散发着圣洁的微光。
她站直身体,白色的亚麻长袍自然垂落,重新掩住了一切,遮住了那方才进行过“净化”仪式的所在。她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无波无澜,无喜无悲,金色的眼眸重新睁开,平静地、漠然地投向地面。
那里,藤丸立香依然保持着背靠石壁的姿势,但头颅已经完全无力地垂向一侧,下巴抵着瘦骨嶙峋的胸口。皮肤失去了所有水分与光泽,紧紧包裹在突起的骨骼上,呈现出一种灰败的、仿佛在沙漠中风化了千年的干枯色泽,布满了细密龟裂的纹路。眼窝深深凹陷下去,眼球消失,只剩下两个黑洞洞的、干涸的窟窿,茫然地对着前方的虚空。嘴唇微张,依稀还能看出最后时刻凝固的、混合痛苦与某种陌生情绪的形状。原本年轻、富有活力、承载着无数希望的躯体,此刻已彻底萎缩、干瘪,变成了一具轻轻一碰就会碎裂的、空荡荡的皮囊与枯骨,轻飘飘地倚在墙角,仿佛没有一丝重量。只有那身残破不堪、沾满灰尘与干涸污渍的迦勒底标准制服,还勉强套在这具枯骨般的支架上,手腕处,那三道曾象征无限可能的鲜红令咒,此刻只余下焦黑褪色的浅淡痕迹,很快连这痕迹也会彻底消失。
人类最后的御主,曾于冠位时间神殿见证人理烧却,曾跨越七个特异点联结无数英灵之光,曾背负着泛人类史最后希望的火种,此刻如同燃尽的薪柴,被榨取了最后一丝光与热,只剩下冰冷、空洞、毫无价值的余烬。
阿尔托莉雅静静地注视了这具遗骸片刻,金色的眼眸中依旧没有丝毫波澜。然后,她微微抬起了右手,掌心向上,对着那枯骨。
没有咒文,没有光芒爆发。只是一个简单的、意念驱动的动作。
那具干枯的遗骸,从指尖开始,无声地化为最细微、最纯净的白色光尘,如同被最高级别的净化术式分解一般,迅速向上蔓延。光尘飘散,不落地面,而是直接融入了周围的空间,仿佛被这囚室本身、被圣都卡美洛的“固定”法则所吸收、同化。不过数息之间,那曾名为藤丸立香的少年存在过的一切物质痕迹,便彻底消散在了空气中,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残留。囚室里只剩下冰冷光滑的石壁,天花板中央那永恒不变的发光符文,以及空气中那缕即将彻底散去的、混合了神圣冷香与某种生命精华挥发后的、奇异而短暂的气息。
净化,已完成。残渣,已清除。
阿尔托莉雅放下手,白色的袍袖轻轻垂下。她转过身,赤足踩在冰冷的石地上,向着那扇厚重的石门走去。步伐稳定,节奏均匀,背影挺拔如松,周身那神圣的威压与光辉没有丝毫减弱,仿佛刚刚完成的并非一场残酷的吞噬,而仅仅是一次寻常的祈祷或冥想。
石门在她面前无声滑开。门外,走廊中,高文卿如同最忠诚的雕塑般肃立着,白银的盔甲在走廊壁灯下闪烁着冷硬的光泽。见到狮子王走出,他立刻以无可挑剔的姿势微微躬身,右手抚胸:
“王。”
“净化之仪,已然完成。”阿尔托莉雅的声音平静如常,如同在陈述天气,脚步没有丝毫停顿,继续向前走去。“冗余之残渣已彻底净除。圣枪伦戈米尼亚德对时空、对‘正确’历史之固定,将再无阻碍。永恒静滞之基石,更为稳固。”
“是。”高文低下头,应道。在他低垂的眼帘下,那总是充满坚定与忠诚的蓝色眼眸中,极快地掠过一丝极其复杂、难以言喻的微光,像是痛苦,像是挣扎,又像是更深沉的、被绝对信仰压制下去的迷茫。但这丝异样仅仅存在了一刹那,便被他重新抬起的、写满绝对忠诚的脸庞所掩盖。“王之意志,即为我等剑锋所指。”
狮子王没有再回应。她迈着恒定不变的步伐,走向长廊尽头那片更加明亮、更加恢弘、充满了神圣光辉的区域,走向她那位于圣都核心、光芒万丈的永恒王座。圣都卡美洛依旧在这片被固化的时空中巍然屹立,圣枪的光辉依旧照耀着这片被“净化”的土地,仿佛要将这静止的“正确”永恒延续下去。
只是,那曾为人理存续而燃烧的、微弱的、却无比顽强坚韧的最后火种,已然在无人知晓的黑暗深处,被“女神”以“净化”之名,以圣枪之力,彻底榨取、熄灭、归于虚无。
人类的最后希望,断绝于女神对“永恒正确”的偏执追求之下,终结于圣枪之主那冰冷神性腹中,化为了加固这静止囚笼的、微不足道的一缕尘埃。
失败的气味,是铁锈、焦土、还有魔力回路过载灼烧后挥之不去的辛辣焦臭,混着喉咙深处涌上的血腥甜腻。
藤丸立香背靠着冰冷粗糙的石壁,缓缓滑坐下去,身体与石头摩擦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在这死寂的囚室里格外刺耳。手臂上,那三道曾联结着无数奇迹、象征着希望与抗争的鲜红令咒,此刻只余下焦黑扭曲的灼痕,像三条丑陋的伤疤盘踞在皮肤上,每一次心跳都牵扯着神经末梢,传来一阵阵深入骨髓的、闷雷般的钝痛。耳边仿佛还残留着方才战场上的余响——玛修那声带着哭腔与决绝的“前辈——!”,伴随着她手中那面巨大十字盾“拟似宝具·已然遥远的理想之城(Lord Camelot)”在圣枪无匹光芒下碎裂的、令人心胆俱裂的清脆爆鸣;达芬奇亲在通讯频道里急促到变调的呼喊与最后被狂暴魔力乱流彻底淹没的刺耳杂音;还有高文卿那沉稳、冷漠、不带丝毫个人情感,如同宣读律法条文般的声音,穿透爆炸的轰鸣,清晰地在废墟上空回荡:
“此身即为圣都之壁,此剑即为法则之刃。凡王之治下,皆为正理。王命,不可违抗,不容置疑。”
圣都卡美洛。宏伟,圣洁,巍然屹立于这片被“狮子王”的意志所固化的特异点大地上,散发着净化一切、终结一切的神性光辉。就在片刻之前,这里还是迦勒底一行人眼中必须攻破的、囚禁人理希望的最终堡垒,是他们跨越无数艰难险阻、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抵达的决战之地。而现在,它成了囚笼,一座光芒万丈、却冰冷彻骨的囚笼。
宏伟的殿堂内,白银的骑士们肃立两旁,盔甲锃亮,面容隐藏在头盔的阴影下,只有冰冷的视线如同实质,钉在被无形力量压制、跪在冰冷玉石地面的藤丸立香身上。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魔力与神圣气息,混合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威压。王座高踞于层层阶梯之上,尽头之塔——圣枪伦戈米尼亚德——静静矗立在王座旁,枪尖流淌着凝固时空般的微光。
王座之上,端坐着那位“女神”。
阿尔托莉雅·潘德拉贡。曾经的不列颠红龙,骑士王,迦勒底记录中值得信赖的盟友与强大的从者。但此刻,端坐于此的,是“狮子王”,是以圣枪为凭依,将自身神性与“固定”概念强行融合,意图以圣都之威净化人理、塑造“永恒静止之国”的、高踞于人类之上的审判者与执行者。她身披白银与蓝色相间的神圣铠甲,金色的长发如熔化的阳光垂落肩侧,头顶是简约而威严的王冠。但最令人心悸的是那双眼睛——曾经碧绿如湖、时而清澈时而坚毅的眼眸,此刻化为了纯粹的金色,如同两颗凝固的太阳,里面再也映不出任何属于“阿尔托莉雅”的人性波澜,只有俯瞰尘世、漠视兴衰的神性冰冷,如同在观察脚下微不足道的蚁群。
“无垢之人,无暇之魂,携异世之理,行逆反之举。”她的声音在大殿中响起,并不洪亮,却带着奇异的共鸣,仿佛直接响彻在灵魂深处,庄严,宏大,遥远得像是从天际传来。“汝之执着,源于羁绊;汝之抗争,起于妄念。此等情感,此等联系,皆为人理冗余之残渣,文明前行之桎梏。于此光辉之下终结,亦为一种……净化。”
没有审判的程序,没有辩解的余地,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或审视。她的宣判简洁,直接,如同陈述一个早已注定的自然法则。话音落下的瞬间,她手中并未动作,仅仅是那金色的瞳孔光芒微微一闪。
嗡——
无形的力量,并非物理的冲击,而是更高维度的“固定”与“排斥”之力,瞬间笼罩了藤丸立香。他感到自己与周围世界的“联系”被强行扭曲、剥离,身体被一股无可抗拒的伟力包裹、束缚,如同被封入琥珀的昆虫。视野中,大殿的景象迅速倒退、模糊,耳边最后掠过的是贝德维尔卿那撕心裂肺却又被某种力量强行压抑的呐喊,以及兰斯洛特卿那压抑着无尽痛苦的沉重呼吸。
下一秒,天旋地转的感觉袭来,然后是沉重的撞击和彻底的黑暗。
等他再次恢复些许感知,已身处这高塔深处的囚室。
没有窗户,只有四面冰冷光滑、不知何种材质构成的灰白色石壁,严丝合缝,毫无瑕疵。唯一的光源来自天花板中央一块自发光的、刻满复杂卢恩符文的石板,投下冰冷而不带温度的白光。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石尘的干燥气味,以及一丝极其淡薄、却无法忽视的、类似古老教堂深处焚烧极品乳香与没药混合后的奇异冷香,这香气非但不能让人宁神,反而加剧了空间的孤寂与压抑。最令人绝望的是,他与迦勒底的通讯、与所有从者间的契约联系,都被压制到了近乎断绝的程度,只有手腕上那三道灼痕还残留着微弱的、仿佛随时会熄灭的刺痛感,提醒着他曾经拥有的力量与背负的责任,也反衬出此刻的无助。
魔力被彻底抑制,身体因为连番激战和最后的冲击而遍布暗伤,疲惫如同最沉重的铅水,灌满了每一寸骨骼、每一块肌肉。他挣扎着,用尽最后力气挪到墙角,背靠冰冷的石壁蜷缩起来,试图保存一丝体温,也试图从这微不足道的支撑中汲取一点虚幻的安全感。
人类最后的御主,迦勒底仅存的希望,曾连接泛人类史无数闪耀星辰的纽带,此刻如同被遗弃的残破玩偶,孤零零地躺在这被神性光芒彻底遗忘的角落。失败带来的不仅是身体的创伤,更有信念动摇的裂痕。玛修她……还活着吗?达芬奇亲她们是否安全撤离?医生……罗曼医生牺牲所换来的时间与机会,难道就要这样毫无价值地断送在这里?一个个问题如同毒蛇,啃噬着他残存的理智。
他强迫自己思考,在绝望的泥沼中寻找可能存在的藤蔓。思考这囚室的结构,思考抑制魔力的符文原理,思考残存的一丝令咒联系能否被再次激活,思考外面那些圆桌骑士中是否还存在一丝动摇的可能……但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向那双金色的、非人的眼眸,和那柄曾指向星辰、此刻却指向人理尽头的圣枪。那光芒并非救赎,而是终结的宣告。
时间在这里失去了刻度。没有日升月落,没有饥渴困倦的明确周期,只有永恒不变的冰冷白光和死寂。或许过去了几个小时,或许已经几天。疲倦如潮水般反复冲刷着意识的堤岸,但他不敢真正沉睡,生怕一旦放松,那紧绷的弦就会彻底断裂,或者错过某个渺茫的、可能根本不存在的转机。
就在他因极度疲惫而意识开始模糊,眼皮沉重得快要合拢时——
厚重的、刻满封印符文、本应坚不可摧的石门,无声无息地,向一侧滑开了。
没有铰链的摩擦,没有守卫沉重的脚步声,甚至没有空气流动的细微声响。只有一道身影,被自身散发出的、柔和却充满绝对存在感的白金色光芒拉长的、笔直而威严的影子,先一步投射在囚室粗糙冰冷的石地上,将那单调的灰白切割成明暗分明的两半。
藤丸立香的心脏猛地一缩,残存的睡意被瞬间驱散。他挣扎着想爬起来,摆出哪怕是最无力的防御姿态,身体却因久未活动和魔力压制而异常沉重僵硬,根本不听使唤。最终他只是勉强用肘部撑起上半身,背脊更紧地抵住石壁,抬起沉重的头颅,用布满血丝却依旧努力保持锐利的眼睛,望向门口。
狮子王,阿尔托莉雅,走了进来。
她褪去了那身标志性的、华丽而沉重的神圣铠甲,只穿着一袭式样极为古朴简洁的白色亚麻长袍。袍子质地柔软,却毫无褶皱,自然地垂落,勾勒出挺拔修长的身形轮廓。金色的长发并未束起,如同流淌的熔金般披散在肩头背后,在昏暗囚室自身光芒的映照下,每一根发丝都仿佛在散发着微光。她没有佩戴王冠,面容平静无波,但那份源自圣枪、源自其“女神”位格的神性威压并未因此减少分毫,反而因为去除了盔甲的物理阻隔,更直接、更纯粹、更沉重地压迫过来,充盈了整个狭小的空间,让藤丸立香感到呼吸都变得困难。她手中没有握着那柄象征性的圣枪,但赤足立于石地的姿态本身,就充满了“裁决”与“终焉”的意味,比任何武器都更具威慑力。
她走进囚室,石门在她身后无声地关闭,隔绝了内外。冰冷的白光下,只有她自身散发的、温暖与冰冷奇异交融的白金光晕,成为这空间唯一的光源与中心。
阿尔托莉雅在距离藤丸立香几步远的地方停下脚步,金色的眼眸平静地垂下,落在他身上。那目光并非审视,也非探究,更像是在“确认”某个物体的状态,或者在进行某项仪式前必要的“观察”。眼神中没有憎恨,没有怜悯,没有好奇,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属于更高存在俯视低维造物的漠然。
片刻的静默,只有藤丸立香自己粗重压抑的呼吸声在石壁间微微回荡。
然后,阿尔托莉雅缓缓抬起了右手。手臂的动作优雅而稳定,仿佛早已演练过千万遍。她的指尖在空中看似随意地划过一道简洁的、却蕴含着某种宇宙至理的弧线。
嗡——
空气发出轻微的震颤。一个由纯粹白金色光芒构成、结构复杂精密到令人目眩的卢恩符文,随着她指尖的轨迹凭空浮现,静静悬浮在她掌心前方。符文缓缓旋转,每一个笔画都流淌着神圣而庞大的能量,散发出温暖却不灼热的光芒,将阿尔托莉雅平静的面容和藤丸立香惊愕的脸都映照得一片明亮。
符文成型后,轻轻飘起,如同拥有生命的精灵,缓缓飞向蜷缩在墙角的藤丸立香,在他紧缩的瞳孔注视下,没入了他胸口正中。
“呃——!”
藤丸立香身体猛地一震,发出一声压抑的闷哼。预想中的剧痛或冲击并未到来。相反,就在符文没入身体的瞬间,一股温润、醇和、仿佛浸泡在生命之泉中的暖流,以胸口为中心,轰然炸开,瞬间涌向他四肢百骸的每一个角落!连日激战积累的、深入骨髓的疲惫感,如同烈日下的朝露,迅速蒸发消散;身上各处伤口隐隐的刺痛和不适,被轻柔地抚平、愈合;魔力被彻底压制带来的那种空虚、乏力、仿佛与整个世界隔着一层厚玻璃的滞涩感,也如同破碎的冰层般片片剥落!
力量感,一种前所未有的、充沛到几乎要满溢出来的活力感,重新回到了这具饱经摧残的身体。他甚至能清晰地听到自己血液在血管中欢快奔腾的声音,感受到肌肉纤维充满弹性的收缩力量,指尖传来的触感变得异常敏锐。他难以置信地抬起手,看着自己原本有些苍白、此刻却迅速恢复健康红润、连细微擦伤都消失不见的手掌,又猛地抬头,死死盯住几步外静立不动的“女神”。
“为……什么?”他听到自己嘶哑干涩的声音在囚室中响起,带着无法掩饰的惊愕与更深沉的警惕。这绝非善意。迦勒底的记录,以及他与“阿尔托莉雅”并肩作战的经历(尽管是不同侧面),都清晰地告诉他,眼前这位“狮子王”的行事逻辑早已偏离常理,其“善意”往往比纯粹的恶意更加致命。
“此非慈悲之举,亦非救赎之途。”阿尔托莉雅的声音适时响起,打断了他混乱的思绪。她的声音依旧平稳无波,听不出任何情绪起伏,却罕见地带上了一丝近乎“解释”的意味,尽管这解释本身冰冷如斯。“污浊之杯,难以盛接无暇清泉;残破之器,不配承纳神圣恩泽。汝之躯壳,将行承载最终‘净化’之仪,需暂且恢复其完满之态,以为容器。”
净化?仪式?容器?!
这几个词如同冰锥,狠狠刺入藤丸立香刚刚因身体恢复而稍缓的心神。迦勒底对“狮子王”理念的分析、对“圣拔”的观察、以及对“固定”概念的研究碎片,瞬间在脑海中拼凑出一个模糊却令人毛骨悚然的图景。这绝非简单的处刑或囚禁!
“你要做什么?!”他厉声喝问,身体本能地向后猛缩,背脊重重撞在冰冷的石壁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试图调动体内刚刚恢复的魔力,哪怕只是一丝,来激活令咒或进行最基本的强化,但魔力依旧沉寂,仿佛被更高级别的力量彻底“管理”着,只能用于维持这具身体的“完满”。
阿尔托莉雅没有回答。她只是向前迈出了一步。赤足踩在冰冷的石地上,依旧没有发出丝毫声响,只有那白色的袍角轻轻拂过地面。随着她的靠近,那股神圣的、温暖的、却令人窒息的神性气息如同实质的潮水,越来越浓烈地包裹上来。她走到藤丸立香身前,停下,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两人的距离近得藤丸立香能清晰地看到她金色眼眸中自己缩小、惊惶的倒影,能闻到她身上那股冰冷的、混合了钢铁、阳光与古老誓约的奇异气息。
然后,她做出了一个让藤丸立香大脑瞬间空白、连恐惧都暂时凝固的动作。
她微微俯身,伸出了左手——那只没有佩戴任何饰物、骨节分明、带着常年握剑留下的薄茧、却依旧修长有力的手,轻轻探向藤丸立香的脸颊。指尖带着微凉的温度,动作甚至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属于“阿尔托莉雅”这个存在本身的、久远记忆般的生涩与……近似“温柔”的触碰。她的指尖拂过他沾着灰尘、残留着疲惫痕迹的脸颊,动作轻缓,如同拂去一件珍贵瓷器上的尘埃。
但她的眼神,依旧冰冷如万载寒冰雕琢的神像,没有任何情感的温度,只有一片绝对的、非人的平静。这矛盾的触感与眼神,比任何直接的暴行更让人心底发寒。
“无谓挣扎,”她低语,声音近在咫尺,带着温热的气息拂过藤丸立香的耳廓,那声音低沉,近乎叹息,却字字清晰,如同最后的判决书,“此身所行之道,即为‘正确’,即为‘终结’。人理冗余之残渣,文明痼疾之具现,当于圣枪光辉之下彻底净除,归于永恒静滞之‘无’。汝之终结,亦为汝之……归途。”
话音未落,她原本垂在身侧的右手,倏然抬起,五指张开,掌心对着藤丸立香,虚虚一按。
“嗡——!!!”
远比之前更强烈、更宏大的无形力场瞬间爆发!这不是物理的冲击或压迫,而是直接作用于空间、规则乃至存在本身的“固定”之力!藤丸立香感到自己周围的空间瞬间“凝固”了,变成了比最坚硬的合金更牢固的囚笼。他整个人被这股力量死死地、彻底地“钉”在了背后的石壁上,从头发梢到脚趾尖,连最细微的颤抖都无法做到。呼吸变得极其困难,肺部每次收缩都仿佛在对抗千钧重压。只有眼球还能勉强转动,惊骇欲绝地瞪着近在咫尺的阿尔托莉雅。
阿尔托莉雅收回了拂过他脸颊的左手,双手自然垂落身侧。然后,在藤丸立香几乎要瞪裂的眼眶注视下,她开始进行下一个动作。
她微微低下头,目光落在自己白色亚麻长袍侧边的系带上。那系带是同样质地的亚麻编织,打着简洁的结。她抬起双手,动作依旧缓慢,带着一种近乎仪式性的、庄重而精准的韵律,开始解开那个结。
系带松开。她双手轻轻拉住袍襟,向两侧微微分开。
白色的亚麻长袍前襟随之敞开,露出了其下的景象。
那并非寻常人类的躯体。形态依然是完美无瑕的女性身躯,肌肤莹白如玉,在自身散发和白金符文映照的光晕下,流转着一种圣洁而冰冷的光泽,仿佛是由最上等的光之宝石雕琢而成,毫无瑕疵。但真正让藤丸立香灵魂都为之冻结的,是在那平坦紧实、线条优美的小腹正中,脐下三寸的位置——
一个复杂、精密、宏大到了极点的、由纯粹白金色光芒构成的图案,正在缓缓浮现、旋转、变得清晰。那图案的线条仿佛由无数微缩的、相互勾连的圣枪伦戈米尼亚德投影交织而成,又像是某种阐述宇宙“固定”、“终结”、“净化”终极真理的法则具现化,每一个转折,每一道弧线,都蕴含着令人头晕目眩的庞大信息与神性威能。图案的中心,并非实体,而是一个缓缓逆时针旋转的、深邃无比的微型漩涡,那漩涡仿佛连通着“无”的本身,散发着冰冷、神圣、却又充满绝对“吞噬”与“净化”意味的恐怖吸力!
神圣,完美,非人。充满了至高无上的美感,却也充满了令人绝望的、作为“异物”即将被“处理”的恐惧。
藤丸立香的呼吸彻底停滞了。所有的疑惑、侥幸、微弱的希望,在这一刻被眼前这超乎理解的景象碾得粉碎。他明白了,完全明白了那“净化仪式”意味着什么。这绝非死亡那么简单,这是更本质的、更残酷的“处理”方式!
“不——!!!!!!”
一声混合了极致愤怒、恐惧、不甘与最后抗争意志的嘶吼,终于冲破了被无形力场压迫的喉咙,在狭小的囚室中爆开,撞在石壁上,激起微弱而绝望的回响。藤丸立香用尽刚刚恢复的、以及灵魂深处榨出的每一分力气,疯狂地挣扎起来!肌肉绷紧到极限,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咯”声,被固定在石壁上的身体因为剧烈的对抗而微微震颤。但这一切在狮子王那源自圣枪的“固定”之力面前,显得如此可笑而徒劳。力场纹丝不动,如同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了他身上。
阿尔托莉雅对他的挣扎与嘶吼恍若未闻。她的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金色的眼眸低垂,看着自己小腹上那缓缓旋转的光芒图案,仿佛在确认其状态。然后,她向前一步,两人的身体几乎贴在一起。那散发着微光的神性躯体带来的不是温暖,而是一种刺骨的、神圣的、令人灵魂都要冻结的寒意。
她微微调整了一下站姿,分开了双腿。然后,在藤丸立香瞪大到极致、充满血丝的眼睛的绝望注视下,她缓缓地、平稳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仿佛在将圣枪钉入大地以固定人理般的沉重与决绝,沉下了腰肢。
接触,发生了。
但并非预想中肉体的碰撞。在接触的刹那,藤丸立香感到的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直达灵魂最深处的“对接”与“侵入”!他小腹上那个光芒图案的中心,那个缓缓旋转的微型漩涡,猛然扩张,产生一股无法抗拒的、冰冷到极致却又带着神圣灼热感的恐怖吸力!这股吸力并非作用于他的肉体,而是直接作用在他体内那刚刚被恢复、充盈澎湃的生命力本源之上——那是他作为御主与无数英灵缔结契约的根基,是跨越无数特异点凝聚的信念与羁绊的显化,是维系着他“存在”的最核心的“精气”!
这股精纯而庞大的生命能量,在这神圣漩涡的吸力下,开始被疯狂地、高效地、不可逆转地抽离、攫取、引流!仿佛他整个人变成了一口被强行凿穿的泉眼,生命之泉正哀鸣着被抽向那光芒的无底深渊。
“啊啊啊啊——!!!”
难以言喻的感受让藤丸立香发出了不似人声的惨嚎。那是比肉体凌迟更痛苦的、生命本质被掠夺的剧痛!是信念与存在被强行撕裂、吞噬的绝望!与此同时,阿尔托莉雅那沉下的腰肢并未静止。她开始了动作。
极其缓慢,却沉重如山岳,稳定如时光流逝般的起伏。
那不是情欲的律动,而是某种宏大的、充满“终结”与“固定”仪式感的、仿佛圣枪一次次钉入历史与命运节点的庄重律动。每一次深深地、彻底地下沉,那神圣漩涡的吸力就暴涨数倍,吞噬精气的速度就加快数分,仿佛要将藤丸立香灵魂都吸扯进去;每一次缓缓地、平稳地抬起,都带来短暂的凝滞,仿佛在进行“确认”、“转化”或“消化”,那光芒图案会随之微微明暗变化。她的动作精准,稳定,带着一种非人的、机械般的精确性,却又蕴含着神性的威严。
“呃……哈啊……住手……阿尔托……莉雅……!”藤丸立香的嘶吼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混合着剧痛、窒息与某种完全陌生感觉的呻吟。巨大的、被侵犯被掠夺的愤怒与恐惧,与身体在这超越理解的、神圣而暴戾的仪式中被强行激发出的、完全陌生的、混合了冰冷神性压迫与毁灭性生理快感的复杂反应,如同两股狂暴的乱流,在他体内疯狂对冲,将他残存的意志撕扯得支离破碎。他想到了玛修举盾挡在身前的背影,想到了达芬奇亲灵子转移时的叮嘱,想到了医生最后那释然又歉然的微笑,想到了风雪中的俄罗斯、燃烧的北美、波涛汹涌的七海、神明盘踞的巴比伦、迷雾笼罩的伦敦、还有那最终冠位时间神殿中,无数人为之奋战、牺牲的泛人类史……
不能在这里结束!不能以这种被“净化”、被“吞噬”的方式结束!迦勒底!人理!大家……!
但一切挣扎与呐喊都是徒劳。力量,生命力,意识,都在那持续不断的、缓慢而坚定的起伏与吞噬中飞速流失。视线开始模糊、摇晃,阿尔托莉雅那绝美而冰冷如雕塑的脸庞在眼前晃动、重叠,金色的眼眸中清晰地倒映着他因痛苦和快感而扭曲、逐渐失去神采的面容,但那眼眸深处,只有一片亘古的、神性的漠然,无悲无喜,无波无澜。
白色的、炽热的、粘稠的、内部仿佛闪烁着无数细微羁绊光点的液体——那是高度浓缩的生命精华与灵魂能量的混合物——开始不受控制地从藤丸立香体内涌出,如同溃堤的洪流,尽数没入那光芒的、缓缓旋转的神圣漩涡之中,被瞬间吞噬、分解、净化。那漩涡的光芒似乎因为吸收了这高质量的“祭品”而变得更加凝实、璀璨,仿佛一颗微型的、正在孕育着什么的白金星体。
阿尔托莉雅的起伏变得更深沉,更缓慢,仿佛在进行最后的、彻底的汲取与“固定”。她的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一种绝对的、沉浸在神圣职责中的专注。她甚至微微仰起了线条优美的脖颈,闭上了那双金色的眼眸,长长的睫毛在光晕下投下淡淡的阴影。喉咙深处,溢出一声极轻、极悠长的、仿佛叹息又仿佛满足的气音,周身那神圣的白金光晕在这一刻明亮、凝结到了极致,将她整个人衬托得如同降临凡间的、执行最终审判的光之神祇。
藤丸立香最后看到的,是囚室天花板上那些冰冷的、模糊的发光符文纹路。最后感觉到的,是身体被彻底掏空、轻飘飘仿佛下一刻就要化为光尘消散的绝对虚无,是手腕上那三道令咒灼痕最后一丝微弱的、不甘的灼热如同风中残烛般彻底熄灭,是灵魂深处与遥远某处(也许是迦勒底,也许是某个英灵座)最后一丝微弱联系的、如同琴弦崩断般的清脆碎裂感。
然后,是无边无际的、温柔而冰冷的黑暗,如同回归了生命最原始的、未被召唤的“无”。没有痛苦,没有恐惧,没有遗憾,甚至连“自己”这个概念,都随之消散了。
……
阿尔托莉雅缓缓地、极其平稳地抬起了身体。
那沉重如山的起伏终于停止。覆盖在小腹上的、那复杂到极致的光芒图案,迅速黯淡、收缩,最终彻底隐没在她莹白如玉的肌肤之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仿佛从未出现过。小腹恢复光滑平整,线条优美,依旧散发着圣洁的微光。
她站直身体,白色的亚麻长袍自然垂落,重新掩住了一切,遮住了那方才进行过“净化”仪式的所在。她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无波无澜,无喜无悲,金色的眼眸重新睁开,平静地、漠然地投向地面。
那里,藤丸立香依然保持着背靠石壁的姿势,但头颅已经完全无力地垂向一侧,下巴抵着瘦骨嶙峋的胸口。皮肤失去了所有水分与光泽,紧紧包裹在突起的骨骼上,呈现出一种灰败的、仿佛在沙漠中风化了千年的干枯色泽,布满了细密龟裂的纹路。眼窝深深凹陷下去,眼球消失,只剩下两个黑洞洞的、干涸的窟窿,茫然地对着前方的虚空。嘴唇微张,依稀还能看出最后时刻凝固的、混合痛苦与某种陌生情绪的形状。原本年轻、富有活力、承载着无数希望的躯体,此刻已彻底萎缩、干瘪,变成了一具轻轻一碰就会碎裂的、空荡荡的皮囊与枯骨,轻飘飘地倚在墙角,仿佛没有一丝重量。只有那身残破不堪、沾满灰尘与干涸污渍的迦勒底标准制服,还勉强套在这具枯骨般的支架上,手腕处,那三道曾象征无限可能的鲜红令咒,此刻只余下焦黑褪色的浅淡痕迹,很快连这痕迹也会彻底消失。
人类最后的御主,曾于冠位时间神殿见证人理烧却,曾跨越七个特异点联结无数英灵之光,曾背负着泛人类史最后希望的火种,此刻如同燃尽的薪柴,被榨取了最后一丝光与热,只剩下冰冷、空洞、毫无价值的余烬。
阿尔托莉雅静静地注视了这具遗骸片刻,金色的眼眸中依旧没有丝毫波澜。然后,她微微抬起了右手,掌心向上,对着那枯骨。
没有咒文,没有光芒爆发。只是一个简单的、意念驱动的动作。
那具干枯的遗骸,从指尖开始,无声地化为最细微、最纯净的白色光尘,如同被最高级别的净化术式分解一般,迅速向上蔓延。光尘飘散,不落地面,而是直接融入了周围的空间,仿佛被这囚室本身、被圣都卡美洛的“固定”法则所吸收、同化。不过数息之间,那曾名为藤丸立香的少年存在过的一切物质痕迹,便彻底消散在了空气中,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残留。囚室里只剩下冰冷光滑的石壁,天花板中央那永恒不变的发光符文,以及空气中那缕即将彻底散去的、混合了神圣冷香与某种生命精华挥发后的、奇异而短暂的气息。
净化,已完成。残渣,已清除。
阿尔托莉雅放下手,白色的袍袖轻轻垂下。她转过身,赤足踩在冰冷的石地上,向着那扇厚重的石门走去。步伐稳定,节奏均匀,背影挺拔如松,周身那神圣的威压与光辉没有丝毫减弱,仿佛刚刚完成的并非一场残酷的吞噬,而仅仅是一次寻常的祈祷或冥想。
石门在她面前无声滑开。门外,走廊中,高文卿如同最忠诚的雕塑般肃立着,白银的盔甲在走廊壁灯下闪烁着冷硬的光泽。见到狮子王走出,他立刻以无可挑剔的姿势微微躬身,右手抚胸:
“王。”
“净化之仪,已然完成。”阿尔托莉雅的声音平静如常,如同在陈述天气,脚步没有丝毫停顿,继续向前走去。“冗余之残渣已彻底净除。圣枪伦戈米尼亚德对时空、对‘正确’历史之固定,将再无阻碍。永恒静滞之基石,更为稳固。”
“是。”高文低下头,应道。在他低垂的眼帘下,那总是充满坚定与忠诚的蓝色眼眸中,极快地掠过一丝极其复杂、难以言喻的微光,像是痛苦,像是挣扎,又像是更深沉的、被绝对信仰压制下去的迷茫。但这丝异样仅仅存在了一刹那,便被他重新抬起的、写满绝对忠诚的脸庞所掩盖。“王之意志,即为我等剑锋所指。”
狮子王没有再回应。她迈着恒定不变的步伐,走向长廊尽头那片更加明亮、更加恢弘、充满了神圣光辉的区域,走向她那位于圣都核心、光芒万丈的永恒王座。圣都卡美洛依旧在这片被固化的时空中巍然屹立,圣枪的光辉依旧照耀着这片被“净化”的土地,仿佛要将这静止的“正确”永恒延续下去。
只是,那曾为人理存续而燃烧的、微弱的、却无比顽强坚韧的最后火种,已然在无人知晓的黑暗深处,被“女神”以“净化”之名,以圣枪之力,彻底榨取、熄灭、归于虚无。
人类的最后希望,断绝于女神对“永恒正确”的偏执追求之下,终结于圣枪之主那冰冷神性腹中,化为了加固这静止囚笼的、微不足道的一缕尘埃。